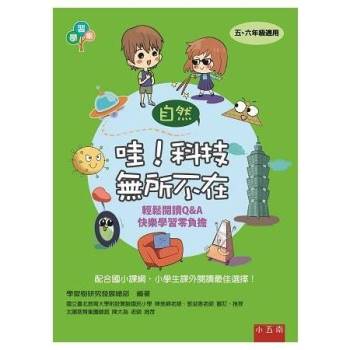一、八甲庄的英雄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西元一八五三年,這年是大清國艱困、動亂的一年。二月,長毛軍攻陷南京城,定其為國都,改稱作天京,洪秀全正式登上太平天國的皇帝大位。老態的大清帝國尚未從十一年前對洋人的挫敗中站穩起來,又再次陷入空前混亂、分裂的危機中。憂心的咸豐皇帝雖一心振作,力圖仿效先祖康熙大帝的英明敢為,但似乎已時不我予,整個帝國正一步步陷入前所未有的風暴中。
孤懸海外的臺灣島,成了饑饉的難民和投機者尋求生機的新天地。在北臺灣淡水廳轄下的大河道,一艘艘帆船從唐山甚至異邦絡繹而來。新移民乘船從河口溯流而上,睜大了眼睛看著青碧的山水和陌生的村落。這時每個人的眼中都閃爍著企盼的光芒,對他們而言──故鄉的苦難、威逼的官府似乎已遠在天邊了!「艋舺!」突然有人大喊起來,那傳說中遍地貨財的天堂正逐漸浮現在他們眼前。
「大船入港了!大船入港了!」碼頭上的力伕大聲吆喝起來,守備的兵勇們也精神抖擻地聚攏過來。在碼頭上麋集的人群中,立著一個英挺的身影,他是八甲庄的莊主林佑藻,人稱「佑公」。他身長不足六尺,並不很魁梧,但炯炯有神的雙眼,看起來很有威嚴。此刻,他專注地看船靠攏碼頭,心中惦念著自己的貨和新到的同鄉,「恁去問問看,有沒有咱同安鄉親?」他對身旁的手下低聲說。
碼頭上三邑人的兵勇排成一列,「人貨分開!人丁受檢,貨課價稅!」馬弁吆喝著。三邑指的是泉州的晉江、惠安、南安三個地方,這三地的人最早來到艋舺,是艋舺地頭的老大。同安人林佑藻在一旁冷眼旁觀,他轉頭對義弟高士遠說:「用咱自己的力伕!這批貨不一樣!」高士遠點點頭,很明白地立刻去操辦。就在這時,碼頭上起了一陣騷動,同安人的力伕和三邑頂郊的人拉扯推擠起來。「伊娘的!三邑狗欺人太甚!」一個同安力伕大聲咒罵著,「把整個碼頭霸佔起來,別人怎麼活?」「恁同安人才是狗呢!胳臂往外彎,甘心做漳州人的走狗!」三邑力伕回罵,掄起拳頭就揮過來,兩派力伕頓時扭打成一團。兵勇們見狀操著長矛衝上前,一個刀兵把長矛刺向同安力伕,那被刺的人唉叫了一聲不支倒地。「為什麼只對咱同仔?明明是三邑的先動手,恁三邑兵可要公正一點啊!這是故意欺負同安人嗎?」高士遠伸手抓住兵勇的長矛怒喝,他是個年近四十的高大漢子,身長有六尺以上,身手非常俐落。林佑藻拉了一下馬褂,跨步向前,他伸手擋住了高士遠,低聲說:「阿弟,忍一下,今天接好了貨比較重要!」這時馬弁趕過來,「佑公!叫你的人立刻退後!阮的事頭可是官批的生理!這你應該很清楚!」他左手撫著腰刀,右手指著林佑藻大聲說。高士遠當下一個劍步向前,護在林佑藻身前,大罵道:「小小的狗弁竟敢對阮阿兄無禮!」他怒目圓睜,一副天不驚地不怕的氣勢。林佑藻輕撫著高士遠的肩頭,「阿弟!忍一下!今天的貨很重要!咱們接了貨就走!」他小聲說。
「頭家!」這時一個同安士紳過來叫林佑藻,他年約四十五、六,名叫林士英,是八甲庄的帳房,算起來也是林佑藻的堂哥。他湊到林佑藻的耳邊說:「頭家!巡檢大人已打點好了!二十根條子!」他伸出左手食指和中指,比畫二十根金條的意思。「好好!」林佑藻點著頭,「巡檢大人來了嗎?」他問。「就在那邊!」林士英指著碼頭另一頭。「咱們走吧!接了貨就直接回八甲庄!」林佑藻說。高士遠狠狠瞪了馬弁一眼,「改天再輸贏!」他說,沒好氣地跟著林佑藻往那頭走去。
巡檢大人身著官服立在碼頭上,威風凜凜地下令:「下郊箱子裡裝的都是官批通行的要件!不許亂動!價稅已課,改天我會直接去龍山寺和恁的頭家算!」「是是……」馬弁哈著腰應著,立刻讓出了道。巡檢大人帶來的十多個官兵迅速接管了這一段碼頭。馬弁往另一頭走去,似乎不服氣地噘著嘴;這時,一個三邑兵勇湊過來小聲說:「那二十幾口箱子……可能裝的是槍械!我向水伕頭打聽來的……」馬弁回頭瞪了一眼,「我會向龍頭報告的!」他說。
清明才過,艋舺的河面仍吹著陣陣寒風,但碼頭上倒是熱鬧一片,連妓女們也趕來迎接新到的生理。一艘接著一艘的戎克船等著靠攏碼頭,有些等不及的水手,就在船舷邊和岸上的妓女打情罵俏起來。那些新到的移民怯生生地在一旁觀看,他們有的仍暈得站不穩,雙手緊抓著船舷,向河中乾嘔著;稍覺好一點的,三兩成群的跪下雙膝,口中唸唸有詞地向神明和祖宗祝禱感恩。
這時一艘載著福州杉和瓷器的大船擱淺了,碼頭上的人驚呼道:「看那艘紅頭仔!」林佑藻也注意到那艘大船,他對身旁的林士英說:「艋舺的河道有泥沙淤積了!」他邊說邊跨步向前,對著大戎克船上的水手喊道:「先錨定!把穩舵!等漲潮再靠碼頭!」大戎克船上的水伕頭認出是佑公,客氣地應道:「好咧!佑公,您的瓷器破不了一片!咱們還要載您的茶葉、樟腦、米和大菁回廈門呢!」林佑藻爽朗地笑了,他朝船上揮揮手──「得閒來八甲庄泡茶!」
這時碼頭上兩派力伕又起了爭執,原來是在爭擺貨的空間。「恁八甲庄的貨不能越線!」三邑兵勇大吼著。高士遠過去據理力爭──「一樣課了價稅,為什麼下郊的貨只有這麼一點地方擺!恁三邑人腹腸這般狹窄,怎麼做大生理呢?」馬弁神氣地走過來,他瞪著高士遠說:「有問題去找咱龍頭!這是龍頭定的規矩,誰都得遵守!」林佑藻一旁冷眼看著,他邁步向前,輕聲對高士遠說:「阿弟!今天咱就再忍一次,這問題也到該解決的時候了!阿弟,你聽我的……三邑人囂張的日子不會太久了!你應該懂我的意思……」高士遠低下頭,「這口氣真快憋不住了!」他提高了音量,抬起頭怒視著馬弁,「有種改天到祖師公前決鬥!叫安溪白董見證,輸的人丟到淡水河飼魚蝦!」馬弁用鼻孔輕哼了一聲──「哼!我的武藝不輸你!誰怕誰?」
碼頭上的人越聚越多,「這裡真是人看人!」林佑藻說,冷靜地穿過擁擠的人群。他今年雖才四十三歲,但走起路來步伐沉穩,很有長者風範;八甲庄的同安人近年來正巴望著他好好帶領,企盼伊們能在艋舺地頭更興旺壯大起來!對鄉親的期望,林佑藻一向是明鏡般清楚,也早作了力爭圖強的盤算。他在人群中揮了揮手,兩頂軟轎就朝這頭靠過來。「借過!借過!讓讓……」轎夫邊吆喝邊推開擋道的貨郎。「這些安溪貨郎個個是天生的生理底,伊們什麼都能賣──從日用什貨到壯陽補酒,還有妓女最愛的簪花、粉膏和成疊的木屐板,可說是能掙錢的、人愛的……樣樣都有!」林佑藻唸著。「恁做生理可不能學土匪路霸,總不能不給人過路吧?」轎夫揮起苧麻鞭吆喝起來。「哪敢?恁做大生理的是老大!阮小買賣的滾都來不及!」安溪貨郎哈著腰應道,伊們雖是如此應著,但肩擔卻也沒移開一吋;「佑公!這裡有上好的番仔煙!要不要試看看!」一個安溪貨郎巴著林佑藻邀生理。林佑藻輕鬆地笑起來,揮手制止了轎夫的鞭撻,「恁安溪人畢竟沒三邑人鴨霸,也不曾給咱同安人壞臉色看,今天我就捧場一些吧!」他說,扔下了些碎銀,「莫算貴了!敢賣我貴,改天我兄弟把你扔到淡水河中飼魚蝦!」他哈哈大笑起來。一旁的林士英提醒頭家──「安溪人個個精得跟鬼一樣!伊們生理雖做得不大,賺的可也不少!要注意價錢和斤兩!」林佑藻笑著點頭,心裡卻思忖著另一件大事,「改天我一定要去找安溪老大白其祥好好談談!」他對自己說。
林佑藻、林士英一人一頂軟轎走在前頭,高士遠騎著唐山馬跟在後面,十幾個兵伕吆喝著護在左右,看來真是浩蕩威風。「近十年來,八甲庄的氣勢是越來越壯盛了!」林士英說。一行人精神振奮地向東行進,經過舊街口時,見到道旁的三邑人正冷眼覷著他們,「當初收容伊們,如今搖擺得如此!」有人故意提高聲音咒罵起來。突然間,從道旁人群中飛出一顆石頭,直接朝八甲庄隊伍扔過來。高士遠大喝一聲──「誰人扔的?」他蹬了一下馬肚,迅速地護到林佑藻身邊來。這時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同安兵伕們手撫腰刀轉身朝外警戒。「咱們快走吧!前頭就是草店尾,那裡就是安溪人的地盤了!」林佑藻顯然並不想生事。
一行人逃命似地跑離了舊街口,穿過草店尾大街,安溪人的祖師廟就在眼前了。「歇喘一下!」林佑藻示意隊伍停下來。「佑公,今日親自去接船阿!」一個安溪老人家在廟前向他招呼。「誒,出來活動活動!恁的白董在嗎?」林佑藻問道。安溪老人家笑著說:「伊阿生理越做越大,這幾日都不在祖師廟!」林佑藻輕鬆地說:「無礙!只是想跟伊問候一下……」他轉頭吩咐高士遠:「你和士英到草店尾街口等咱的貨!記得要點清楚!莫和任何人起衝突!」他說完,帶著幾個護衛恭敬地走進祖師廟,「今天咱也來拜祖師公!」林佑藻虔誠地鞠了個躬。他專注地捻香拜求:「小民是八甲庄的林佑藻,今天特來祈求祖師公保祐!小民雖是同安人,但咱同仔從不排斥敬拜您老人家!絕不像三邑人那樣不把您放在眼裡!眼前三邑人幾乎已霸了艋舺碼頭,再這樣下去,同安人和安溪人的生理將無以為繼……唉……全面開戰怕是不能免了!小民求您老人家保庇八甲庄就如同庇護安溪人一般!您的神力威靈一定可阻擋頂郊的砲火和槍刀,求您助咱同仔好好教訓三邑惡霸。下郊若得成功,屆時咱同仔一定會感謝您,對您永遠奉祀不絕!」林佑藻說到這裡,將手中的筊杯恭敬地擲在地上。奇怪的是……他連擲了三次,祖師公都沒應他。他遲疑了一下,又點了三支香,「祖師公在上,小民林佑藻今日冒昧請教再三。眼下三邑人已逼壓太甚了!不是我要滅伊們,是伊們先欺人太甚,叫咱下郊就快活不下去了!小民雖出身草莽,仁義之心不敢一日忘懷,我若起義兵,保證不濫殺無辜!那三邑仔一旦讓出艋舺地盤,我願意與安溪人和平共享!任何人只要不鴨霸壟斷,我就願意和伊們和平做生理!今日我用我的性命向您起誓──只要您老人家保庇小民、只要天不滅我下郊,我一定和三邑人做法不同!不管是安溪人、漳州人、客人、粵人、社番、青番……就算是英夷、紅毛……我都願意和伊們和平做生理!我有肚量和大家一起發財!我林佑藻出身寒門,十一歲隨母渡臺依親,只為了求一條生路!小民歷盡萬苦,阮父母又雙亡於匪徒手中,幸賴社番阿母呶把花氏庇護教育,方得以成人立業。小民心中所念想的──就是顧生活!與人為善、發達生理造福大眾!只要三邑人讓咱共管艋舺碼頭,我就會立即停止殺戰,絕不違誓言!」林佑藻吃力地說出心中所有不平和想法,才唸完誓辭,雙膝就跪倒在祖師公前。他身後的同安鄉親竊竊私語起來──「佑公今日……怎麼這樣……這可是安溪人的神祇阿!」林佑藻沒理睬身後的雜音,他虔誠地再擲筊,一連三次,祖師公仍沒應他。氣氛頓時變得凝重,班首張士義上前低聲說:「佑公!咱還是回去求自己的城隍爺吧!」林佑藻輕聲地嘆了一口氣,「這祖師公守的……可是咱八甲庄的門戶阿!」他若有所思地說,「無論如何,我今日仍要萬分感恩和真誠地起誓──只要天不滅我下郊,每年正月初六我林佑藻一定供上大豬公謝恩!」
林佑藻是個意志如金石般堅強的漢子,今日臨時起意的祝禱竟得不到祖師公任何應答,不免讓他悵然若失。他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出廟門,這時突然傳來「哈!哈!哈!」的三聲大笑。「誰?誰敢笑咱頭家?」張士義朝笑聲的方向斥道。原來是一個襤褸不堪的乞丐正朝著這頭咧嘴傻笑,他是個瘋癲的老人,模樣倒是蠻斯文的,他口中喃喃自語著:「笑杯!笑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死車卻著一活!歪喙雞專食大粒米!」張士義氣沖沖地走過去,想教訓那老乞丐。林佑藻聽得出神,似乎很欣賞這位「天子門生」的指點,「莫為難伊!」他說,走過去扔下些碎銀,心中反覆唸著乞丐方才說的話。突然間,他轉身邁開大步又走進廟門,再度跪在祖師公前,虔誠地唸道:「祖師公在上,無論此次鬥戰是勝是敗,我林佑藻都要停止殺戮!咱下郊只要不滅,往後絕不再起戰端,咱一定和所有族群和平做生理!絕不違背誓言!我身為八甲庄頭人,只祈求祖師公保佑同安生靈,莫讓八甲庄絕祀,讓咱得以延續香火!」他祝禱完,又擲了一筊,結果第一次就是信杯。眾手下發出讚歎聲,林佑藻起身再拜,沉默地走出廟門。
林佑藻和隨從在廟旁安溪人的茶棚等了半個時辰,見日頭已斜迤上廟前老茄冬的樹梢。這時不遠處一行牛車緩緩靠近,林士英和高士遠押著長長的十幾車貨物已經抵達了。林佑藻親自斟了兩碗鐵觀音茶,迎在茶棚前,「恁辛苦了!」他一一敬了茶。「不累!阿兄別客氣!貨一件不少!」高士遠那六尺魁梧之軀一個翻身就下了馬背。林士英也屈身跨出轎子,「佑公!有件事真奇怪!」他湊到林佑藻耳邊低聲說,「頂郊進了幾十車油桶!桶裡不知是什麼油?」林佑藻皺了一下眉頭說:「是很奇怪!伊們難道缺油嗎?」林士英憂慮地說:「氣氛不對!油……是火攻的武器啊!」林佑藻點點頭:「咱八甲庄確得提防伊們放火!聽說黃龍安年輕時就曾放火燒了整排漳州人的店屋!」他說著轉身對高士遠說:「今日起,庄內每戶都要儲備打火的平安水!」大家聽了都頻頻點頭,又喝了些茶,然後在林佑藻一聲令下,大隊人馬緩緩地朝八甲庄前進。「天黑前,所有貨都要進庄內!」林佑藻說。
四下漸漸黯淡下來,林佑藻坐在轎上沉思,他的思緒如軟轎起伏般蕩漾起來。他想到安溪頭家白其祥近來提醒他的話──「聽說頂郊已準備霸了艋舺全部河岸!咱應該提早因應才好!可以請縣丞、巡檢大人及各大頭人出面協調,但情勢似乎不太樂觀!因為三邑老大黃龍安近日已在龍山寺公開嗆聲──艋舺已全是頂郊官批的地盤!」在憂愁不安的思緒中,林佑藻想起二十八年前的往事──他那年十五歲,跟隨父母翻山越嶺到雞籠港附近賣布,他們省吃儉用地打拼,好不容易售出了所有貨物,眼看辛苦的汗水就將換得報酬。那知……就在一個風大的黑夜裡,雞籠山的土匪兇惡地奪去了他們的一切。那夜十五歲的林佑藻和母親驚恐地蜷縮在茅屋後的草叢中,阿爸叮嚀他們絕不可被發現。那時風很大,土匪的火把一直跳躍不停,火光中依稀可見刀械的反光,大約來了十幾個匪徒。「交出銀子!交出貨!交出女人!」土匪頭吼叫著。他隱約可見阿爸驚慌的身影──他不停地打躬作揖,「阿里大王!阮批貨的錢是借來的,實在沒能力孝敬您……」他哭喪著臉苦苦哀求,謙遜卑下地跪地瞌頭!土匪頭用腳踹阿爸的身體,他竟連哼一聲都不敢!「叫伊交出命吧!想賺錢竟敢不先拜地頭!」林佑藻永遠記得土匪那聲索命的吆喝,然後……他在芒草的間隙中見到阿爸死去的景象。土匪頭用大刀砍斷了阿爸的脖子,而阿爸卻至死連一句咒罵也沒還擊。就在砍殺阿爸的大刀揮下的那一刻,年輕的林佑藻顫抖地起身大喊──「不要殺我爸!不要殺我爸!所有錢都給恁……不要殺我爸!」二十八年來,那一幕景象一直縈繞在林佑藻記憶深處,一旦浮現便如歷歷在目般清晰,從未隨時光流逝而有丁點模糊。二十八年後,他仍不明白──那夜自己是如何逃過一命的。土匪一發現草叢中的母子,立刻就追殺過來。林佑藻聽到阿母的驚呼聲──「兒阿!你緊走!莫管我!」「不行!咱一起走!」他大喊一聲,背起阿母驚慌地奔逃,回頭瞥見土匪的火把如鬼魅般逼近,好幾次眼看就要追上來了。林佑藻驚恐地跳下山溝,感到母親手臂滲出的濕黏鮮血已滴淌到他胸前,他戰慄著加快腳步往樹叢中奔竄。這時他聽到山坡上方土匪的吼叫聲,不禁哆嗦地唸起──「城隍爺救命!城隍爺救命!」因為這趟出門做生理前,阿爸曾帶一家人去拜過城隍爺,他記得那時阿爸虔誠地叮嚀道──「阿藻!你永遠要記住……城隍爺是咱同安人的庇護神!咱同仔走到那裡都不能忘記這點!」土匪仍緊追不捨,索命的火光愈逼愈近。林佑藻從斜坡滑下,隱約看到一條山徑。在滑落途中,母親的頭似乎撞到東西,她微喘著氣輕哼了一聲。「我兒阿!這樣逃不了……你把我藏在那片草叢中,自己趕快先走吧!」阿母在佑藻耳邊說。林佑藻不肯放下母親,雙手將阿母扣得更緊了。母親用手指掐他的肩頭,急切地說:「馬上放下我!不然我就咬舌自盡!若不這樣……我倆都死定……」林佑藻回頭見那跳動的火光已在小徑上方不遠處,他強忍著淚水把母親藏在一塊青石後方的草叢中,揪著心不捨地繼續向前狂奔。他又跑了約半里路,見到右前方有個小村莊,心想──「這可有救了!」他喘著來到莊前的隘門,三個漢人隘丁持著長槍攔住他。他說不明白,口中一直喊著──「救人!救人!土匪!土匪!」那時他也受傷了,額頭上淌出的鮮血流過他的臉頰,他感到暈眩,虛弱得幾乎要倒下來。他永遠記得隘丁們驅趕他的神情,伊們操著同安口音說──「咱們保衛莊頭,不惹麻煩!」他突然感到一種澈悟心寒的憤怒,咬緊牙關對自己說:「阿藻!絕不能放棄!除了靠自己……沒人會救你的!」他繼續在蜿蜒的山徑踉蹌向前,耳邊忽起忽落的寒風傳來土匪雜遝的腳步聲,那索命的聲響似乎已近在咫尺了。在漆黑起風的山路上,他連跑帶顛地又走了一段路,才隱約聽到近處有狗吠聲響起。那時他已雙腿虛軟,看不清前方靠近的人影,只覺得突然間眼前一黑,整個人就昏死過去了。「我這條命是社番阿母救的!」林佑藻在回憶的思緒中激動自語著,「我這條命是雞包里社番救起的!呶把花阿母是我的再生母親!」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只可惜自己的生母還是沒救出來!而且……之後竟連屍骨都給野獸咬得殘缺不全!」每次回憶起這些往事,林佑藻都心如刀割,在眼眶打轉的淚水也就無聲地溢出來,他對人的看法從十五歲那年起了變化,他下定決心要壯大起來──「這是個比力量的社會!自己有實力才是活下來的根本!求人活命絕不是頭路!」他經常如此提醒自己。
林佑藻一行人走在田邊土徑,從新起橫街口右彎進來,前方不遠處就是八甲庄了。近千戶的莊落在暮色中朦朧地浮現,在暮色中有一種越來越模糊的虛幻感。突然間,北方的天空響起幾聲悶雷,閃電從北面沼澤上空斜斜地射下,林佑藻凝神望著八甲庄稍縱即逝的輪廓,「今春的雨水不夠!」他憂心地唸道,想到近來安溪老大白其祥轉來的訊息──「頂郊黃龍安已正式回絕了共築水圳引淡水河水灌溉的提議!」他實在不明白為什麼三邑人要拒絕這個可以增加稻米產量的意見,「伊們不正做著稻米出口的生理嗎?」他感到心煩。這時轎子已搖搖晃晃地進了八甲庄,林厝那棟雙進雙護龍大宅的龐然身影就在前方不遠處了。「阿母!孩兒帶了上好的番仔煙給您!」林佑藻一想到阿母,嘴角就展露出快活的笑意。「若無社番阿母、阿舅頭目幫忙,我哪有可能取得八甲庄的墾照?眼前的一切就自然完全不存在了!沒有呶把花阿母,就沒有今日的佑藻!」他滿心感恩地回想著。
一行人在庄內廣場卸貨。林佑藻一一慰問了幫手,請大伙兒進龍屋內用餐,「餐後請各股首到堂屋議事!」他回頭對林士英說。林佑藻飯也沒吃就三步併成兩步地來到阿母的房間,看見阿母已立在門口等候他。「阿母!」林佑藻喊了一聲,上前攙扶母親,「阿母!您坐著就好嘛!」林佑藻邊說邊取出番仔煙呈給老人家,心頭頓時有一種回到家的輕鬆感覺。自從阿母親生的兩個兒子相繼在鬥戰中死去,十多年來老人家就一直住在八甲庄,對眼前這個同安人生的兒子簡直比親兒還親。
阿母細細地瞧著身前英挺的林佑藻,「恁去碼頭還順利嗎?」她問。「嗯,很順利……阿母您莫擔心。」林佑藻趨前替阿母點上了水煙。阿母滿佈皺紋的臉龐掛著一絲憂慮,「你一定受了三邑人的氣!我看得出來!」阿母邊說邊咕嚕咕嚕地抽起水煙,「現在的情勢……唉……我是清水般明白!」她說。林佑藻笑著用臉頰貼上阿母的面頰──這是二十多年來母子間習慣性的親膩動作,「阿母!佑藻已如山石般強壯,我一定可以保護阿母的!您莫憂心……」他摟住阿母的肩頭說。「好……好……阿母相信你!」阿母用厚實的手輕拍著林佑藻的胳膊,「記住!一定要提防三邑人!」阿母皺癟的雙唇嘟囔著,又呢喃起她已說過無數次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艋舺還沒有現在的名字,紗帽廚人在大溪口碰到唐山來的三邑人。伊們拿著番薯、鹿肉換唐山人的布匹、鐵器,把河岸的茅屋借給三邑人住。那些瘦弱的三邑人從河岸上來,虛弱得幾乎像是半死的人!紗帽廚人可說是救了伊們的命,還讓伊們借住在紗帽廚的土地上。三邑人的頭目曾對天發誓──『只借住大溪口!雙方永久和平做生理!』但不久……伊們就違背誓約,開始燒殺紗帽廚人的村落!將紗帽廚人的屍體丟棄在田野中!伊們像蝗蟲般侵占紗帽廚的土地,用戎克載著一船接著一船的三邑人上岸,那人頭就像河沙般數不盡!戰敗的紗帽廚人親像流浪的牲口那樣四處逃竄,少數人到了麻少翁地界,大部份的人被逼入大河,成了踩不著土地的漂流鬼魂!三邑人像瘟疫般滅了紗帽廚社,紗帽廚人還來不及哭泣就完全消失在漫漫的黑夜中,只剩下隨風飄蕩的長長嘆息聲!咳咳……」阿母輕咳起來,「記住!要緊快壯大起來!我兒呀!三邑人不會放過八甲庄的!」她吐了幾口青煙,深慮地叮嚀著兒子。林佑藻緊握住阿母的手,「孩兒一定記住阿母的話!」他恭敬地說。
林佑藻叫大房妻子端來飯食,說說笑笑地和阿母一同用了晚餐。大房妻是擺接社頭目的女兒,和呶把花阿母一向很親近;林佑藻取得八甲庄地界的土地,她也幫了很大的忙。
林佑藻輕鬆地吃完了晚餐,看見林士英已在廊下等他,「十二股大哥都到齊了!」林士英說。「到右側堂屋議事!」林佑藻邁開步伐,「叫阿弟佑珍、佑成也來!」他回頭交代著。這時他看到拆箱取出的貨已搬到中庭,兩百支槍和四門鐵炮整齊地擺在地上。林佑藻拿起一把火槍仔細檢視,「呂宋人的貨還是得仔細驗驗!」他對身旁的林士英叮嚀著,「改天你叫士遠、士義領著各股大哥去試試!不行的就要退貨!」
林佑藻的大瓦厝位在八甲庄前段中央,是一座雙進雙護龍的大宅,宛如一座堡壘。大伙兒陸續進入右側堂屋──這是間長方形的廂房,房內擺了三張大圓桌。林佑藻在中央的圓桌坐定,林士英、高士遠、張士義、林佑珍、林佑成在他身旁依次坐下,各股大哥也一一就坐。林佑藻請下人奉上了熱茶,他站起身來說:「各位大哥!恁辛苦了!今日佑藻請大家來商議的事,是關係咱八甲庄存亡的問題!首先我要拜託各位──絕對不可對外泄漏任何今日商議的內情!這是關係全庄生命的機密!是不容有一絲差錯的!佑藻今日以至誠將命運與各位兄弟同繫,一切皆為了八甲庄的生存,一切都是為了咱下郊的興旺!眼下三邑頂郊霸佔了艋舺碼頭,咱下郊已面臨毀敗的威脅!所以我決心與頂郊一戰!一定要趁伊們還沒準備好,先發動突擊,一舉把頂郊趕下淡水河!這場戰爭確切的時間還沒敲定,但肯定是在今年之內。唐山有消息傳來──大清國陷入分裂、動亂,長毛頭目洪秀全在南京已稱了皇帝!眼下朝廷自顧不暇,已無力干預臺島紛爭!只要咱們不扯旗造反,朝廷是不會壓制的!我想這情勢頂郊也很清楚,所以近來伊們的動作才會越來越大!眼前雖說是危機重重,但也是八甲庄擴張發展的天賜良機!頂郊鴨霸的作風,我相信大家已忍耐得夠久了!把命運交給伊們顧,等於是沒命!所以這一戰無論如何是免不了的!佑藻幸賴祖宗庇佑,諸位同安兄長提攜,得以開創八甲庄基業,我絕不會坐以待斃,坐視八甲庄毀於三邑人之手。然而人各有志,諸位股首若有不願參與戰事者,可先避居他處,佑藻願價購其房舍、物件,一切悉從所願!若願留下打拚,則佑藻決以全部身家性命與之戮力同心,奮力求勝!一旦成功,我誓與諸英豪共享艋舺新局!我所圖者乃同安人所以自存、發展之道,絕非為一己之私,望諸鄉長、英豪共襄義舉!」
在場所有人都起身鼓掌──「我等願隨佑公打拚!咱同仔不輸人、不輸陣!」眾股首大聲回應,「我等誓死與頭家同心同命,不殺滅頂郊絕不罷休!」當下呼喊聲不絕。林佑藻立起身來致意──「我今誓與諸英豪同命!誓與八甲庄同命!」他說著紅了眼眶,想起近年頂郊種種欺凌和失去碼頭控制權後的百般委屈,他不禁握拳重擊桌面,「八甲庄存亡在此一戰!下郊興衰在此一舉!」他大聲說。
林士英拿出自己手繪的地圖在大家面前展開,他不愧是個秀才,地圖畫得非常精確。「首先要加強防禦措施!加緊操練兵勇!畢竟咱們的人比三邑頂郊少得多!只能以精兵取勝!也一定要提防伊們先下手強攻!」林佑藻點點頭,「少多少?」他凝視著林士英問。林士英嚴肅地應道:「八甲庄約一千戶,現有兵勇近六百人!三邑頂郊約三千戶,現有兵勇近兩千人!伊們又佔了碼頭之便,增補軍械、槍砲比咱們方便得多!」林佑藻輕鬆地說:「以少勝多,歷史上的例子也不少嘛!」林佑藻生性堅毅樂觀,就算碰到難題,也總是信心滿滿的。「把不必要的花費省下來,三個月內增補兵勇到八百人!」林佑藻堅定地說。他揮手示意手下把一件藍染粗布短褂取來。他迅速褪去身上的絲綢衣裳,把它拋到一邊去,然後雙手接過藍布短褂,用力抖了幾下,一氣呵成地穿上身來,「從此刻起,這就是咱八甲庄的戰服!一日不勝頂郊,我林佑藻就一日不穿綢緞!」他高聲說。眾人都起立喝采,「咱誓與頭家同心!從此刻起,咱全都換上藍布戰服!不達成功,絕不終止!」
林士英示意下人把成疊的藍衫取來,不一會兒所有在場的人都換上了藍布褂。「大家穿得一樣,在作戰的時候是很重要的!」林士英說,「而且粗布耐用、便宜,藍染處理用大菁染,咱自己就能做!兩個月內,八甲庄所有兵勇都要穿一樣的服裝!」林士英說完,轉身拿一枝竹竿指示著他繪製的艋舺地圖。「這就是咱八甲庄的位置!」他說,「南面和東面是咱自己的稻田。下邊的萬安街可通下坎庄,那裡的漳州人和咱很友好!北面是一大片沼澤地,這裡通行困難也杳無人煙,可作為咱的退路!西面是最緊迫的前線──南段以河濠分界,一直到土炭市、剝皮寮都是兩郊的中間地帶。剝皮寮東側就是八甲庄的西南門戶,要立刻加強隘門防備,李士傑大股配一門火砲防守這裡,兵勇至少一百人!河濠一帶緊鄰敵方,由陳士通兄弟的六股鎮守,配備火砲兩門,最南由陳士有股防備,負責支援李士傑股。西面北段就是蓮花池到祖師廟一線,這裡易守難攻,由張士崑兄弟兩股防守。至於西北方面,因為是安溪人的地盤,加上有祖師廟阻擋,防備並不困難,由蔡瑞章兄弟一股防守!八甲庄正北方,從新起後街經新起橫街一線,由高士遠、曾萬得固守,高士遠股配置火砲一門,負責把守八甲庄正門。」林士英分配完責任區,轉身朝林佑藻深深一鞠躬──「請主帥裁示!」林佑藻屈身攙扶林士英,「各位股首大哥!有任何高見或是不明白的地方,請現在就說!否則,方才軍師所擬即為軍令!」他嚴正地說。
陳士通大哥率先提出質疑,他大聲說──「咱人少,應採攻勢!方才軍師所言為何全是守備呢?」他年約四十五、六,是個高大魁梧的漢子,身長逾六尺,目光銳如利刃,有一股猛將的氣勢。陳士通與弟弟陳士有、陳士賽、陳士合、陳士仁、陳士預共六人擁有八甲庄最強的武力,因此說起話來一向是最大聲的。林士英向他一鞠躬,微笑著說:「士通所慮極是!恁兄弟之六大股實際上就是攻擊主力!頂郊的帥營一定是在龍山寺,這是明擺的!從八甲庄到龍山寺,最近的路線就是這條直接!」林士英用竹竿在地圖上比畫了一條直線,「我預定三個月內打造十座高梯,屆時將發動跨河濠攻擊,直取三邑人的大本營!我希望彼等六股要善加隱匿,不能暴露咱攻擊主力的位置!若先遭受攻擊,彼等只守不攻,未得軍令,不准擅進!」陳士通點點頭應道──「明白了!遵命!」這時守剝皮寮東側的李士傑似乎面有難色,他欲言又止,斜眼看看陳士通,並未開口說話。林士英說:「世傑乃我八甲庄之青年才俊,必可勝任無虞!」
高士遠立起六尺的魁梧身驅,「師爺!」他說,「我受佑公我阿兄之恩甚深厚,若起義舉,誠願身先士卒,在前線衝殺才符吾願!為何反而令我股殿後呢?」林士英拍拍高士遠的肩膀,「士遠不愧是八甲庄英雄!我方才已說了──『堅守退路和進攻是同樣重要的!』以我對三邑頭人黃龍安的瞭解,他若攻八甲庄,勢必力求完全殲滅!只要咱八甲庄不被全滅,戰事最後的勝負就仍在未定之天!你的任務事關重大,三個月內要做好穿越沼澤地的演練。若三邑人先攻北面,你就遁入沼澤地,其餘各股迅速向北馳援。依黃龍安的個性是不會善罷干休的,屆時三邑人若深入沼澤地,咱便可兩面夾擊!」林士英微笑著說。「可是……咱不是要採取攻勢嗎?咱的勝算不在保全,咱要以少勝多,只有主動進攻一途!一定要先下手突擊!將頂郊殺個措手不及!才有勝算嘛!」高士遠似乎仍不贊同軍師的佈署。林士英拱拱手,轉身向林佑藻作揖,「請主帥裁示!」他恭敬地說。林佑藻欽佩地看著眼前的林士英,心想──「沒想到……這個一度流落艋舺河岸的落魄秀才竟有此經天緯地之才!」他欣慰地點著頭──「軍師所言穩妥!」然後轉身對高士遠說──「我弟忠義豪氣,愚兄也甚嘉許!軍師要你守北鎮,其實是把八甲庄存亡絕續的大任都委託在你手中,你應感從才是!」他說著朝高士遠微微點頭,「士遠與我親如手足,當知吾意!」林佑藻輕鬆地說。高士遠一見到林佑藻開口,臉上質疑的神情頓時消散,轉身向林士英鞠躬,「遵命!我會盡心盡力的!」他恭敬地說。
林士英又交待了一些細節,處置了刀械、槍枝與火砲的分配、佈署事宜。林佑藻點起水煙,輕鬆地吸著。他回想起和高士遠初次見面的那一天──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在一個寒冷的冬日午後,高士遠穿著單薄的短褂,腰間佩帶著大刀,英挺地立在三邑人在蕃薯市街的隘門口。那時他還是個頂郊新僱的傭兵,一個在艋舺地頭上流浪的羅漢腳。那天林佑藻和林士英等一行人到大溪口碼頭去接貨,回程剛好路過那裡。林佑藻遠遠的便一眼瞧見高士遠高大英挺的身影,他不禁在心中暗暗叫道──「頂郊連小小的隘勇,竟也豪氣的如此!」「問題是……如此英雄怎只放在僻陋的街巷隘門口呢?真是屈煞好漢!」他的思緒漫遊起來。突然間高亢的喧鬧聲響起,幾個人在隘門口爆發了拉扯衝突。「怎麼回事?」林佑藻好奇地覷著。隘門那頭,有三個黑衣漢子正揪著一個哭鬧的丫頭,那丫頭約莫十來歲,正哭喊著猛力掙扎。一個黑衣漢子生拉硬拽地想把她拖走,另一個用腳猛踹小姑娘,第三個臉上長痣毛的瘦漢怒斥道──「再逃就殺死妳!扔去艋舺河飼魚蝦!」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守隘門的英雄一個箭步上前,輕而易舉地就撂倒了三個黑衣漢子。腳踹姑娘的漢子被英雄一腳踢到幾丈外,倒在石板路上爬不起來。拉扯姑娘的漢子揚起雙拳猛力擊來,只見那英雄雙手向上一架,稍一扭轉,那黑衣漢子使拳的雙臂已被牢牢擒住,痛得唉叫求饒。林佑藻忍不住拍手叫好──「好功夫!好功夫!」他大聲誇讚起來。一旁的林士英小聲對他說:「又是個妓女戶逃出來的丫頭!看來還是個雛呢!」林佑藻昂首走向前,林士英拉了拉他的胳膊──「佑公!咱不要管閒事!」他顧忌地說。這時只見長痣毛的瘦漢退到一角,口中大罵著──「你是哪來的流氓?堂堂頂郊竟出如此潑漢!阮春風樓可是官批的生理,你不要在艋舺討生活了!阮叫龍頭打斷你的狗腿!」他雖驚嚇得杏眼圓睜,但一張嘴可不願停下來。林佑藻走向前,先向英雄拱拱手,「幸會!幸會!」他笑著說。接著他也去慰問黑衣漢子,一副和事佬的模樣。那長痔毛的瘦漢彷彿見了救兵,諂媚地對林佑藻說:「佑公!您快來主持公道!咱都是生理人!那潑漢存心搗亂,如此怎有天理?」「恁三個查甫人欺負一個姑娘才沒天良!」那英雄怒喝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嗎?」林佑藻仍是笑瞇瞇地,彷彿管定了這事。「唉……佑公,您不知道……這丫頭已跑了好幾次了!還是個雛……就刁得如此!給打了好幾回,竟然還敢再逃!阮頭家可是花了大錢正經地向伊叔叔買的!是銀貨兩訖的!若真給這雛跑了,叫咱怎麼向頭家交代呢?」長痔毛的龜公皺著眉訴苦起來。林佑藻豪邁地大笑──「我當是個什麼嚴重的事呢?恁頭家馬頭跟我熟,也算是生理場上的好兄弟!我正缺個丫鬟,就將這姑娘讓給我吧!」他說著回頭對林士英說:「讓馬頭賺一倍!就這麼說定了!」龜公雖仍面有難色,但也不敢頂撞林佑藻。林士英塞了些碎銀過去──「怎麼?不認識佑公嗎?這ㄚ頭就這麼訂了!銀子咱下郊少不了給恁!」「沒天良!光天化日竟敢逼良為娼!」那英雄又過來大罵。龜公嚇得閃到一旁,嘴巴仍叨唸著──「瞧這德性!佑公您快替我主持公道!」這時突然一條皮鞭從天而降,狠狠地打在英雄背上,「狗奴才!敢多管閒事!」隘門弁頭已趕過來了,只見他一面怒罵一面又揚起鞭子要再打。林佑藻二話不說,一把扯住了皮鞭,「弁爺!這漢子是我故鄉的親戚!請您擔待點吧!算是給我一個面子!」他誠懇地說。弁頭認得林佑藻,語氣緩和下來──「桀驁不馴!來不到一個月,竟敢專橫如此!這個月一分餉銀也別想領!」弁頭轉頭罵那英雄。林佑藻細細打量著好漢──「聽壯士口音,可是同安人士?」那英雄點點頭,對弁頭的鞭打似乎心有不平。「為何會到艋舺來?」林佑藻又問。「我本是彰化縣泉人,道光年漳泉械鬥被毀了家,父母家人亦皆亡故,不得已才流浪到艋舺地界!我是唸過書院的,絕不是桀傲不馴的羅漢腳!」英雄恭敬地應答。「好好……」林佑藻笑起來,「在下林佑藻,是同安下郊的生理人!但我最欣賞唸過書的英雄了!」弁頭不敢再罵,但不耐煩地說:「倒敘起舊來了!既是同安人,何不請佑公自己帶回去管教!咱龍頭寧可僱客家人,也不愛用同安人!我還正愁沒法去交代呢!」林士英聽了狠狠瞪了弁頭一眼,林佑藻倒仍是一派輕鬆──「那好!我也正缺個好管閒事的,這壯士就由下郊收用了!」他說完示意身旁的林士英塞些銀子給弁頭。那弁頭笑微微地應道──「我也直說了!這潑漢除了有些蠻力,實在也沒啥路用!您老就斟酌地用吧!」林佑藻聽了大笑起來──「謝了!」──即使事隔十多年了,他就是在夢裡想到這事,仍會欣慰得笑不停。那天林佑藻領著高士遠回到八甲庄時,一輪明月已高掛天際;於是他給那姑娘取了個「月白」的名字,並且把她許配給高士遠。而高士遠也果然很爭氣,沒幾年功夫,就成了八甲庄一根重要的柱石。林佑藻很欣賞高士遠俠義的性格,便和他結為異姓兄弟,之後也認了士遠的兒子作義子,替義子取名叫「高劍」,意思是正義之劍。就在林佑藻思緒漫遊的時候,槍枝的分配起了爭執──兩百支槍分給十二股,是很難平均的!林士英的意思是多給河濠六股,負責把守八甲庄正門的曾萬德卻認為應該多留槍枝守大本營,守剝皮寮隘門的李士傑也不服氣。林士英請示主帥,林佑藻笑著問高士遠:「兄弟之意如何?」高士遠豪邁地應道──「我贊同軍師的看法!事實上我股反而想多引進番弓,弓箭在大沼澤中作戰可能更有利!」林佑藻似有同感地點頭說──「難得士遠思慮到這一點!那火槍子一旦浸濕,可能就不能放了!」最後由他裁定──「每股分十五枝火槍,其餘二十支由軍師彈性調度。各股也要加強弓箭手的訓練!」當下大家都點頭同意了。林士英又詳細解說了火槍的使用方法。這時高士遠身旁一個白面的年輕人站起來說話:「咱人少,應該要有外交聯合!大隆同的同安鄉親、興直和加蚋仔的同安庄子都應該去聯繫!若是伊們和咱一起發動攻擊,頂郊就等於是被圍著打了!」說話的年輕人身長不足六尺,體格也不魁梧,但聰明伶俐一副書生模樣,他名叫林礬,本是個落魄的讀書人,因為生計困難,年前投靠到八甲庄來,目前一家人跟著林佑藻學做生理,算起來也是林佑藻的同鄉遠親。林士英起身誇讚道──「林礬弟所言極是!外交是作戰中重要的一環!咱不只要聯絡同安鄉親,艋舺南邊的漳州人也應去交陪!但比較有爭議的擺接林本源……還是暫時不要去接觸為妥!畢竟前年伊們才剛和艋舺及周邊的泉州人戰過……」林佑藻頻頻點頭──「應該!應該!林礬思慮清楚,辯才無礙,可助咱做外交!」他欣喜地看著林礬。突然間,林佑藻皺起眉頭──「還有安溪人!千萬別忘了這群精明的生理人哪!伊們可是守著咱的門戶命脈啊!雖說安溪頭人白其祥和我一向要好,但伊是純粹的生理人,和氣生財、互利往來是唯一的考量!而且聽說白其祥和頂郊龍頭也很有交情……」林士英聽了,立刻起身說:「對!最要緊的就是先拉攏安溪人!」
林士英在會議近尾聲時,對大伙兒說:「現在已是三月底,攻擊的日子雖還未定,但不會很久了!我現在只能告訴大家──一定是在下半年!因為淡水廳同知大人上半年是駐在艋舺,咱給他老人家一個面子,上半年就不惹事了。等到下半年他移駐竹塹時,咱就可擇日起義啦!」猛將陳士通站起身應道:「咱給同知大人面子,那可不保證頂郊也會這麼想!所以,大家不但要嚴守祕密,從此時此刻起就一定要加強戰備!」林佑藻笑著點頭說:「士通所慮極是!大家理應如此!」這時他注意到身旁的佑珍、佑成似乎神情落漠,心想可能是完全沒分配任務給他們的原故,他拍著兩個弟弟的肩膀說:「你倆和阿兄一起督辦糧草吧!咱八甲庄一年的租穀不到一千石,三邑頂郊少說也有三千石!對渡貿易的收入咱也不及伊們的一半!所以糧草支應是最緊要的!」兩個弟弟默默地點頭贊同。
會後,各股大哥調來人手,依軍師分配如數地搬運槍械。林佑藻問高士遠:「我的義子高劍近來可好?」高士遠歡喜地應道:「壯得像牛!冊倒是還沒唸熟!和伊阿母學做些鮮花生理。」林佑藻呵呵笑起來──「要做生理,書還是得讀的!阿遠!和我三兄弟一起去給城隍爺燒個香吧!」高士遠欣快地答應──「到戶外走走也好!」林佑藻又向忙得額頭冒汗的林士英打招呼──「阿兄,早點歇息吧!您今天真是辛苦啦!」
林佑藻一行四人步出林厝,見那明月已近中天。月光下的秧田散放出青杏般的土香,從伊們腳下一直延伸到遠處的蓮花池畔。月光下厝旁的竹叢在微風中搖曳,發出刷刷的聲響。「這青嫩的新葉到了五月就可以包粽了!」林佑藻輕鬆地說。高士遠似乎有心事,無言地凝望著遠方。「阿弟!怎麼了?」林佑藻問道。「嗯……剛才阿兄說要聯絡漳州人,我心裡不好受!」高士遠悒悒地說,「漳州人和我有殺父、殺母的深仇大恨!」林佑藻輕撫著高士遠的肩頭,「賢弟!阿兄瞭解!阿兄瞭解!」他輕聲地說,「但那是彰化的漳州人幹的!不是淡北的漳州人!阿弟!你應該瞭解阿兄的個性……總有一天……阿兄一定會替你報仇的!就像你曾助阿兄報了殺父之仇那樣!畢竟……父仇是不共戴天的!」佑珍、佑成不解地看著哥哥,林佑藻長長地噓了一口氣,娓娓提起八年前的往事──「那是個乾燥的秋天,阿兄領著高士遠、陳士通以及三個隨從,騎著馬從八甲庄出發。咱選擇沿著沼澤地東側走,一直朝東北方行進,刻意避開所有熟悉的庄社,向著目標雞籠山的方向前進。進入山區後,攀升的路非常崎嶇,處處可見飄落的黃葉。灰濛濛的天空中,咱不時看見南飛的雁鴨,耳中盡是此起彼落的哀鳴聲。咱們走了兩天山路,沿途見到藍色羽毛的美麗雉鳥、粗如碗口的老藤,共穿越了三條溪流,較大的河還必需乘社番的莽甲方能渡過。不久咱走出有冒煙泉水的山谷,前方就見到大海了。雞包里社是在浪濤拍擊的海岸邊,社裡有蛇木柱築成的茅草屋,海濱還有數間古怪的圓石屋。我先到海邊去呼喚生母,二十年前的往事又歷歷在目般浮現腦海中。那時十五歲的我,無力安葬母親殘缺的遺體,就自作主張將母親海葬了,我希望母親的靈魂能順著潮水返回故鄉唐山去。二十年後,我已有力量替父母報仇,每一刻想的都是仇人的血,我壓抑著如波濤起伏的心情,靜靜地在海邊沉思了三天。我向大海祈禱──希望她賜給我力量!到了第三天,該打聽的消息都獲得了,我送了厚禮給社番頭目,設宴答謝社番也順便向伊們辭行,但絕口不提二十年前的事。歡宴席間,頭目好意地介紹一個來此批魚貨的同安商人給我認識。那人叫林藍田,身長不足六尺,結實清瘦,有一雙真誠的眼睛。據說那人本來在雞籠山附近做生理,因受土匪頭阿里脅迫,只得逃回奇武卒社附近河岸搖鼓走街做生理營生。他為人熱誠豪爽,與雞包里社人很有交情。他每半年都會大老遠地來此批魚貨,然後帶回去製作魚乾販賣。當伊知道我要到阿里大王的地界去做生理,就一直苦勸我不要去,伊講:『阿里是個要錢不要命的惡鬼,完全不講道理!是個見了財貨,就連親人都要殺害的畜牲!』我對林藍田兄的好意非常感謝,笑著對伊說:『我膽子沒那麼大!我只是想送些禮物給阿里,看伊能不能恩准我到雞籠港賣布,做點小生理!』林藍田兄又勸我說:『阿里伊是土匪!不是生理人!就算得到伊的同意,你賣布換來的錢財也帶不出伊的地盤!』我當時心中著實感激,真沒料到在海邊的番社中能碰到如此真誠善心的鄉親。我一再感謝藍田兄,真摯地對伊說:『我一定會格外小心的!我告訴伊──我是艋舺八甲庄下郊的林佑藻!以後一定會專程到奇武卒去拜訪伊!願意跟伊做互相牽成的夥伴!』第二天,咱一行六人就緩緩進入阿里的地盤。等了兩天,送了很多禮物、錢財,咱才終於得到阿里的接見。那是個淒清乾涼的秋日午後,咱們已跪在阿里大王身前,謙遜卑下地拜見伊。那時伊看來已六十多了,雖然歲月帶來了老態,但那雙鷹鷙般兇惡的眼睛,竟和二十多年前殺咱阿爸時一模一樣!我在心中吶喊道:『就是這個禽獸!不會錯的!』」當我向伊獻上最貴重的絲綢時,我的雙眼已幾乎要噴出火來!我把絲綢布慢慢展開,然後突然抽出藏在其中的匕首,一個箭步上前猛力割斷了阿里的喉頭,就像殺雞一般!這個動作我已在夢裡演練過千百遍了!當鮮血像噴泉般濺出的時候,高士遠和陳士通跳起來搶阿里身旁的刀械,然後俐落地砍死了阿里旁邊的三個護衛!我接過高士遠手上的大刀,狠力一揮,阿里的狗頭就滾落到地面。我當時感到一股暢快的熱氣衝上胸口,冷冷地叫道:「這──是我替我阿爸還你的!」接著咱六個人一路殺出去,又砍倒了五個土匪,其餘的匪徒就嚇得四處逃竄了!
林佑藻說完,嘆了一口氣說:「這還是我第一次親口對人提起這事!」他的表情似乎挺輕鬆。四個人都沉默下來,無言地走在八甲庄沁涼的夜色裡。「其實……殺人也是要講道理的!」半晌,林佑藻淡淡地說,「我殺阿里是為了報殺父之仇!將來我殺三邑人則是為了求生存!不只是為我自己而已,也是為了整個下郊!頂郊已經逼迫太甚了!如此下去,下郊是活不了的!生存的威脅是絕不能忍的!但是……我並不是要滅了所有三邑人,那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我真正的目的是要大家公平分配艋舺地盤!然後和平共存,好好來做生理!畢竟生理才是最實際的!」佑珍、佑成從沒聽過林佑藻報父仇的故事,心情似乎受了些驚嚇,一時仍無法平復。「咱……咱們很感謝阿兄收容照顧!」伊們吞吞吐吐地說。林佑藻愣了一下,「咱是親兄弟!別說客氣話!我和恁雖不同母親,但確是至親手足!所以當我有能力之後,就立刻想到去找恁!我絕不要我的手足兄弟流落在別人的莊子!但願那種事永遠不會再發生!」林佑藻真切地說。三兄弟緊挨著向前走,有兩隻夜鷺從他們頭頂飛過,發出嘎嘎的叫聲。林佑藻注意到月光下的茅草屋頂,「只要一有能力,全庄的屋頂都要換成瓦片的!」他對高士遠說。
他們走過長長的巷道,轉角處就是金同利糕餅店──也是八甲庄寒磣的「城隍廟」。事實上,那實在不算是一間廟,同安故鄉來的城隍爺侷促在店前一角。「啊!是佑公!這麼晚了還沒休息?」店主陳金絨老爺子的兒子陳浩然向林佑藻打招呼。「怎麼?你也還沒休息!」林佑藻趨前拱手問候。「趕炊一批紅龜!」陳浩然應著。「嗯,生理人就該這麼拚才對!」林佑藻說。陳浩然是個五十出頭的斯文漢子,做糕餅的功夫相當了得,他製的糕餅甚至遠銷到府城去。他客氣地問:「佑公,要叫我阿爸嗎?」林佑藻連忙搖搖手──「不用了!老爺子應該歇息了!不要吵伊!」林佑藻回頭望一望八甲庄沉靜在夜色裡的莊舍,轉身點了三柱高香,他恭敬地來到城隍爺跟前──「城隍爺在上:小民是八甲庄的林佑藻!您老人家委屈了!小民十二萬分感激您老人家這些年的庇護,佑藻先向您起誓──這回只要八甲庄不滅,我一定傾全力給您老人家起廟!」他說到這裡,雙膝跪落地來,士遠和佑珍、佑成也跟著跪在他身後。陳浩然詫異地看著四人。林佑藻口中唸唸有詞──「咱同仔已被三邑人逼入困境!望您老人家護佑八甲庄每一寸土地、每一條性命,給咱指出一條生路!咱同安人將世世代代奉祀您!」他說到這裡眼眶泛著淚水,虔誠地瞌了三個頭。
他們四人拜完城隍爺,乘著涼風往回走。高士遠感慨地說:「在咱艋舺,三邑人的龍山寺已超過百年!就連安溪人的祖師廟也起了六十年以上!咱同仔何時才能替城隍爺起廟?」林佑藻堅定地說:「一定會的!無廟不成庄!咱同安人一定要謹記起廟的事!我林佑藻絕不會忘了今夜的誓言!」佑珍問哥哥:「金同利的城隍爺金身真是從唐山來的嗎?」林佑藻停下腳步,「這是千真萬確的事!」他肯定地說,「阿兄就在那條船上!這事陳金絨老爺子也跟我說過好幾次──『嘉慶二十六年,泉州同安發生大饑荒,乾渴的大地顆粒不收,餓死的人就倒在行道邊。因你阿爸三年前已先去了臺灣,所以十一歲的你是和母親到臺灣依親的。一百多個咱同安鄉親擠上了一艘大帆船,那些乾瘦驚恐的同仔很多人還是平生第一次坐船,每個人就這麼懸著一顆心搖搖晃晃地航向大海去。在擁擠的船艙中,有一個臉頰抹著汙泥的瘦小身影,暈船嘔吐得特別厲害,那人其實是個婦人,也就是佑藻你的生母。我陳金絨緊抱著同安霞城臨海門祖廟分來的城隍爺金身,口中不停地向伊老人家祈禱。船過黑水溝時,整個船身被拉扯得發出吱嘎的聲響,就像快散架了似的。咱同安鄉親們都跪下來向城隍爺祈求,每個人都信誓旦旦地說──只要能活著到臺灣,一定永遠奉祀城隍爺伊老人家!』阿兄和生母後來果真平安地抵達台灣北部的滬尾港,當咱們見到青翠綺麗的山巒,踏上濕潤溫暖的沃土,覺得就像已經到了天堂一般!」林佑藻停頓了一下,「但……誰會料到……之後阿爸會死在土匪的刀下呢?還有我阿母……我永遠不會忘記用草席包裹住伊殘缺遺體的景象!因為附近庄社的人怕得瘟疫,不准腐爛的大體入內,我只得在海邊請人火化了阿母的遺體,然後把骨灰通通撒進大海中。阿母是金門的同安人,我希望她的靈魂可以回到故鄉去!」林佑藻說到這裡,雙眼又迷濛起來,「我……林佑藻絕不會再求人饒命的!不管碰到多艱困的處境,咱同仔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拚到底!」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俎豆同榮:紀頂下郊拚的先人們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35 |
小說/文學 |
電子書 |
$ 210 |
小說 |
$ 308 |
小說 |
$ 308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俎豆同榮:紀頂下郊拚的先人們
這才是真正的「艋舺」!
台灣史上最慘烈的內戰,
第一部逼真重現淡北「頂下郊拚」的長篇小說
超級名作《無卵頭家》之後最精彩的一部作品!
神隱作家王湘琦構思四十五年戮力磨筆,
逼真重現一百五十年前淡北先民驚天一戰!
咸豐三年,淡北四雄頂立,艋舺頂郊梟雄泉州三邑「龍頭」(黃龍安)、下郊商賈泉州同安「佑公」(林佑藻)、清水祖師廟泉州安溪茶商「白董」(白其祥),以及擺接漳州豪門林國芳。
頂郊黃龍安握有艋舺渡頭控制權,處處壓制下郊貿易行商,引發下郊八甲庄頭人林佑藻不滿,密訪漳州人林本源家族,期以小搏大、扳倒頂郊,平分艋舺渡頭控制權。黃龍安則記恨彰泉械鬥時,下郊拒不出兵救援,造成頂郊重大損失。
雙方屯兵購料,大戰一觸即發,位於頂、下郊交界的白其祥,素與雙方交好,雖極力安撫促和,仍無法避免泉州人自相殘殺的血戰!
究竟誰對誰錯,已無法說清,敗逃的八甲庄戰士犧牲生命奮力搶回城隍爺的金身,林佑藻對著堆積成山的屍體灑淚,為兄弟復仇已非首要任務,帶領庄人另圖新局,才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黃龍安在「頂下郊拚」雖獲得勝利,但與擺接林家的衝突仍持續著,最後,誰才是淡北這片金色大地的霸主?
作者簡介:
王湘琦,一九五七年生,師大生物系、高雄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現為精神科專科醫師,同時也是三峽靜養醫院院長。曾以〈沒卵頭家〉獲第一屆聯合文學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時報文學獎等。著有小說集《沒卵頭家》、長篇臺灣歷史小說《俎豆同榮》。
章節試閱
一、八甲庄的英雄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西元一八五三年,這年是大清國艱困、動亂的一年。二月,長毛軍攻陷南京城,定其為國都,改稱作天京,洪秀全正式登上太平天國的皇帝大位。老態的大清帝國尚未從十一年前對洋人的挫敗中站穩起來,又再次陷入空前混亂、分裂的危機中。憂心的咸豐皇帝雖一心振作,力圖仿效先祖康熙大帝的英明敢為,但似乎已時不我予,整個帝國正一步步陷入前所未有的風暴中。
孤懸海外的臺灣島,成了饑饉的難民和投機者尋求生機的新天地。在北臺灣淡水廳轄下的大河道,一艘艘帆船從唐山甚至異邦絡繹而來。新移民乘船從...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西元一八五三年,這年是大清國艱困、動亂的一年。二月,長毛軍攻陷南京城,定其為國都,改稱作天京,洪秀全正式登上太平天國的皇帝大位。老態的大清帝國尚未從十一年前對洋人的挫敗中站穩起來,又再次陷入空前混亂、分裂的危機中。憂心的咸豐皇帝雖一心振作,力圖仿效先祖康熙大帝的英明敢為,但似乎已時不我予,整個帝國正一步步陷入前所未有的風暴中。
孤懸海外的臺灣島,成了饑饉的難民和投機者尋求生機的新天地。在北臺灣淡水廳轄下的大河道,一艘艘帆船從唐山甚至異邦絡繹而來。新移民乘船從...
»看全部
作者序
我第一次聽到「頂下郊拼」的故事,是在八歲那年,是從母親的口中聽說的。我的外曾祖父姓「高」,一家人原是居住在艋舺八甲庄的泉州同安人,後來因一場械鬥而敗逃至大龍峒,然後再輾轉遷居大稻埕。那故事令我十分感動,說的是一個戰敗的故事,也是一個從失敗中再站起來的故事。四十五年來,我好幾次嘗試將這故事寫出來,但始終力有不逮。眼看自己已一天天地衰老,距離去見先人的日子也一天近似一天,我終於戰戰兢兢地再拏起我那已禿的筆,勉力地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對我來說,這是一段自我挑戰的歷程,也是追憶省思的心靈探索。我試圖更清楚...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一 八甲庄的英雄
二 頂郊雄主黃龍安
三 安溪人的生理
四 廣結善緣
五 河濠大戰
六 頂下郊拚
七 攜神敗逃
八 三郊總長
一 八甲庄的英雄
二 頂郊雄主黃龍安
三 安溪人的生理
四 廣結善緣
五 河濠大戰
六 頂下郊拚
七 攜神敗逃
八 三郊總長
商品資料
- 作者: 王湘琦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12-24 ISBN/ISSN:957522912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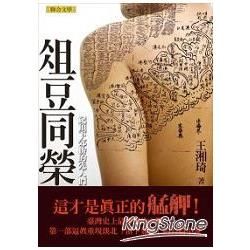
 2011/08/27
2011/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