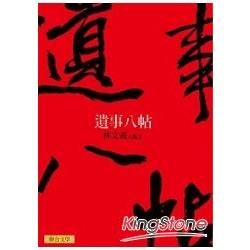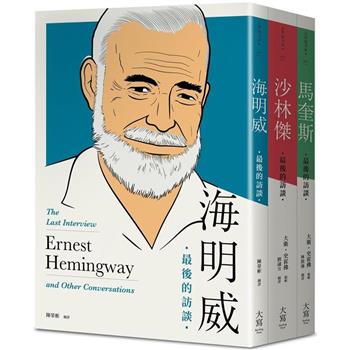旅行過海角天涯的作家,猶若流雲飄浮,湧潮傾聽;溫潤如交響詩的特異文體縈繞於曾經暴烈的革命壯懷,文學是他借以一生的名字,亦是歷經千折百迴的凜冽宣示、內在靈魂對決的終極救贖。
《遺事八帖》以大散文結構,巨視時代,襯之文史;藉以盆地古大湖、流亡與遷徙、山水寄情、殖民地印象、屠殺和禁錮、思想謎結、知識份子、揣臆未來諸題旨,呈現壯闊、美麗的文字美學異采。
這是林文義散文四十年允為最具代表性的定音大書,更是虔誠著力的扛鼎之作;為深愛的臺灣留記,敬獻給亂世紅塵中依然堅定秉持真情實意的文學信約。
八帖簡介
1.魚龍前書
臺北盆地。幾近一生的文學書寫,以之為題,我誕生的所在,想是老去亦不會離開的地方;悲歡離合、愛恨交熾,猶若永恆戀人。
從這裡出發,再回到這裡。循環的生命符碼及其次序,說是熟諳卻又彷彿陌路……猶若最深邃的情愛,總是乍近還遠。我生死與之的家園,置身、浸潤的晝夜晨昏,真的全然明晰這座首都之城嗎?一定還有未知的迷思未解。
我總漫思於千年之前,揣臆古生代的盆地許是大湖雲夢,族和傳說的龍潛匿深水,是否就是內海的岬灣?凱達格蘭人的祖靈看見過嗎?於是寫過一首詩以此為題,襯托出今時的人塵喧囂對照從前的幽然悄靜……意味書寫者本質半遁世主義之消極,這是我的不幸。
半遁世主義。盆地之子能夠主何處?文字如此允諾只怕徒留訕笑及不合時宜之譏,但頑強如我,就是一廂情願地抒寫己念。很多人與事都是難以預測及護持,文字堅定的留存亦是一種見證,後人如何評比、議論,就由它自去;我只純粹的編織一方夢土,曾經存在或不存在的臺北古大湖,如此壯闊,如此蒼茫。
2.雙桅船
合該是七歲以前,依稀彷彿的祖父帶我穿過大稻埕民生西路盡處的六號水門,看見擱淺河岸,已然斑剝、碎裂的雙桅木殼船;七歲以後,疼愛我的祖父就因矽肺過世了。
很多年以後的初秋,北美西岸的史丹佛大學東亞圖書館。我總是不太專心的不時側首遙看那扇哥德式窗外未紅的那株五葉風,桌間堆積著近代史書籍,偶爾巧遇臺灣來此研究的學者魏萼以及美國教授馬若孟,他們正為蔣經國基金會合寫一本書:《四十天與四十年》。
只是頷首致意,並未交談。我試圖尋求各種史料,比較三百年間距的前之鄭成功,後之蔣介石與臺灣的關鍵;不諳學術,僅為文學借題。「民族英雄」和「民族救星」?從前的造神運動毋寧過於沈重,或許回歸於人性本質看待,真正的生命才能鮮明、活絡起來。兩者相似之處,在於改朝換代的被迫離鄉來臺,島嶼接納了兩顆殘破、悲憤的心靈,而他們為臺灣此後做了什麼?
二十三年後,終於以之作題用「雙桅船」意象,描摹兩者無鄉可返的沈鬱。被禁錮於瓶中的雙桅船,靜止在湮遠的歷史裡,大海潮湧,故國呼喚,永遠回不去的鄉愁。
3.硫火之雪
硫火,遙想到乾燥以及炙熱。如若描寫水文及歷史,自然而然的想起清代旅行家郁永河來臺的採硫軼事雪之意象恆屬北方,喜愛日本,盡行扶桑,遇雪則悅,靜美的茫白。
年少時曾在陽明山竹子湖借居十月,文學初旅就在四季遞換之間啟程;四十年後石然有幸重返大屯山脈背後臨海的別墅落腳,彷如一種因緣促成的奇妙,冥冥中是否要我懺思青春年華的任性及不馴,或許如愛妻所祈願,盼我淨心滌塵,晚雲及晨星相映山風海雨之靜好。
靜好、寧謐的山居偶宿,在此竟因大自然的靈氣而不思筆墨,就是單純地近山眺海。似乎冬季未寒,深秋時庭園裡的楓葉不紅,那株櫻花逐出綻開,倒教我深深思念山居的主人,已故的知心摯友盧修一先生;好意提供租借於此的盧夫人陳郁秀女士想是多少明白我的惦念,慷慨且信賴的予我夫妻二人親炙故交遺址。
硫火之熱,霜雪之寒,猶若人生行路,晝與夜的現實情境確是冰炭滿懷;相信傷逝多年的盧修一先生早就深諳。離開了生老病死的輪迴宿命,花開葉落,山居靜寂,我乃沈定。
4.日島
從前的臺灣,現今的沖繩。歷史來去的激流亂雲,彷彿延綿著殖民年代的幽幽哀歌。
偶而聆聽母親反覆說起日本殖民臺灣的昔憶,時光膠囊般地打開,卻是支離的碎片,難以組裝、拚湊;八旬母親那時青春正好,二十歲的美麗女孩,驚見面目全非的戰後流離。
我所直覺想到的多的是日本文學,少的是風光明媚;作家與地景融合的自是三島由紀夫之於京都,我曾靜坐在三島自戕前幾個星期,住宿過的「柊家」旅館房間,他書寫的桌前,窗外靜美的庭園,酷似遺著最後絕筆之描景。
大江健三郎的義憤到老依然難平,三十歲撰述的《沖繩札記》至今仍是爭議不休;我並不很欣賞大江的作品,但我敬佩他的道德良知。他凜冽質疑「日本人」的定位,亦如同我思索「臺灣人」的本質:殖民者早已離去,某些人的心卻還是自困於「被殖民」的孤兒心態。
如若不被歷史的遺緒所制約,以為熟悉實質還是陽明一的日本,毋寧在文化層面值得深入究尋蘊涵,他們將千年前的唐代幾乎完整的臨摹、留存。我試圖借著旅行與書寫,對這個位於亞洲卻異於亞洲的島國,恆是逸興盎然。
5.紅與白
文史作家陳芳明以歷史學者定義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初的二二八事變乃是「兩個相異文化的衝擊」,誠哉斯言!比起近十年偏頗的以此不幸事件操弄族群、製造紛爭的政客及御用文人而言,可謂持平之論。隨後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更是令人髮指的法西斯式之國家暴力。
似乎,這歷史陰影曾經猶若鬼鬼魂般地久久不去。紅的血,白的花……我最初以小說形態呈現那極其灰黯年代的前人身影,在二十年前;而今是散文的反思,祈望以昔為鏡,撕裂復融合,認知相異但求傾聽且理解、尊重。歷史可以寬恕但不能遺忘。識者諍言如是清明。
這般沈痛的命題,彷彿試圖在荊棘之中種植玫瑰,起自由衷的良美初心,文學的溫潤。
父親他們那一代人,是全然幻滅的犧牲者,而後帶著破缺碎夢告別塵世,下一代的我們必須以最莊嚴的敬意、凜冽的文字,留下他們曾經青春、漂亮的身影……。
血緣傳承悲劇因子,下下一代人卻要唱出歡樂之歌;前人說過:小說比歷史更真實。不再是禁忌的今時,我再次執筆描摹六十年前最黑暗無明的苦難,猶如燃起千盞燭光的壯美。
6.光影迷離
如今抵達府城臺南,幾乎不識舊貌,尋覓年少時服役的網寮軍營,幸而還保留在榮民醫院對面已然高樓四起的街角;芒果樹還在嗎?
我回想當年那青澀、羞赧,野戰服的少男,晨起帶著《葉珊散文集》穿過蓊鬱如林的芒果樹群,有些凝滯、躊躇的青春苦悶……。
不諳退伍後初臨這繁複大社會的明暗,人心多端、詭譎的迷離;光影切割著自以為一切都是美好的愚騃,自然反挫得難以相信。
很多年後的冬夜人在土耳其旅行,兩個月前領了自立晚報易主後自請離職的資遣費,神傷地告別一生最為衷愛的副刊編輯檯,失業之外,我堅執的理想與信念也隨之顛躓、消逝。資本主義可以掠奪、耗損所有的良知和美質,冬夜微雪是耶誕前夕,客船從希臘渡海去土耳其邊境,我知道從前的種種,永遠回不來了。
文學評家張瑞芬教授言之:我以散文寫日記。確是知己者言。亦如已故作家郭松棻所喻:書寫是因為害怕失憶。因之我心須留存湮遠的從前,穿梭光影,解析迷離,彷彿一個不存在的烏托邦一直是存在雲霧深處;不可能或可能的發生,永遠是文學中光影迷離的魅惑。
7.鬼道
佛典和聖經的差異,在於「無我」與「救贖」之別;那麼何以千百年來,人類還是坐困於無數的糾葛、煩鬱之心病,難以真正解脫?
十年來,臺灣的知識份子終於令我澈悟:風骨與人格已是被封存在古老的地窖底層,成為灰燼。見風轉舵,遇權貴則曲身,政爭乍起,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亦是我個人在幾年前斷然引退於政論節目的主因,沒風骨何以為人?
或許是我一廂情願的主觀認知,與這未見提昇卻早就沈淪的亂世格格不入,不合時宜;他者安之若素,我卻不以為然,何以如此?埋怨自己因為瞭解太多,就苦了我這一向秉持「完美主義」的愚騃,看來只能遁世以終了。
魯迅早做先知之言:人吃人的社會。他悲痛的是民智未開的中國。八十年後誇言民智已開的臺灣,正應驗著魯迅「人吃人」的印證。人比鬼還要可怕?知識份子的無格、虛矯、逢數是今時臺灣最大的不幸,喜將靈魂典押給撒旦,自陷鬼道,我依然以不忍之心寫下如是直覺,猶若夜讀魯迅之書,只能掩卷嘆息。
狄更斯名言:這是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不幸的臺灣,我們的明天又是什麼?
8.未來的未來
這是未來的預言,還是憂杞的現在。
憂杞數位化的電子書,圖書館將成廢墟之預言。紙頁之書終成螢幕上冰冷的符碼,是進步還是退化?我依然院美於墨香溫潤的紙本閱讀,抵死不從的以筆紙書寫,似乎悲壯,卻自信雄壯、沈穩!科技,只是晶片的遊戲。
真的是這樣嗎?我是固執還是矇昧己心?
四十年前美國太空總署發射的「旅行家二號」探測船飛向無垠的宇宙,永遠不會歸返;猶若那年我十八歲,決意文學起程,至今不渝……此時,我忽然想起:探測船到哪裡了?孤獨的穿過險惡的隕石群,它,至今還嗎?萌生撰寫〈未來的未來〉就如同一份思念。
其實是寫給未來的孩子(他們在電子書尋搜?)。很多年之後,孩子們是否只能在博物館裡,隔著玻璃比頭論足的指著舉世僅存的一冊紙本書?會有那樣的場景,在未來的未來。
未來的未來,我們早就不在了。此刻寫下的文字,印刷的書籍,百年後飛灰煙散,無人記取;但是必須在今時虔誠、勇健的留下,未來的孩子得以知悉從前的現在。就像永不歸返的「旅行家二號」遠行四十年,我還思念著。
作者簡介
林文義
1953年生於臺灣臺北市。少時追隨小說、漫畫名家李費蒙(牛哥)先生習繪,早年曾出版漫畫集6冊,後專注於文學。18歲寫散文、48歲撰小說、53歲習新詩。
曾任出版社、雜誌社總編輯、報社記者、研究員、《自立副刊》主編、國會辦公室主任、廣播與電視節目主持人、時政評論員,現專事寫作。著有散文集:《歡愛》、《幸福在他方》、《迷走尋路》、《邊境之書》等37冊。短篇小說集:《鮭魚的故鄉》、《革命家的夜間生活》、《妳的威尼斯》3冊。長篇小說集:《北風之南》、《藍眼睛》、《流旅》3冊。詩集:《旅人與戀人》。主編:《九十六年散文選》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