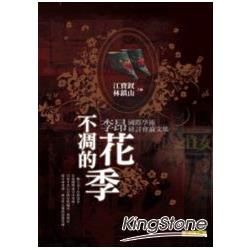迷向/鹿港大街
這個地方,真難找路。
我們一直在迷路。
然後便是無止的空白。
浩蕩的空白裡不休止地問道:鹿港有沒有鹿?它是一座鹿足雜沓的港嗎?大街綿長而蜿蜒,石磚路窄仄而欹斜,陽光和屋影勾肩搭背,一起編織成一張時間的蜘蛛網,圈住所有過路迷向的蟲蟻。
迷路的人永遠也走不出去。是我最初的鹿港印象與最後的記憶。
留不住的青春歲月,流過盤古神話的不死之身,點點滴滴地在閱讀裡一再地死去復活。經歷了李昂的花季、婚禮,懷抱著有曲線的娃娃,我的青春長跑者,再也走不出去了,你將往哪裡去?或者只能坐下來,在複沓的文字裡呼吸。
這時候,我的鹿港印象與記憶,是我的,還是被李昂的文字所建立?
容我溯跡李昂的鹿港。鹿港是一個殘存過去光輝的地方,如果有人在那裡「長期住過,相信該更能了解這類由家族聯合起來的小鎮,只屬老年人」,進行著施淑所謂「小鎮瑣碎冗悶的生活」,李昂說,對她那個「年齡的女孩,是太大的一種負擔」。這個負擔轉變為對現狀莫名的抑鬱和逃避、對未來的迷惘與惶惑,被禁錮而愈來愈濃烈的慾望,流淌於字裡行間,一種囁嚅摸索、憧憬窺伺的夢幻,一種恐懼不安、刺激好玩的期待,一種悠然成形又似無有的妄念蠢動。於是,鹿港是李昂的青春叛逆出走之地,與其在「荒漠與隔離」的古老市鎮「靜坐等待變化或救贖的空茫」,不如來個徹底的「反叛」,藉由聯考的機會逃向「充滿『異鄉人』的世界」──台北。在面對自己人生聯考的「一場硬仗」之後,當時仍施行戒嚴體制的台灣,整體社會猶瀰漫著一股沉悶的氣息,不論是政治空間的緊縮、族群意識的壓抑,或者是現代生存的苦悶本質等等因素,一起集結為如同存在主義者思考的人生過程之荒謬異狀以及面對真實生活的「噁心」(La Nauss,沙特名著)情境,而抒發其個人「情結」的文字創作,便成為「存在者」李昂的自我紓解之道了。李昂所採取的姿態是對當時社會的「性禁忌」來個書寫上的空前「叛逆」──她曾對她的姊姊施淑表示:性是「與自身最有關的」。
何其有幸的,李昂找到她的道路。
意樓講古/婦人殺夫
不要走丟了。
也許是我走路的姿態,殘留著過往兩度小鎮盤桓的迷惘,一路不斷地招引來不同的聲音來叮嚀。
步伐跨過天后宮、文開書院,掠過周定山、洪炎秋,在聯合文學所帶領的大隊人馬之下,我們來到意樓。
意樓裡歲月斑剝已經被改妝修復,楊桃樹撐起了故事的情節。有一個少婦,夫婿去內地時訣別於樓下,園子裡這棵楊桃樹是他親手種的,以楊桃的成熟約定回來的日子。但少婦數盡了所有的日子,楊桃樹伸枝展葉,結了一年又一年的果實,卻誰見夫婿的蹤影?在這樣千年等待真情現身的參差光影裡,我們談起少女李昂的自我歲月,鹿港舊鎮所賦予她的變形記憶,飄浮著佛洛伊德、卡繆、齊克果、孟祥森的一大批存在主義譯本,以及法國女作家莒哈絲《如歌的行板》,從此,市井傳說與地方禮俗雜錯,像是一杯攪拌的珍珠奶茶,或黑咖啡上盪出顏色數層的冰淇淋,為李昂後來的書寫奠定了基本的風格。
李昂所逃離的鹿港,畢竟翻轉成為提供她創作的泉源,銘刻生命經驗與記憶的所在;就像是,女性曾經是她要逃離的身分,又作為李昂自我最後依歸的認同。李昂文本中的鄉土與女性議題同時成熟於八○年代。而代表作便是《殺夫》。
是什麼樣的壓抑,使得妻子以屠刀殺豬般肢解了丈夫?是什麼樣的環境,可以成為承載《殺夫》的地景?是什麼樣的勇氣,蘊育而且寫下這樣的作品,挑戰眾夫之憤怒?
《殺夫》後來成為台灣文學史上備受讚揚的重要作品之一,榮獲1983年聯合報中篇小說首獎。然而這本書發行後,卻被保守的評論家大肆撻伐,視為「驚世駭俗」、「傷風敗俗」、「墮落」和「社會亂源」。當「開明」的讀者認為,《殺夫》的女主角林市是受到丈夫殘忍的虐待而精神崩潰,不該為其殺夫行為負責時,立即引發了一場充滿爭議性與法律控訴的風暴。《自立晚報》的時評版表示,這種見解毫無根據。社會受法律的約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寬恕謀殺罪行,特別是妻子殺害丈夫這種行為。時評版又說,有許多方法可以使虐待案件受到司法正義的審判,為報復而殺人是天理難容之事。假使有作品支持或鼓吹復仇主義和報復殺人,這將摧毀社會和諧與法律權威,造成可怕後果。不久後,《文壇雜誌》更是針對《殺夫》有關性描寫的駭人處理手法,發表一系列的評論,並暗示李昂是一位毫無羞恥心,在性方面受挫的單親婦女,她那對肉體與性事的露骨描寫已違反早期社會道德規範,因此她該受到如此嚴重的批判。甚至有些評論家控告李昂剽竊,說她的作品大玩性文字遊戲。殺夫事件成為台灣文學史上十四件重大議題之一。
不要在任何人,不管是善心還是惡意,在創作這件事的發聲裡,走丟。
林投姊/會旅行的鬼
最怕訪問台灣的舊鎮。在不同的時間裡,每一次都發現被沖蝕毀壞了一些什麼,古老的房子被砌起的大樓占去天空了,朗闊的天際線被切斷了。
這不是佛家的看法嗎?成住壞空。有什麼是能留住的呢?一切已在的空間,已在的實體,都只能朝壞毀的方向走。
是假日,鹿港大街像一般的觀光市肆,從各方來的步伐與方音煮成一鍋的水,不斷地仍在攀爬文明的沸點,而屬於時間的歷史卻悄悄地從牆間屋隙裡墜落。
在我看,以鹿港所經歷的過去,它只留下今日的景光,不免似被紈袴子弟揮霍後,雖是構架還在,裡子卻多少是空洞了。
所幸的是,文學家的想像不僅重塑歷史,而且在墜落的時光裡,打造出嶄新的歷史。
《殺夫》事件後,李昂關於性別與鄉土的思索日趨於成熟,眼界擴大,她的筆觸遂去開啟更廣大的書寫空間,台北都會的《暗夜》生活,《北港香爐人人插》、《迷園》、《看得見的鬼》裡對台灣歷史的反省與建構,性別政治扣住了國族認同,其後,耗時近十年所完成的《自傳の小說》將地理空間擴大至日本及海峽對岸。先是,二十世紀後期,中國崛起,台灣也開放大陸探親,於是海峽兩岸之間長期的對立與往後態度上的依違糾葛問題,頓時浮上檯面,也在在牽引國人不同程度的反應,橫跨兩岸題材的書寫對象遂成為李昂關注的焦點;1987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讓作家李昂敏銳地察覺到政治議題的書寫,已經成為可能,再加上偶然的契機裡,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深深吸引她的目光,李昂所面臨的創作瓶頸,因日本之旅而重獲契機,便毅然重拾中輟的筆觸,完成了以性別、政治、國族、歷史、情慾、認同、記憶為訴說核心的《自傳の小說》以及猶如註記的《漂流之旅》散文記述。而後別出心裁的《鴛鴦春膳》則進一步結合了日常生活中的飲食文化。《七世姻緣:台灣/中國情人》則是因應中國崛起後,關於民族、文化、血緣的艱難探索。
在九○年代,李昂「性別/國族」此一階段的書寫,使她的著作重心轉入「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的創作層次。而在跨世紀後的女同、飲食、情慾書寫的連結,被改編為電視劇、電影,以及她個人的電視名嘴角色,李昂,對於許多讀者,仍舊是一個謎面拆解了很多層仍找不到謎底的謎。
然而,我們何需拘限於謎底?豈不更應該著眼於謎面所表呈的啟示。去聖邈遠,寶變為石,惟有文字能流過盤古的神話之身,將在鹿港的大街小巷,海陸天空,一再地死去並復活,所有行走的風聲,都將被認出,是一個又一個不捨得人間煙景的鬼魂,決定將自己的命運寄予永恆的飄盪,守護創作的繆斯,在這片生長著林投樹林繁茂的土地。
尾聲
義無反顧的勇氣與決心,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李昂對社會體制的衝撞,對父權結構的挑戰,對文字藝術的堅執,在在為她打造了進入文學史的條件。就只是如此便教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自博士論文起研究李昂迄今,竟爾二十年。歲月催人老,在某種意義上,這個李昂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既特別為女性文學的經典化而籌辦,卻也是我對自身青澀年光的回顧。感謝來自國內外學者的慨然投入,使得研討會成為可能;感謝《聯合文學》對文學恆久的守護,讓此次特輯順利完成;自然更不能不感謝李昂的青睞,同意由我來籌辦這場盛宴。在這個過程裡,李昂與我點點滴滴所建立的姊妹情誼,使曾經辦過無數學術活動的我領受了前所未有的經驗,但願它將是另一個文學故事的起點。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不凋的花季:李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5 |
小說 |
$ 425 |
小說/文學 |
$ 440 |
華文文學研究 |
$ 440 |
華文文學研究 |
$ 450 |
現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不凋的花季:李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0年5月國立中正大學舉辦「第四屆經典人物—『李昂跨領域』國際學術座談會暨研討會」,本書收編此研討會的部分論文,分為「專題演講」、「論述」、「座談會」與「國際論壇」四部分,大抵涵蓋了李昂作品中有關兩性、政治、情欲、國籍認同,以及李昂與國際文壇的對話等各種面向,凸顯其跨領域的豐富性。
【關於李昂】
本名施淑端,台灣鹿港人。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美國奧立崗州立大學戲劇碩士。著有小說《花季》、《愛情試驗》、《她們的眼淚》、《殺夫》、《暗夜》、《一封未寄的情書》、《迷園》、《北港香爐人人插》、《禁色的暗夜》、《自傳の小說》、《看得見的鬼》、《花間迷情》、《鴛鴦春膳》、《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其中《殺夫》已有美、英、法、德、日、荷蘭、瑞典、義大利、韓國等國版本。《迷園》亦已迻譯成日、法文出版。《自傳小說》在日本出版。《暗夜》在法國出版。《看得見的鬼》在德國出版。散文《貓咪與情人》、《漂流之旅》、《愛吃鬼》,社會紀實作品《外遇》,以及人物傳記《施明德前傳》。作品曾由《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舊金山紀事報》、《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法國《世界報》、英國《衛報》等評介。2004年獲法國文化部頒贈最高等級「藝術文學騎士勛章」。
作者簡介:
江寶釵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文學理論、台灣文學、女性文學。主要著作有《台灣古典詩面面觀》、《嘉義地區古典文學史》、《白先勇與台灣文學史的構成》,主編當代小說讀本《島嶼妏聲》、《小說今視界》、《時代新書》,研討會論文集《樹的見證──鄭清文文學論集》、《泥土的滋味──黃春明文學論集(與林鎮山共同主編)以及嘉義作家作品集、民間文學集等多種。
章節試閱
迷向/鹿港大街
這個地方,真難找路。
我們一直在迷路。
然後便是無止的空白。
浩蕩的空白裡不休止地問道:鹿港有沒有鹿?它是一座鹿足雜沓的港嗎?大街綿長而蜿蜒,石磚路窄仄而欹斜,陽光和屋影勾肩搭背,一起編織成一張時間的蜘蛛網,圈住所有過路迷向的蟲蟻。
迷路的人永遠也走不出去。是我最初的鹿港印象與最後的記憶。
留不住的青春歲月,流過盤古神話的不死之身,點點滴滴地在閱讀裡一再地死去復活。經歷了李昂的花季、婚禮,懷抱著有曲線的娃娃,我的青春長跑者,再也走不出去了,你將往哪裡去?或者只能坐下來,在複沓的文...
這個地方,真難找路。
我們一直在迷路。
然後便是無止的空白。
浩蕩的空白裡不休止地問道:鹿港有沒有鹿?它是一座鹿足雜沓的港嗎?大街綿長而蜿蜒,石磚路窄仄而欹斜,陽光和屋影勾肩搭背,一起編織成一張時間的蜘蛛網,圈住所有過路迷向的蟲蟻。
迷路的人永遠也走不出去。是我最初的鹿港印象與最後的記憶。
留不住的青春歲月,流過盤古神話的不死之身,點點滴滴地在閱讀裡一再地死去復活。經歷了李昂的花季、婚禮,懷抱著有曲線的娃娃,我的青春長跑者,再也走不出去了,你將往哪裡去?或者只能坐下來,在複沓的文...
»看全部
作者序
世界李昂.在地鹿港/江寶釵
在記憶的岸上打水漂兒。打中鹿港的這個漂兒,漪起的第一圈晃蕩著大學畢業旅行裡憧憧的一群臉,我與我的同學們,正準備到中學去教書,這是學生生涯最後的告別式;接著再來的一圈是初結婚時,我與丈夫摩托車飆在風裡的一雙臉……。
歐巴桑,這條路怎麼走?誰來告訴我,從這裡走,會通往哪裡去?
在記憶的岸上打水漂兒。打中鹿港的這個漂兒,漪起的第一圈晃蕩著大學畢業旅行裡憧憧的一群臉,我與我的同學們,正準備到中學去教書,這是學生生涯最後的告別式;接著再來的一圈是初結婚時,我與丈夫摩托車飆在風裡的一雙臉……。
歐巴桑,這條路怎麼走?誰來告訴我,從這裡走,會通往哪裡去?
目錄
【序】
世界李昂.在地鹿港/江寶釵
【論述】
日本文化界與李昂的對話
──以吉本芭娜娜(YOSHIMOTO Banana)和小川洋子(OGAWA Yoko)為主/藤井省三
夢鎖泉漳兩岸情
──試論李昂《七世姻緣》的跨地情愛書寫/廖炳惠
李昂與卡夫卡存在主義小說比較論/蔡振念
論李昂小說的敘事轉折
──立足於鹿城故事、《殺夫》、《迷園》的觀察/張重崗
性別.凝視.再現
──李昂小說《殺夫》、《暗夜》之電影改編與影像詮釋/黃儀冠
李昂小說中的流言/陳艷姜
歷史的虛構性與她的故事(Her Story)
──讀李昂《自傳の...
世界李昂.在地鹿港/江寶釵
【論述】
日本文化界與李昂的對話
──以吉本芭娜娜(YOSHIMOTO Banana)和小川洋子(OGAWA Yoko)為主/藤井省三
夢鎖泉漳兩岸情
──試論李昂《七世姻緣》的跨地情愛書寫/廖炳惠
李昂與卡夫卡存在主義小說比較論/蔡振念
論李昂小說的敘事轉折
──立足於鹿城故事、《殺夫》、《迷園》的觀察/張重崗
性別.凝視.再現
──李昂小說《殺夫》、《暗夜》之電影改編與影像詮釋/黃儀冠
李昂小說中的流言/陳艷姜
歷史的虛構性與她的故事(Her Story)
──讀李昂《自傳の...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江寶釵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4-24 ISBN/ISSN:978957522970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9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