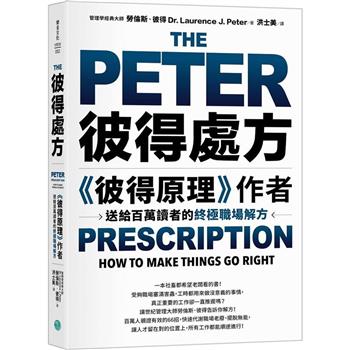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來去花蓮港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來去花蓮港 作者:方梓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4-2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10 |
文學 |
$ 237 |
中文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小說 |
$ 270 |
小說 |
$ 270 |
現代小說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0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來去花蓮港
書中的阿音和初妹,一個是閩南女子,一個是客家女子;一個不識字,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如地母多產,一個無法生育。她們分別從鶯歌、三義來到花蓮,用不同的方式在花蓮的土地上生根開拓自己的人生。或許她們都沒有新女性的觀念,但她們用手、用腦、用子宮、用體力實踐女性的能力,擘劃家族的藍圖。與這兩個日本時代的女性做對比的是現代都會女子闕沛盈,她以空虛的新女性主義生活,在前往花蓮見母親的過程回溯台灣女性的發展,也是在檢視自己。
全書以閩、客、國語三種語言交織;作者用細膩的筆法描繪耕作、生活及女人的思維,娓娓道來這部平實動人的故事,其對細節的描述和時代氛圍的掌握格外精緻巧妙,呈現出台灣女人輾轉流離卻堅韌不拔的女性群像,所有世代的女人讀完都會忍不住一掬感動的淚水。
作者簡介
方梓
本名林麗貞,台灣花蓮人,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國立東華大學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曾任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總編輯、全國文化總會學術研究組企畫、《自由時報.副刊》副主編、總統府專門委員,及大學兼任講師。著有《人生金言》、《他們為什麼成功》、《傑出女性的宗教觀》、《第四個房間》、《采采卷耳》等。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