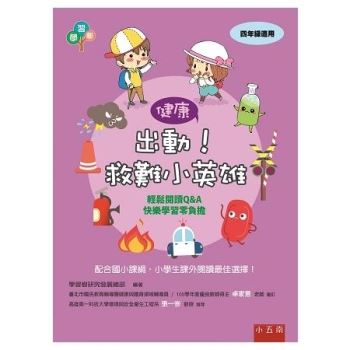鏊
鏊,就是鏊子的簡稱。鄉村裡稱某些食物器具時,多用一個字代替,像人物暱稱,器物亦然。譬如這面鏊子,姥姥就對我說:去你三姥娘家借個「鏊」。
鏊是村裡的一種烙餅工具。在飲食單裡應該屬於「器部」。
鐵匠藝人孫炳臣在村裡最會鑄鏊子。鑄鏊子用生鐵,平面圓形,中間稍凸,烙餅時可以來回反覆顛倒,易於透熟,不焦糊。
村裡的鏊子們主要有石鏊子,鐵鏊子兩種。外觀上有三條腿的,有不帶腿的。孫炳臣鑄的鏊子質量好,名聲都傳到五十里外的滑縣鎮,我們那一帶優秀的烙餅大師和巨匠都用孫炳臣鑄的鏊子才能大顯身手。近似珠聯璧合。有人在冬天還大老遠騎自行車來,抖落一身簌簌碎雪,說要訂他一個鏊子。村裡人一問,吸一口涼氣,這傻傢伙竟是來自百里開外的安陽。
全村人都好吃烙餅,孫炳臣也好吃烙餅,經常讓媳婦在家裡用自己的鏊子烙餅,一張張小荷葉般大。全村就數他家的鏊子有油,滋潤,渾圓,像領袖的面龐,顯得亮堂。一張烙餅把在手裡,再就蔥,那就有點像帝王在御膳。
我姥姥總結過,如果扳指頭查一下,村裡凡是好吃烙饃的人家,大都是不會過日子,他們吃了上頓不想下頓。有點「作鬧」。因為烙饃費糧、費油。家家生活都拮据緊張。
有一天,本是鐵匠手藝人的孫炳臣超出專業範圍,忽然竟當起了「預言哲人」。
在飯場上,他邊吃烙餅,邊問別人:「我咋覺得這黨的政策就像鏊上的烙餅————不停在翻來覆去?」
那一年,滑縣城裡來的革命工作隊正好在村中開展工作,由李書記帶隊,李書記警惕性高。嗅到了烙餅上的異味。認為這孫炳臣屬於「反黨言論」。一下子算是在小村裡丟了一顆炸彈。
鏊子無辜。一句村裡常用的歇後語,因為使用的地點不對,時間不對,鏊上煎人,聽者有心,就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最後輾轉,去新鄉監獄裡勞教。孫炳臣走後,爐火熄滅。村裡從此不再鑄出好鏊子。烙餅事業低谷,顯得蕭條、冷落。
三年後,有人捎來信道:孫炳臣死在監獄。
我姥爺歎口氣,說,他這種死法,要是放在古書上,就叫「瘐」。
看老書多,識老字。我姥爺是村裡最有學問者。並因此耽誤了許多農活。
儘管都是一個字,但「鏊」和「瘐」之間並無聯繫。這一點可不像餅和鏊。
2010.8.8.
白芝麻
(用於捉拿妖怪的農作物)
姥爺在北中原播種的芝麻一共有兩種:白芝麻,黑芝麻。
前者用於軋油食用,後者用於入藥療疾,主治少白頭。我青年時就是少白頭,一地散雪。上學時讀到岳飛《滿江紅》,裡面有一句很抒情的句子「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一怔。總疑心老師是在挖苦我。就覺得鄉村老師沒有岳飛胸懷之大。
後來知道黑芝麻治白髮這個單方,如獲至寶,就開始一把一把地喃食芝麻,一個療程下來,風淡雲輕。頭髮照樣白,芝麻照樣黑。可見年華虛度不是一把黑芝麻所能阻擋得了的,是歷史大潮流。
不過到現在,這種「少白頭」大家都恭稱「時尚灰。」一種領潮流的髮式,好幾個奧斯卡獎得主就是如此這般梳理。一地雪。
陶弘景對芝麻評價最高,「八谷之中,惟此為良。」但這樣突出一種打擊一片的效果並不好,卻襯托著另外農作物都不是良種,在莊稼內部,肯定要讓麥、豆、谷、粟之類的其它七谷們生氣。
芝麻還可以作漁業道具,這是我親身實踐得來。我剛開始上班謀生,在黃河畔一個叫蘆崗的鄉村營業所當信貸員,黃河汛期時常「上水」(就是氾濫發水),這期間,我摸索出來一個捉蝦米的方法:把幾捆芝麻桿系整齊放在水裡,一段時間之後再拉出,裡面會一一鑽滿蝦米。因殘餘芝麻香味吸引,黃河蝦貪小便宜。每次把芝麻捆往外一磕,能倒出來一小碗左右的活蝦米,活蹦亂跳。蝦米可以生吃。鹹,鮮。
那時黃河兩岸貧窮,大水浩淼,好在河水尚未被現代化污染。
芝麻有很高的出油率,是鄉村油類中上品。鄉村油坊一般有毛驢,石磨,油錘,打油匠的吆喝聲。芝麻還有另一個功能,就是捉拿妖怪可以作道具使用。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姥爺在鄉間講過一個故事。
說,過去一個求學的書生被一隻狐狸精迷惑住,經常夜半約會。同伴發現近段時間這書生面黃消瘦,體質下降,那時還不流行減肥健美,就認定為魅所纏,會影響高考前途。但書生早被愛情沖昏頭腦,打死也不信。這一天,這愛管閒事的同伴就交給書生一個小布袋,讓其等下次美女再來約會,作別時就把這個布袋送給她。相當於現在送一名牌坤包。
這位書生一一照辦。
小布袋裡裝了一袋子飽滿的白芝麻粒。分明還裝了一布袋比白芝麻還多的點點心計。心計都是黑色的。
果然,第二天清早這書生看到碎芝麻粒,一路宛轉,自床上撒向門外,他就尋著芝麻粒,紆紆曲曲穿林過野,一直尋到大別山下,見山中有一洞口,芝麻粒從此進去,這書生入洞,最後見一個皮毛漂亮弧線優美的牝狐,正在那裡酣睡。身邊放著那一個贈送她的芝麻布袋。貌若信物。
姥爺喝道,不出所料,正是一個妖怪。
他講完匆匆要去北地澆芝麻田了。
我倒是吃了一個大驚,就攆著問:「那大別山不是歷史書上常說的革命根據地嗎?」
2010,2,17
箅子和箅梁的關係
箅子,唯一的作用是架設鍋中間,用以蒸熟食品。南方箅子多用竹製品,北中原竹少,箅子原材料都使用高粱稈子。
和鏊子一樣,箅子在村裡我們也喊一個字,音讀「裱」,去聲。
我們家裡的箅子都是姥姥用高粱稈子編製,她叫「穿箅」,秋後選擇好那些均勻的高粱稈子,一一碼好,用納鞋底的細棉線穿引。有點像古人牛皮繩穿漢簡。
姥姥要穿很多張秫秸箅子,捲起來掛在牆上,多餘的要贈送親戚(我家的親戚大都不會穿箅,手懶)。那種箅子簡單,大方,乾淨,光滑,從不粘鍋。如一張雨後夏荷。
再說箅梁。箅梁則算是一個「學名」,村裡不這樣稱呼,俗稱「樹柯杈」。天然取捨。是用一個「丫」形或「人」形樹枝,草草修理刻制而成,架設在鍋中,上面才棚架箅子,用以蒸饃時不至於漏掉,饅頭失足落水,晚年失節。
村後樹類主要有柳,槐,構,楝,榆,楊,桑。
那些柯杈箅梁都是我姥爺在村後樹林裡隨手砍下,再剝樹皮,一一刮平,整理光滑。箅梁一般用柳木、榆木的枝柯最好,木質發甜。那些楝木、槐木很少用,木質味道發苦。
箅梁壽命大於豬羊雞鴨。一架箅梁要使用十年,二十年。可以說,在鄉村它才算是經歷日子「水深火熱」的考驗。
箅子和箅梁的關係算是「親密戰友」,形影不離,膚肌相擁。
現在烹飪界器具裡,早已沒有箅子和箅梁這一說,炊具器材通通都使用鋁製品、不銹鋼、鐵製品、塑料品諸類,快餐年代的時光來臨,人人心急,內心裡會經常發出來「叮叮光光」的工業之聲,煩躁,上火,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它們離以上我說的這些草木元素都很遙遠。
我當年不曾想到過未來,我如今就恍然如夢。
2011。3。15
菠菜遮醜
有一天正我吃飯,姥爺隨口問我:菠菜產於哪裡。
我答:村東北地。還和孫百文家的地頭相連。
我姥爺糾正說,菠菜最早不是產於東北地,是產於離村裡很遠的阿拉伯(後來上學知道,就是現在西亞海灣一帶,那裡的駱駝都披著一張魔毯在《一千零一夜》裡面日夜趕路)。
我姥爺接著說,這菜由古代波陵國傳入唐朝,就叫菠菜了,還叫波斯草。村裡另一位教小學的孫百文老師也有學問,竟叫它「紅嘴綠鸚哥」,因為葉綠根紅。出身成份好。 後來我也開始有學問了,竟還讀到宋人張耒一首詩,題目名字竟長如一條菠菜麵條————《波稜乃自波陵國來蓋西域蔬也甚能解面毒予頗嗜之因考本草為作此篇》。累牙齒。
姥爺種菠菜一般是冬季播種,來春收穫,這種菠菜在村裡叫「埋頭菠菜」。在村外田地,那些菠菜以貼著地皮長的小棵子為最好吃,個子高的菠菜就算傻大個,梗虛,肚裡顯得空洞無物。
菠菜一般食用是涼調,蒸菜饃,或菠菜泥。姥姥有時會用菠菜汁和面,拌勻,再擀麵條,下出來的麵條是綠色的,像條條柳絲。白碗綠面,是另一番口味。
菠菜是鄉村菜民裡最平常之菜,屬於賤菜,但是它可以作秀,菠菜的種種人為行為有點像現在兩岸三地那些作秀的「花瓶明星」。我們縣裡的廚子們把它和豆腐同燒,叫「翡翠白玉版」,再加水制湯,叫「翡翠白玉湯」,焯水後剁碎做羹,叫「翡翠羹」,如果和清蒸魚相配,叫「碧波魚」。
還有一道更誇張的。水發銀耳,焯水切小塊備用,擇洗乾淨的菠菜取內心,焯水涼淘後,把銀耳菠菜一同入盆,加鹽、香油、醋、白糖調製即成。你猜這菜叫什麼,它竟敢叫「青天白玉」,因為和「青天白日」接近,要是在「文革」期間,肯定打個反革命。
菠菜葉子翠綠,亦入畫,但大家不屑,小家不為,畫松,畫牡丹,畫林黛玉,畫蘭花指,畫張飛的鬍子,都多不畫它。菠菜之色有點像一篇平淡無奇文章裡,忽然冒出來的一條好句子。
菠菜在人民的視覺上是增色之菜,大庭廣眾之下,如果烹飪大師的一盆羹湯做失敗了,可以撒上幾葉菠菜葉子遮醜,用以及時挽救。像官員召見明星匆忙出場前的打粉遮斑。
2011。3。15客鄭
搬零嘴兒
鄉村自有屬於自己的飲食時間。不次於「北京時間」。
一個村子有一個村子多年形成的飲食頑固習慣,不易改革。在留香寨的一日三餐,俗話叫做「一天三頓飯」。
一餐稱「一頓」,三頓各有其名。早餐稱早起飯、清早飯、頭晌飯;午餐稱晌午飯、晌飯;晚餐稱後飯、夜飯、黑夜飯、後晌飯、還有一個專用名字,叫「喝湯」。哪怕你晚飯是吃噎死人的干飯,也得約定成俗喊「喝湯」。有一傳說,這裡先不表。
正餐之間的另外進食叫「墊補」,「搬嘴」、「搬零食」,零食又叫「零嘴兒」。「搬零嘴兒」是村裡一個專用「食詞」,相當於老鼠地下搬運,多是小孩子間的食事,大人一般不為。大人們如要「搬零嘴兒」,肯定會讓一村人笑話。故:兒童尚可,大人不宜。
我眼窄,至今尚未見世界上我國和「他的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搬零嘴兒。
話說這一天,我從喂牲口的飼養員蔡老廣那裡偷得一把炒過的料豆,攆著鬧心的鈴聲急急上學。料豆炒得半生半熟,像嗑嗑巴巴的古文。是喂牲口們的。我姥爺說過,牲口吃料豆乾活才有力氣。就像人得吃白面。一匹驢子一天必須要定量吃四兩豆子,因人為剋扣,那些驢嘴多吃不夠。人嘴大於驢嘴。
在村裡說「某某吃料豆」,是罵人的話。村裡人私下都知道:飼養員蔡老廣是偷生產隊裡的牲口料豆才養活全家。只是都不明說。
學校那些白色凌亂的鈴聲攤滿骯髒的課本之上。正是上一節討厭的算術課。老師往黑板上寫字母,她一轉身,我就往嘴裡急忙填一顆黃豆。咯崩一聲。一個字母。再轉身,再填豆。再咯崩一聲。
三天之後,內部出亂,傳聞有某一小人告密,說我在課堂上「搬零嘴兒」。
回家,挨大人揍一次。載入日記,屁股發熱,牢記終生。
2011.4.6.清明節後
吃雜菜
一碗雜菜的成份一般有如下五種:粉條、豆芽、麵筋塊、海帶、白菜。
也許會有神來之筆,譬如掠過的烏鴉留下一粒新鮮鳥屎,飛機掉下一盒日本豬肉罐頭。但這種命中率極小。
灶台上,以上諸位雜菜是不分階級地混在一起,必須要大火燒熬。鄉村上等的雜菜還會漂浮有幾塊小肉片,水落石出。像一村芸芸百姓裡忽然冒出幾個紅色黨員。顯得分外醒目,搶眼。
《東京夢華錄》裡倒是有一道「雜菜羹」,可惜孟元老鋪排出的原料不詳,我推斷就是我們北中原雜菜的前身。世上凡「雜」,肯定不純,雜,皆屬政治產物或平民食物。國家以正統自居,雜菜多與平民為伍。古典的皇帝和現代的總統、主席一般都不會端一碗雜菜蹲在門檻大嚼。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雜菜,就像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粹一樣。一次夜半,偶看日劇盜版碟子,方知道「穿浴衣看煙火吃雜菜攤煎餅」,才是人間正經事。其它都可暫時不提。
在北中原,「吃雜菜」並不全是說要去吃雜菜,它只是一個隱喻,是鄉村版語系裡的「完蛋」、去世、作古、死掉之意 。
北中原飲食話語氛圍常常會籠罩著一個人的一生,裡面包含社會元素很多,譬如見面說「吃過了?」就是問好。「啥時吃你的鯉魚?」這是道喜。如果自己還是光棍,這是問自己何時結婚,如家裡有孩子,是問孩子何時結婚。再如果話鋒一轉,問「啥時吃你的雜菜?」那就是咒你去完蛋。
平常日子裡,鄉村把處理喪事稱「過白事」,每一個村都自發組織有「紅白理事會」,有點近似當下聯合國愛管事的常任理事國。譬如村宴上飲酒的標準如何,每瓶不超過錢數如何。就是不讓你生產核武器!
我們村標準是每瓶白酒不超過三元,後來提高到三塊五,四元,四元五,五元。通貨膨脹,水漲船高。為了面子,大家都想造核,要放原子彈,要講排場。但是到最後每個聯合國成員國還是要端一碗雜菜,大家蹲下吃。
街面傳來狗叫,聲巨如獅。它們也聞到氣味,那是雜菜的魅力。
村東李老仙大人入冬去世,兒子大操大辦「白事」七天,李老仙的兒子是鄉長。門口送禮送物車輛達一里長。有好事者統計,共計碾死狗一隻,鴨一隻,雞三隻。
村西人說,「走吧,今個去吃李老仙的雜菜。」
肉多於菜。石出水落。是上等的好雜菜。
一月之後,有一張公告下來:某某縣某某村某某鄉長因借其父去世藉機大肆斂財,觸犯黨章,涉規犯事。
村裡人說,這是專門對李老仙的兒子李鄉長的,都是吃李鄉長他爹的雜菜吃出來的。另一種禍從口出。
2010,5,7
吃桌
在鄉村,你如果越過高高的炊煙與雞鳴,去找一個熟人,門軸響過之後,門開一細縫,這家小孩子會出來,露出一方豁牙, 如上學考試慌張時一道沒做的填空題。小孩子是一臉幸福的樣子:
「我爸不在家,早去吃桌啦!」
那口氣分明有點得意與自豪。
在鄉村,你可千萬不要認為這孩子他爸的牙齒硬,是銅牙鐵齒。「吃桌」不是去啃木頭桌子,而是酒宴的借代。鄉村把赴宴統稱為 「吃桌」。
在鄉村卻不是誰都能吃桌。能吃桌的人,都是鄉村有身份和頭面的人。能被人看上,多為毛主席在「老三篇」文章裡說的那些 「李鼎銘」之類鄉村人物。
吃,在鄉間永遠是第一位。無論紅白喜喪,在鄉間都需要吃桌,生死之事是鄉下人生活裡花銷開支最大的兩項,像沉甸甸的兩塊石頭,壓在人肩上,最後,壓在人心上。
平民「辦桌」就不如鄉長家氣派。
這一年寒冬歲尾,村中一個老光棍張老賢的爹去逝了。叫「辦白事」。辦理喪事時,鄉村裡要這位老光棍辦十多桌酒席,用於答謝招待村中幫忙的鄉黨及左鄰右舍。
老光棍卻一減再減,最後每桌合款三十元:六個菜,另外加一瓶兩塊錢的燒酒。即使這般,十多桌一共還得三百多元。相當於他家一年出力流汗之後的收入。
「走,吃桌去」。大家奔走相告。
大家奔走相告。「走,吃桌去」。
像鄉間的風,吹過許多雙正在聳立著的空蕩蕩的耳朵。鄉間所謂的好事都如新鮮的露珠,會讓最乾枯的狗耳朵也一時生動而新鮮。
村兩頭的狗們,開始慌裡慌張地奔跑相告,準備在村中央會師。一狗臉莫名其妙的喜悅。
這個詞單從字面上望文生意地解釋也對。果然,一村的硬「桌」,半天功夫,都被一顆顆更硬的牙齒卡嚓卡嚓吃掉!
看著滿院一地鍋碗瓢盆的狼籍相,老光棍悶悶吸著草煙, 煙圈如一條條繩索低垂,緊張得幾乎要套在他脖子上。分明感覺那繩子在逐漸勒緊。
我日他祖宗!他關心的是:自己如何用力氣填補這次因為「吃桌」而吃出來的一個深如冬井般的大窟窿?
炊具初考
一,鐵鍋。鐵鍋又稱飯鍋、大鍋。像盛夏池塘裡的荷葉一樣,鍋在村裡形狀大小不等。母親是這樣區分鍋的:八印、七印、六印、五印、四印。
由大到小。像主席團外事出訪成員下機或座席的順序。
有一年下冰雹,大如小棗,砸傷許多路人。村裡一個名人正好從滑縣高平集上買鍋歸來,就頂鍋而行。叮叮噹噹。從容信步。這人就是我二大爺。行為可入《世說新語》。
二,鍋蓋。木製,有一個把手,前街的趙木匠說:桐木料做鍋蓋最好,料輕。鍋蓋常以七塊或八塊木板拼成,村諺:「鍋蓋,鍋蓋,七塊,八塊。」那是為了怕裂。
我家還有一種鍋蓋,是姥姥用高粱秸葉編製,純天然紅白兩種顏色,用一條棉布條墊在鍋蓋下,纏繞在蓋和鍋中間,防止蒸氣流出。洩了元氣。
三,炊帚。刷鍋的必需品,一般用高粱穗扎綁製成,我姥姥叫「捆炊帚」。一把 炊帚用到最後瘦小了,就叫「炊帚骨朵」。像鄉下人宿命。
四,風箱,又稱風掀,用以吹火。風箱可有許多話題。姥姥能從拉風掀的節奏中知道一個人的心情好壞。風箱也有表情的。我姥爺卻常說「風掀裡的老鼠————兩頭受氣。」
以後沒有了風箱,此語意背景肯定不明矣。
五,燒火棍。用以撥調灶裡燃燒的柴草,一般都是隨手取一棵樹枝、秫桿使用。我姥爺說,楊門女將裡的楊排鳳還有一把鐵燒火棍。我又問,有銅的嗎?有。有金的嗎?姥爺想想,有,孫悟空的金箍棒。
燒火最需要技巧,姥姥把那支燒火棍輕輕一撥,三兩下,灶火就會通紅。我卻燒得狼煙滾滾,烏煙瘴氣,嗆得不停咳嗽。
剛好,那天姥爺下晌從田地回來,放下籮筐,驚奇問道:「這是熏草狐洞嗎?」
2011.3.17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一個人的私家菜:說食畫的圖書 |
 |
一個人的私家菜:說食畫 作者:馮傑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5-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9 |
二手中文書 |
$ 270 |
小說/文學 |
$ 300 |
文學 |
$ 334 |
現代散文 |
$ 334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一個人的私家菜:說食畫
一冊別樣散文,卻是一本關於吃的書,
又不是純粹的吃書,它是屬於詩人「一個人的吃」。
無國宴豪華大餐,皆民間平常食事。寫的不是食單,是記憶裡親情,文化殘存餘脈。有世相細節,味蕾記憶,有親情人事,童言食語。形式上圖文並茂,藕斷絲連,呼應相補,內容上斷章取義,摭拾採擷,趣味盎然。作者在「煮字烹詞,搶詞奪理」。既是鄉村食單、俎上文字,又是時代痕跡、晚風殘月。字裡瀰漫文字的味道,行間穿行著口味鄉味,更有心味。作者在「與食俱進」,相當於一堆漫不經心的「文字的零食兒。」
讀這樣的小食單是在「搬食」--搬文字的零食兒。
本書作品曾在臺灣《聯合報》、《中國時報》、《中華日報》開設文圖專欄。
作者簡介:
馮傑,
一九六四年生於中國烹飪之鄉河南長垣。
少年始涉世謀生,從事過多種職業。
獲過《聯合報》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
著有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台灣九歌出版社)、《泥花散帖》(台灣印刻出版社)。
七歲時會炸油饃,十七歲時會做撈麵,三十七歲時記錄食單,現在畫畫。
章節試閱
鏊
鏊,就是鏊子的簡稱。鄉村裡稱某些食物器具時,多用一個字代替,像人物暱稱,器物亦然。譬如這面鏊子,姥姥就對我說:去你三姥娘家借個「鏊」。
鏊是村裡的一種烙餅工具。在飲食單裡應該屬於「器部」。
鐵匠藝人孫炳臣在村裡最會鑄鏊子。鑄鏊子用生鐵,平面圓形,中間稍凸,烙餅時可以來回反覆顛倒,易於透熟,不焦糊。
村裡的鏊子們主要有石鏊子,鐵鏊子兩種。外觀上有三條腿的,有不帶腿的。孫炳臣鑄的鏊子質量好,名聲都傳到五十里外的滑縣鎮,我們那一帶優秀的烙餅大師和巨匠都用孫炳臣鑄的鏊子才能大顯身手。近似珠聯璧合...
鏊,就是鏊子的簡稱。鄉村裡稱某些食物器具時,多用一個字代替,像人物暱稱,器物亦然。譬如這面鏊子,姥姥就對我說:去你三姥娘家借個「鏊」。
鏊是村裡的一種烙餅工具。在飲食單裡應該屬於「器部」。
鐵匠藝人孫炳臣在村裡最會鑄鏊子。鑄鏊子用生鐵,平面圓形,中間稍凸,烙餅時可以來回反覆顛倒,易於透熟,不焦糊。
村裡的鏊子們主要有石鏊子,鐵鏊子兩種。外觀上有三條腿的,有不帶腿的。孫炳臣鑄的鏊子質量好,名聲都傳到五十里外的滑縣鎮,我們那一帶優秀的烙餅大師和巨匠都用孫炳臣鑄的鏊子才能大顯身手。近似珠聯璧合...
»看全部
目錄
【序】 癖 /管管
A 鏊
B 白芝麻 箅子和箅梁的關係 菠菜遮醜 搬零嘴兒
C 吃雜菜 吃桌 炊具初考
D 冬瓜房子 豆莢三種 打涼粉 豆腐渣工程 打包
E 鵝不食拾遺
F 方甘蔗 仿試傅山吃的麵食
G 菇的分類 瓜忌 改變自己身份的蒜茄子 疙瘩湯 狗屎拌磚頭
H 黃葉根涅磐 黑糖 喝湯 糊塗 紅薯的處理方法 化腐朽為神奇 蛤蟆墨 紅豆腐
J 雞撐 角兒 薑兩種 講土語的酒 金針可度 雞脯食餅 荊芥魚藿香魚薄荷魚香椿魚等等魚都不是魚 荊芥飥兒
K 口有餘香的香 扣 磕子迷路
L 烙餅裹大蔥 烙餅志 綠豆丸...
A 鏊
B 白芝麻 箅子和箅梁的關係 菠菜遮醜 搬零嘴兒
C 吃雜菜 吃桌 炊具初考
D 冬瓜房子 豆莢三種 打涼粉 豆腐渣工程 打包
E 鵝不食拾遺
F 方甘蔗 仿試傅山吃的麵食
G 菇的分類 瓜忌 改變自己身份的蒜茄子 疙瘩湯 狗屎拌磚頭
H 黃葉根涅磐 黑糖 喝湯 糊塗 紅薯的處理方法 化腐朽為神奇 蛤蟆墨 紅豆腐
J 雞撐 角兒 薑兩種 講土語的酒 金針可度 雞脯食餅 荊芥魚藿香魚薄荷魚香椿魚等等魚都不是魚 荊芥飥兒
K 口有餘香的香 扣 磕子迷路
L 烙餅裹大蔥 烙餅志 綠豆丸...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馮傑
- 出版社: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5-22 ISBN/ISSN:978957522984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9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