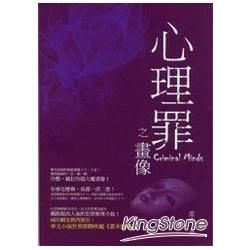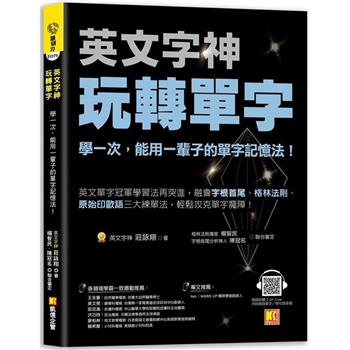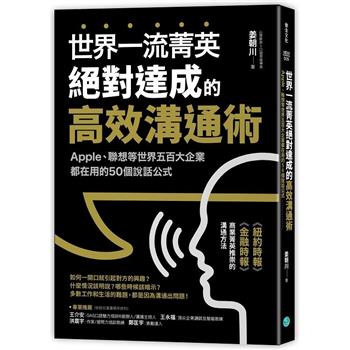序 怪物
昨天晚上,他們又來找我了。
他們還是照例不說話,默默地站在我的床前。而我,照例還是僵在床上動彈不得,眼睜睜看著那些燒焦的、無頭的軀體圍在我的周圍。而他,依然在我的耳邊輕輕說出:其實,你跟我是一樣的。
我已經習慣了和他們在夜裡相遇,可是,仍然大汗淋漓。
直到他們一言不發地離去,我才重新聽見杜宇在對面那張床上平靜的呼吸。
窗外清冷的月光靜靜地潑灑進來,宿舍裡的火焰早就消失不見了,有點冷。
我費力地翻了個身,手摸到枕頭下那把軍刀,感覺到粗糙、略有起伏的刀柄,呼吸慢慢平靜。
我又重新沉沉睡去。
偶爾我也會回到師大看看。我會坐在男生二宿舍門前的花壇上,那裡曾經有一株很老的槐樹,現在是各種五顏六色、叫不出名字的鮮花,在微風中輕薄無知的搔首弄姿。我常常凝望著眼前這棟七層高的現代化學生公寓,竭力回想它曾經的樣子。顏色褪盡的紅磚,搖搖欲墜的木質窗戶,油漆斑駁的鐵皮大門。
以及那些曾經在這棟樓裡進出的年輕臉孔。
突然間,我感到深深的傷感,就好像被一種脆弱的情緒猛然擊中。而記憶的閘門,也在不經意間悄悄打開,綿綿不絕,一發不可收拾。
如果你認識我,你會感到我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大多數時候,我都盡可能獨處。一個人吃飯,一個人走路,連聽課,都避免跟其他人坐在一起。
不要靠近我。我常常用眼神阻止那些試圖瞭解我的人。所有人都對我敬而遠之,而我,卻熟悉身邊所有人的脾氣、個性、生活習慣。如果你在教室裡、食堂裡、校園的路上,看到一臉色蒼白,看似漫不經心,卻在不住打量別人的人,那個人,就是我。
我住在J大南苑舍B座313房間。我的室友叫杜宇,法理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大概是因為同住一室的原因,在法學院裡,他是為數不多經常跟我說話的人。他是個心地善良的人,看得出他處心積慮地想和我搞好關係,也讓我在法學院裡顯得不那麼孤獨——儘管我並不在乎這一點——不過,我並不拒絕和他偶爾聊聊天,包括他那個嬌氣得有點誇張的女朋友陳瑤。
「喏,一起吃吧。」
我正端著飯盆,一邊吃著拌著辣醬的刀削麵,一邊聚精會神地看著電腦上的一張圖片和下面的文字說明,沒有留意杜宇和他女朋友是什麼時候走進宿舍的。
那是一串剛剛烤好的羊肉串,上灑著辣椒和孜然粉,黃色的油流淌下來,散發出一股焦糊味。
我想當時我的臉一定比身後的牆還白,我直愣愣地看著伸到我面前的這串烤羊肉,喉嚨裡咕嚕嚕地響了幾聲後,就把剛剛吃了一半的午飯,吐回了手中的飯盆裡。
我捂著嘴,端著盛滿還在冒著熱氣的嘔吐物的飯盆奪門而出,身後是陳瑤詫異的聲音「他怎麼了?」
我無力地斜靠在衛生間的洗手檯邊,草草地用水洗了把臉。抬起頭,牆上污漬斑駁的鏡子裡映出一張被水和冷汗浸濕的、蒼白的臉,眼神呆滯,嘴角還殘留著一點沒有洗去的嘔吐物。
我彎下身子又乾嘔了幾聲,感到胃裡空蕩蕩的,實在沒有什麼可吐的了,就顫抖著勉強站起來,湊近水龍頭喝了幾口涼水,在口腔裡轉了轉,吐了出去。
把飯盆扔進垃圾桶,我搖搖晃晃地走回了寢室。
寢室裡一片慌亂。陳瑤弓著腰坐在杜宇的床上,地上是一大攤嘔吐物,屋裡彌漫著一股酸腐的味道。杜宇正捏著鼻子,把一個臉盆扔在她的面前。
看到我進來,陳瑤抬起滿是冷汗和淚水的臉,用手指指我,想說什麼,卻被又一陣劇烈的嘔吐把話壓了回去。
杜宇尷尬地看著我:「剛才瑤瑤也不知你怎麼了,看到你正在電腦上看什麼東西,很好奇,就過去看了一眼,結果就……」
我沒有理會他,徑直走到電腦桌前。那是我正在瀏覽的一個網頁,上面有幾張圖片。其中一張是一個已經腐敗的頭顱,臉部及脖子上的皮膚已經被剝掉,另外三張分別是被害人被砍掉四肢的軀幹和左右臂。這是2000年美國威斯康辛州發生的一起殺人案的現場圖片。我把這幾張圖片下載到硬碟上的「過度損毀」資料夾中。
我站起身,走到陳瑤身邊,彎下腰說:「你沒事吧。」
陳瑤已經吐得虛弱不堪,看見我,驚恐地掙扎著往後縮,「你別靠近我!」
她哆哆嗦嗦地抬起一隻手,指指電腦,又指指我,嘴唇顫抖了幾下,終於從牙縫中蹦出兩個字:「怪物!」
「瑤瑤!」杜宇大聲呵斥道,一邊不安地看了看我。
我對他笑笑,表示不介意。
我真的不介意。我是怪物,我知道。
我叫方木,在兩年前的一場災難中,我是唯一的倖存者。
第一章 強姦城市
J城的春天悶熱不堪。儘管樹枝上仍舊空空蕩蕩的,連點綠芽都看不見,可是氣溫已經上升到了十七八度。邰偉坐在飛馳的吉普車中,不耐煩地又解開了一個釦子。
他很煩躁,卻並不僅僅是為了這個過分熱烈的春日。作為一個員警,邰偉遇到了從警十年來最棘手的案子。
2002年3月14日,J市紅園區臺北大街83號明珠社區32號樓402號居民陳某(女性,漢族,31周歲)被殺死在家中。根據驗屍的結果,死亡時間為14時至15時之間,死因為機械性窒息。從現場勘查的情況來看,室內沒有被翻動過的痕跡,財物也沒有丟失,初步排除了入室搶劫殺人的可能。死者上身赤裸,下身衣物完整,沒有性侵犯的痕跡,也不像是入室強姦殺人。不過讓人感到意外的是,死者在死後被兇手開膛,所用的刀具遺留在現場,經被害人丈夫辨認,是死者家中的一把菜刀。警方在廚房裡發現一個杯子,杯子裡的殘留物質經檢驗後認定為是死者的血液和牛奶的混合物。
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一種傳說中的怪物——吸血。
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J市又連續發生兩起入室殺人案,被害人都為25歲至35歲之間的女性。死者都被開膛,並且在現場都發現了被害人的血液和其他物質的混合物。
市局成立了專案組負責偵破此案,可是將近一個星期過去了,案件偵破毫無進展。正在專案組焦頭爛額之際,一個從C市出差來J市的刑警丁樹成卻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人大跌眼鏡的建議:去找一個在J大在讀的犯罪學研究生。作為專案組負責人之一的邰偉最初以為他在開玩笑,可是丁樹成卻極其認真地向他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2001年夏天,C市連續發生四起強姦殺人案。四個被害人都是25至30歲之間的白領,兇手將被害人強姦後再用繩子將被害人勒死。案發地點分別發生在C市正在興建的四座高層建築的頂樓天臺上。當時,丁樹成的頂頭上司,市局經文保處處長邢至森剛剛被提升為C市公安局副局長。新官上任三把火,邢副局長向新聞媒體透露了案件的部分情況,並在電視上向市民保證半個月之內破案。兩天後,一封觀眾來信擺在了專案組的辦公桌上,信中說兇手是一性心理扭曲的變態者,因為無法與女性建立正常的關係,所以藉著強姦殺人來發洩自己的慾望,並斷定兇手的年齡不會超過30歲。專案組的幹警最初以為這只是一偵探小說愛好者的突發奇想,並沒有當回事。邢副局長聽說此事後卻顯得很有興趣,指派專人去調查發信人的資料。當他得知這名觀眾是一個叫方木的C市師大應屆畢業生的時候邢副局長顯得十分興奮,馬上把他找到了市局。兩個人在辦公室裡談了半個小時後,邢副局長親自開車送他到四個案發現場去了一趟。回來後又把案件的全部資料搬到辦公室裡,方木在仔細看過了所有資料之後,又在某天深夜(驗屍結果顯示,案發時間應該在夜間10點至11點左右)去了一趟案發現場,這一次丁樹成也陪同前往。這個男孩在其中一個樓頂上(同時也是所有案發現場中最高的一個建築)站了很久,最後說了一句讓丁樹成印象頗深的話。
「他不是在強姦那個女人,他是在強姦這座城市!」
回到局裡後,他向專案組提出了如下建議:第一,調查全市範圍內的低檔錄像廳(註:指專門播放錄像帶影片供人欣賞的店。店內設有隔間包廂,客人可自行挑選喜愛的影片在裡面欣賞。),特別是附近有正在施工的建築工地的錄像廳,尋找一個年齡在20至25歲之間,偏瘦,短髮,身高在165至170公分,習慣手為右手,左手帶著手錶,手腕處有一條抓痕,大約高中學歷的戴眼鏡男子;第二,在全市正在作業的施工隊中,尋找具有上述特徵的人;第三,在C市周邊的鄉鎮尋找一個聯考落榜,進城打工且具有上述特徵的人,尤其是那些家中只有男性長輩的獨生子或者只有男性兄長的人。他甚至大膽斷言兇手被捕時會穿著白色襯-衫。
專案組的成員對這種近乎異想天開的猜測半信半疑,邢副局長卻指示下屬按照方木提供的犯罪嫌疑人特徵進行搜索。兩天後,一個位於小火車站附近的小錄像廳老闆說她認識一個這樣的人,他就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上打工。這個工地上的工人經常結伴來錄像廳看影片,這個人每次都是一個人來,而且專挑後半夜播放黃色影片的時候來。有一次,遇到了同一個工地的同事,他竟滿臉通紅地偷偷溜走了,因此給老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警方來到了那家工地,並且在老闆的指認下在工棚裡找到了這個人。這個人叫黃永孝,是工地的測量員。當幹警出示證件並要求查看他左手手腕的時候,黃永孝突然跳起逃跑,但是很快被幹警制服。帶回局裡審問之後,黃永孝對他犯下的四起強姦殺人案供認不諱。
黃永孝,男,21歲,高中學歷,C市八台鎮前進鄉人。2000年聯考落榜後,黃永孝選擇重讀一年再次參加聯考,結果還是名落孫山。之後黃永孝就隨其叔父進城,曾經在多個建築工地打工,但每次時間都不長。後經其叔父介紹,在該建築工地打工,因為有一點學歷,所以被安排做測量員。
黃永孝被捕的時候的確穿著一件很舊,但是洗得很乾淨的白色襯衫。
方木對犯罪嫌疑人的外貌、家庭背景、工作環境、生活習慣的描述與黃永孝驚人的一致,唯一的出入就是黃永孝父母離異多年,黃沒有男性兄弟,只有一個姐姐,並隨著母親嫁到了外地,已經斷絕了來往。但這已足以讓幹警們對這貌不驚人的男孩刮目相看。他們甚至懷疑黃永孝作案的時候方木就在現場看著,否則不可能做出如此準確的描述。
方木的解釋是:從現場來看,被害婦女的褲子被脫到膝蓋以下,膝蓋處都有擦傷,並且在天臺的圍欄上發現了被害人的少許皮膚組織,這與被害人胸乳處的擦傷吻合。這意味著兇手強姦的時候採取後入式的體位。
這是一種頗有意味的姿勢。
首先女性在採取後入式進行性交的時候如果被男性從¨後按住上¨或者抓住雙手的話,掙扎的幅度是最小的,加上褲子被脫到膝蓋處,雙腿的活動空間受限,因此,是最不可能遭到激烈反抗的姿勢。其次,從性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後入式的性交是最為原始的性交體位,由於在性交時會使男性產生強烈的征服感和滿足感,因此,後入式帶給男性的心理刺激要遠遠超過其他體位。
那一晚,方木站在夜色深沉的天臺上,整個城市的夜景盡收眼底。他看著遠處燈火通明的高樓大廈,腳下光影搖曳的車流。
粗暴的前後聳動,身下服飾高貴的女人在無力地掙扎。在視野開闊的高處痛快地一瀉而出……
方木閉上眼睛。
這個城市某個高級住宅中,那個急地等待自己妻子的男人,你沒有想到你的老婆正在我的胯下像狗一樣地被我凌辱吧?
也許在他眼裡,整個城市就是一個巨大的女性生殖器。他一定在那一瞬間感到了征服這座城市的快感吧。
那麼,在現實中,他就一定是一個失敗者
將不正常的性虐殺行為作為發洩對社會仇恨的方式,這意味著性行為對他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既讓他感到超乎常人的好奇、神秘、興奮,又讓他感到羞恥。如果男性能夠在早期與女性建立起正常關係的話,那麼這種對性過分強烈的感覺會隨著社會閱歷的增加而慢慢消除。因此,兇手很可能是一個與女性無法建立正常關係的人,而這種人,往往在一個缺乏女性關懷的環境中生活。同時,具有這種性心理的人年齡不會太大。一來,如果年紀較大,就可能藉由其他正常的社會經歷及時消除這種心理;二來,這種心理往往在青春期出現。如果他年齡較大的話,早就會犯案,而近年來並沒有類似案件發生。
因此,兇手,男性,年齡不會超過25歲,家中沒有女性長輩,或者只有兄弟,具有挫敗的人生經歷。
關於案發地點。建築工地的頂層,顯然是滿足兇手征服城市心理的好地點,同時也意味著他對於這類場所的熟悉。因此,兇手應該是一個在建築工地有從業經驗的人。而這樣一個性心理異常的低收入者,可能去過某些色情場所。嫖娼?應該不會,即使有,次數也不會太多,因為他的經濟條件不允許。
比較合適的地方是那些低檔的,常常在午夜之後播放色情影片的錄像廳。
驗屍發現,其中一個女性被害人左手的指甲斷裂,而斷離的指甲就落在屍體仰臥的位置附近。奇怪的是,在所有被害人中,這名死者身上的傷痕最少。這說明死者對於強姦並沒有進行過分激烈的反抗,結合指甲就在屍體不遠處找到的情況,指甲可能是在兇手強暴被害人之後,在動手勒殺她的過程中,由於被害人的拼命掙扎造成的。在斷離的指甲中發現了不屬於被害人的皮膚組織(血型為A型),那麼死者的指甲很可能是在和兇手的身體接觸後被撕裂的。由於兇手採用的是背後勒殺的方式,所以被害人的雙手能夠接觸到的部位有,最大的可能就是兇手的雙手。方木注意到指甲是被撕裂而不是折斷。這就意味著指甲在劃破兇手皮膚的時候,肯定與某種物品接觸後發生撕裂。手上的什麼東西能夠把指甲撕裂呢?方木首先想到的就是手錶,而且極有可能是金屬材質。
一個在建築工地打工,手上還戴著金屬質地的手錶,這本身就有點不同尋常。那麼這個人一定是想表現出他的與眾不同。
那他就應該是一個具備一定教育程度的人。
在建築工地打工——具有一定教育程度——有人生挫敗的經歷——年齡不超過25歲。
最貼切的答案是:一個來自農村的聯考落榜生。
如果是這樣一個人,那他一定還會有別的方式來凸顯他與其他工人的差別。例如,有別於一般工人油膩污穢長髮的乾淨俐落短髮,表明他「知識份子」身份的眼鏡,也有可能是一件別於沾滿水泥工作服的白襯衫。
那麼,他就是一短髮、偏瘦、戴眼鏡、穿著白襯衫、左手腕戴金屬手錶的人(左手腕應該有被害人留下的抓痕。而把錶戴在左手上的人,習慣手通常是右手)。
方木陳述完自己的理由之後,專案組的幹警們一片沉默,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複雜的表情。的確,當推理的過程被一步步抽絲剝繭後,破案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再簡單不過的事情。而這個過程,又有幾人能準確地邁出第一步呢?
還是邢至森打破了沉默:「嗨,你當初把黃永孝的名字告訴我們不就完了,也省得我們費事了。」
大家哄的一聲笑開了。
方木沒有笑,始終盯著自己腳下的那塊地板出神。
案件順利送交檢察院起訴。C市市民也紛紛交口稱讚警方破案神速。邢至森想給方木一定的物質獎勵(之前邢至森委婉地向方木解釋,警方不可能向公眾宣佈本案是在一個22歲的大學生幫助下破獲的,方木表示理解。)方木拒絕了。邢至森問方木有什麼要求,方木的回答很簡單:在黃永孝上法庭之前和他單獨面談一次。
儘管很多人對這次面談充滿好奇,不過在方木的堅持下,局裡還是安排方木和黃永孝進行了一次不受打擾的面談,整個談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方木整整記了半本筆記本和兩卷錄音帶。丁樹成曾經聽過一段錄音,從談話的內容來看,涉及本案的很少,方木似乎更關心的是打從黃永孝有記憶起到21歲之間的人生經歷。
黃永孝5歲時,父母離異,媽媽帶著比他大一歲的姐姐改嫁到外地。從此,黃永孝就跟父親生活在一起。黃從小就性格內向,不愛與人交談,但是刻苦求學,一直被認為是村子裡最有可能考上大學的人。8歲的時候,黃永孝無意間撞見父親與村裡的一個有夫之婦偷情,還因為這件事被父親毒打一頓。14歲的時候,當時在讀初中的黃永孝被一個高年級的女生帶到山上。當那個女生將黃永孝的手直接按到自己乳房上的時候他被嚇壞了,連滾帶爬跑下了山。可是兩年後,16歲的黃永孝在一次下田勞動的時候,突然把身邊一個一直與他關係不錯的女生(與黃永孝是同班同學)按倒在田地裡,在她身上亂摸亂親。那個女孩嚇得大聲哭叫,引來了村人,才將女孩解救下來。後來在父親賠了一頭驢以及村裡長輩的調解下,此事才算平息。黃永孝的成績卻自此一落千丈。兩次聯考失利後,黃永孝就隨叔父進城打工。一年多裡,黃永孝輾轉換了五個工地,歷盡城裡人的白眼和排斥。由於性格內向,又比較孤傲,所以在每個工地待的時間都不長。閒極無聊的時候,黃永孝就去街邊的錄像廳看武打片。也正是在這裡,黃永孝第一次看到了A片。自此一發不可收拾,整日腦子裡都是A片裡女性充滿誘惑的胴體,直到他在一天深夜跟上了一個晚歸的白領女性……
之後方木幾乎成了C市公安局的「顧問」。在他的協助下,一共破獲了一起綁架案、一起敲詐勒索案、兩起殺人案。在上z案件中,方木對犯罪嫌疑人特徵的描述對案件的偵破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章 有記號的人
聽完方木離奇得近乎荒謬的故事,邰偉有些將信將疑。
「他,那個叫方木的學生,」邰偉斟酌了一下自己的詞句,「他在給犯罪嫌疑人畫像?」
丁樹成點點頭。
「真的有這麼厲害麼?」
丁樹成笑笑,他湊過來,表情神秘地問:「你知道羅納爾多為什麼是世界第一前鋒麼?」
「唔?你說什麼?」邰偉有點莫名其妙。
「為什麼郝海東不能成為世界第一前鋒?」
邰偉目瞪口呆地看著丁樹成。
「天賦。這傢伙有察覺犯罪的天賦。」
邰偉在J大研究生處查得方木住在南苑五舍B座313寢室,可是到宿舍樓卻撲了個空,同他住一個寢室的男生說方木去打籃球了。邰偉問方木長什麼樣。男生笑笑說:「你不用問他的長相。你只要看見一個獨自在球場上練罰球的人,那就肯定是方木。」
天氣很好。校園裡是微微吹過的暖風和好聞的花粉味道。大學生們大多脫下了厚重的冬裝,穿著輕便地在校園內穿梭,偶爾還能看見幾個急不可待地穿上短裙的女孩子。邰偉拉住一個抱著籃球的小個子男生,問他籃球場怎麼走,小個子男生非常熱心地給他帶路。
籃球場位於校園的西南角,是一大塊用鐵絲網圍成的水泥場地,一共有八塊完整的籃球場。邰偉依次走過這些聚集著生龍活虎的小夥子的場地,留心尋找著那個獨自練習罰球的男孩。
他並不難找。在場地最邊緣的一塊球場上,有一個男孩站在罰球線上,揚起手,籃球在空中劃出一條弧線,準確地落在籃框中。
邰偉走到場地邊,看著男孩一遍遍重複著同樣的動作:揚手、投籃、入框、撿球、走回罰球線、揚手、投籃、入框……男孩的動作標準、優美,出手的籃球幾乎無一落空。
「有事麼?」突然,男孩目不斜視地冷冷拋過來一句。
「哦?」邰偉有些猝不及防。他尷尬地清清嗓子,「咳咳,你叫方木吧?」
男孩揚起的手略略停頓了一下,然後手指一撥,籃球飛出後沒有直落籃框,而是撞在籃框上,又彈回他的手中。
男孩捧著籃球,轉過身。他的臉色潮紅,鼻尖上有細密的汗珠,臉頰凹陷,下巴顯得尖尖的,濃密的眉毛此刻緊鎖在一起,而他的眼神——
冷漠、疲倦卻又銳利無比,彷彿能夠刺破午後強烈的光線直鑽進對方的身體裡。
邰偉在這樣的目光下不由得打了個寒噤,他躲開對方的視線,剛想開口,卻發現自己並沒有為與方木的初次見面準備一個合適的開場白。
「你……你認識丁樹成吧?」
方木的眉頭皺得更緊,他盯著邰偉說:「你是員警?」
說完,不等邰偉回答,就逕自走向球場邊的長椅。邰偉遲疑了一下,也跟著走過去坐下。
長椅上放著一個很舊的書包,方木從裡面拿出一包面巾紙,抽出一張擦擦臉,又掏出眼鏡戴上。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麼?」臉上仍然毫無表情。
邰偉感到一絲不快,但是想想此行的目的,還是從皮包裡拿出一疊資料,遞給了方木。
「我是市局刑警隊的,我叫邰偉。今年三月份以來,我市連續發生了三起入室殺人案。這是這三起案子的一些資料。我聽說你……」說到這裡,邰偉發現方木並沒有聽他說話,而是全神貫注地看手中的資料,就悻悻地閉上嘴,拿出來準備表明身份的警官證也悄悄地塞回了口袋。
沒有比和這樣的傢伙坐一下午更讓人厭煩的事了。方木始終一言不發地坐著看資料。邰偉最初還耐心地擺出隨時準備傾聽的姿勢,時間久了,肩膀酸得厲害,也開始不耐煩起來。他伸展開四肢,向後舒服地靠在椅子上,百無聊賴地四處張望著。
剛才方木投籃的那塊場地已經被幾個男生佔據了。這些二十出頭的男孩子在球場上不惜體力地奔跑著,爭搶著,不時發出興奮的尖叫,時而為一個動作是否犯規、一次得分是否有效大聲爭論著。邰偉看著這些精力充沛的男孩子,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在警校讀書時的日子,嘴邊漸漸浮現出一絲微笑。
猛地,他意識到身邊的這個人其實就是這些男孩子中的一員,而他,和這些沒心沒肺的男生多麼不同!彷彿有什麼記號,使他與周圍的人物涇渭分明。他不由得再次轉過頭來看著方木。
方木看得很慢。他低垂著腦袋,眼睛始終盯著手中的圖片、現場報告及驗屍報告。有幾次抬起頭來,邰偉以為他要說什麼,忙湊過頭去。可是方木只是凝望著遠處的風景,並不說話,少頃,又低下頭仔細地看資料。邰偉注意到他對幾張現場圖片格外關注。
終於,他站起身來,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然後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把資料遞給一直盯著他的邰偉。
「這個人,男性,年齡在25歲至35歲之間,身高不會超過175公分,應該比較瘦。」
邰偉盯著方木,幾秒鐘後,他忍不住開口問:「就這些?」
「對,就這些。」方木乾脆地回答。
邰偉感到大失所望。他以為方木會像丁樹成所講述的那樣,具體、詳細地描繪出兇手的外貌、生活環境、家庭背景。可是方木只給出了這樣一點模棱兩可的結論。老實說,方木所判斷的,並不是什麼有價值的線索:採用如此殘忍手段的,多是男性,而且,大多數連環殺人犯的年齡都不會超過40歲。至於身高和體重,根據現場發現的犯罪嫌疑人的腳印,也能夠推斷得出來。另外,現場遺留的痕跡表明兇手曾和被害婦女有過激烈的搏鬥,這意味著兇手不會太強壯。
「根據這些資料和現場照片,我只能看出這些。」方木好像看穿了邰偉的心思。不過他隨後又補充道:「另外,我感覺這個人精神上有點問題,至於什麼問題,我不能肯定。」
哼,邰偉在心裡說,傻子也能看出這兇手是個變態!
「變態和精神障礙是兩回事。」
邰偉不由得一驚,他意識到方木已經在幾秒鐘之內兩次窺破他的心事。為了掩飾自己的驚訝,他站起身來,向方木伸出手去。
「好吧,謝謝你,如果還有什麼需要你請教的,我們會再連繫你。再見。」
方木握住邰偉的手。邰偉感覺到那隻手冷冷的,沒有一絲熱度。
「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再見。」
「哦?」邰偉揚起眉毛。
「我們再見面的時候,就意味著又有人死了。」
邰偉張張嘴,卻什麼也沒說出來,只好點點頭,轉身走了。
走出籃球場的時候,邰偉忍不住回過頭來,卻發現方木已經不在長椅邊了。向旁邊一看,方木正背對著他孤獨地投籃。此時已暮色深沉,籃球場上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幾個人,方木的身影在越來越黑的天色中愈發模糊,只能辨別他不斷揚起的手和籃球在空中斷續的軌跡。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心理罪之畫像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5 |
二手中文書 |
$ 220 |
推理小說 |
$ 32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心理罪之畫像
連環謀殺案倖存的推理天才VS. 狡猾又變態的反社會兇手
以人命為賭注,操弄心理遊戲者,必死於心理遊戲之下......
一個喜歡把牛奶和人血攪拌在一起喝下去的殺手,他是有特殊的疾病還是傳說中千年不死的吸血鬼?
C市連續發生四起強姦殺人案,被害人都是25至30歲之間的女性,這是報復殺人還是另有不為人知的欲求?
被砍掉雙手的足球守門員;被虐殺致死的七歲活潑女童;被剝掉全身皮膚的化學系女學生;被催眠而攻擊同窗好友的研究生......看似毫無關連的各宗命案背後,卻是一次以人命與鮮血作答的「考試」。
當這個看不見的魔鬼肆無忌憚地奪去方木身邊一個又一個朋友的生命,方木又將如何面對這公然的挑釁?他能否擺脫創傷後的夜夜夢魘,在最後關頭「畫」出魔鬼的樣子......
以恐怖懸疑為外衣,以人性悲憫為筋骨
網路超高人氣的犯罪推理小說!
兩岸網友熱烈預告:華文小說世界即將吹起《雷米旋風》!
作者簡介:
雷米
警察學校教師,熟悉警方辦案流程、精通犯罪心理學。
他將所擅長的犯罪心理專業知識,以及國內外的真實犯罪案例,大量運用在小說之中,使作品富有縝密的邏輯推理,豐富多面的人性掙扎,並自然穿插法學、刑事偵查學、現場勘察學、法醫學方面的知識,讓故事更具說服力、感染力。
以心理罪系列小說聞名於網路,主要作品:
第七個讀者
心理罪之畫像
心理罪之教化場
章節試閱
序 怪物 昨天晚上,他們又來找我了。 他們還是照例不說話,默默地站在我的床前。而我,照例還是僵在床上動彈不得,眼睜睜看著那些燒焦的、無頭的軀體圍在我的周圍。而他,依然在我的耳邊輕輕說出:其實,你跟我是一樣的。 我已經習慣了和他們在夜裡相遇,可是,仍然大汗淋漓。 直到他們一言不發地離去,我才重新聽見杜宇在對面那張床上平靜的呼吸。 窗外清冷的月光靜靜地潑灑進來,宿舍裡的火焰早就消失不見了,有點冷。 我費力地翻了個身,手摸到枕頭下那把軍刀,感覺到粗糙、略有起伏的刀柄,呼吸慢慢平靜。 我又...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雷米
- 出版社: 瑞昇文化 出版日期:2009-01-26 ISBN/ISSN:97895752682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08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