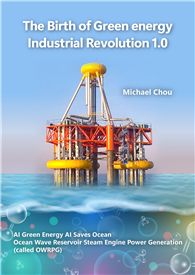1900年清朝覆滅前夕,上演了一齣義和團的大悲劇,同時也使得華北地區的基督徒,面臨了中國基督宗教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約有一萬五千位天主教友被殺。在歷史上,中國政府從未像對這次事件一樣,發動大規模的訪談調查及資料蒐集,動員許多研究資源,進行史料彙編及多次召開相關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此運動也是歐美日重要學者的研究對象。雖然如此,此運動仍缺乏基督徒的觀察向度。
本書以迄今較受忽視的教會調查及文獻為主,也以與各種類型史料的比對為研究方法,以直隸的天主教友為對象,論述此運動的進程、團民及信眾的組織及發展、信眾的不同類型及行動的選擇。閱讀之際,相信讀者將經歷時而悲憫,時而扼腕,時而感佩的各種情緒。
除歷來以反帝愛國的觀點來研究此運動的中國大陸主流詮釋模式,以及他國人士的各種衝突挑戰理論觀點外,本書提出對於義和團的起源、發展及結局的另類論述。
總之,本書在史料上較完整,視野較獨特,閱後將會有兩層收穫:不但使吾人因如此豐富的研究論述,得到對義和團另一種新的了解,也可以觀察及判斷作者以信者的內在角度卻力求客觀的努力過程及結果。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崩落天朝的天國子民:義和團時期的直隸天主教會(懷仁叢書15)的圖書 |
 |
崩落天朝的天國子民:義和團時期的直隸天主教會(懷仁叢書15) 作者:陳方中 出版社:光啟文化 出版日期:2017-01-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536頁 / 17 x 23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崩落天朝的天國子民:義和團時期的直隸天主教會(懷仁叢書15)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方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在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現任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其專長為中國天主教史,特別是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主題包括:民教衝突、義和團、天主教的本地化、中梵外交關係、當代臺灣天主教史等。
曾編撰《于斌樞機傳》,與江國雄合撰《中梵外交關係史》,另撰有中國天主教史論文多篇。
自2003年開始進行義和團的相關研究,本書係十餘年研究的綜合。
陳方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在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現任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其專長為中國天主教史,特別是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主題包括:民教衝突、義和團、天主教的本地化、中梵外交關係、當代臺灣天主教史等。
曾編撰《于斌樞機傳》,與江國雄合撰《中梵外交關係史》,另撰有中國天主教史論文多篇。
自2003年開始進行義和團的相關研究,本書係十餘年研究的綜合。
目錄
序|韓德力神父007
緒論011
第一節 「義和團運動」仍然值得研究嗎?011
第二節 六類基本史料019
第三節 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範圍026
第一章 直隸的教會與教友029
第一節 直隸教會歷史029
第二節 耶穌會的直隸東南代牧區035
第三節 遣使會的直隸北及直隸西南代牧區043
第四節 地區性教會運作與教徒宗教生活049
第五節 教友群體053
第六節 民教衝突與地區性的政教關係063
第二章 平民與拳民071
第一節 正常與異常並存的華北農村071
第二節 正統—多元—異端的倫理宗教體系078
第三節 拳民的秘密宗教背景081
第四節 拳民和民間信仰的關係088
第五節 民間信仰與秘密宗教間的義和團103
第三章 義和團運動局部期直隸及山東交界地區的民教衝突113
第一節 冠縣梨園屯與威縣三村113
圖一 梨園屯事件地圖137
表一 梨園屯、冠縣十八村、威縣義和團138
第二節 神拳139
圖二 平原事件地圖170
表二 山東神拳171
第三節 直隸河間府一帶的攻擊事件173
圖三 景州義和拳地圖189
表三 直隸東南代牧區 1899 年 6 月至 1900 年 1 月被拳民威脅教友點190
第四章 義和團運動狂亂期直隸的一般情形191
第一節 由醞釀至爆發191
圖四 梁召事件地圖196
圖五 清苑事件地圖206
圖六 淶水事件地圖224
第二節 天津地區的教友225
圖七 靜海與西青地圖242
第三節 北京教友的狀況243
圖八 北京城區地圖272
表四 直隸從局部期轉向狂亂期的中間階段273
第五章 義和團運動狂亂期教友的不同選擇277
第一節 第一種選擇:逃難277
第二節 教友的第二種選擇:背教292
第六章 直隸北及直隸西南代牧區教友堡寨305
第一節 北京周邊305
圖九 桑峪地圖312
圖十 京東地圖316
第二節 京東地區317
第三節 宣化地區331
圖十一 宣化地圖345
第四節 保定地區346
圖十二 保定地區地圖355
第五節 直隸西南代牧區356
圖十三 西南代牧區地圖(一)362
圖十四 西南代牧區地圖(二)363
表五 直隸西南代牧區教友堡寨364
表六 直隸北代牧區教友堡塞365
第七章 直隸東南代牧區教友堡寨367
第一節 獻縣地區367
第二節 任邱及河間381
圖十五 任邱及河間地圖395
第三節 景州朱家河與青草河396
圖十六 獻縣、景州與深州地圖406
第四節 威縣三村及其他407
圖十七 威縣地圖421
表七 直隸東南代牧區教友堡寨422
第八章 現象、原因與輪廓423
第一節 教友方面423
第二節 拳民方面447
第三節 拳民反教的原因467
結語477
後記487
圖十八 局部期地圖490
圖十九 狂亂期地圖492
參考書目495
中文人名索引515
南懷仁研究中心出版品簡介529
緒論011
第一節 「義和團運動」仍然值得研究嗎?011
第二節 六類基本史料019
第三節 研究的目的、方法及範圍026
第一章 直隸的教會與教友029
第一節 直隸教會歷史029
第二節 耶穌會的直隸東南代牧區035
第三節 遣使會的直隸北及直隸西南代牧區043
第四節 地區性教會運作與教徒宗教生活049
第五節 教友群體053
第六節 民教衝突與地區性的政教關係063
第二章 平民與拳民071
第一節 正常與異常並存的華北農村071
第二節 正統—多元—異端的倫理宗教體系078
第三節 拳民的秘密宗教背景081
第四節 拳民和民間信仰的關係088
第五節 民間信仰與秘密宗教間的義和團103
第三章 義和團運動局部期直隸及山東交界地區的民教衝突113
第一節 冠縣梨園屯與威縣三村113
圖一 梨園屯事件地圖137
表一 梨園屯、冠縣十八村、威縣義和團138
第二節 神拳139
圖二 平原事件地圖170
表二 山東神拳171
第三節 直隸河間府一帶的攻擊事件173
圖三 景州義和拳地圖189
表三 直隸東南代牧區 1899 年 6 月至 1900 年 1 月被拳民威脅教友點190
第四章 義和團運動狂亂期直隸的一般情形191
第一節 由醞釀至爆發191
圖四 梁召事件地圖196
圖五 清苑事件地圖206
圖六 淶水事件地圖224
第二節 天津地區的教友225
圖七 靜海與西青地圖242
第三節 北京教友的狀況243
圖八 北京城區地圖272
表四 直隸從局部期轉向狂亂期的中間階段273
第五章 義和團運動狂亂期教友的不同選擇277
第一節 第一種選擇:逃難277
第二節 教友的第二種選擇:背教292
第六章 直隸北及直隸西南代牧區教友堡寨305
第一節 北京周邊305
圖九 桑峪地圖312
圖十 京東地圖316
第二節 京東地區317
第三節 宣化地區331
圖十一 宣化地圖345
第四節 保定地區346
圖十二 保定地區地圖355
第五節 直隸西南代牧區356
圖十三 西南代牧區地圖(一)362
圖十四 西南代牧區地圖(二)363
表五 直隸西南代牧區教友堡寨364
表六 直隸北代牧區教友堡塞365
第七章 直隸東南代牧區教友堡寨367
第一節 獻縣地區367
第二節 任邱及河間381
圖十五 任邱及河間地圖395
第三節 景州朱家河與青草河396
圖十六 獻縣、景州與深州地圖406
第四節 威縣三村及其他407
圖十七 威縣地圖421
表七 直隸東南代牧區教友堡寨422
第八章 現象、原因與輪廓423
第一節 教友方面423
第二節 拳民方面447
第三節 拳民反教的原因467
結語477
後記487
圖十八 局部期地圖490
圖十九 狂亂期地圖492
參考書目495
中文人名索引515
南懷仁研究中心出版品簡介529
序
序
1982 年當我們在比利時魯汶大學設立南懷仁研究中心時,研究中國的天主教會歷史,是我們中心的優先領域。然而,這段歷史非常複雜且令人困惑,許多人對它有不同的詮釋與誤解:包括十七及十八世紀的禮儀之爭,十九世紀發生的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以及義和團拳亂,以至二十世紀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宗教問題。不管是在中國或西方,許多關於以上歷史事件的出版物,時常充斥著意識形態的偏見與無知。
為了澄清過去的史實,南懷仁研究中心根據東西方所保存的歷史文獻來提倡學術研究。這樣的動機是值得讚賞的,因為只有此形式的研究能夠揭露客觀的史實,並讓東西方達成進一步的理解,從而達到我們最終的目標-與中國建立一新的友好關係。至目前為止,中心已舉辦過十二次的國際學術會議,當中有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學者、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學者發表他們的論文,這些研究都出版在我們的叢書之中:包括英文版的「魯汶中國研究叢書」,迄今已出版了 36 本;另外還有中文版的「懷仁叢書」(委託台灣的光啟文化事業出版),目前也出版了 15 本書。
陳方中博士在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史所作的研究,為我們的中文叢書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內容,這研究受到學術界的矚目,因為它討論了中國教會史上最具爭議的主題之一—義和團拳亂。陳方中博士現為輔仁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1993 年還在念博士的時候,曾在我們研究中心的協助下,到比利時的新魯汶大學學過兩年法文,因此能閱讀法文的檔案。他曾到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以及遣使會的檔案室蒐集史料;此外,他還前往新魯汶大學的檔案館,以及聖母聖心會在比利時魯汶 KADOC 的檔案室。他也在中國和台灣的許多大學與圖書館蒐集各種文獻資料。在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上,同時掌握中國官方檔案與西方傳教士及外交人員的報告是有必要的,但在實際的研究中,卻很少人真的如此做,因為這牽涉到西方人閱讀中文的困難,以及中國人對理解西方文獻的相同困難。在同時使用中外文資料的情況下,陳方中博士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並在討論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的教會結構,以及宗教衝突的相關領域,逐漸成為了專家。
義和團拳亂這一主題過去曾有許多備受爭議的研究與書籍出版,中國學者在固定意識型態的前提下,多半又只使用中文的檔案與文獻,因此對傳教士及基督徒的敘述有許多誤解。再者他們的詮釋角度也經常與史實相矛盾。有的西方歷史研究者所採用的是基督新教傳教士的報告,在當時的環境中難免有對天主教方的抨擊,但同樣的這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成份。對此,西方天主教學者有他們的看法,他們試圖從自身信仰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文獻記載的客觀事實。但是,非中國人的天主教學者也許會缺乏中國天主教學者的洞察力,因為中國人會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待事實。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方中博士有關義和團的研究是相當特別的,因為他同時具有中國人、天主教徒與歷史學者這三種身份,而在他的研究中他也盡量同時使用中文及法文的資料。在他文章的一開始,他就將如何使用這些不同性質的史料,發展為他寫作這本書的方法。由於義和團是一個距離現在不太遙遠的重大事件,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除了中國官方及西方傳教士的檔案外,還有許多當時的文人記載了他們所見的事件經過,甚至在一般民眾群體中也能保留下來口傳的記憶,這些不同來源的史料,成了交叉比對過去義和團拳亂敘述的利器。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用了遣使會及耶穌會的法文材料,也引用了大量中國官方的檔案以及當時文人的記錄,還有許多教會內外的訪談記錄。從文中也可以看出陳方中博士去過一些事件發生的地點,這無疑對他了解中國教會的內在生命有許多體會。這就使得這本書在義和團拳亂這個老問題上,能提出新的見解。
我們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區在內蒙,在義和團拳亂時也遭遇了重大的傷痛。陳方中博士這本書所描述的地區在直隸,也就是現在的河北省、北京市與天津市,雖然不是同一個區域,但兩個地方是相連的,在張家口外的西灣子及宣化一帶,有些地方還是重疊的。有關於內蒙地區的義和團拳亂,譚永亮(Patrick Taveirne CICM)博士在他的鉅著《漢蒙相遇與福傳事業—聖母聖心會在鄂爾多斯的歷史 1874-1911》也有很長的篇幅,比較這些敘述,可以發現義和團拳亂在不同的地區,其原因及經過是類似的。
我們以陳教授的研究成果為榮,因此將此書納入我們的懷仁叢書之中,衷心將此書推薦給讀者。
緒論
第一節 「義和團運動」仍然值得研究嗎?
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現在海峽兩岸的歷史學者,不約而同都減低了對義和團運動的興趣,但原因不盡相同。臺灣歷史學者在過去幾十年中,基本上對此問題興趣都不高,主要是因為資料有限。臺灣學者們早期所能掌握的資料是《義和團》四冊,這個由北京中華書局在 1950 年出版的叢書,蒐集了四十八種書彙集成四巨冊,利用這四巨冊的《義和團》, 真正寫成研究論著的是戴玄之。 他在 1963 年出版了《義和團研究》一書。 除了戴玄之以外,同時期的學者較少人往社會史領域鑽研,更不用說更深入的秘密宗教範圍。在 1980 年代以後的臺灣學者,逐漸有更多社會史或秘密宗教的研究論著出現,但一般來說,這些學者們關心的是較早期或更長時段的論題。 利用臺北故宮或是中央研究院的檔案,學者們可以看出較大範圍的輪廓,但義和團運動只是其中的一個短時段,而在細膩度上,當然比不上除了檔案,還有實地訪談調查資料的大陸學者。
在少用及誤用教會史料的情況下,典型中國大陸學者義和團研究的一大特徵是反帝愛國史觀。按照林華國的意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侵略勢力派遣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教會就成為西方國家在中國內地進行侵略活動的重要工具。為了擴大教會勢力,外國傳教士用各種手段拉中國人入教。」於是不少地痞流氓加入了教會,官府怕洋人,在發生民教糾紛時,通常偏袒教民;民眾積怨難伸,只得自己組織反抗,此所謂「反洋教鬥爭」。在這樣的背景下,甲午戰後,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國民眾普遍要求集中力量反抗外來侵略。在這個大環境下,以『扶清滅洋』為口號,以打擊侵略者為主要目標的義和團運動也就應運而生了。」
為大多數中國大陸的義和團研究者而言,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愛國性質就如同林華國的綜合一般,是不太需要再去證明的前提。我們可以在絕大多數文章中找到類似的論述,在此不一一舉例。反帝愛國史觀也影響了他們對史料的解讀,舉路遙、程歗描寫〈河北景州、棗強、衡水地區的義和團運動〉為例,在他們的敘述中有如下字句:
義和團攻打朱家河,完全是由於朱家河教會侵略勢力壓迫所引起。朱家河教堂原是天主教直隸東南教區的一個重要侵略據點。
朱家河教堂曾佔有三頃土地……這裡教堂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十分嚴重。
平時教民踐踏農家墳地,破壞人家風水;教民還在集上賤買貴賣,詐扣物產,無事生非,搗亂市集。
教會的侵略勢力激起了廣大民憤,它同附近各地的村民形成了嚴重對立的局面。
從這個實際調查所得的描述,基本上與林華國的論述完全相符。不過,這種描述也帶有一定程度成見。
西方學者沒有中國這種特殊的學術環境,他們在思想自由的狀態下進行研究。少了意識型態的八股,他們的作品若獲准在中國國內出版,往往可以得到廣大的迴響。最為中國研究者熟悉的西方義和團研究者是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和柯文(Paul A. Cohen)。前者撰有《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 將山東劃分為六個地理區域,運用大量中文史料,深入探討社會及文化背景,是一本頗受推崇的名著。不過基本上,這本書在義和團運動的動機上,仍持守反帝愛國史觀,除了在白蓮教問題上與中國學者意見不同,其觀點與典型義和團研究者並無太大差異。
典範轉移的代表性人物是柯文。在其早年研究民教衝突時,他就肯定文化衝突及社會摩擦是造成民教衝突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礎上,他一開始觀察義和團運動的眼光就和一般學者不同。在 1990 年他參加研討會時發表了一篇〈有爭議的往事:作為歷史與神話的義和團〉,柯文認為歷史學者雖然在追求真實,但實際上也不斷在製造義和團的神話。他舉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為例,說明了不同時期神話的建構過程。他認為:
對中國歷史學家來說,拋棄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風靡一時的,拙劣的神話化的形式是輕而易舉的,然而,要克服新文化運動將義和團神話化為迷信的作法,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視其為反帝愛國的神話卻是非常困難的。
1997 年相同架構的專著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出版,很快的中國也在 2000 年 10 月翻譯為中文出版,名為《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與神話的義和團》, 這本書的重點在呈現從義和團運動開始後,各種所謂神話建立的過程,以及柯文自己作為歷史學者,嘗試建立的義和團敘述。
柯文以上述專著為基礎,在 2000 年山東大學舉辦的「義和團運動一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義和團,基督徒和神—從宗教角度看一九○○年的義和團鬥爭〉, 他認為在基督徒和義和團之間存在著宗教競爭與鬥爭關係,並非反帝愛國的概念推動義和團運動。雖然這種論調早在十年前柯文即已提出,但或許是因為梵蒂崗的封聖問題,主流的義和團歷史學者此時大肆批評柯文,從另一角度看,也使得這篇文章更受大陸學者注意。
在同一次研討會中,法國學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Bruquière)女士的文章〈義和團運動期間直隸省的天主教民〉 也引起廣泛討論。她使用遣使會的法文檔案,研究直隸西南遣使會傳教區的情形。她的結論是:攻打教友的義和團,既非來自遠方,絕大部分亦非來自於有人際互動的村民,而是附近有一定距離的地方,或是董福祥部隊的士兵。巴斯蒂認為:
它所表現的不是民族意識的覺醒,而是個人與集體的恐慌。……我們尤其不應從這種反應中得出天主教民與當地社會關係緊張的極端性結論。
狄德滿(R.G. Tiedemann)早期的觀點也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民族遭受壓迫的產物。他 1991 年即已大致完成,但 2011 年才翻譯成中文出版的《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 Chin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則加入了他一些修正的意見。他認為:「傳教事業於 1860 年後於山東地區的穩步發展,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中國鄉村秩序的矛盾正不斷深化。」這代表他將所謂的帝國主義侵略等外因,視為義和團興起的第二或第三因素。在另一篇名為“Anti-Christian Conflict in Local Context-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 Sanjie:Patriot, Protector, Banditor or Revolutionary”在多年鑽研大刀會後,狄氏討論龐三杰這個人物,在不同時期呈現的複雜面貌,是對所謂反教人物非常傑出的分析作品。另一篇最近的作品“Missionaries, Imperialism and the Boxer Uprisng:Some Histori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中,他認為即使是最具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安治泰主教(Johann Baptist Von Anzer),也不能說與義和團的興起有關,因為不論是神拳或梅花拳,都不是以安治泰所屬山東南部聖言會傳教區為主要發生地。這些文章也都是對反帝愛國史觀的質疑。
柯文的論文在 2000 年義和團會議時,尚且引起中國學術界官方,公開撰文點名批判,但他和狄德滿等外國學者,強調義和團運動內因的觀點,卻逐漸在中國義和團研究圈發酵。中國本來就具有社會史研究的優勢,義和團史學在此方面也有非常深入的調查訪談,由鄉土材料出發,中國歷史學者也開始修正反帝愛國史觀的某些觀點。代表人物是程歗,1990 年的義和團會議時,他發表了〈民俗信仰與拳民意識〉一文,將中國人的信仰系統劃分為三個相互聯繫而又彼此區別的次系統:正統的宗教系統,民俗的神祕信仰,以及異端的宗教信仰。在這背景上:
各地團壇並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特定教門的直線延伸,但是從文化背景的角度看,這種帶著濃厚神秘色彩的政治軍事集團,同樣是按著上述的信仰傳承和社會組織的運動規律而形成的。……義和神壇的觀念,儀式和風習之所以在許多方面同民間宗教息息相通,根本原因就在於它們都是社會成員地位低下而又帶有反抗性的團體,並且都根植和運動在鄉土民俗的文化大舞臺上。
這裡描述了義和團更深入的根源,相對來說,所謂帝國主義壓迫就是第二或第三考慮的因素了。
程歗在 2000 年義和團研討會的論文〈社區精英群的聯合行動〉,被刊登在《歷史研究》2001 年第一期。這篇傑作對梨園屯事件的各種史料做了非常詳細的爬梳。在排比檢查各種史料後,他認為 1960 年代所做有關村中公產的口述訪談,其實是不合歷史事實的,是一種扭曲的歷史記憶,但表達出村人對天主教傳入後,鄉村倫理秩序被破壞的焦慮。在細膩的閻氏家族結構中,清楚看到家族中部分成員信教後,造成的人際、經濟乃至文化的衝突。程歗也從「社區精英」的概念,補充了以往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認知,他以趙三多為例,說明傳統士紳的角色,在社會動盪的時代,被拳師、教首和巫覡所替代。
程歗的學生張廣生在同一次研討會中,發表了〈日常生活、權力與真相─玉皇閣廟產之爭的歷史記憶〉一文,他檢視梨園屯事件的相關史料,運用話語權力的概念,說明各種描述玉皇閣廟產之爭說法的主觀性,因敘述的角度不同,其實廟產問題不是只有一個固定觀念的。從一種較廣義的角度看,程歗和張廣生的論文是貼近後現代史學的,他們和大寫歷史的固定觀點辯論,重新挖掘史料的背後意涵,同時再重新建立敘述,如此或多或少也減少了反帝愛國史觀的限制。
在《歷史研究》的 2002 年第五期,有路遙〈義和團運動發展階段中的民間秘密教門〉一文。路遙以其對祕密宗教各支脈流傳的雄厚基礎,分析義和團運動期間,義和團人數最多的聚集地-北京,所謂的義和團,係分別屬於廣義八卦教中的乾字團與坎字團,其後又有聖賢道及九宮道等不屬八卦教系統的秘密宗教加入。路遙這一篇論文清楚說明了北京地區義和團與秘密宗教各支派的聯繫與關係,解決了長時期論述不清的問題。
2003 年第四期的《歷史研究》,李里峰的〈從「事件史」到「事件路徑」的歷史─兼論《歷史研究》兩組義和團研究論文〉一文,分析了上述 2001 年第一期,及 2002 年第五期共 7 篇義和團文章。李里峰認為這些文章有兩種類型,一種「把事件本身當成研究對象」,另一種則把事件視為歷史上社會結構的動態反應,試圖挖掘出事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視歷史的一種視角,一條路徑,可以稱之為「事件路徑」的歷史。
李里峰在其論文中還有一段有趣的自白:
記得還在準備學士論文時,指導老師就告誡我們一定要避開諸如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樣的選題,因為與之相關的問題要麼早被「研究透了」,要麼是我們尚無力涉足。近年來的研究狀況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種說法。
從李里峰的話可以驗證得知,中國大陸學者也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研究,在達到高峰之際,不管質或量其實都呈現下滑趨勢。作為事件史本身,義和團運動已被研究透了,只有少數相當有史識的歷史學者,可以運用一樣的史料寫出不一樣的文章;或是將義和團運動,當成一個事件路徑,關心其後更長時段或更大範圍的歷史結構問題。李里峰另一方面也有不方便說的原因,只要義和團運動的研究仍與現實政治沾上邊,只要中國大陸的歷史研究仍必須堅持唯物史觀,即使中國歷史學者對義和團運動有新觀點,多半也不敢在此問題上標新立異。簡單說,在沒有真正開放的環境中,最好不要碰這些敏感的題目。
作為事件史的義和團,其相關的問題大約可分為義和團的源流、性質、經過、東南自保、八國聯軍、辛丑議和等。 若按研究範疇,與社會史、軍事史、宗教史、外交史、政治史等相關。歷史的基礎研究倚重史料,所謂「研究透了」即是所有史料延伸的論題都已被反覆研究了,但真是這樣嗎?大部分義和團研究者在論及義和團興起的原因時,都會將目標指向教士教民的恣意妄為,而在義和團運動的經過中,教民與拳民的對抗,甚至可稱為戰爭,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絕大部分的研究其實都忽略了教會方的史料。在喪失史料辯護權的情況下,在進行這一部分的敘述時,難免會有偏頗或佚失。反過來說,若教會方史料得到客觀及充份的使用,作為事件史的義和團運動會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面貌。
平實的說,中國大陸的義和團研究者何嘗不想使用教會方的史料,但教會史料所使用的多語言,是漢語的歷史研究者很難跨越的門檻。在義和團運動時期,直隸有三個代牧區,直隸北及直隸西南是遣使會負責的區域,直隸東南代牧區屬耶穌會,他們都是來自法國的團體。在山東北部的方濟各會來自義大利,山東南部的聖言會來自德國,在塞外內蒙古傳教的聖母聖心會來自比利時,他們的文獻有法、荷兩種文字。在河南是米蘭外方傳教會,來自義大利,東北的巴黎外方傳教會顧名思義來自法國。各個傳教團體的文獻在他們母院或是羅馬,這種分散的狀態,是語言之外的另一困難。而這些資料是屬於這個團體所有,並不受國家相關檔案法規的管理,因此檔案管理者可決定讓研究者使用與否,以及如何使用。換一種角度說,他們不希望這些資料被反對教會的人,當成攻擊教會的證據。因此他們對不認識的研究者,經常抱有懷疑的態度。凡此種種,長此以往,是教會史料逐漸淡出義和團研究的一部分原因。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義和團研究「事件史」的部分,其實尚有缺乏之處。也就是說在拳教衝突方面,尚未利用教會史料補足敘述的缺口,更遑論進行微觀個別事件的因果關係分析。所以,義和團運動尚未被研究透徹,還有許多工作可作。而在檢視義和團的研究成果時,還可以發現另一個現象,就是因固有的成見,以致對史料做出錯誤的解讀。因此,在進行後續的研究前,必須要先對義和團運動的相關史料進行分類,各類型史料因作者的性質,其敘述是有其基本差異的。
1982 年當我們在比利時魯汶大學設立南懷仁研究中心時,研究中國的天主教會歷史,是我們中心的優先領域。然而,這段歷史非常複雜且令人困惑,許多人對它有不同的詮釋與誤解:包括十七及十八世紀的禮儀之爭,十九世紀發生的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以及義和團拳亂,以至二十世紀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的宗教問題。不管是在中國或西方,許多關於以上歷史事件的出版物,時常充斥著意識形態的偏見與無知。
為了澄清過去的史實,南懷仁研究中心根據東西方所保存的歷史文獻來提倡學術研究。這樣的動機是值得讚賞的,因為只有此形式的研究能夠揭露客觀的史實,並讓東西方達成進一步的理解,從而達到我們最終的目標-與中國建立一新的友好關係。至目前為止,中心已舉辦過十二次的國際學術會議,當中有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學者、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學者發表他們的論文,這些研究都出版在我們的叢書之中:包括英文版的「魯汶中國研究叢書」,迄今已出版了 36 本;另外還有中文版的「懷仁叢書」(委託台灣的光啟文化事業出版),目前也出版了 15 本書。
陳方中博士在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史所作的研究,為我們的中文叢書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內容,這研究受到學術界的矚目,因為它討論了中國教會史上最具爭議的主題之一—義和團拳亂。陳方中博士現為輔仁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1993 年還在念博士的時候,曾在我們研究中心的協助下,到比利時的新魯汶大學學過兩年法文,因此能閱讀法文的檔案。他曾到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以及遣使會的檔案室蒐集史料;此外,他還前往新魯汶大學的檔案館,以及聖母聖心會在比利時魯汶 KADOC 的檔案室。他也在中國和台灣的許多大學與圖書館蒐集各種文獻資料。在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上,同時掌握中國官方檔案與西方傳教士及外交人員的報告是有必要的,但在實際的研究中,卻很少人真的如此做,因為這牽涉到西方人閱讀中文的困難,以及中國人對理解西方文獻的相同困難。在同時使用中外文資料的情況下,陳方中博士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並在討論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的教會結構,以及宗教衝突的相關領域,逐漸成為了專家。
義和團拳亂這一主題過去曾有許多備受爭議的研究與書籍出版,中國學者在固定意識型態的前提下,多半又只使用中文的檔案與文獻,因此對傳教士及基督徒的敘述有許多誤解。再者他們的詮釋角度也經常與史實相矛盾。有的西方歷史研究者所採用的是基督新教傳教士的報告,在當時的環境中難免有對天主教方的抨擊,但同樣的這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成份。對此,西方天主教學者有他們的看法,他們試圖從自身信仰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文獻記載的客觀事實。但是,非中國人的天主教學者也許會缺乏中國天主教學者的洞察力,因為中國人會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待事實。
在這樣的背景下,陳方中博士有關義和團的研究是相當特別的,因為他同時具有中國人、天主教徒與歷史學者這三種身份,而在他的研究中他也盡量同時使用中文及法文的資料。在他文章的一開始,他就將如何使用這些不同性質的史料,發展為他寫作這本書的方法。由於義和團是一個距離現在不太遙遠的重大事件,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除了中國官方及西方傳教士的檔案外,還有許多當時的文人記載了他們所見的事件經過,甚至在一般民眾群體中也能保留下來口傳的記憶,這些不同來源的史料,成了交叉比對過去義和團拳亂敘述的利器。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用了遣使會及耶穌會的法文材料,也引用了大量中國官方的檔案以及當時文人的記錄,還有許多教會內外的訪談記錄。從文中也可以看出陳方中博士去過一些事件發生的地點,這無疑對他了解中國教會的內在生命有許多體會。這就使得這本書在義和團拳亂這個老問題上,能提出新的見解。
我們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區在內蒙,在義和團拳亂時也遭遇了重大的傷痛。陳方中博士這本書所描述的地區在直隸,也就是現在的河北省、北京市與天津市,雖然不是同一個區域,但兩個地方是相連的,在張家口外的西灣子及宣化一帶,有些地方還是重疊的。有關於內蒙地區的義和團拳亂,譚永亮(Patrick Taveirne CICM)博士在他的鉅著《漢蒙相遇與福傳事業—聖母聖心會在鄂爾多斯的歷史 1874-1911》也有很長的篇幅,比較這些敘述,可以發現義和團拳亂在不同的地區,其原因及經過是類似的。
我們以陳教授的研究成果為榮,因此將此書納入我們的懷仁叢書之中,衷心將此書推薦給讀者。
聖母聖心會
韓德力神父
(Jeroom Heyndrickx, cicm)
韓德力神父
(Jeroom Heyndrickx, cicm)
緒論
第一節 「義和團運動」仍然值得研究嗎?
這個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現在海峽兩岸的歷史學者,不約而同都減低了對義和團運動的興趣,但原因不盡相同。臺灣歷史學者在過去幾十年中,基本上對此問題興趣都不高,主要是因為資料有限。臺灣學者們早期所能掌握的資料是《義和團》四冊,這個由北京中華書局在 1950 年出版的叢書,蒐集了四十八種書彙集成四巨冊,利用這四巨冊的《義和團》, 真正寫成研究論著的是戴玄之。 他在 1963 年出版了《義和團研究》一書。 除了戴玄之以外,同時期的學者較少人往社會史領域鑽研,更不用說更深入的秘密宗教範圍。在 1980 年代以後的臺灣學者,逐漸有更多社會史或秘密宗教的研究論著出現,但一般來說,這些學者們關心的是較早期或更長時段的論題。 利用臺北故宮或是中央研究院的檔案,學者們可以看出較大範圍的輪廓,但義和團運動只是其中的一個短時段,而在細膩度上,當然比不上除了檔案,還有實地訪談調查資料的大陸學者。
在少用及誤用教會史料的情況下,典型中國大陸學者義和團研究的一大特徵是反帝愛國史觀。按照林華國的意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侵略勢力派遣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教會就成為西方國家在中國內地進行侵略活動的重要工具。為了擴大教會勢力,外國傳教士用各種手段拉中國人入教。」於是不少地痞流氓加入了教會,官府怕洋人,在發生民教糾紛時,通常偏袒教民;民眾積怨難伸,只得自己組織反抗,此所謂「反洋教鬥爭」。在這樣的背景下,甲午戰後,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國民眾普遍要求集中力量反抗外來侵略。在這個大環境下,以『扶清滅洋』為口號,以打擊侵略者為主要目標的義和團運動也就應運而生了。」
為大多數中國大陸的義和團研究者而言,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愛國性質就如同林華國的綜合一般,是不太需要再去證明的前提。我們可以在絕大多數文章中找到類似的論述,在此不一一舉例。反帝愛國史觀也影響了他們對史料的解讀,舉路遙、程歗描寫〈河北景州、棗強、衡水地區的義和團運動〉為例,在他們的敘述中有如下字句:
義和團攻打朱家河,完全是由於朱家河教會侵略勢力壓迫所引起。朱家河教堂原是天主教直隸東南教區的一個重要侵略據點。
朱家河教堂曾佔有三頃土地……這裡教堂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十分嚴重。
平時教民踐踏農家墳地,破壞人家風水;教民還在集上賤買貴賣,詐扣物產,無事生非,搗亂市集。
教會的侵略勢力激起了廣大民憤,它同附近各地的村民形成了嚴重對立的局面。
從這個實際調查所得的描述,基本上與林華國的論述完全相符。不過,這種描述也帶有一定程度成見。
西方學者沒有中國這種特殊的學術環境,他們在思想自由的狀態下進行研究。少了意識型態的八股,他們的作品若獲准在中國國內出版,往往可以得到廣大的迴響。最為中國研究者熟悉的西方義和團研究者是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和柯文(Paul A. Cohen)。前者撰有《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 將山東劃分為六個地理區域,運用大量中文史料,深入探討社會及文化背景,是一本頗受推崇的名著。不過基本上,這本書在義和團運動的動機上,仍持守反帝愛國史觀,除了在白蓮教問題上與中國學者意見不同,其觀點與典型義和團研究者並無太大差異。
典範轉移的代表性人物是柯文。在其早年研究民教衝突時,他就肯定文化衝突及社會摩擦是造成民教衝突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礎上,他一開始觀察義和團運動的眼光就和一般學者不同。在 1990 年他參加研討會時發表了一篇〈有爭議的往事:作為歷史與神話的義和團〉,柯文認為歷史學者雖然在追求真實,但實際上也不斷在製造義和團的神話。他舉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為例,說明了不同時期神話的建構過程。他認為:
對中國歷史學家來說,拋棄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風靡一時的,拙劣的神話化的形式是輕而易舉的,然而,要克服新文化運動將義和團神話化為迷信的作法,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視其為反帝愛國的神話卻是非常困難的。
1997 年相同架構的專著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出版,很快的中國也在 2000 年 10 月翻譯為中文出版,名為《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與神話的義和團》, 這本書的重點在呈現從義和團運動開始後,各種所謂神話建立的過程,以及柯文自己作為歷史學者,嘗試建立的義和團敘述。
柯文以上述專著為基礎,在 2000 年山東大學舉辦的「義和團運動一百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義和團,基督徒和神—從宗教角度看一九○○年的義和團鬥爭〉, 他認為在基督徒和義和團之間存在著宗教競爭與鬥爭關係,並非反帝愛國的概念推動義和團運動。雖然這種論調早在十年前柯文即已提出,但或許是因為梵蒂崗的封聖問題,主流的義和團歷史學者此時大肆批評柯文,從另一角度看,也使得這篇文章更受大陸學者注意。
在同一次研討會中,法國學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Bruquière)女士的文章〈義和團運動期間直隸省的天主教民〉 也引起廣泛討論。她使用遣使會的法文檔案,研究直隸西南遣使會傳教區的情形。她的結論是:攻打教友的義和團,既非來自遠方,絕大部分亦非來自於有人際互動的村民,而是附近有一定距離的地方,或是董福祥部隊的士兵。巴斯蒂認為:
它所表現的不是民族意識的覺醒,而是個人與集體的恐慌。……我們尤其不應從這種反應中得出天主教民與當地社會關係緊張的極端性結論。
狄德滿(R.G. Tiedemann)早期的觀點也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民族遭受壓迫的產物。他 1991 年即已大致完成,但 2011 年才翻譯成中文出版的《華北的暴力和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 China: Christian Miss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on the Eve of the Boxer Uprising),則加入了他一些修正的意見。他認為:「傳教事業於 1860 年後於山東地區的穩步發展,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中國鄉村秩序的矛盾正不斷深化。」這代表他將所謂的帝國主義侵略等外因,視為義和團興起的第二或第三因素。在另一篇名為“Anti-Christian Conflict in Local Context-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 Sanjie:Patriot, Protector, Banditor or Revolutionary”在多年鑽研大刀會後,狄氏討論龐三杰這個人物,在不同時期呈現的複雜面貌,是對所謂反教人物非常傑出的分析作品。另一篇最近的作品“Missionaries, Imperialism and the Boxer Uprisng:Some Histori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中,他認為即使是最具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安治泰主教(Johann Baptist Von Anzer),也不能說與義和團的興起有關,因為不論是神拳或梅花拳,都不是以安治泰所屬山東南部聖言會傳教區為主要發生地。這些文章也都是對反帝愛國史觀的質疑。
柯文的論文在 2000 年義和團會議時,尚且引起中國學術界官方,公開撰文點名批判,但他和狄德滿等外國學者,強調義和團運動內因的觀點,卻逐漸在中國義和團研究圈發酵。中國本來就具有社會史研究的優勢,義和團史學在此方面也有非常深入的調查訪談,由鄉土材料出發,中國歷史學者也開始修正反帝愛國史觀的某些觀點。代表人物是程歗,1990 年的義和團會議時,他發表了〈民俗信仰與拳民意識〉一文,將中國人的信仰系統劃分為三個相互聯繫而又彼此區別的次系統:正統的宗教系統,民俗的神祕信仰,以及異端的宗教信仰。在這背景上:
各地團壇並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特定教門的直線延伸,但是從文化背景的角度看,這種帶著濃厚神秘色彩的政治軍事集團,同樣是按著上述的信仰傳承和社會組織的運動規律而形成的。……義和神壇的觀念,儀式和風習之所以在許多方面同民間宗教息息相通,根本原因就在於它們都是社會成員地位低下而又帶有反抗性的團體,並且都根植和運動在鄉土民俗的文化大舞臺上。
這裡描述了義和團更深入的根源,相對來說,所謂帝國主義壓迫就是第二或第三考慮的因素了。
程歗在 2000 年義和團研討會的論文〈社區精英群的聯合行動〉,被刊登在《歷史研究》2001 年第一期。這篇傑作對梨園屯事件的各種史料做了非常詳細的爬梳。在排比檢查各種史料後,他認為 1960 年代所做有關村中公產的口述訪談,其實是不合歷史事實的,是一種扭曲的歷史記憶,但表達出村人對天主教傳入後,鄉村倫理秩序被破壞的焦慮。在細膩的閻氏家族結構中,清楚看到家族中部分成員信教後,造成的人際、經濟乃至文化的衝突。程歗也從「社區精英」的概念,補充了以往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認知,他以趙三多為例,說明傳統士紳的角色,在社會動盪的時代,被拳師、教首和巫覡所替代。
程歗的學生張廣生在同一次研討會中,發表了〈日常生活、權力與真相─玉皇閣廟產之爭的歷史記憶〉一文,他檢視梨園屯事件的相關史料,運用話語權力的概念,說明各種描述玉皇閣廟產之爭說法的主觀性,因敘述的角度不同,其實廟產問題不是只有一個固定觀念的。從一種較廣義的角度看,程歗和張廣生的論文是貼近後現代史學的,他們和大寫歷史的固定觀點辯論,重新挖掘史料的背後意涵,同時再重新建立敘述,如此或多或少也減少了反帝愛國史觀的限制。
在《歷史研究》的 2002 年第五期,有路遙〈義和團運動發展階段中的民間秘密教門〉一文。路遙以其對祕密宗教各支脈流傳的雄厚基礎,分析義和團運動期間,義和團人數最多的聚集地-北京,所謂的義和團,係分別屬於廣義八卦教中的乾字團與坎字團,其後又有聖賢道及九宮道等不屬八卦教系統的秘密宗教加入。路遙這一篇論文清楚說明了北京地區義和團與秘密宗教各支派的聯繫與關係,解決了長時期論述不清的問題。
2003 年第四期的《歷史研究》,李里峰的〈從「事件史」到「事件路徑」的歷史─兼論《歷史研究》兩組義和團研究論文〉一文,分析了上述 2001 年第一期,及 2002 年第五期共 7 篇義和團文章。李里峰認為這些文章有兩種類型,一種「把事件本身當成研究對象」,另一種則把事件視為歷史上社會結構的動態反應,試圖挖掘出事件背後所隱藏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視歷史的一種視角,一條路徑,可以稱之為「事件路徑」的歷史。
李里峰在其論文中還有一段有趣的自白:
記得還在準備學士論文時,指導老師就告誡我們一定要避開諸如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樣的選題,因為與之相關的問題要麼早被「研究透了」,要麼是我們尚無力涉足。近年來的研究狀況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種說法。
從李里峰的話可以驗證得知,中國大陸學者也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研究,在達到高峰之際,不管質或量其實都呈現下滑趨勢。作為事件史本身,義和團運動已被研究透了,只有少數相當有史識的歷史學者,可以運用一樣的史料寫出不一樣的文章;或是將義和團運動,當成一個事件路徑,關心其後更長時段或更大範圍的歷史結構問題。李里峰另一方面也有不方便說的原因,只要義和團運動的研究仍與現實政治沾上邊,只要中國大陸的歷史研究仍必須堅持唯物史觀,即使中國歷史學者對義和團運動有新觀點,多半也不敢在此問題上標新立異。簡單說,在沒有真正開放的環境中,最好不要碰這些敏感的題目。
作為事件史的義和團,其相關的問題大約可分為義和團的源流、性質、經過、東南自保、八國聯軍、辛丑議和等。 若按研究範疇,與社會史、軍事史、宗教史、外交史、政治史等相關。歷史的基礎研究倚重史料,所謂「研究透了」即是所有史料延伸的論題都已被反覆研究了,但真是這樣嗎?大部分義和團研究者在論及義和團興起的原因時,都會將目標指向教士教民的恣意妄為,而在義和團運動的經過中,教民與拳民的對抗,甚至可稱為戰爭,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絕大部分的研究其實都忽略了教會方的史料。在喪失史料辯護權的情況下,在進行這一部分的敘述時,難免會有偏頗或佚失。反過來說,若教會方史料得到客觀及充份的使用,作為事件史的義和團運動會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面貌。
平實的說,中國大陸的義和團研究者何嘗不想使用教會方的史料,但教會史料所使用的多語言,是漢語的歷史研究者很難跨越的門檻。在義和團運動時期,直隸有三個代牧區,直隸北及直隸西南是遣使會負責的區域,直隸東南代牧區屬耶穌會,他們都是來自法國的團體。在山東北部的方濟各會來自義大利,山東南部的聖言會來自德國,在塞外內蒙古傳教的聖母聖心會來自比利時,他們的文獻有法、荷兩種文字。在河南是米蘭外方傳教會,來自義大利,東北的巴黎外方傳教會顧名思義來自法國。各個傳教團體的文獻在他們母院或是羅馬,這種分散的狀態,是語言之外的另一困難。而這些資料是屬於這個團體所有,並不受國家相關檔案法規的管理,因此檔案管理者可決定讓研究者使用與否,以及如何使用。換一種角度說,他們不希望這些資料被反對教會的人,當成攻擊教會的證據。因此他們對不認識的研究者,經常抱有懷疑的態度。凡此種種,長此以往,是教會史料逐漸淡出義和團研究的一部分原因。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義和團研究「事件史」的部分,其實尚有缺乏之處。也就是說在拳教衝突方面,尚未利用教會史料補足敘述的缺口,更遑論進行微觀個別事件的因果關係分析。所以,義和團運動尚未被研究透徹,還有許多工作可作。而在檢視義和團的研究成果時,還可以發現另一個現象,就是因固有的成見,以致對史料做出錯誤的解讀。因此,在進行後續的研究前,必須要先對義和團運動的相關史料進行分類,各類型史料因作者的性質,其敘述是有其基本差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