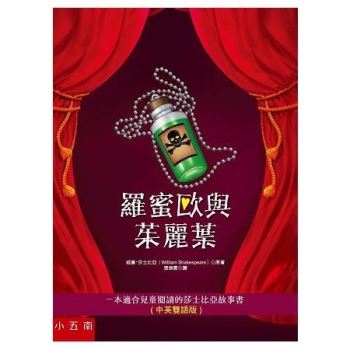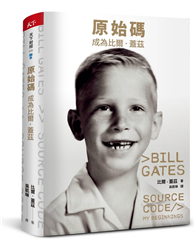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韓國小媳婦愛的逆襲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韓國小媳婦愛的逆襲 作者:穆香怡 出版社: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 出版日期:2021-01-1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大眾心理學79折起 |
$ 228 |
中文書 |
$ 229 |
兩性關係 |
$ 234 |
婚姻/家庭 |
$ 234 |
社會人文 |
電子書 |
$ 260 |
基督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從韓妻到耶穌的跟隨者
在韓妻的婚姻生活中,日日跟隨耶穌的腳蹤。每篇文字都是愛的記號,書寫了心中的感動,更記錄了上帝恩典的軌跡。
從溫馨慧黠到真誠反思
跨文化經驗賦予韓妻雙重視野,溫馨耐讀的文字中,處處流露出作者的慧黠,跌宕之處屢見真誠的反省,願意放下自己,在神的愛裡互相成全。
從餐桌愛語到實作食譜
書中傳授六道韓國料理食譜,以愛調味,以情烹煮,不僅大快朵頤,更讓彼此心心相繫,每一道都是滿載幸福的好滋味。
本書是作者記錄與韓國先生的異國婚姻生活。全書分成五個部分,分別是「婚禮和婚前」、「新婚生活」、「婚姻進場」、「食譜短文」和「附錄」。
先以婚禮拉開序幕,再按照婚前、新婚和婚後多年的順序,寫愛情、異國文化與婆媳、夫妻和親子關係,有詼諧幽默、輕鬆家常,也有深沉內省,從中看見人妻的自我追尋、信仰落實,以及有別於世俗潮流的價值觀。
|作者介紹|
穆香怡
資深韓妻,婚前曾於海外宣教五年,與韓國阿里郎結縭十三載,育有二子。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韓國國立首爾教育大學雙重語言教師資格認證;作品曾獲獎於「全國學生文學獎(高中組)」、「政大中文系散文選」、「基督教雄善文學獎」、「創世紀文學獎」、「飛揚雜誌徵文比賽」、「現代詩篇徵文比賽」。
曾為靈修月刊《豐盛人生》寫稿四年,曾在《基督教論壇報》刊登〈給宣教士的信〉、〈讀書樂〉和〈韓妻密語〉專欄。
除了中文寫作,也從事韓中翻譯:《傾聽的藝術》(2013,太雅出版)、《如果沒有財產,就留給孩子讀書的方法》(2013,太雅出版)、《耶穌花園聖經學習》(中主出版)。
本書為第一本個人散文集。目前進行中的專欄有靈修月刊《每日活水》的〈心靈捕手〉和《基督教論壇報雅歌版‧我與聖靈的禱告時光》。
Facebook粉絲團:穆香怡的小時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