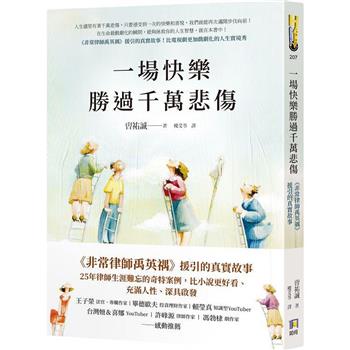在人口有百分之三是殺手的博多,趁華九會遭受「殺手殺手」反擊而大亂之際,各方地下組織展開了地盤爭奪戰。
為了保護林而主動出擊瓦解華九會的馬場、雖與馬場敵對卻同樣在追殺華九會成員的猿渡與新田、惡夢纏身的林,以及──突然發生的「林憲明連續殺人案」。
被捲入充滿算計與恩怨的地盤爭奪戰的殺手們,悲哀的過去再次被掀起。活在地下社會的男人們,賭上情誼的搏命對決即將展開!
面對一同走過地獄的前任搭檔,
悲傷過去造成的宿命對決,將如何收場?
本書特色
★2018年1月動畫播映!小野大輔、梶裕貴、小林裕介、中村悠一、浪川大輔等豪華聲優主演。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博多豚骨拉麵團3的圖書 |
 |
博多豚骨拉麵團(3) 作者:木崎 ちあき / 譯者:王靜怡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博多豚骨拉麵團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