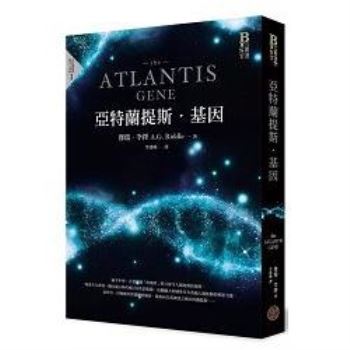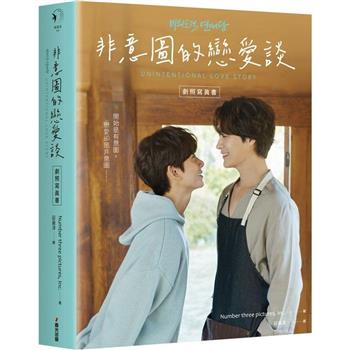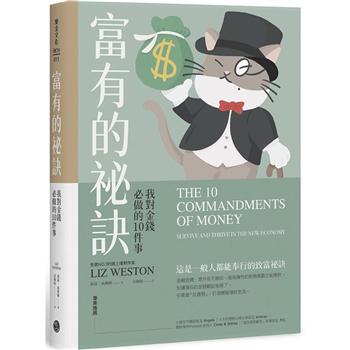第一章 血脈相連
葉山珠美
滴答、滴答、滴答……秒針聲響迴盪在昏暗的空間中。
仰望牆上時鐘,時間已經過了晚上九點。
好慢喔。
還沒好喔……
我在坐起來很不舒服的長椅上,深吸一口帶著藥味的空氣後嘆氣。
這是「島出中央醫院」住院大樓三樓,走廊尾端的候診室。從我那個腦袋會自動補上「實在有夠」來強調的鄉下地方老家開車過來,大概一個小時。我正在本地人口中名符其實的「最後堡壘」,也就是本地唯一的綜合醫院,等候父親手術平安結束。據說是要切除長在脊椎的腫瘤,再置換人工骨骼,大費周章的手術。
連接候診室的走廊照明不久前逐一熄滅,總覺得氣氛有些詭異。
寂靜的走廊上,有時會隨著腳步聲出現護士往來交錯的剪影。她們刻意壓低音量的腳步聲,感覺上反而更突顯院內的寂靜。「噗嗯~」,那彷彿在地面爬行的低沉聲響,應該是朦朧飄浮於黑暗中的自動販賣機的呼吸聲。
是因為空氣乾燥的緣故嗎?喉嚨有點卡卡的。
我稍微清清喉嚨。那聲音彷彿一路迴盪到走廊最深處,讓人不禁肩頭瑟縮。
夜晚的醫院有種獨特的恐怖。讓人覺得,到處都有無數隱形的緊繃線條,縱橫交錯。病患靜靜躺在熄了燈的病床上,在幽暗中各自靜靜陷入沉思,而從他們身上散發出近似「思念」的東西,就像蜘蛛絲結在漆黑建築物內部……那不是會營造出一股難以言喻的緊張與恐怖嗎?我就是這麼覺得的。總之,對於從沒住院過的我而言,這個充塞封閉感的昏暗空間,簡直就是瀰漫異樣寂靜的異世界。
然而,卻有個女性完全不把這種氛圍當一回事,發出幾近搞錯場合的開朗聲音,剛剛一屁股在我身邊坐下。
「小珠,肚子餓了嗎?我有香蕉喔。好甜、好甜的香蕉喔。要不要吃?」
個子嬌小、身材纖瘦,臉有夠小,這麼說雖然不好意思,但是胸部也小,要二十歲的我叫「媽媽」未免也太娃娃臉的那個人,正因為是長期持續曝曬在熱帶陽光下的人種,肌膚有些黝黑。
「現在不要。肚子還不餓。」
我簡短回答。
「為什麼?晚餐不是也還沒吃嗎?小珠是個可愛的女孩。減肥什麼的,根本不需要。所以,吃吧。」
夏琳用純潔少女般的圓滾滾大眼睛仰望我,一邊遞出熟透的香蕉。這個外表看來年輕得很,戶籍上卻已經成為我「繼母」的菲律賓女性,今年應該三十九歲了。
「我才沒在減肥。」
我自言自語似的說,不過姑且接下香蕉,省得麻煩。
但是,就是沒心情吃。
「小珠,快看、快看,這個香蕉有很多褐色的斑點喔。這就是香蕉好吃的證明喔。」
夏琳說完一笑,將自己那根香蕉剝皮後,以幸福的臉龐自顧自地大快朵頤。
我隱忍住嘆息,轉向前方。明明才剛看過,卻再次仰望牆上時鐘。手上的香蕉,感覺格外冰涼。那溫度讓我莫名感到淒涼。
「別擔心。爸爸桑,會好的。小珠,最要緊的是打起精神喔。」
嘴巴塞滿香蕉的夏琳這麼說。然後有些黝黑、孩子般的細瘦小手,輕輕觸碰我的背。那隻手開始緩緩上下移動,原來是在輕撫我的背。
想撥開那隻手……倒還不至於,反而覺得「好溫柔喔」。只是,同時還感受到一股絕對不算輕微的違和感。
違和感……
是的。這種感覺不是厭惡,而是違和感呢。
要說我討厭夏琳……其實並非如此。我很清楚這一點。只是,自從她成為我的「家人」,成為我「繼母」的這三年間,我始終擺脫不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違和感。我沒那麼世故圓滑,能壓抑這種違和感或假裝沒事,同時也不是個心胸寬大的成熟女性吧。單純就只是那樣……我覺得。說不定,只是想要那麼覺得就是了。
我往身旁瞄了一眼。
生於異國的女性嘴角含笑,眼神卻是盈滿憂慮地仰望我。
「小珠,打起精神來喔。」
「嗯,不要緊。我,還是,吃香蕉好了。」
夏琳的手停止動作,從我背部移開。違和感的殘渣會暫時留存吧。但是,我決定別放在心上。
我撥開已經浮現所謂「甜斑」(sugar spot)的褐色斑點的香蕉皮,從尖端咬了一小口。口感黏稠,的確很甜。讓人想起輕拂過夏琳生長的南國,感覺甜膩的風的滋味。
「小珠,好吃嗎?」
閃耀光澤的漆黑眸子望著我,這麼問。
「很好吃喔,夏琳。」
我沒叫她「媽媽」,一如往常直呼名字。
儘管如此,夏琳還是純真地展露微笑。
「香蕉還有一根喔。我已經飽囉。這也給小珠。」
夏琳從看來廉價的二手托特包,拿出香蕉給我看。
「不用了。我也飽了。」
我微微苦笑搖頭時,昏暗走廊深處,傳來護士由遠而近的急促腳步聲。
不久後,腳步聲終於停在我們面前。
那是位年約三十,雙眼細長的纖瘦女護士。她的身材修長,看起來大概有一百七十公分。一百六十公分的我,從長椅起身,身旁一百五十公分的夏琳也立刻跟進。
「葉山小姐,抱歉,讓您等這麼久。等得都累了吧。」
護士滿懷歉疚,雙眉垂成八字型,不過口氣有別於說出口的內容,感覺輕快。所以,我開始放下心裡的大石頭。手術肯定很順利。
「不會,沒關係。」
我回答後,仰望護士。
「那個,手術方面呢,雖然比預期還要花時間,不過總算平安完成了。」
夏琳抓住我的右手臂說:「Nice。」
「只是……」
護士說到這裡,語調有些下沉。
「欸?」我稍微歪頭。
「花的時間遠比預期還要長,患者的體力都被消耗掉了。所以,今天還是會在麻醉作用下,繼續沉睡呢。」
「啊……喔,好,我瞭解了。」
「不好意思耶。」
受到護士誠惶誠恐的神情影響,連我也跟著變得誠惶誠恐。
「不會,沒關係的。啊,對了,體力消耗會不會妨礙術後復原之類的啊……」
「不會有那種事的,請放心。」
我吐出安心的嘆息。那是連自己都嚇一跳的深沉嘆息。
「可以見爸爸桑嗎?」
個頭嬌小的夏琳,幾乎像在看天花板似的詢問護士。
「可以喔。現在已經被送進ICU,我帶妳們去。」
那麼,請往這邊走……護士小姐說著轉向昏暗的走廊。
我也隨著那個瘦長的背影,邁出步伐。
夏琳原本抓著我右手臂的手一鬆開,立刻說:「啊,包包忘記了。」然後自顧自地開朗笑著,抓起長椅上裝有香蕉的托特包,小跑步跟上來。
來到走廊中段,左側有個護理站。裡面有五位護士輕聲細語地交談,同時俐落工作。我斜眼望向那幅情景,一行人隨之從護理站前走過,緊接著往左手邊拐個彎。那裡有個昏暗的電梯間。身材修長、眼睛細長的護士,按下那個為了讓輪椅人士也能按到,設置較低的「上」按鍵。
「小珠,太好了呢。爸爸桑會好起來。我也好高興喔。」
背後響起夏琳爽朗的聲音。那與熄燈後的醫院極不搭調的聲調,讓護士的側面露出苦笑。
開始覺得有點丟臉的我,轉頭對她「噓」了一聲。
「啊,不好意思耶。噓~好喔。噓~」
夏琳模仿我,將食指立在嘴唇前方,圓滾滾的雙眼隨即瞇起,露出淘氣的微笑。
◇ ◇ ◇
從「鳥出中央醫院」回老家的沿途,幾乎不是海岸就是山裡。道路護欄沿路雖然都設置了路燈,但是視線不良的彎道或隧道一個接著一個,車子開起來實在累人。而且今晚又下著雨。那是似乎隨時都會變成雪的臘月冰雨。
「還好,小珠開車一起來呢。開到那裡的電車很少,謝謝妳喔。」
纖瘦背部整個陷入副駕駛座的夏琳,朝我這邊說。的確,這個時間的電車,一個小時有沒有一班都不知道。
「話說回來,夏琳為什麼搭電車去醫院呢?」
既然有駕照,可以開爸爸的車過來啊……我心裡這麼想,所以開口問她。結果,夏琳脖子一縮。
「爸爸桑的車,壞掉了。電瓶,空空。引擎,發不動。」
「哎呀呀。」
十之八九恐怕又是停車後沒關車燈,導致電瓶沒電、車子發不動吧。糊塗蟲夏琳以前也曾有過大概兩次相同前科。
車子沿著海岸駛向險升坡。
我踩下這輛被父親不屑地稱為「破銅爛鐵」的黃色輕自動車(註1)油門。都已經踩滿深了,欲振乏力的愛車卻幾乎沒加速。也是啦,畢竟是之前已經開過十幾年的舊款,行駛里程都累積到某個程度了,買到的價格也只花了區區「五圓」,沒什麼好抱怨的了。順道補充一下,以「五圓」這種破盤價買到這輛車的是父親,而那段過程還真是充滿我父之風。
那是前年,我才十八歲那時候的事……
父親的某個酒友大叔,偶然間來到我們家經營的「架上的麻糬居酒屋」喝酒時,隔著櫃臺出現這麼一段對話。
「喂,正太郎呀。我那台車,又~整組全壞了啦。聽說你有個學弟是在賣車的?那傢伙,能不能幫忙回收啊?」
「正太郎」是父親的名字。父親額頭上緊緊綁著印有商號的藍色毛巾,戴著一副橘色太陽眼鏡,正在櫃臺內分解本地產的魚,做成生魚片擺盤,一邊回答。
「又是化油器掛掉嗎?」
「我哪知道啊,反正就是引擎發不動。」
「喂,老頭兒,既然如此,那輛車,我幫你買下來吧。」
「啊?要買?你知道,那可是一輛發不動的車喔?」
「也不礙事。」
「發不動的車,你是打算花多少錢買啊?」
父親此時放下菜刀,抬起頭來。
「這個嘛,希望光棍老頭兒能交到一個色色女友共結良緣,用五圓跟你買怎麼樣(註2)?」
「哇哈哈哈。五圓喔,還真是傑作啊。」
「反正是發不動的破銅爛鐵了。與其被人家收一筆報廢車處理費,五圓跟你買要好多了吧。」
「嗯,是吧。好,我明白了。破爛車就以五圓賣給正太郎。隨時都可以過來牽車喔。」
所以啦,父親就這樣以五圓承接了一輛發不動的輕自動車。他事後立刻打電話給當地做汽車維修的學弟—常田壯一郎,請他幫忙修理。這個人就是我的一位同學常田壯介的父親,聽說那時候憑藉學長學弟的關係,硬是拗到了不花半毛錢的修理費。傳聞說,常田先生相對地也獲得在我們店裡「三天喝到飽」的權利。
以五圓獲得一輛跑得動的輕自動車的父親,後來決定將車子送我,慶祝我進大學。
「小珠也終於要到大城市去,成為花樣年華的文學部女大生了,有輛車子,說什麼都比較方便吧?而且啊,只要有了這傢伙,噗~一聲,就能輕輕鬆鬆開回家來啦。」
這就是,父親送禮時的補充說明。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這個獨生女即將遠走他方,覺得寂寞,所以要盡量開著這輛車,頻繁回家來喔……的意思。
從那之後過了兩年,很感激的是這輛黃色破爛車從沒故障過。不僅如此,在此期間還加裝了音響與車用導航,另外也換了輪胎與輪圈,達成大幅度的進化。起初開車時還是初學者的我,沒兩三下就習慣了駕駛,後來還開始載著大學同學到處遊山玩水,每個月也會花單程三小時的時間,回老家一趟。
但是,以「花樣年華的文學部女大生」身份,從住慣的城市公寓,開著這輛黃色破爛車回老家……都已經是過往雲煙了。其實,我早就放棄了大學生的身份。我大概三個月前,已經悄悄向大學學務處提出了退學申請。
退學之後的我,一邊在超商與餐廳打工賺錢,同時勤奮研究與文學毫無關連的領域。我忙著大量閱讀與「創業」相關的書籍,還有網路資訊。除此之外,我也花一整天時間,參與保健所舉辦的「衛生法規」、「公眾衛生學」、「食品衛生學」講習,取得「食品衛生負責人」證照。這對於我即將投入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一張證照。
凡此種種,我在積極籌備創業事宜之餘,也很清楚差不多該向父親報告已經從大學退學,同時商量一下想回老家發展的事,所以懷抱著有點緊張的心情,嘗試打了電話……結果,天底下哪有這種事!在電話中受驚的人,竟然是我。
「喔,小珠啊。我正想打電話給妳耶。這就是人家說的完美時機呢。」
「嗯?是喔。什麼事?」
「唉,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啦。就只是想先跟妳說一聲,要是我死了,妳可要跟媽媽好好相處啊。」
蛤?
什麼死不死的,怎麼回事?
什麼媽媽,是說夏琳嗎?
「什麼,東西?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明天,要動一下脊椎手術啦。」
父親彷彿音痴哼歌般這麼說。
「咦……明天?重點是,你說手術是指什麼?我怎麼從來都沒聽說過這回事?」
「那是當然啦。這是第一次跟小珠妳說啊。」
「等……那麼重要的事,應該事先好好跟自己女兒說清楚吧?」
撇開自己連「大學不念了」這種大事都還沒告訴父親,我嘟著嘴巴抗議。
「啊哈哈,不用那麼擔心啦。」
「當然會擔心啊!」
「就跟妳說,沒什麼大不了的啦。」
「要是真沒什麼大不了的,動什麼手術啊。給我說清楚喔,受不了耶。」
「不要那麼大聲嘛。總而言之呢……」
總而言之呢,悠哉的父親據說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脊椎長了一顆大腫瘤,因為還滿痛的,所以得趕緊切除,然後將置換的人工骨骼「塞進去」。
「你說腫瘤……欸,等一下喔。」
開始有些恐慌的我,讓父親發出嘲弄的笑聲。
「喂喂喂,什麼嘛。小珠,妳是覺得本大爺真的會死喔?」
「嗯……畢竟,都說有個大腫瘤了……而且剛剛還說,『要是我死了』……」
「喔,我忘記講了。很遺憾,那腫瘤是良性的耶。哇哈哈哈哈。」
「良性?」
「嗯啊。」
「那,不會死囉?」
「傻了啊妳,怎麼可能真的死嘛。」
「絕對?」
「唔,絕對。我在死之前都會活得好好的啦,啊哈哈哈。」
「……」
我說,講話再怎麼隨性輕浮也該有個限度。我雖然火大到不行,但是心情一放鬆就感覺雙腿發軟,將自己要講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後來就忙著問些隔天的手術時間、住院事宜準備好了沒、或是關於那個良性腫瘤之類的問題。雖然父親對我說:「有夏琳在醫院照顧我,小珠就好好去念文學什麼的。」卻被我當頭斥喝:「說那什麼話,怎麼可能嘛!」於是,今天就急忙開著黃色破爛車,飆車趕到醫院去。
我將油門踩到底爬上陡坡,緊接著是和緩的下坡。這裡中途會有個大彎的下坡,是個常因速度過快引發事故的車禍熱點,在本地很有名。我一邊滑行一邊間歇性地踩煞車,慎重轉動方向盤。
「小珠,肚子餓了耶。」
夏琳說。
「啊?不是才剛吃過香蕉嗎?」
「光吃香蕉不夠喔。等我們到家,就吃好吃的東西,一邊乾杯喔。」
「乾杯?」
「女兒回家來了,家人也很開心啊。爸爸桑也是,只要小珠回來就會乾杯喔。還有,慶祝爸爸桑手術成功喔。」
夏琳嘴裡迸出的「女兒」一詞,在我胸口淺處形成彷彿小石子的違和感,滾過來滾過去。而且,那句「回家來了」也讓我心頭一震,心臟漏跳一拍。因為不論如何,那並不是單純的「回家來了」,而是「大學不念,回家來了」。
不論父親還是夏琳,都必須告訴他們這個事實才行。只不過呢,畢竟父親是那種個性,就算說出口,起初或許會有些吃驚;不過,只要確實說明原因,感覺上就會意外瀟灑地諒解我的決定。「唉,國中畢業的我可能也沒立場說這話就是了,不過人生也不是只有念書。小珠就來當我們店的店花好了」,他結尾肯定會這樣一笑置之。
他就是這樣的人,從以前就是這樣。而夏琳,一定會站在父親身旁笑嘻嘻,感覺會說什麼「那樣很Nice喔,全家一起生活,是最幸福的喔」。
話雖如此,我好歹也是年滿二十的成年人了,眼見父親手術當前,這件事暫時祕而不宣的體貼,畢竟還是有的。
就跟向女人示愛一樣,如果想跟別人說什麼要緊事,必須講究「就是現在」的時機喔……既然父親都常這麼告誡我了,那我在這當下保持沉默,也是無可奈何的吧……暫時就先這麼想好了。
「快到了喔。肚子都咕嚕咕嚕叫了耶。」
夏琳摩擦瘦扁的肚子,一邊說。
「超商那裡,不用順便繞過去一下嗎?」
「不用喔。一回到家,冰箱裡就有很多好吃的東西喔。」
這輛破爛輕自動車,翻過最後一個山頭,進入小小的市區街道。
我在二十年前出生,然後持續生活了十八年的偏鄉聚落……
是個名字很美,叫作「青羽町」的町(註3)。
這片西側被層層深山環繞的土地上,有一條名為「青羽川」的翡翠色清流流過,形成一片扇形平原,居民密集生活其上。東邊則是湛藍海洋。
在這裡,新綠的春天就去採山菜,孩子一到暑假就成群結隊跳進青羽川或海裡游泳,大人則享受香魚、山女鱒、岩魚的垂釣之樂。最近,也有越來越多人划獨木舟遊河。滿山遍野紅葉似錦的秋天,就是採菇季節。時序接著進入冬天,大家會叨唸著「好閒、好閒啊」,一邊湧進某人家中,夜夜圍爐、暢飲當地美酒。其中,還會有無畏寒風跑到海岸邊,釣來冬天滋味更肥美的「寒冬烏魚」、「寒冬瓜子鱲」的瘋狂男人。
青羽町是一個能親近豐富自然資源,當地居民往來密切的聚落。離開這裡到大城市後,我有多麼以自己的故鄉為榮啊。但是就算是這種地方,也難抵大時代的洪流,年輕人的外流勢不可擋,人口在數年前已經跌破八千。人口過少與高齡化,也成為這個聚落如今最嚴峻的問題。
青羽川滿載的河水如同澄澈無瑕的汽水,河口附近有個小港口,當地漁民每天早上都會將新鮮魚貨打撈上岸。我的祖父與父親都曾當過漁夫,後來因為漁船過於老舊,祖父辭世,再加上父親腰痛加劇,父親於是順勢放棄當漁夫,上了岸。接著,就在熟悉的港口附近,開了一間主打海鮮料理的「架上的麻糬居酒屋」。那是剛好十年前的事了。我們雖然是一家只要坐進十五個人就會客滿的小酒館,不過因為父親豪邁直爽的個性,還有美味的新鮮魚貝,來客數還算穩定。
「架上的麻糬居酒屋」,這個像鬧著玩的店名,當然是主張「人生就是要搞笑」的父親所命名。順帶一提,父親的座右銘就是「架上麻糬掉下來,得來全不費工夫」(註4)、「單純活著就已經是穩賺不賠」,所以也很能理解為什麼會取這種奇怪的店名。我在就讀小學國中一貫學校時期常被一些白痴男生取笑說是「架上麻糬店花」,但是如今對於這個像鬧著玩的店名,卻反而有股依戀。
我會這麼說,也是因為某天喝醉的父親曾這樣說。
「所謂的『架上掉下一顆麻糬』,簡單來說不就是很走運嗎?而所謂的走運,也就是受到神明疼愛。所以說,我只要每天晚上喝酒,跟大家嘻嘻哈哈,彼此開開心心的,神明也會覺得很開心,自然而然就會聚在這裡。然後呢,正因為是神明聚集的地方,運勢就會慢慢大開啦。」
要打造出一個讓大家開開心心、神明也開開心心,運勢大開的地方……
父親這樣的想法,如果要以「喜歡」還是「討厭」來一刀切,我可以非常單純地說出「喜歡」。而且根據日本神話,天照大神也是因為受到石窟外開心歌舞的其他神明引誘(註5),最後才會從原本隱遁的天之石窟走出來的。所以我後來也慢慢覺得,父親的話也並非一無是處。果然,神明也喜歡開開心心的呢。
補充說明一下,我們家就住在那間運勢很好的店舖二三樓,各樓層窗戶都能將青羽灣的明媚風光盡收眼底,真的非常舒服。特別是在吃早餐時,一邊眺望地平線彼端莊嚴神聖的旭日東升,即使是個孩子也會覺得真是種奢侈;晚上,不論是遠眺漆黑地平線上整列漁火,又或傾聽遠方浪潮聲一邊安穩入眠,都讓我深深覺得自己好幸福。
我國一時因車禍撒手人寰的母親,也很喜歡這個家。她還常家事做到一半,就突然停下手邊工作,眺望廣闊的青羽灣,沉靜微笑。
「再一下,就到家了喔。」
夏琳的聲音,讓回憶中的母親臉龐煙消雲散。
「對啊。」
「有點,開始下雨了喔。」
「嗯。」
我頷首,在青羽川河口的橋樑前方將方向盤往左打。那是一座被當地人單純稱為「大橋」的紅色大橋。
「希望明天可以變暖喔。我,是從菲律賓來的,所以很怕冷喔。」
夏琳雙臂抱胸,表演受凍。
「也是呢。」
我噗嗤一笑。順著沿岸細長道路往海那邊前進,不久後就能慢慢看見河口對岸青羽港的路燈。往對向的左手邊一看,那裡就是我們家。
車子滑進店舖前面沒鋪柏油的空地,我選擇沒有積水的位置停好車,打到P檔,拉起手煞車後熄火。蹚蹚它它它蹚……車內頓時充塞寂寥的聲響,那是敲擊這輛便宜車車頂的雨聲。
「小珠,謝謝妳開車喔。」
「嗯。」
我們分別套上外套,拿起東西下車。我們在雨中,小跑步繞到店舖後方。
夏琳將鑰匙插進後方玄關大門,開了鎖。
連夏琳擁有老家鑰匙這種瑣事,都會讓部分的自己感受到小小的違和感,我對此不禁想嘆息。
「哇嗚,都濕掉了。雨,好冷喔。小珠,快進去。」
一拉開門,夏琳推著我的背,讓我先進去。這樣的體貼,反過來說也讓人感受到「夏琳是這個家的人,而我是外來客人」的結構。我也厭惡自己會心胸狹窄地這麼解讀,而這次,真的發出了一聲小小的嘆息。
我步上二樓,開啟起居室暖爐。順手也打開暖桌開關。
跟我住在這裡那時候相較,這個起居室感覺有點雜亂。夏琳並不擅長整理。像是脫下的衣服就扔在那邊,用過的餐具也擱在暖桌上。
家裡變成這副樣子,父親都沒有什麼感覺嗎……
我突然望向起居室內側的佛壇。
母親生前很愛乾淨,不論什麼時候都會把這個景致優美很棒的家,整理得乾乾淨淨的耶。
當我走近佛壇想點香時,背後響起聲音。
「小珠,久等了。」
是夏琳從一樓店舖冷藏庫隨便選了幾樣小菜,用托盤跟啤酒一起端上樓來了。夏琳將暖桌上用過的餐具隨意推向一旁,將啤酒與小菜擺到空出的位置。
「夏琳。」
「怎麼了?」
「乾杯前,可以先點香嗎?」
夏琳也沒理由拒絕,我姑且還是先請示了一聲。
「當然啊。那很好。我也要點香喔。」
我站在佛壇前。家中打掃並沒有做到面面俱到,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只有佛壇內外,還有牌位全都擦得光潔亮麗,讓我稍微鬆了口氣。
我用百圓打火機,點燃左右兩邊蠟燭。
背部感受到夏琳就站在身後,一邊用蠟燭點了香。
我輕輕將香插進香爐,將缽敲響。
細長白煙,裊裊爬升。
我雙手合十,緊閉雙眼。
眼前,再次浮現母親充滿慈愛的微笑。
母親在七年前死後,佛壇右側本來一直都放著遺照。那張照片是我與父母親一家三口,在附近防波堤釣竹莢魚拍下的。不規則反射在藍色水面的陽光,讓照片中的母親有些刺眼似的瞇眼微笑。那抹溫柔的微笑,簡直就是我們這個幸福家庭的象徵,每次只要一看到那張遺照,心情就會變得心酸又溫暖。
但是四年後,父親與夏琳再婚,佛壇旁的母親遺照也在同時不見蹤影。是新任妻子不喜歡前任妻子的遺照嗎?又或是父親顧忌新任妻子的感受呢……?真相不得而知。當時已經十七歲的我,刻意不去觸碰那件事。只是我還記得,當我在平常收納坐墊或熨斗等物品的壁櫥角落,發現母親遺照被隨便塞在那裡時,一股炙熱的情緒瞬間從內心深處的湧泉咕嚕咕嚕冒出來,獨自泫然欲泣。我從狹窄黑暗的壁櫥中,「救出」母親遺照,抱在胸口,隨即拿到三樓自己的房裡。然後,輕輕收藏進書桌抽屜。
從此之後,我每次都會打開抽屜,悄悄面對母親幸福洋溢的微笑。雖然不是漫畫「哆啦A夢」,但是那個書桌抽屜對我而言,就像是能夠返回那個幸福時期的某種時光機器。
兩年後,我離開家鄉到城裡去的時候,決定將母親遺照與書桌一起留在自己房間。因為母親真的好愛這個家,總覺得不想帶她到大城市去。相對的,我每個月都會開著黃車子回來一次,就算是短暫停留的時間,也會將母親遺照從抽屜裡拿出來,立在桌面上。
媽媽。
我回來了。
我在沒有遺照的佛壇前,緩緩睜開雙眼。
放下原本合十的雙掌。
已經移動到旁邊去的夏琳,替我站在佛前,以彷彿日本人的熟練手法將缽敲響,然後供上兩柱清香。
「為什麼是兩柱呢?」
「爸爸桑跟我的喔。」
夏琳露出一副「這是當然的吧」的樣子,然後睜著圓滾滾的大眼睛合掌,以一如往常的開朗聲音開始對牌位訴說。
「繪美,小珠回來囉。爸爸桑的手術也很成功喔。不用擔心喔。」
我從旁望著她那樣子,不自覺停止呼吸。媽媽的名字「繪美」從夏琳嘴裡迸出來的時候,對我造成一股不小的衝擊。
鬆開掌心的夏琳,轉向這邊。
「小珠,OK了喔?」
「欸?啊,嗯。」
「那,來乾杯喔。我的肚子都咕嚕咕嚕叫囉。」
夏琳彷彿遭受斥責的孩子一臉狼狽,雙手一邊壓著自己腹部。那樣子實在好笑,讓我輕笑出聲。夏琳也有些害臊地「嗚呼呼」發笑。
我們面對面,雙雙把腳伸進暖桌。
「日本的暖桌,我最喜歡了喔。」
夏琳說著,拉開罐裝啤酒拉環。
「冬天,還是要有暖桌呢。」
我也「噗咻」一聲,拉開拉環。
「那,小珠。為了手術成功,乾杯喔。」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小珠的幸福宅配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小珠的幸福宅配車
★帶著笑容前進吧!為某人努力時,必然有人正支持著你。
★日本療癒系作家森澤明夫以偏鄉為題,獻上感人新作!
★《夏美的螢火蟲》、《守候彩虹的海岬咖啡屋》等多部作品皆改編為暢銷電影。
在鄉下城鎮裡,少子化和高齡化日益加劇。小珠為了幫助因行動受限而成為「採買弱者」的獨居老人,決定從大學休學並創業經營起移動販賣的「跑腿宅配車」。
可是,煩惱和糾紛接踵而來。與菲律賓籍繼母夏琳的隔閡、繭居不出的同學真紀、拯救不完的獨居老人,以及與重要的人離別……儘管如此,小珠相信只要在這裡,好多事情都能一一實現。
每個人都可以鼓起勇氣,在這裡為人生展開「小小冒險」……
作者簡介:
森澤明夫 Morisawa Akio
1969年出生於千葉縣。早稻田大學畢業。2007年以《海を抱いたビー玉》出道成為小說家。《津軽百年食堂》、《ライアの祈り》等多部作品被翻拍成電影。「不思議的海岬咖啡屋」(原作《守候彩虹的海岬咖啡屋》)榮獲第38屆「蒙特婁世界電影節」兩項大獎。最新被翻拍成電影的作品《夏美的螢火蟲》,以柔和溫暖的作風,追求「幸福的本質」而獲得廣大的支持。另著有《癒し屋キリコの約束》、《大事なことほど小声でささやく》、《きらきら眼鏡》、《エミリの小さな包丁》等書。
譯者簡介:
鄭曉蘭
古怪難搞的水瓶女,興趣是與主流唱反調,夢想是踏遍世界各角落,身分是日文口筆譯者、特約記者、華語教師,其他客串角色族繁不及備載。熱愛文字、創作與動物,將閱讀寫作還有錢領的「翻譯」,視為終極夢幻職業。譯作包括《島與我們同在》、《日向》(時報出版)、《私人生活》(青空文化)、《企鵝公路》、《夏美的螢火蟲》(台灣角川)等。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血脈相連
葉山珠美
滴答、滴答、滴答……秒針聲響迴盪在昏暗的空間中。
仰望牆上時鐘,時間已經過了晚上九點。
好慢喔。
還沒好喔……
我在坐起來很不舒服的長椅上,深吸一口帶著藥味的空氣後嘆氣。
這是「島出中央醫院」住院大樓三樓,走廊尾端的候診室。從我那個腦袋會自動補上「實在有夠」來強調的鄉下地方老家開車過來,大概一個小時。我正在本地人口中名符其實的「最後堡壘」,也就是本地唯一的綜合醫院,等候父親手術平安結束。據說是要切除長在脊椎的腫瘤,再置換人工骨骼,大費周章的手術。
連接候診室的走廊照明...
葉山珠美
滴答、滴答、滴答……秒針聲響迴盪在昏暗的空間中。
仰望牆上時鐘,時間已經過了晚上九點。
好慢喔。
還沒好喔……
我在坐起來很不舒服的長椅上,深吸一口帶著藥味的空氣後嘆氣。
這是「島出中央醫院」住院大樓三樓,走廊尾端的候診室。從我那個腦袋會自動補上「實在有夠」來強調的鄉下地方老家開車過來,大概一個小時。我正在本地人口中名符其實的「最後堡壘」,也就是本地唯一的綜合醫院,等候父親手術平安結束。據說是要切除長在脊椎的腫瘤,再置換人工骨骼,大費周章的手術。
連接候診室的走廊照明...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森澤明夫 譯者: 鄭曉蘭
- 出版社: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3-26 ISBN/ISSN:978957564118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432頁 開數:14.7x21 cm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