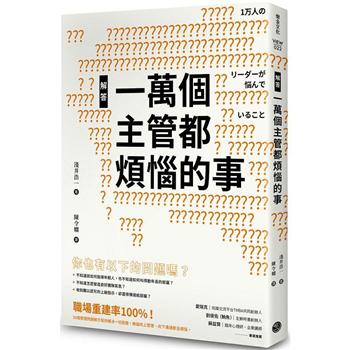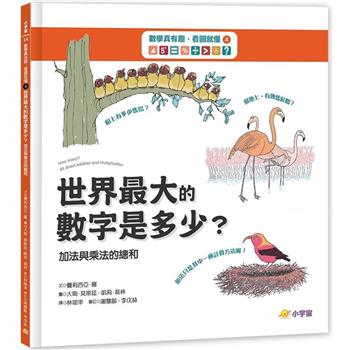推理史上最好鬥雙人組再度上場,
倒楣的是別人?還是自已?
倒楣的是別人?還是自已?
「想找碴?我奉陪!這就是老子的作風。」
建築顧問二宮接到議員祕書請託,解決與黑道間的糾紛。事務議員祕書聲稱,因議員補選拉票問題而與麒林會間產生誤會,事務所竟遭人投擲火焰瓶。但麒林會背後有組員超過百名的大幫派撐腰,道上無人願意出面調解,二宮無奈之下,只好求助已遭幫派破門的桑原。嗅出選戰背後的龐大金錢利益的桑原,不惜上演全武行,然而失去幫派後盾的代價實在太大──
為了奪取貪腐議員祕書、黑道幫派爭相蠶食的巨大利益,
失去代紋、赤手空拳的桑原及二宮這對「瘟神」搭檔,
即將迎戰最大危機!
本書特色
★第151屆直木賞得獎作 史上最好鬥雙人組,兇惡再登場!
★日劇、電影改編不編,娛樂小說巔峰之作!
★桑原及二宮這對「瘟神」搭檔,迎戰最大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