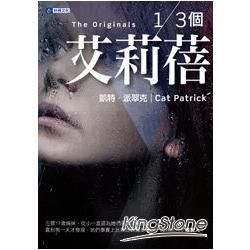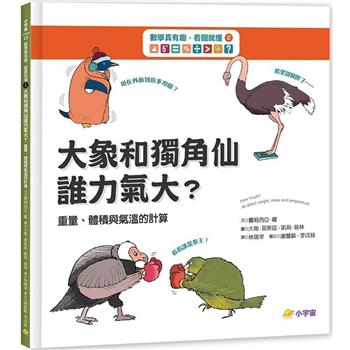「別忘了洗掉妳的指甲油。」
媽從廚房的走道對我叮嚀這件事,就在她早上出門前的最後一分鐘。這真是目前我們做過最大的調動。諷刺的是,她竟然還敢叨唸我:她自己五分鐘前說要在我們在家上學時間開始前去寄帳單,結果馬上又回來了,因為她既忘了帶帳單,也忘了帶車鑰匙。我對她翻白眼,接著她又出門了,然後,我低頭看著我擦得很完美的白色指甲。
「為什麼妳的指甲油總是那麼快就脫落?」我皺眉問艾拉。她聳肩,她的眼睛望著房子腳下的山谷。我知道她也對於我們任務分配的調動感到很沮喪。她站起身,在離開前把她的早餐麥片碗放到水槽裡,大概是去刷牙了。我把椅子推開,起身上樓,沿著長廊走向媽的房間去找去光水。
我推開門,迎向清冷黑暗的房間,輕輕打開天花板電燈的開關。我走過地毯發出嘎吱聲,眼角卻瞥見門後的牆上,有如美術館般地懸掛著棕色木質相框,裡面分別鑲著三張小嬰孩的照片。當我停下來仔細審視時,我感到脖子後方如同針扎般刺痛的熟悉感覺。
不管是誰都會覺得這三張照片是同一個孩子穿著不同的衣服,並且做出不同表情,但是,貨真價實,這是三個不同的孩子。艾拉嘴張得開開地;媽說她被一根長棍上的蝴蝶給催眠了,這是攝影師用來吸引她注意力的方法。她的背景一直都是百貨公司。蓓思在她的照片裡,像是一隻聖伯納犬一樣流著口水。而我則在號哭著,大概是因為有人把我放到一個水桶裡。
讓我肩頸毛髮直豎的是躺在抽屜角落某處的另外一張照片——這只不過是一張欣喜的父母所拍下的四乘六吋大頭照——這張照片中的嬰兒與牆上照片的嬰兒們,如出一轍。就在某處,有一張「原體」的照片,屬於那個死去的嬰孩。
這個嬰孩的媽媽複製了我們。
「妳在這裡做什麼?」蓓思從背後問我,狠狠地嚇了我一跳,害我跳起來時把肩膀撞到牆壁上。「抱歉!」她說,邊笑著。蓓思總是很喜歡嚇別人。
「我在找指甲油去光水。」我說,轉身背向照片中複製他人而來的這些臉孔。
「順便參觀榮譽榜,」蓓思說,對著照片揮手,「天哪,艾拉真是個長相奇怪的小孩。」
我咯咯輕笑,然後我們同時安靜下來。我說:「這難道都不會讓妳不安嗎?」
「哪方面?」蓓思問。
「就是說我們不……正常。」我說。
「莉琪,妳別傻了。我們很正常。」蓓思說著對我搖搖頭,「我們只不過碰巧是被複製出來,而不是用普通的方法產生的。」
「不知道耶,」我說:「有時候這讓我覺得有自卑感。」
「那妳就不應該這樣想。」蓓思繼續說:「妳是個很棒的人。不過我告訴你,如果我們繼續站在這裡呆頭呆腦地盯著小時候的照片看,還不趕快把功課做完,媽很快就要讓我們兩個感到自卑了。妳已經在她的本週觀察名單上,千萬不要讓事情更糟,我們走吧!」
我讓我自己被拉出媽的房門,一邊想著學校裡的同學會不會覺得複製人很反常,想著他們要是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知道會怎樣想?我的指甲油仍舊是擦得好好的,當我關上身後的電燈時,脖子也仍舊刺痛著。
「拿去吧!」艾拉說,她在午餐時間掏出項鍊給我。我們在門廊前,車子的引擎尚未熄火;這回我是在門口等待的那個人。
「謝謝。」我收下項鍊並戴上,一邊想著對於任何其他人來講,這條項鍊大概看來像是個傳家之寶,一個小盒子內裝著深愛親人的照片。但是這條項鍊遠遠不只於此。
「早上一切都進行順利嗎?」我問。
「是啊,還好。」艾拉回答,吐了一口氣,「課堂一如平常;我跟那個叫大衛的男生在學生會小聊了一下,」她停下來,看著我幾秒鐘才接著說:「還有……我考試拿了優等。」
艾拉寫下了教室的號碼,但是當我下午走進西班牙文三的課堂時,還是感到緊張。出於本能,我走到我們的位置上:第一排,最靠右的位置。這是我們在教室裡選擇的位置,只要那個位置是空的,我們就會坐在那裡。我們這麼做主要是出於方便——有時候如果有人生病了,我們需要彼此遞補——不過事實上我們其中之一(啊哈,就是蓓思)也是有一些妄想式的強迫傾向。
我坐到椅子上,往後靠,玩弄著髮梢,假裝自己看起來很無聊的樣子。就像其他人一樣,現在應該是我今天的第六堂課,而不是第一堂課。我試著看起來疲倦,甚至就在桑切斯老師出現時,假裝打了個呵欠。他把教師手冊大聲的丟到講台上,然後向大家問好。
「各位同學好!」他大聲的說,歡欣的神情好像我們是他在地球上最喜愛的人。他大聲擊掌了幾次,可能是想把我們從午餐後的昏睡狀態中驚醒,回到下午的課堂上。比起由我媽媽教授西班牙文,我很開心可以跟一個真正以西班牙為母語的老師上課,我還算喜歡他的滑稽風格。
「桑切斯老師好!」我大聲回應。沒有其他人回答。有一些人在竊笑著。桑切斯老師抬起眉毛看著我,微笑著。
「馬屁精!」我背後的某個女孩低聲咒罵了一句。
我沒有回頭去看是誰說的,但是我學到教訓。接下來的課堂時間,我只有在被老師點名時才回答。但是那並不意味著我心裡不知道答案,而且,跟三角函數不同,這堂課上我全部都答對了。
平心而論,伍德伯里高校是僅存少數還保留著藝術課程的公立學校,還會提供像是音樂、繪畫、陶藝、舞蹈的課程。我雖然是不太想高喊「團隊精神!」、穿著暴露的服裝,不過,我向來喜歡各種舞蹈風格。所以,從艾拉那邊交接過來的舞蹈選修課,對我來說是一個禮物。
第七節課,我充滿自信的走向體育館旁的舞蹈教室玄關,不需要停下考慮或是問路。可能是因為我曾經大老遠繞路去上歷史課,只為了順道經過這裡看看跳舞課在做什麼。謝天謝地,現在,輪到我了。
我找到二十七號寄物櫃——這是指定的——輸入我們一成不變的密碼鎖:三、三十三、十三。在裡頭,我找到一件黑色露背背心的舞衣,附有內衣襯墊;一件黑色細繩舞裙,在臀部的位置令人尷尬地印著「跳舞吧」;一件紅色的連帽外套用來遮蓋手臂與上半肩背;一雙裸色絲襪;一雙黑色已經磨合腳型的爵士舞鞋。彈指之間,我已經換好衣服,迫不急待地想和擠滿整間教室的其他同學們一起練習我剛剛跟艾拉學會的舞蹈。
「我真希望她今天會教完我們整支舞。」正當我要從寄物櫃走向跳舞教室時,一個紅髮女孩愛莉森從背後對我說。之前負責前半段時,我也曾經遇過她:每當我們在穿堂擦身而過,她總是會道一聲「哈囉」。
「就是啊。」我回答,幸好艾拉幫我做準備,「我們已經卡在中間這個段落一整個禮拜了!」
「我覺得直接跳整首舞還比較簡單,」愛莉森說:「我寧可一次學完,全部從頭到尾跳,也不要一直停下來修正每個段落。」
「一點也沒錯!」我回答她,感覺有點尷尬,但是我叮嚀自己不要忘記,雖然我覺得我不認識愛莉森,她卻覺得她認識我,「而且妳知道嗎,如果學完一樣東西之後,可以睡個覺消化一下,就會記得更清楚……」她點頭同意。「欸,我打賭她今天如果可以把整支舞教完,明天大家就可以搞定這支舞了。」
「妳真天才。」愛莉森說,帶著溫暖的笑。
「不敢當。」我笑著說,並把我一頭長髮挽到腦後盤成髮髻,從鏡牆中確認有沒有分歧的髮絲。
「上場時間到!」老師就位時,愛莉森說。
然後,接下來的四十五分鐘,我樂不思蜀。
因為汗濕淋漓,我讓頭髮繼續綁在腦後去上「創意寫作」的課程,而且我把所有的淋浴時間拿來跟愛莉森一起把整支舞──整支舞──再跳了三次。帶著跳舞的高亢心情,瑪丹娜的歌聲還在耳邊縈繞,我漫步到創意寫作課堂上,直直走向靠右邊的第一排的位置。一直幾乎走到坐在那個位置的人腿邊,我才意識到這個位子已經有人坐了。我趕緊停步,不確定怎麼做才好。我應該隨便找個空位子坐下,還是跑出去打電話給艾拉?正當我猶豫不決時,坐在我的位置上的這個男孩感覺到我的注視而回過頭。
突然間,我覺得整個房間變得非常溫暖。
「妳好嗎?」他問候了一句,笑得時候皺起額頭。我不認識他,但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感覺可以轉譯成:「瞧夠了嗎?」
他坐在座位裡用一種滑稽的方式移動著,桌子也好似漂浮起來。接著,他讓牆壁也開始出現波紋。他是怎麼做到的?我不禁好奇,但是持續並不久,因為我感覺到地面也開始變得彎曲不平。我伸手扶住身邊的桌子;我們這裡發生了地震。只是似乎沒有其他人警覺到這件事。
我聽到那個男孩問:「妳還好吧?」
我沒有回答。
因為我昏倒了。
當我幾秒鐘或幾分鐘後醒來時,我的同學們從他們的位置上看著我,有些人幸災樂禍地笑著,有些人則關心地瞧著我。我第一個想法是,謝天謝地,我今天沒穿裙子。第二個想法是項鍊,我的手迅速摸著脖子,這個禮拜以來第一次感到心上輕鬆:項鍊不在脖子上。我一定是把項鍊留在體育館的寄物櫃裡了。
「艾莉蓓?」阿莫斯老師站在我上方,關切地詢問:「妳還好嗎?」
「我還好。」我低聲說道,感覺自己像個笨蛋。我看著那個男孩從坐位中探出半個身體,現在又鬆懈下來回到座位中。
「妳確定嗎?」阿莫斯先生詢問。「妳看起來很蒼白。」
躺在地板上,看著阿莫斯先生在我上方這樣盯著我看,感覺很奇怪;我可以往上看到他的大鼻子。我準備坐起身來,一邊轉開視線回望那個男孩。
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他其實長得蠻可愛的。不過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可愛。假若分別來看他五官的各個部位,他的長相十分稜角分明。他的下巴和嘴巴有著銳利的線條;他的鼻子完美直挺地伸展到了某個點,接著好像是碰到一棵樹或是另外一個人的肩膀一樣被壓扁。他留著一頭只能稱之為斜飛機頭的髮型,就好像他側站在電風扇旁邊,但是電風扇吹出來的不是風,而是噴霧定型液。他長得人高馬大,即使是坐著也好像一座高塔,用他淺棕色的眼睛好奇地看著我。我正在想他的樣子看起來就好像夜間超級英雄在白天偽裝的另一個身分時,他開口說話了。
「她跌到地板上摔得蠻重的,」他以低沉輕柔的聲音說:「也許她需要去找布拉迪小姐。」
「說得很對。」阿莫斯老師點頭說道:「讓我扶妳起來,艾莉蓓。」他伸出他的手,接著對全班同學說:「有沒有人自願陪她去保健室找護士小姐?」
「不用了!」我說,趕緊跳起身來。我不能去保健室,否則護士小姐會打電話給我媽。媽媽就會叫我回家,準備雞湯給我喝,然後還要比三歲小孩更早上床睡覺。「真的,我真的沒事。」我說:「我上一節是舞蹈課,我跳過頭了,所以有點頭重腳輕。」阿莫斯老師皺眉看著我,所以我又加了一句:「而且我沒吃午餐。」
「好吧,那至少去買點東西吃。」他邊說邊搖頭:「妳們這些女孩子!」我不禁懷疑他是不是覺得我有厭食症之類的毛病。
「太好了!」我很快回答,「我現在就去。」
「必須有個人陪妳去,確保妳真的沒事。有沒有人自願?」他跟我一起環顧了教室一周,沒有人自願。我不怪他們,畢竟這學年度才剛剛開始幾個星期,而且我去年也還沒轉過來這間學校。確切來說,我還是新來乍到。
「我陪她去。」那個男孩自願了。我手臂的毛髮直立。
「那真是好極了。」阿莫斯老師說。雖然現在還處在有點頭暈目眩的狀態,我不禁好奇:是嗎?好極了?
阿莫斯老師寫了通行證交給我們,他說:「慢慢來。」
當我準備離開教室時,我的腿有點不聽使喚;那個男孩跟在我後面。在我們走到門廊前,阿莫斯老師繼續上課:「至於其他人,請打開你們的筆記本,準備開始一個有趣的寫作練習。我要你們寫兩頁的文字,都從『這一切都要從這隻狗開始說起……』這一個句子作為開場白。」
那個男孩低低輕笑著。當我們終於走到門廊上,我轉身面對他。
「謝謝你陪我來,」我說:「但是,我真的沒事。如果你想要的話,你可以去閒晃一下。」
「沒關係,」他用隨和的音調說著,輕飄飄地傳到我的耳朵裡,「我也餓了。」
「喔,好吧。」我說,意會過來了。我只不過是一個去食物販賣機的免費通行證。儘管如此,儘管我們才剛剛相遇,我努力克制自己因為有他在身邊而露出微笑的衝動。
我們沿著英文課堂外長長的迴廊,沉默地行走。我迫不及待想問他叫什麼名字,但是我不確定艾拉會不會已經問過了,所以我閉緊嘴巴。雖然我們不發一語,我卻觀察著每件事情:他昂首闊步的步伐;他真誠地問候零星幾個路過的同學的方式,好像他認識學校裡每個人;還有,就在他拿出他的iPhone手機滑過螢幕一會後,他笑的樣子。
「這條門廊上有一個鬼魂。」他說,把手機螢幕朝向我,讓我可以看到這個「鬼魂偵測器」的應用程式。
「你該不會付錢買這種東西吧?」
「沒啦,這是免費的,但是我買過比這個更糟的。」他說著邊替我拉開學校活動中心的門把。伍德伯里高校的建築是伸展開來的車輪狀設計,每棟大樓都以學校活動中心/食堂為中心向外擴散。
「謝謝!」我說。他點頭回禮,帶著淺笑。當我們走到販賣機前,他將iPhone放下,從口袋中掏出幾枚零錢。
「妳想吃啥?」他問,手指著一排排擺放著糖果、洋芋片、雜糧棒及飲料的架子。
「你不用幫我付錢買東西吃。」這句話讓他整個笑了開來,他的笑讓我覺得好像把奶油刀插進電燈插座裡,有被電到的感覺,不過是感覺很好的那種。
「妳把包包留在教室裡了。」
我低頭往下看,好像要是我有記得帶的話 ,我的包包會在我脖子上懸盪著。但是他是對的,我身上沒有半毛錢。「好吧,那我想要一條特趣(Twix)巧克力棒。」
「選得好。」他買了兩條巧克力棒跟兩瓶水,並把我的那一半分給我。
「謝謝。」
「沒什麼,應該的。」他說。
「嗄?」我問,我們同時拆著巧克力棒包裝,「為什麼這樣說?」
「我來不及。」我疑惑地揪著臉抬頭看著他,他澄清:「我試著要接住妳,可是卻來不及。所以我至少應該幫妳買一條巧克力棒。」
「你可真有騎士精神啊!」我忍不住笑出來。
「我能不能把這句話錄下來,然後回家放給我媽媽聽?」我們開始走回教室。
「那當然。」我還想加一句什麼詼諧的話,但卻想不出來。
我們再次安靜下來走過英文課堂外的迴廊,但是就在抵達我們教室大門前,他轉身面對我。
「妳今天看起來不一樣。」
「呃……」我不確定該說什麼。我身體僵住,手上抓著礦泉水瓶,牙齒中間搞不好卡著巧克力。
「噢。」
他停了幾秒,好像還想多說點什麼,但最後他只是對著門點了一下頭,然後走進去教室裡。我跟在後面,礦泉水的塑膠瓶已經不堪我鉗子般的緊握。我再一次感覺到慶幸,還好我沒有帶著項鍊:我相當確定我的心跳已經暴衝到逼近紅色緊戒區。當我在教室中唯一沒人的位置坐下──就在那個男孩正後方──我想著剛剛發生的事情有多不尋常。
也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終於有人注意到了。
他注意到我。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1/3個艾莉蓓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277 |
美國現代文學 |
$ 298 |
社會人文 |
$ 308 |
英美文學 |
$ 308 |
英美文學 |
$ 315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1/3個艾莉蓓
十七歲的少女艾拉、莉琪與蓓思從小一直以為她們是同卵三胞胎……直到有一天她們發現一個驚人的家庭祕密:她們事實上比親姊妹還要親——因為她們是複製人。因為害怕她們的身分曝光,進而導致身為科學家的媽媽被揭發進行人類複製而違法入獄、三個女兒被政府單位抓去研究,俾斯特一家開始過著改名換姓的生活,由「單親媽媽帶著一個女兒艾莉蓓」的生活當作掩護。艾拉、莉琪和蓓思輪流去上學、參加社交活動,她們三個人共同分享了艾莉蓓.俾斯特這個角色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莉琪遇到席恩.凱立,一個似乎能看到她最深處靈魂的男孩。隨著他們的戀情發展,莉琪發現自己並不是她的姊妹們的另一個複本;她是一個獨立個體,擁有自己的渴望與夢想。莉琪開始深入挖掘身世背後隱藏的祕密,而這個科學造就的不尋常家庭既有的平靜假象,也逐漸分崩離析……。
本書特色:
「作者派翠克運用高度浪漫愛情驚悚元素,訴說生活條件異於常人的女孩歷險記,使她的作品具有獨特魅力。這是她的第三部小說,可能也是迄今最好的一部……必定會使讀者們目不轉睛。」——美國出版家週報(Publishers Weekly)
讀者們將十分享受本書的速度感以及關於科學倫理兩難的省思。挑動人心。」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你讀過凱特.派翠克的書了沒?如果還沒,那一定要來看看。《1/3個艾莉蓓》另闢蹊徑,將身分認同、家庭之愛,以及生物倫理學等各種主題雜揉至成長小說中,還有一段浪漫迷人的青春愛情故事。」——嘉碧悠.澤文(Gabrielle Zevin),獲獎書籍《他方——少年失憶症患者的回憶錄》(Elsewhere, Memoirs of a Teenage Amnesiac)與《天賦人權》系列(The Birthright Series)作者
章節試閱
「別忘了洗掉妳的指甲油。」
媽從廚房的走道對我叮嚀這件事,就在她早上出門前的最後一分鐘。這真是目前我們做過最大的調動。諷刺的是,她竟然還敢叨唸我:她自己五分鐘前說要在我們在家上學時間開始前去寄帳單,結果馬上又回來了,因為她既忘了帶帳單,也忘了帶車鑰匙。我對她翻白眼,接著她又出門了,然後,我低頭看著我擦得很完美的白色指甲。
「為什麼妳的指甲油總是那麼快就脫落?」我皺眉問艾拉。她聳肩,她的眼睛望著房子腳下的山谷。我知道她也對於我們任務分配的調動感到很沮喪。她站起身,在離開前把她的早餐麥片碗放到水槽...
媽從廚房的走道對我叮嚀這件事,就在她早上出門前的最後一分鐘。這真是目前我們做過最大的調動。諷刺的是,她竟然還敢叨唸我:她自己五分鐘前說要在我們在家上學時間開始前去寄帳單,結果馬上又回來了,因為她既忘了帶帳單,也忘了帶車鑰匙。我對她翻白眼,接著她又出門了,然後,我低頭看著我擦得很完美的白色指甲。
「為什麼妳的指甲油總是那麼快就脫落?」我皺眉問艾拉。她聳肩,她的眼睛望著房子腳下的山谷。我知道她也對於我們任務分配的調動感到很沮喪。她站起身,在離開前把她的早餐麥片碗放到水槽...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凱特.派翠克 譯者: 楊偉湘
- 出版社: 台視文化 出版日期:2013-09-18 ISBN/ISSN:978957565996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