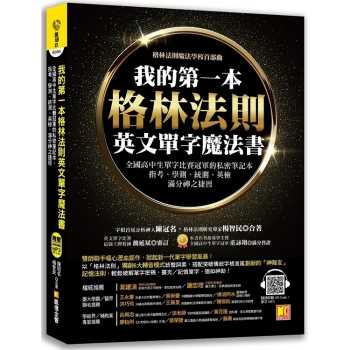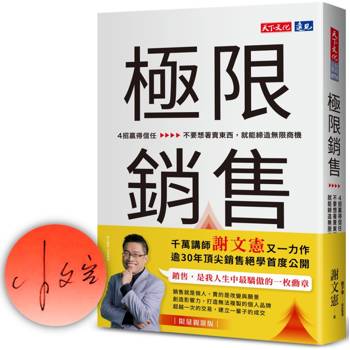導讀 ?
家的召喚與嚮往 前臺東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張子樟
「家」是一個深受作家喜愛的少年小說題材,無論是大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庭或外籍新娘家庭的描述,都會涉及到「愛」──人性中亙古不變的善的展示或追尋。許多故事中動人的描述都是家人或家族之間的互動或糾葛,繞著「愛」這個重大主題而演繹擴充。畢竟,「人間有愛」的境界是一般人所嚮往、所追求的,而「愛」的起點往往是「家」。「家」的召喚與嚮往是許多經典作品的主軸,人們在《柳林中的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早就讀到了一段作者藉鼴鼠的家對主人的召喚,凸顯「家」的魔力的動人文字。
十九世紀的苦兒苦女尋親和流浪故事一直是適合兒童閱讀的好作品。在這些闡釋「愛的追尋」的故事中,主角的冒險經歷與奮鬥過程常為小讀者帶來一些啟示及激勵的作用。這些主角的遭遇常常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他們往往必須歷經各種艱巨的考驗,才能與家人重逢,從此才能在正常家庭裡過著有愛滋潤的美好生活。當代少年小說名家艾非(Avi)的《鉛十字架的祕密》(The Cross of Lead)與《少年克里斯賓》(At the Edge of the World)也是這種類型的故事。
十九世紀中葉後期,不少美國墾荒者湧入西部,從事墾荒工作,期盼能在異鄉成家立業。這些勇者除了要面對陌生的大自然四季轉換的挑戰外,還得學會如何與當地原住民相處。這類「拓荒之旅」明確宣揚墾荒者在新土地上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新「家」。蘿拉?懷特(Laura Ingalls Wilder) 自傳型的《小木屋系列》是墾荒小說中相當受人歡迎的。她的家人懂得如何在墾荒時期自我調適、步向成長。《海狸的記號》(The Sign of the Beaver)也是墾荒故事,只是主角麥特並不是隻身前往;他父親在荒地蓋好房子後,才返鄉接麥特的媽媽與妹妹,與親人重聚是可期待的。《海蒂的天空》(Hattie Big Sky)中十六歲海蒂的故事卻非如此。
海蒂經年累月寄人籬下,不停的在親戚家之間「穿梭」進出。她對於不得不看人臉色生活感到十分厭倦,一聽到從未見過面的查斯特舅舅在蒙大拿留下一大片土地讓她繼承,加上郝特叔叔的鼓勵,她決心離開這個自己不是很喜歡的家,嘗試去找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她領悟到,原來離「家」的目的在於尋找一個更好的「家」。
對於人生地不熟的海蒂來說,在一塊全然陌生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家,是一份挑戰性很高的工作;幸好有卡爾?慕勒一家人的幫忙,加上公雞吉姆、莉菲等人的加持,使她有力氣繼續苦撐下去。她在狼點剛下火車時,把野草香味認定為家的香味。五個月後,她相信她是擁有家園的海蒂。然而天災(冰雹、旱災、大風雪等)人禍(反德人士四處放火、口頭威脅等) 不斷,她勉強苦撐了一年,最後不得不放棄。她活在艱苦生活中,在務實時刻仍保有浪漫情懷:「或許,我就是四處為家的海蒂。或許這就是我的命運,我的召喚。問題是:我的理智如此告訴自己,我的心卻完全不買帳。我的心想要有個歸宿,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最後她在離去的火車上回顧說:「在草原上的那一年,我確實找到了一個家。我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家,也在別人的心裡找到了家。」
十分巧合的,二○○七年紐伯瑞獎的三本得獎作品《樂琦的神奇力量》(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幸運小銅板》(Penny from Heaven)與本書都以小女孩為主角,這三位早熟懂事的小女孩最關切的是追尋一個更好的家。相較之下,海蒂的命運最為悲慘,因為樂琦雖然擔心照顧她的布莉琪一走了之,但她還有一個名義上的「缺席」父親;小銅板即使父親不在了,但父母親雙方的家族都真心接納她,尤其是義裔父親的傳統大家庭給她的溫暖更使她深刻體會「家」的真義。
更湊巧的是,小銅板碰到了二次大戰美國的反義風潮,而海蒂面對的是一次大戰的反德風潮,日裔移民在二次大戰期間也同樣受到歧視待遇,讀者在許多其他文類的文字中,讀到類似的描述。美國縱然堅稱是個自由平等的國家,單憑「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並不見得能澈底解決膚色歧視、族群互斥的難題。從「大熔爐」的口號出發演變為「沙拉」(不同人種各有特色地展現在同一個沙拉碗裡) 到本書所謂的「拼布」比喻(如派瑞麗說:「……拼布就像交朋友……越是不一樣的布,越是不一樣的人,擺在一起才更完美。」)美國的族群問題仍然是個有待更進一步探討與解決的問題。
作者透過詳細的蒐集與整理功夫,再以細膩筆觸刻劃出曾祖母二十世紀初在蒙大拿的墾荒經過。她的筆下不時出現令人一再回味的話語:「我的胃有如吃了一桶沒熟的青蘋果。」、「他再度握起我的手,像是握著他媽媽最貴重的瓷茶杯那般溫柔。」、「我仔細看看自己的錢包,任何蛀蟲待在裡頭都會餓死。」、「有些籬笆讓人們更親近,就像卡爾?慕勒幫我建的這一段籬笆。」、「我不但種了農作物,也種下了友誼的種籽。 」、「關懷別人比種田重要,原則比黃金重要,正確的選擇比大家的選擇重要。」這些句子足以讓讀者莞爾或深思。
除此之外,她對當時年輕一代的莫名愛國熱,也有其特殊的觀察角度,這可以在她對「我」的好友查理的描繪中看出來。從查理來自前線的信中,不難發現:他們這群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熱者,自以為有能力拯救與改造整個世界,但與現實問題面對面時,才覺察出自己的微小。這可說是種成長中的頓悟,有了這層頓悟,我們不必擔心年輕的一代是否有能力維繫這個世界的正常運作。在刻劃女主角堅毅性格、墾荒者之間的互助之餘,作者也暴露了多種人性的低劣層面,例如狂妄、歧視、貪婪等。善惡並列,讀者可從中體驗人生。
後記 ?
後記╱克比?萊森
我的曾祖母海蒂?伊尼斯?布魯克斯?萊特年輕時,曾經獨自在蒙大拿東部墾荒。聽到這件事時,我簡直無法置信。我完全不會把西部拓荒精神和這位個子嬌小、不引人注意的老太太聯想在一起。我相當感興趣,花了好幾個星期調查這件事情,想知道得更多,卻一無所獲。有一天,我湊巧找到了蒙大拿土地管理辦公室的紀錄,發現在她名下有個土地申請號碼,真是興奮極了!我到國家資料館查詢,很快就找到她的申請文件,從此開始上癮。
雖然我的曾祖母並未留下任何日記,其他的墾荒者卻有;經由圖書館交流輾轉借了這些日記(上帝保佑我們的圖書管理員和圖書館系統),我一讀就是十幾本。每個人去西部墾荒的原因都不同,但是他們擁有共同的遭遇:做不完的活兒、心痛、損失,還有──令人無法置信的──對這些艱困日子的美好回憶。
我還搞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已經開始著手寫這本書。我心想,「只要」寫一個發生在不再使用篷車、已經有汽車的時代裡的墾荒故事就好。我的研究迅速讓我明白:如果要寫一個一九一八年的故事,就必須談到當時的反德氣氛。這本書裡描寫的許多事件,都是當時實際發生過的新聞,包括艾柏卡先生碰到的暴民事件。
這本書的創作幾乎是和伊拉克戰爭同時展開。有一天,我正讀到:一九一八年,商人把德國酸菜重新命名為自由甘藍菜,立刻聽到一則新聞──二○○三年,有些餐廳把炸薯條(French fries) 改名為自由薯條(因為當年法國反對美國進軍伊拉克)。我對一九一八年的生活鑽研得越多,就在現今社會看到更多翻版。
不過,我寫這本書的初衷,畢竟是為了分享一位女性的墾荒故事。真正的海蒂離開愛荷華州的阿靈頓、前往蒙大拿州維達鎮墾荒時,究竟懷抱著什麼夢想?但願我知道。可是,她過世的時候,我只有十歲。十歲的我無法想像:那位白髮老太太的人生會比幫曾孫們烤餅乾更加精采。
我的曾祖母後來真的擁有屬於自己的農場,但我不能讓「我的」海蒂留住她的農場。大部分的墾荒者最後都破產了,鐵路公司確實做了過多的承諾,就跟火車上的胖子說的一樣。雖然真正的海蒂成功了、故事裡的海蒂失敗了,兩人卻都在蒙大拿的草原上找到無價之寶:家庭。還有什麼結尾比這更令人高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