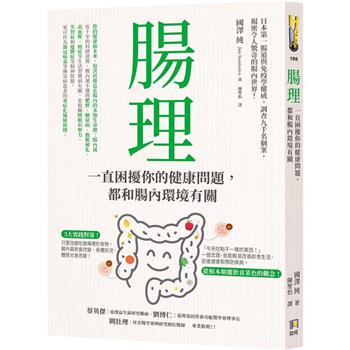因為是這樣如雜貨般堆積的人生,我每天都在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才像是真正的活著。或許要找到自己的呼吸方式並不容易,畢竟除了自己之外,有更多人正在呼吸,而他們也並不清楚該如何生活。
作為一個茶杯能怎麼想呢?如果茶杯也能想的話,那麼人應該更能想了。
每天我們在桌上移動著杯盤,白色的蕾絲鑲邊桌巾,或者綠底黃花的純棉桌布竟成了杯子一生的舞台。
就像大多數的人也看重自己的人生般,茶杯的人生也值得重視。
我們每天遇見相同的人,走進相同的埸景,正如茶杯和糖盒上繪有小熊的托盤,相互碰撞出有聲響的對話。
茶杯人說:嗨!糖盒小姐,今天的糖價如何?妳說白砂糖和黑砂糖和冰糖和咖啡專用糖。哪一種糖比較適合今天的溫度呢?
糖盒小姐說:你說的是天氣的溫度還是咖啡的溫度還是我的心的溫度還是糖的溫度還是茶杯人你的溫度呢?
茶杯人還沒有機會回答糖盒小姐的問題,一隻粗魯的手硬從糖盒裡撈出了兩粒方糖,丟進了茶杯裡。茶杯人被狠狠地拉開,遠離了糖盒小姐的視線,糖盒小姐一臉
茫然,心被掏空了一半,不知道是為了沒有結束的對話,還是身體裡忽然騰出來的空間,少了兩粒方糖的糖盒似乎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那空出來的空間用什麼來填補呢?是用寂寞還是思念?
多年如一日,茶杯人和糖盒小姐的對話始終沒有改變。
對於溫度的正解,茶杯人不能說是沒有考慮,只是沒有時間表達罷了。其實這個發問只是一個開場,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開始說話了,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掙脫粗魯的手的擺布,說出真正想說的話。
那麼他們不改的關係算是活著的嗎?有多少人是這樣活著的,每天走一樣的台步,說一樣的話,彿彷有一隻粗暴的手在操控著他們。
也許在同樣的舞台上遇見一樣的人,是讓我們每天有表達自我、了解別人的機會,今天說不清楚的,明天可以再說。在時間的演進中,微妙的關係也正在發展。
因此思考是活著的,對話是活著的,生命是活著的,想像力是活著的,自己是活著的。
茶杯人會說原來生活竟是如此簡單,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事,演出想像出來的角色。
如同雜貨堆積的人生,在不斷堆疊出自我的形像之後,生命便完成了。
這是一個有關茶杯、糖盒、調味罐、電燈泡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