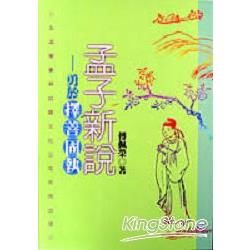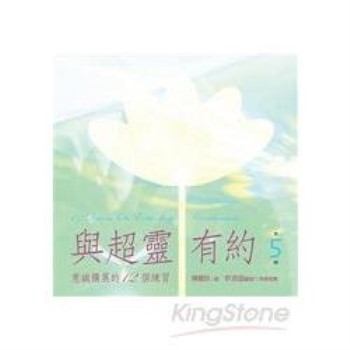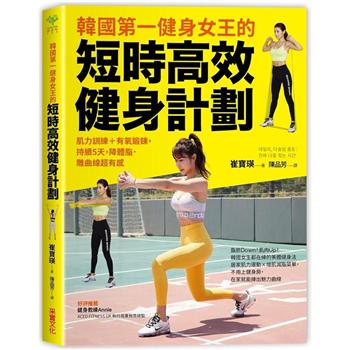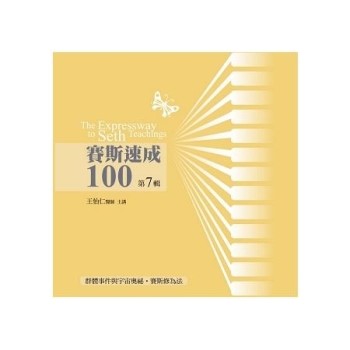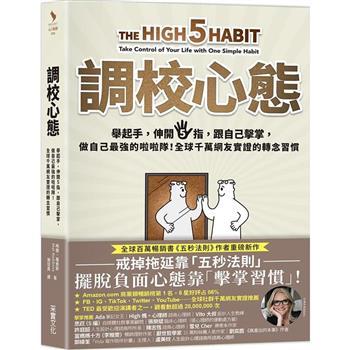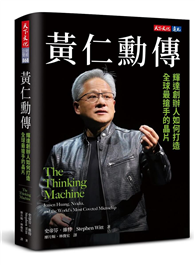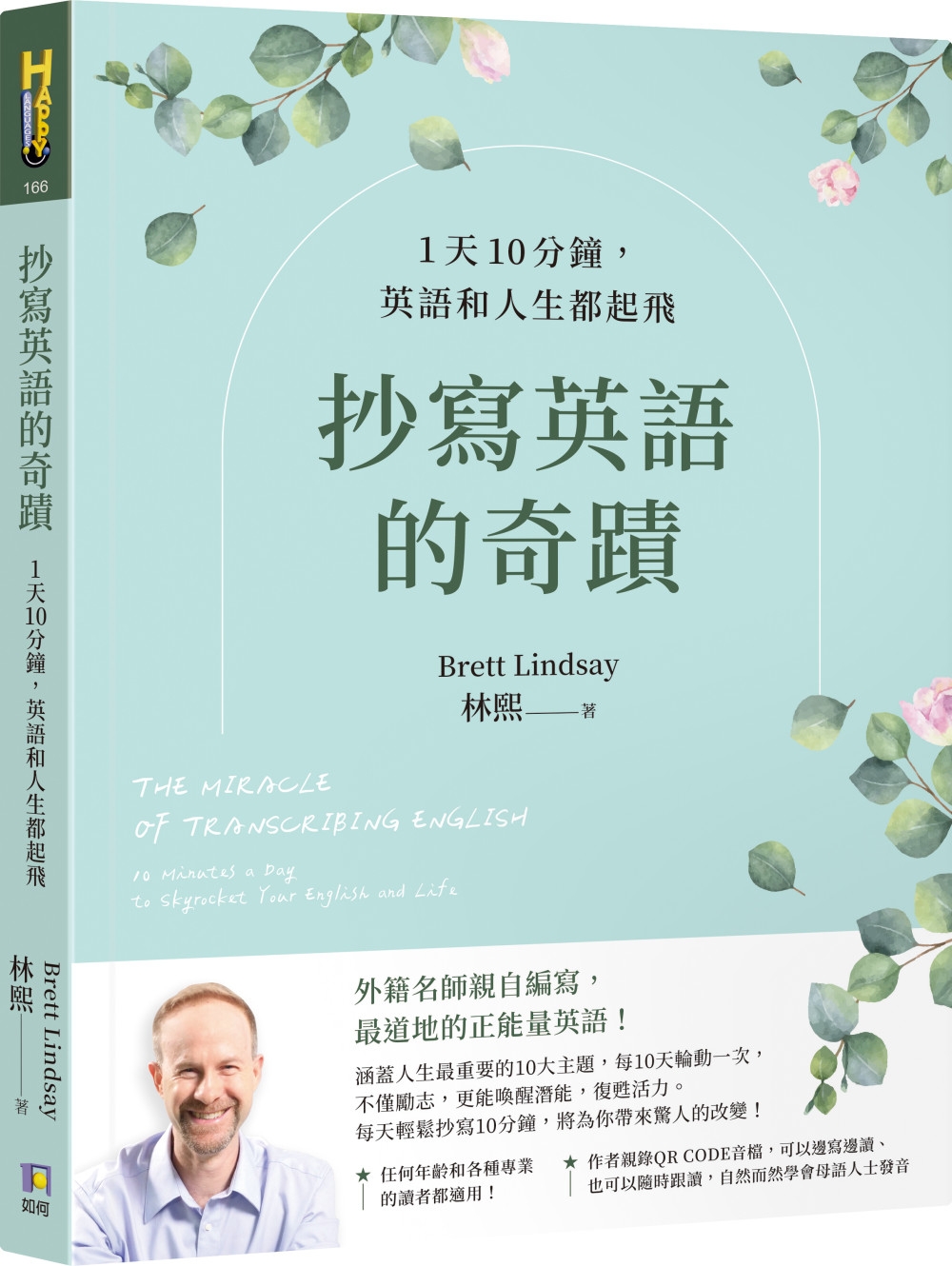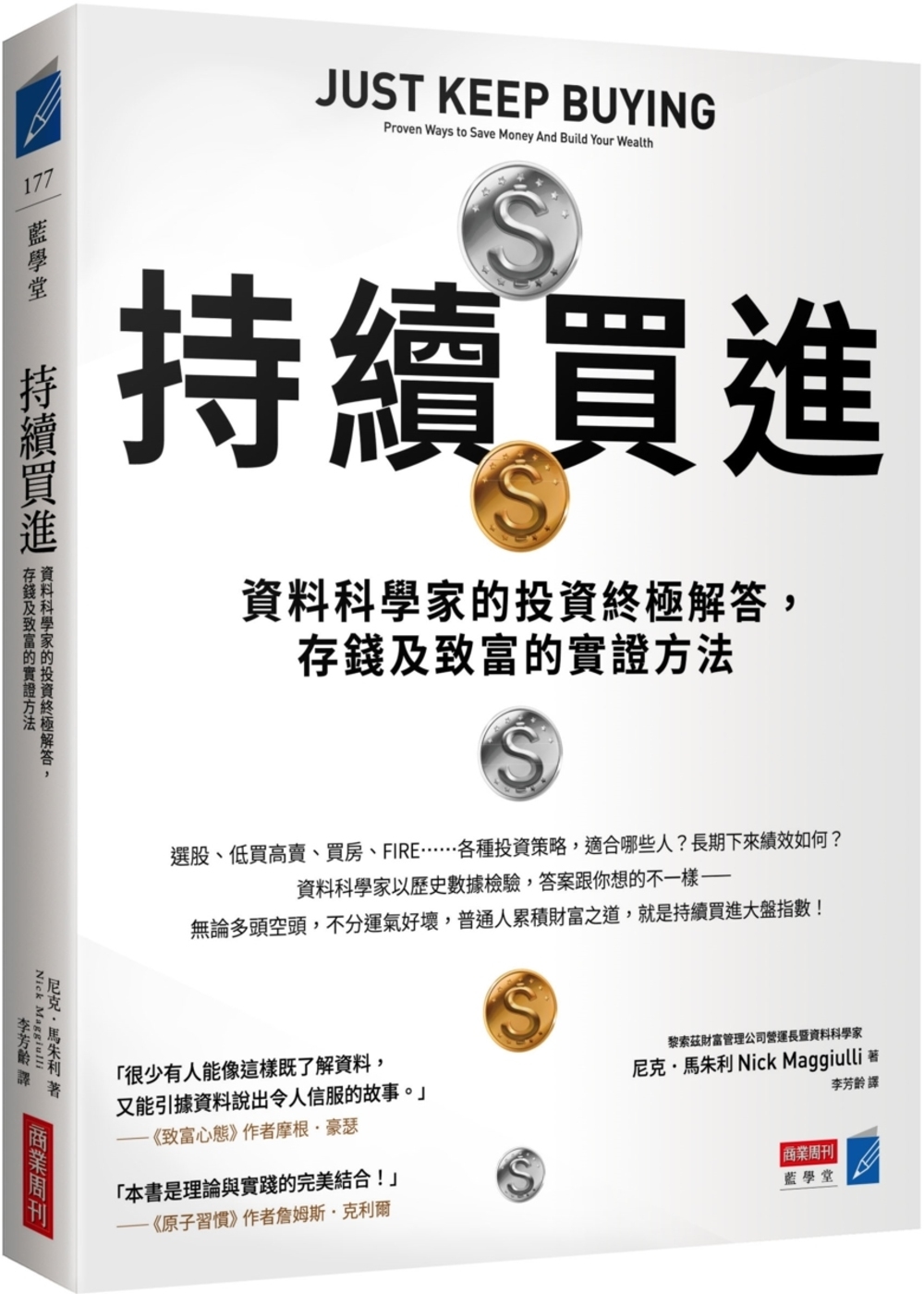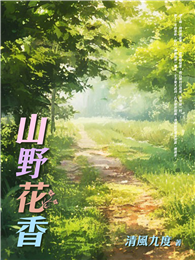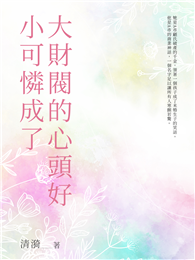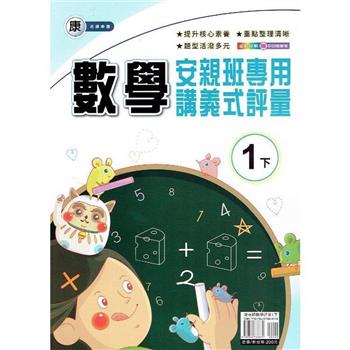擇善固執的勇氣/傅佩榮 孟子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三七二至二八九年之間,比孔子晚了一個多世紀。當時是戰國時代中期,天下的局勢更為混亂,有理想的讀書人也更為少見了。不過,讓人深感驚訝的是,孟子懷有十足的信心,以他卓越的口才,到處宣揚儒家的思想,在氣勢上頗有「一夫當關」的姿態,而在言論上則是深刻與圓融兼而有之,使儒家學說顯得更為完美。
譬如,孔子經常與學生談論「仁」,意思是要因材施教,指引學生走上正確的人生之路。換言之,「仁」字有「人之道」的含意。到了《中庸》,就明白肯定了:「人之道,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於是,「擇善固執」一詞成為儒家的處世原則。但是,有些人誤會了「固執」的意思,以為那是頑固而不知變通;同時又以為「擇善」是選擇自己所認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閉而自大的心態。幸好孟子及時出現,以他的言行做為「擇善固執」的見證。擇善需要靈活的智慧,固執有賴過人的勇氣;智慧加上勇氣,同時還以「仁義」為其核心,然後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大學》裡面所標舉的「三達德」(智仁勇),在孟子身上具體的展現出來了。
孟子是怎麼做到的呢?首先是修養工夫,以「不動心」為其初步階段,這時需要的是勇氣。他在勇於對抗與勇於無懼之外,特別推崇孔子的勇於自反;因為唯有如此,才可合乎道義的要求,並且這種要求是由內而發的,稱為「集義」。集義是不斷實踐道義的行為,最後的成果是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學習孔子而能有如此親切的體認,並且說得出其中道理的,實以孟子為主要代表。
明白孔子學說是一回事,真正在自己的時代與社會中身體力行,則是另一回事。孟子與諸侯及權貴之士的往來態度與言談立場,足以證明他是兼顧兩者的人物。他提出「民貴君輕」的說法,主張「君臣相待」不可單向而無禮,他欣賞自動奮興的「豪傑之士」,大聲為「狂者狷者」提出辯護,並且嚴厲抨擊四面討好的「鄉愿」。這些言行足以振聾發瞶。
他進而為聖賢畫分類型,認為聖人有四品,亦即清者、任者、和者、時者,讓每一個人可以依其性向而選擇效法的典型。同時他以孔子為最高典範,因為孔子在聖德之外還有與時俱進的智慧,無異於充分實現了人的秉賦,足以做為萬世師表。像孔子這樣的君子,可以做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單單是這樣一句描述,就足以彰顯人類生命既豐富偉大又高尚得難以想像的潛能了。
孟子的說法並非憑空幻想。他再度發揮分類的專長,把人生修養分為六重境界,就是:善、信、美、大、聖、神。首先是善,那是因為人性向善,所以只要真誠面對自己,就會由「心之可欲」而發現善;其次是信(真),只有自己實踐了善,才是一個真正的人;接著是完完全全實踐了善,稱為「充實之謂美」;然後,發出德行的光輝,成為大人;進而可以「化民成俗」,稱為聖人;最後則是「不可知之」的妙境,名之為「神」,亦即「天人合德」。
孟子與孔子一樣,相信「天」會主導一切,同時也接受「命」的安排。在天與命之間,則是人類實現潛能以走向完美的廣大領域。體認了此一道理,則可明白自己內在並無欠缺,而可以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儒家的快樂,其故在此。
本書根據上述理解,分為四輯,依序是:修養工夫示範,堅持人生正途,效法聖賢典範,以及辨析義理之樂。有關《孟子》原典的白話翻譯以及內容解說,請參考筆者的《解讀孟子》(立緒版)。有關孔子與孟子一系列五本簡介,至此告一段落。但願這幾本小書對於年輕朋友能有些許幫助,可以共同來品味儒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