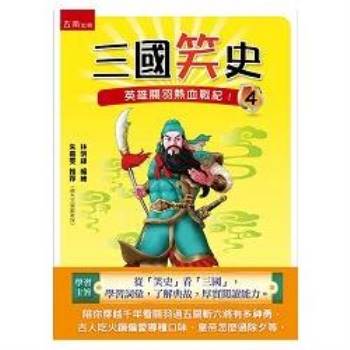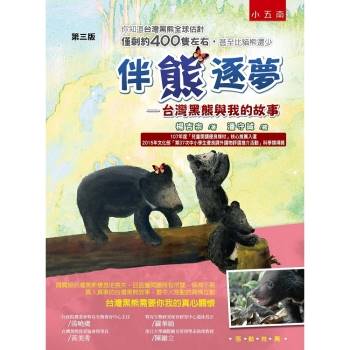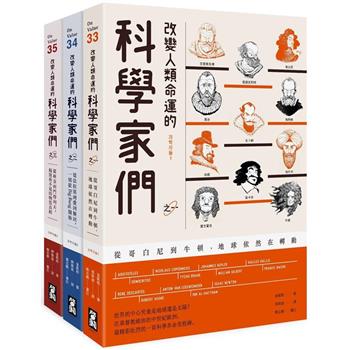一張照片
一切都是從一張照片開始。
那是民國十九年,我才十六歲。那年夏天,我考取了浙江大學農學院附設的高中──農高。和我一同考取的女同學一共只有四人,小姜、小朱、小江和我。我和小江是在入學考試時就認識了的。因為投考的女同學很少,我們又恰好在同一試場,註冊以後,我們要求編在同一寢室,自然而然的就成為好朋友了。小江是寧波人,父母仍住在家鄉,她的大哥是黃埔四期的,那時在杭州保安司令部作大隊長,家住在杭州清波門。小江每個星期六都回家,有時也約我一同去。她的嫂嫂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子女眾多,會做一手好菜。她對我也像待自己的妹妹一般,所以很快的我就拿他們的家當自己的家了。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小江正在房裡看小說,忽然聽見一個粗重的男人聲音在窗外間:「你們看什麼書?」我抬頭一看,窗外正站著一個又高又大的男人,三十光景的年齡,黃黃的長方臉,高鼻子厚嘴脣,兩眼大而有神。「看小說!」小江頭都沒抬的回答了一聲,顯然這位是他家的熟朋友。我覺得小江這樣好像不太禮貌,就對他笑了一下作為招呼,於是他問我看什麼小說。我正在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把書向他揚了一揚,他問我是不是喜歡看翻譯小說,我告訴他什麼小說都看。事實上我正熱中於小說,尤其是許多俄國小說如《罪與罰》,《安娜.克里寧娜》等都看了好幾遍。於是他告訴我如果我們喜歡看小說他可以借給我們看,他那裡什麼都有。原來他是小江大哥的同期同學,那時卻在杭州《民國日報》任總編輯,一個報館的總編輯家裡,當然有很多書的。小江聽他說要借書給我們看,興趣也來了,放下手裡的書,加入和他聊天。
果然,這次以後他每次來江家都給我們帶書來,慢慢的我也和他混熟了。他姓胡,我們叫他胡大哥,因為他的皮膚特別黑,我們又給他取了個綽號「老黑」。我們幾乎每星期都要看兩、三部小說,日子久了,他也記不清那些書是我們看過的,那些是沒有看過的,有一次就提議最好我們自己去他家挑。那個周末,我們從筧橋進城,就叫了一輛黃包車直接從車站到他家裡。
他有一個並不算大的書房,三面都是書架,只有靠右的一頭有一空處,擺著一張大書桌,上面牆上掛著一張照片,我一走進去,還沒有開始看書架上的書,就給那張照片吸引住了。那是一個青年軍官的照片,只見他身上穿著整齊的布軍裝,腿上打著綁腿,腰間束著皮帶,姿勢優美而英挺,那鑲著青天白日軍徽的軍帽下是一張極為英俊的臉,濃黑的眉毛,炯炯發光的眼睛,鼻梁高而挺,嘴脣緊閉但線條柔和而帶笑意,站在那裡整個人是那麼的生動有神。我對著它呆呆的看著,竟忘記去找書了。站在我後面的主人,看我對那照片看得那麼出神,就笑著問我說:
「你認得他嗎?」
「不,不認得。」
給他這一問,我猛然覺察到自己的失態,滿臉緋紅,期期艾艾的竟有點答不上話來了。他倒不介意我的窘態,接下去說:「他是大大有名的胡師長,你們這些小姑娘不知道他,前方的軍人可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你看過很多舊小說,總知道趙子龍、薛仁貴這些勇將吧?他在革命軍人中就被認為是這等人物。」
「報上有他的名字嗎?」
「怎麼沒有,你們看報只知道看副刊,看社會新聞,從不看國家大事,才不知道他呢!」
「你說他是師長,他看起來可很年輕呀!」
「自然年輕,他還只三十歲呢,他的升級不是一步一步升,是跳著升的。你知道,這幾年人家對國家立了多少功勞?」
「你好像對他很清楚似的,他是你的好朋友嗎?」
「自然是,不是好朋友他還會送我照片?你知道他是很少拿照片送人的。」
他顯然很興奮,也很快慰,大約他對這位胡師長確很佩服,現在看我這小姑娘對他有興趣,想趁此機會為他宣傳一番,我呢,心裡也確是對照片中人很是欽羨,我想他真是了不起的人物,這麼年輕就做了師長,聽說作師長要帶好幾千兵,夠神氣的。記得我們家鄉有一位孟明叔,是北伐軍的團長,勇敢善戰,北伐時屢建奇功,三年前他帶著太太回鄉省親,縣長發動了全省仕紳,地方團隊和兩所縣小的學生,在北門十里路外列隊相迎,說是接革命軍,我們女子小學的校長,那位胖胖的張師母,還替孟明嬸打著傘,陪著一同經過歡迎行列,她那圓圓的臉上,充分的表露出:我也有榮焉的笑意,假如這位胡師長也到我們家鄉去走一趟,縣長不知道要忙成怎麼個樣兒啦,於是我又對胡大哥提出許多問題,問他這位胡師長是什麼地方人,什麼出身……。他告訴我,他是浙江人,和我們是大同鄉,黃埔軍校第一期的高材生,剛一畢業就參加革命作戰,追隨 蔣總司令東征北伐經過了不少的戰役,因為他作戰勇敢而又很有智謀,每次作戰都得勝利,人家稱他「常勝將軍」。他剛從軍校畢業時,被分發在教導第一團何應欽將軍部下充任見習官代理重機槍班長,在棉湖之役,他以重機槍班長的身分,帶著一班人,扛著機關槍,一路前衝,衝破敵人一個陣地又一個陣地,把敵人殺得七零八落,紛紛棄槍而逃,這次戰役之後,他馬上升為上尉,接著參加北伐,一路打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打到上海他已升為第一師第二團團長,他帶著一團兵由閔行偷渡黃埔江,占領了莘莊、龍華,和上海兵工廠,進而光復上海,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遍全市,當他進入上海的那一天,集合全團官長,隨帶武裝衛士,乘坐敞篷汽車,直入法大馬路、愛多亞路、跑馬廳、南京路等熱鬧街道,繞行大上海一周,所經過的地方,人潮洶湧,民眾夾道歡呼,本來這些地方都是租界,我們自己的軍隊是不能進入的,他這一次以不可一世的聲勢,陣容堂堂,威風凜凜的長驅而入,租界巡捕,看到這威武的情景也不敢出來阻擾了。這次不但替上海的百萬居民出了一口氣,更為中華民族爭了一口氣,從此國民革命軍威震中外,全世界的人對我們都另眼看待了。
他愈說愈起勁,我愈聽愈入神,那天回家以後,一直想著那張照片上的人,以及關於他的種種故事,心裡想:假如他是我的哥哥多好。記得那次孟明叔回鄉後來看父親,父親曾拍著他的肩膀說:「孟明,桑梓以有你這樣的子弟為榮,我們老大將來大學畢業以後,我要把他送到你那裡去磨練磨練,俾便能為國家盡點力。」現在大哥快要大學畢業了,可是他是學經濟的,那裡能舉寶刀以衛社稷呢?真盼望有機會能見到這位胡師長,看看他到底是怎樣個英勇樣子。
從那次以後,我常常慫恿著小江和我去胡大哥那裡借書,順便看看那張照片,有機會就請他再講些胡師長的故事。同時也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國家大事,國內要聞。果然,「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不但常常會從報紙上發現胡師長的名字,也聽到許多人的口中談到他的種種傳奇故事了。他們說他不但會打仗,更會帶兵,他對士兵就像對自己親兄弟一般,士兵吃什麼他吃什麼,士兵穿什麼他穿什麼。行軍的時候,每到一地,士兵未入營休息他自己決不進入帳篷,士兵未吃飽他自己決不拿起飯碗的。所以他的士兵個個都十分敬愛他,能為他用命。他天生強健的體格,日行百里不覺疲勞,他雖然有馬但從來不騎,只是讓衛士牽著走,因為他不騎馬,他以下的軍官當然不好意思騎了。所以他部隊裡的馬養得特別肥。他們又說,他對士兵雖極愛護,但治軍極嚴,他的軍隊所到之處,絕對不容許有任何擾民之舉,在地方上紮營,不許對百姓占任何便宜,拔營的時候總要士兵把住過的地方打掃得乾乾淨淨,自己親自檢查,臨行時再問老百姓,他們有什麼東西被損壞沒有,如有,一定照價加倍賠償。行軍途中,如需要食用農民田裡的蔬菜瓜果,採用後一定要把錢包好放在原地。據說有一次士兵行軍太急錯過大鎮,路上買不到足夠的蔬菜,採了老百姓一畦白菜,他叫人包了二十塊大洋放在菜田上,第二天早上那白菜主人發現了,大大過意不去,因為那時候一擔白菜只值一塊大洋,一畦白菜頂多只有一擔,怎麼要這麼多錢,於是急忙追去,但他們行軍很快,已經走出五十多里,那農民趕到深夜才到達他們宿營的地方,把剩下的十九元還他,他深感這位農民的善良,好好的招待了他一番,再派快馬送他回家。由於他種種愛民、敬民的舉動,使得老百姓對他都很愛戴,大家叫他「胡青天」,只要是他的軍隊過境沒有不竭誠歡迎的。據說當革命軍北伐之初有「十不怕」的口號,就是:「不怕死、不怕險、不怕饑、不怕窮、不怕遠、不怕疲、不怕苦、不怕痛、不怕硬、不怕凍」,這位胡師長十項都做到了。
由於種種的傳聞,使我對他的印象愈來愈深,仰慕之心也愈來愈切,總希望有機會能見到他。可是,直到我高中畢業,都沒有遇到這個機會。
畢業以後我去上海念大學,大學生的生活是自由活潑的,特別是像我這樣比較喜歡課外活動的人,和男同學接觸的機會更多,但是,誰也沒有使我動心,人家說姻緣是前世注定的,也許月下老人的紅線已經把我和他連在一起了。
在我念大三的那年春天,我和綺嫂去杭州探親,一天早上,我去老師那裡,他正在樓上處理要公,叫我在樓下客廳等一下,客廳外面是個大花園,那正是百花吐豔的時候,我就倚在窗邊欣賞著園裡的景色。過了不久,聽見後面響起了腳步聲,以為是老師下來了,回頭一看,進來的卻是個陌生人,他穿著深灰色的嗶嘰中山裝,中等身材,方臉寬額,濃眉大眼,鼻梁很直,嘴形很美,面色白裡透紅,下巴青青一片,顯然是剛修過臉的。當我和他的眼光一接觸時,就像一道閃光射進我的心裡,立刻感到臉紅耳赤,心頭亂跳,同時也想到這個人好像是什麼地方看見過的,到底是誰卻想不起來了。為了掩飾我的窘態,只好又回過頭去繼續向窗外望看。他呢,既沒有退出去也沒有坐下,好像馬上就繞著客廳裡的那長方桌開始踱起方步來了。又過了好一會,當我等得有點不耐煩的時候,又有腳步聲到客廳門口,我以為這一次一定是老師了,連忙轉過身來。進來的卻是王副官。他對他笑笑,然後很恭敬地對那位客人說:「軍長,先生請你上樓去。」
「唔,好!」他口裡應著,腳步已跨出客廳,只聽見幾步樓梯聲就寂然了,我想他走樓梯一定不是一步步走上去而是越級跳上去的。他出去之後,我已無心再看風景,隨便在門邊一張沙發上坐下,感到心慌意亂地真想跑掉了。
隨後,老師終於下來了,剛才那位客人也跟在他的後面。他一進來就很高興的對我說:
「你來得正好,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然後指著那位已經站在他旁邊的客人說:「這位是胡軍長。」又看著他指指我說:「這位是葉小姐。」
等大家坐下來後,他問了我一些學校的情形以及我來杭州的事,又告訴我他中午就要去南京,因為那邊打電報來有要緊的事要他當天趕去。最後他對我說:「這位胡軍長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學問好得很,你可以多多的請教他。」然後又對胡軍長說:
「大哥,我還要上去理一下東西,你們談談吧。」說著,沒等他作任何表示就匆匆的跑出去了。
客廳裡只剩了我們兩個人,這時我已經知道來客是誰了,這幾年來原來他已從師長升到軍長,他的樣子有些像那張照片,有些不像,時間相隔七、八年,人的樣子是會變的。我覺得他的人比照片更有精神。七、八年來我一直想著他,想認識他,如今,我們終於面對面了,我將對他說什麼好呢。我能告訴他,他是我夢裡的英雄嗎?我能對他表示我私心的渴慕嗎?畢竟我已不再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而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大學生了呵。我臉紅心跳,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幸虧他倒很能掌握情況,老師一走,他就馬上移坐到離我較近的一張椅子上來,用溫和而親切的口吻對我說:
「葉小姐,聽說你現在在上海念書,念幾年級了?」
「三年級。」
「念那一系?」
「政治經濟系。」
「呵,小姐念政治,可了不起,將來一定是個女政治家。」
「哪裡,哪裡,念政治是最沒出息的。」
於是他又問了我許多學校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最容易談,也最不會得罪人,慢慢的我的心平靜下來,態度也自然了,等到二十分鐘談下來,我們已不再感到陌生。後來他說要等著送我老師去車站,問我要不要一道去,我心裡是想說「不」的,口裡卻說「是」,那時時間還早,他提議我們先去附近湖濱公園散散步,我心想裡,剛剛認識怎麼可以和他一同出去散步,正推辭間,鄭先生來了。他是認識我也認識他的,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他聽見胡軍長說出去散步的事,連忙對我說:「來,來,我們一同出去走走。」因有他同去,我也就不再推辭了。出得門來,三個人有說有笑的從第一公園一直走到民眾教育館。
那天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好日子,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鶯飛的時候,湖濱公園桃花盛開,香風陣陣,吹人欲醉,我走在他們兩人中間,有些興奮也有些迷亂,腳步有點飄飄蕩蕩地像走在雲裡,當時忽然想到小江,很盼望能在路上忽然遇到她。她知道我對那位照片裡的英雄有著一份特別的感情,假如她看見我竟真的和他在一起,將是多麼的驚喜。
一小時之後,我們回到老師公館陪他一同去車站,車站裡人潮洶湧,好像還有些部隊上車,胡軍長沒有和我們同車,我想可能他還要送別的人。車開動了,我向老師的祕書何小姐揮手送別,老師是素來不喜歡這些婆婆媽媽式的動作的,一上車他就進入他那預定的房間,繼續辦他的公事去了。
「葉小姐,我送你回去吧!」
當我看著何小姐的手帕在遠去的車窗消逝後,正轉身要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對我這麼說,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這位將軍竟又回來了。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連忙說:「不了,謝謝您,我自己回去。」他好像沒聽見我的話一樣,跟著我朝向車站出口的方向跑。我想,等到了車站門口再說吧。出得站來,前面正停著一輛黑色轎車,我想這車可能是他的,但又不敢斷定,心裡想在快到達車子時向他握手辭謝,哪知當我們走到離車子還有幾步距離的時候,他卻一個箭步跑到車旁把車門打開了,我感到很是尷尬,口裡嘰嘰咕咕的像是又說了一、兩句推辭的話,但他並不理會,只是笑嘻嘻的用他那空著的左手很自然的把我挽上了車,我想,這簡直是軟性的綁票嗎!天下竟有這種強要送客的事,雖這麼想,可是心裡卻是很快樂。
到了家門口,已是吃中飯的時候,想要請他進去吃飯,又不好意思,畢竟我們認識還不到三小時,只好謝謝他就算了。他也沒有什麼表示,只說了一聲「再見」就叫司機把車開走了。他走了之後,我又有點失悔,覺得可能自己對他太冷淡了,得罪了他。吃飯時,綺嫂問我這半天的情形我都懶得講,只說去車站送了老師,匆匆吃了半碗飯就跑到房裡關起房門,想安靜一下,使頭腦清靜一點,把那紊亂的思緒理理清楚。誰知剛進到房裡,外面的門鈴就響了。女傭來報告,外面有客要見二小姐。
他已換穿一套西裝,態度瀟灑儒雅,實在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軍人。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去遊湖或散步,我覺得有點累,不想出去,提議就在家裡談談,他也樂於接受,一談就談了幾個鐘頭;從杭州的天氣談到西湖的風景,再從西湖風景談到有關西湖十景的各種典故。原來他是老杭州,在杭高念過書的,對於杭州情形非常熟悉,雖然我也在杭州念過三年書,還自以杭州作為第二故鄉,但和他比,卻像個陌生人了。他是那麼的健談、說話的聲音和平而有力,眼睛充滿著感情,當你聽著他說話,看著他的表情,是不能不被吸引的。坐到天快黑的時候,他看看表,說是有人請他吃晚飯,才愉快地辭去。
晚上,綺嫂問我什麼時候認得這位先生的,他是什麼人,什麼地方人,我就把這一天的情形告訴她,她聽了之後,笑著說:「二妹,我看要當心,這位軍長的攻心戰術可厲害著呢!」我啐了她一口,埋怨她不該取笑我,如果取笑我,以後什麼話都不告訴她了。姑嫂倆正在談笑著,門鈴又響了。女傭進來說:
「二小姐,下午那位客人又來了。」綺嫂一聽馬上格格大笑起來,她說:「你看,這不是攻心戰術嗎?哪裡有一位普通朋友會這樣積極的?要不,他是著了我家小姐的迷了。」在平時我一定和她鬧一場的,那時卻顧不得了,只對她白了一眼,告訴她等客人走後,一定不饒她。匆匆的修飾了一下,就跑去客廳。
一看我進去,他連忙迎了上來,一邊和我握手,一邊問我:「我晚上來看你,是不是方便?」我想,你既來了還說什麼,就笑著說:「沒有關係。」於是我們又開始聊天,這一次他和我談歷史,我早就聽說他對歷史很有研究,問了他許多歷史上的問題,他都對答如流,對每一件事說來都是如數家珍,並且常常有他獨到的見解,愈談我對他愈佩服。後來我問他一些有關戰爭的問題以及對於他的種種傳聞,他卻避而不答了,他只是說:「這些都是枯燥的題目,我們還是談些有趣的事吧。」我也就不便再問下去了。那天他坐到十一點多鐘,臨走時約我次日同去西湖探勝。說定早上九點來接。
他可真是個守時的,第二天早上,當我們客廳的大自鳴鐘「噹」的一聲,開始敲打九下中的第一下時,門鈴也響了。我們一同坐車到湖濱第四公園,再從那裡僱一隻小船遊湖,我們先到平湖秋月,再到三潭印月,在那裡我們上岸去在那九曲石橋上眺望湖中景色,流連好久,才又下船繼續前進,到岳墳,上去弔岳王墓,走過跪在大門左右的秦檜夫婦石像,看見遊人對他們吐唾液,我們覺得歷史的審判確是很厲害,也是很公正的。中午我們就在岳墳附近的杏花村吃午飯,嘗了一頓道地的寧波菜。後來我們又穿過蘇堤划向西湖,裡西湖的荷葉很茂密,小船穿過,有時頗不容易,但和風吹來,荷香陣陣,划游其間,情趣無窮,情侶們通常都喜歡在這裡划船,尤其是在初夏荷花盛開的時候,遊船更多。我們上去玩了幾處名勝就往回划,回到湖濱已經是萬家燈火了。
在船上的時候,他提議次日陪我去爬玉凰山。他對於爬山似乎特別有興趣,認為奔馳於叢山峻嶺之間,呼吸著大地的氣息,比蕩漾於碧波之上呼吸著荷葉的氣息還要有意思。我雖不同意他的說法,但也很樂意和他一同去爬山。第二天一早便穿上一套輕便衣裙,在客廳等著他,哪知這次他沒有來,只派他的參謀來告訴我,他昨晚接到南京的電話,那邊有要緊公事,已經連夜趕去了。這消息使我很失望,但並不怪他,軍人以身許國,私人的生活永遠只能放在後面的。
過了兩天我和綺嫂也回到上海。那時我們住在法租界薩波塞路的一幢三層紅磚洋房裡,這是一種西歐式的建築,門口進去就是樓梯,樓梯終處就是二樓也就是正房,第一層在樓梯邊進去,像是地下室,除了廚房以外就是下房。我們用二、三兩層,二樓前房本來是父母的臥室,父母回家鄉後就用作飯廳兼客廳,二樓後房是大哥的書房,我的臥室在三樓後進,三樓前面是兄嫂的臥房。我房裡有兩扇大窗開向法國公寓的花園,園中樹木蒼翠、綠草如茵,四周種著各種花木,一年四季都有花開。我常常憑窗欣賞園中景色,春天的時候,和風帶來花香,使我的房中總是芬芳滿室,尤其是每當從外面回家,推門進去一陣香氣迎面而來,使人頓覺心爽神怡,所以雖然房間不大,我卻非常喜歡它。
大約是我們回到上海的第五天早晨,我沒有課,正靠在窗下的沙發上讀一本詩集,媽媽的丫頭阿香急急忙忙的跑進房來對我說:「二小姐,快下去,門口有一位先生要見你,他手上還捧著一盆花呢。」我想那不會是他吧?可能是他打發花店送來的。下去一看,我簡直要笑出來了,原來真的是他,直直的站在門前,兩手捧著一大盆盛開的玫瑰花,那是個綠瓷磚的花盆,恐怕至少也有十斤重吧。我想笑,前去和他招呼,他才想到把花盆放下來。我問他什麼時候來上海的,他說才到了一小時,可見他一到上海就跑到花店去買花了。我深為他的情意所感動,趕快請他上樓去坐。他問我把花放在哪裡,我看那是一株深紅色的玫瑰,已經開出三朵,還有幾朵正含苞待放,那花瓣光柔得像絲絨一般,花形極為完美,一看就知道是名種,我想擺在自己房裡,就叫阿香來拿。他卻堅持要自己捧上去,我拗他不過,只好為他帶路了。到了房裡,讓他把花擺好,就索性請他在那裡坐下。坐定後,他對我說:「你一定覺得奇怪吧?我不送你一束鮮花,卻這麼愚笨地搬來這麼個大花盆。我這樣做是有用意的,這是我送你的第一件禮物,我要它生根發達,年年開出完美的花朵。瓶花插幾天就壞了,這株花謝了又會再開,只要你勤加灌溉,她永遠會枝葉茂盛,紅花常開的。」
這真是深刻的想頭,這種誠意實在可感,我連眼淚都要滾下來了。也就很誠懇的回答他說:「呵,你的意思太好了,真是謝謝你,請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的灌溉,小心的培養,使它的花開得更美,使它的根長得更深。」聽我這樣說,他伸過手來握住我的手,半晌無言。我倆的心在這一剎那間就已經有默契了。
往後我們對這株玫瑰花很重視,不久他住在牯嶺參加廬山訓練團時,來信曾有這樣的一段:「想到玫瑰花開芳香滿室,對鏡梳妝,臨窗讀書之風神,不禁神往久之。」後來上海情況危急時,我送綺嫂轉杭州回家鄉曾把這盆玫瑰也帶到杭州,托她帶回家去,和我兒時手植的茉莉花種在一起。現在事隔二十多年,家鄉淪陷又已十多年,這株好花不知下落如何了!
那天他在我那裡坐了一會兒就提議出去走走,原來他對上海的環境也像杭州一樣的熟悉。想當年他帶領著革命軍坐著敞篷車在上海市遊行的時候,一定像凱旋榮歸一般心裡是非常愉快的。這次他帶我上外灘公園去玩了一會,就請我在南京路一家館子吃西餐,那是一個猶太人開的,以印度咖哩雞飯最為出名,他就為我們各人點了一客。飯後我們又去霞飛路的一家俄國館子聽音樂,在那裡他告訴我許多兒時的故事。
他原籍寧波,三歲喪母,由叔父母撫養,後來老太爺去孝豐做事,再娶繼母,才把他從寧波接去孝豐上學。從小對歷史很有興趣,尤其嚮往歷史上那些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在湖州中學讀書時,聞得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的事,就想前去參加,只是年紀太小又無門路,沒有辦法只有慢慢等待機會。湖中畢業以第一名被保送去杭高念書。後來又回到孝豐教書,在杭州時他加入國民黨,從那以後對於黨務就很熱心,嗣後曾去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為黨工作,所走地方愈多,對於國家的大好山河更有深刻的印象,認為大丈夫應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決不能屈居窮鄉一隅老死牖下,與草木同腐。等到聽說國父創辦黃埔軍校,扣考有志青年投筆從戎,他就決定前去投考。可是,那時的社會仍然不重視武功,一般老百姓還是相信「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舊觀念,所以老太爺他們都不贊成他去。況且他又是長子,家人以他對祖宗的責任為理由,也不願他去冒險,但是他去意已決,還是不顧一切的上路,當時身上穿著一件藍布長衫,足上穿著一雙草鞋,口袋裡只有五塊大洋,臨走時七歲的幼弟送他上路。走到孝豐城門口,他怕幼弟再走回去會迷途,堅要他回家。又因天氣熱,太陽太大,就把手上的一把雨傘叫弟弟撐回去。幼弟哭著說:「大哥,你這樣出門,沒有吃的、沒有穿的,將來怎麼辦?」他回答幼弟說:「大丈夫不能忍凍挨餓還能成什麼事業,你不要急,回去好好念書,將來做個有用的人,大哥只要有點成就,一定會回來看你的。」後來他苦撐著到了上海,問一位在上海做事的好友借了五十塊大洋,就搭船去廣東了。
當他談到這種種往事時,聲調充滿感慨。從他的故事,我對他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尤其是想到他從小喪母,孤苦奮鬥的往事更是感動得想掉眼淚,那天他當晚就回南京去了。
從那次以後,差不多有三個月的光景,他只要有空就跑來看我,有時兩、三天,有時一天,有一次還只有半天,中午到晚上就走了。他來總是約我到公園、海邊或上海附近的名勝古蹟去旅行散步,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興趣,對於大自然的愛好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我們也常常去聽音樂,但很少去看電影,因為他的時間總是那麼短促,我們捨不得浪費時間在黑暗的電影院裡。他是一個看來沉默卻很健談的人,我們在一起時可說無話不談,不過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談政治,不談他本身的職務,我除了知道他南京辦事處的地址外,對於他的防地,他部隊的情形一無所知,事實上,他每次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也是不知道的,他來看我總是突然的出現,從來沒有事先告訴我一聲的,有時我寫給他的信常常會在他來看我之後才收到,原因是他從別的地方來,而我的信是寄到南京去的。他這種行動的保密,公私的分明,是基本的特性,不但那時如此,往後二十五年都是一樣。
在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的一個早晨,他又出現我家門口,一見面就對我說:「快快準備,我們到江灣去玩一天。」江灣是海邊,是我們常去的地方之一,那裡有一家西餐館以海味聞名,我們去總喜歡挑靠海的那一面座位,坐著欣賞海上的風光。他說一個人如果能常常和海接近一定會眼光遠大,心胸遼闊的,以海的偉大海的雄壯來比,人實在是太渺小了。
那天我本來是想在家準備考試的,他既然來了,而且又提議去看海,我只好丟下一切跟他走。從上海去江灣坐汽車大約有半小時,在平時他總有說有笑的,那天他像是考慮一個什麼問題,車子開動以後就很少說話,直到我們快出市區時,他忽然拉住我的左手,看看我手上戴的古老的手表,很認真的說:
「你這個手表很舊了,該換一個新的。」
我不知道他的用意,脫口而出的笑著說:
「換個新的誰送禮呀?」
「我送。」他直截了當的說,一邊就從口袋裡摸出一個綠絲絨的長方形盒子,裡面是一個小巧的白金手表,這一下可把我窘死了,羞得從頭頸紅到額角,我說「誰送禮?」是一句開玩笑的口吻,怎麼會想到他已經預備了一個手表在口袋裡的呢?當我仍在羞得抬不起頭來的時候,他卻像哄小妹妹似的對我說:
「來,讓我替你戴上去試試看,表帶是不是太長,太長可以拿去剪短的。」這時我覺得不得不開口了,就對他說:
「我剛才是說著玩的,謝謝你,這禮物太貴重了,我怎麼好意思收呢!」他聽我這一說,以為我不喜歡那個表,用驚疑的眼光看著我說:
「怎麼?你不喜歡嗎?不喜歡可以拿去換的,請你先收下好嗎?」我不好意思再拒絕,只好把它收在荷包裡,但一路上心神都有點不安,總覺得自己的態度有點太放肆了。
到了那裡我們照例揀了兩個臨海的座位,叫了我們慣吃的菜,吃完飯,他提議我們到海灘去走走,那時已是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初夏的太陽曬得沙灘有點發燙,走了一陣,他看看左面的堤岸示意我說:「我們到那裡去坐一下吧。」沒有等我同意他已大步的向那邊走了。堤岸那頭有一個茶亭,擺著一些籐椅,是供遊客坐的,那時簡直沒有什麼人,我們坐下以後,他和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著,氣氛總有點不像平常一樣,過了不曉得多久,他忽然像下了很大的決心般的,轉過頭來,臉對著我的臉,眼睛注視著我的眼睛,溫和而堅定地問我說:
「霞,我們今年結婚好不好?」
雖然他的聲音是那麼的溫和,他的態度是那麼的誠懇,這句話之對於我卻是那麼有力、那麼響亮,使我的心像受到劇烈的震盪而猛跳。是的,這是我所最願意聽的一句話,也是我盼望著有一天會從他的口中說出的一句話,但是我沒有想到它會來得這麼快,更沒有想到它會在今天,在這一刻被提出來的。我看著他,呆呆的看著他,一時竟答不出話來,內心充滿著感情,兩眼潤溼了,眼淚慢慢地從兩頰流下來。最後我用那迷矇的淚眼看著他,向他輕輕的點了一下頭。就在那一刻,那一剎那,一對強有力的臂膀伸了過來,把我緊緊的摟住了。
回到家裡,我像是酒醉了一般的飛奔上樓,迫不及待的把這消息報告綺嫂,並請她馬上代為寫信去稟告父母,呵!媽媽,親愛的媽媽,我知道這消息會使她多麼的高興,因為她知道我的心,她知道這個婚姻會帶給我最大的幸福的。
晚上,睡在床上,回想著過去的種種,回想到我在杭州念高中的情形,回想到在胡大哥家所看見的那張照片,多麼奇妙的事,一張照片,我竟會對一張照片一見鍾情,而這種虛幻的感情竟會變成事實。我想等我們結婚的那天,我們一定要拍一張很美很美的結婚照,再把這張照片寄給胡大哥,請他把它和那張舊的照片掛在一起。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天地悠悠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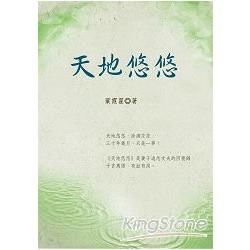 |
天地悠悠 作者:葉霞翟 出版社: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9-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8 |
中文書 |
$ 213 |
社會人文 |
$ 220 |
現代散文 |
$ 225 |
12歲以上 |
$ 225 |
中國當代人物 |
$ 225 |
傳記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地悠悠
本書由作者自述與抗日、剿匪名將胡宗南將軍戀愛、結婚、共同奮鬥,以至宗南先生逝世為止,近四十載的真實故事。文字溫婉質樸,情感真摯動人,不僅可作為散文佳作來欣賞,其中記述胡將軍的人格與事蹟,凸顯出國家動盪的時代背景,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本書特色:
1.紀錄抗日剿匪名將胡宗南將軍四十年的生活歷程。
2.本書是一本回憶錄,也是一部以真摯情感和血淚所刻畫出的中國現代史。全書沒有訓詞,沒有高調,而是動人心弦的真實故事。
3.此書是妻子追念丈夫的回憶錄,是千言萬語有血有肉一部空前的傳記。
4.最平易近人的近三十年國民革命史料,有其特殊的貢獻與崇高的價值。
5.本書文筆優美,歷久彌新,對青年人具啟發性。
作者簡介:
葉霞翟。生於民國三年,卒於民國七十年。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系碩士、博士。曾任光華大學、金陵大學教授,中國文化學院副院長,省立台北師範專科學校校長。著有《家政概論》、《家政學》及論文集《婚姻與家庭》、《主婦與青年》;散文集《軍人之子》、《山上山下》等。
章節試閱
一張照片
一切都是從一張照片開始。
那是民國十九年,我才十六歲。那年夏天,我考取了浙江大學農學院附設的高中──農高。和我一同考取的女同學一共只有四人,小姜、小朱、小江和我。我和小江是在入學考試時就認識了的。因為投考的女同學很少,我們又恰好在同一試場,註冊以後,我們要求編在同一寢室,自然而然的就成為好朋友了。小江是寧波人,父母仍住在家鄉,她的大哥是黃埔四期的,那時在杭州保安司令部作大隊長,家住在杭州清波門。小江每個星期六都回家,有時也約我一同去。她的嫂嫂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子女眾多,會做一手好菜。她...
一切都是從一張照片開始。
那是民國十九年,我才十六歲。那年夏天,我考取了浙江大學農學院附設的高中──農高。和我一同考取的女同學一共只有四人,小姜、小朱、小江和我。我和小江是在入學考試時就認識了的。因為投考的女同學很少,我們又恰好在同一試場,註冊以後,我們要求編在同一寢室,自然而然的就成為好朋友了。小江是寧波人,父母仍住在家鄉,她的大哥是黃埔四期的,那時在杭州保安司令部作大隊長,家住在杭州清波門。小江每個星期六都回家,有時也約我一同去。她的嫂嫂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子女眾多,會做一手好菜。她...
»看全部
推薦序
前言/胡為真(總統府資政)
愛、信任、不畏艱難
這本書所記載的,全部都是真實的故事和感想。雖然隨著時間的逝去,故事中的人、事、物離我們日遠,但故事的精神,仍然歷久彌新;故事所表達的情感,仍然動人心弦。 本書的作者:我摯愛的母親──葉蘋女士(本名葉霞翟),藉著敘述她與夫婿胡宗南將軍的愛情故事,把近代民國的發展,把台灣奮鬥的精神,都用樸實細膩的筆調,生動的表達了出來;而且從字裡行間,自然而然的傳達了人間極為珍貴的價值,那就是真誠的愛,長久的信任,以及不畏艱難的努力。 葉女士本人是散文家,更...
愛、信任、不畏艱難
這本書所記載的,全部都是真實的故事和感想。雖然隨著時間的逝去,故事中的人、事、物離我們日遠,但故事的精神,仍然歷久彌新;故事所表達的情感,仍然動人心弦。 本書的作者:我摯愛的母親──葉蘋女士(本名葉霞翟),藉著敘述她與夫婿胡宗南將軍的愛情故事,把近代民國的發展,把台灣奮鬥的精神,都用樸實細膩的筆調,生動的表達了出來;而且從字裡行間,自然而然的傳達了人間極為珍貴的價值,那就是真誠的愛,長久的信任,以及不畏艱難的努力。 葉女士本人是散文家,更...
»看全部
作者序
三版序
愛、奉獻、大丈夫——再續《天地悠悠》/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一)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從北伐、抗日、反共到遷台,就不幸地一直陷於動亂之中。
我自己在抗戰前一年出生在南京,次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發動蘆溝橋事變,蔣委員長正式宣布全面對日本抗戰。同年十二月發生南京大屠殺,三十萬男女老少死於日軍慘絕人寰的刀槍下。
對全國軍民,尤其熱血青年,那是一個苦難的大時代。他們的吶喊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就在那個生死存亡的年代,國家...
愛、奉獻、大丈夫——再續《天地悠悠》/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一)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從北伐、抗日、反共到遷台,就不幸地一直陷於動亂之中。
我自己在抗戰前一年出生在南京,次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發動蘆溝橋事變,蔣委員長正式宣布全面對日本抗戰。同年十二月發生南京大屠殺,三十萬男女老少死於日軍慘絕人寰的刀槍下。
對全國軍民,尤其熱血青年,那是一個苦難的大時代。他們的吶喊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就在那個生死存亡的年代,國家...
»看全部
目錄
三版序/愛、奉獻、大丈夫——再續《天地悠悠》◎高希均
前言/愛、信任、不畏艱難◎胡為真
輯一
一張照片
萬卷詩書
黎明前後
甘苦之間
再接再厲
求學問道
天地悠悠
輯二
結婚十周年
傾訴
茫茫一百日
去年中秋夜
大將軍的小故事
梅林花開
輯三
天地悠悠此生綿綿
附錄
.一部有血有淚的傳記/張其昀
.文學是人類精神糧食/陳紀瀅
.讀《天地悠悠》/馬星野
.寫在《天地悠悠》出版前/穆中南
.要作大丈夫──先父胡宗南將軍逝世三十周年紀念/胡為真
.三分之一──先父胡宗南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感言/胡為...
前言/愛、信任、不畏艱難◎胡為真
輯一
一張照片
萬卷詩書
黎明前後
甘苦之間
再接再厲
求學問道
天地悠悠
輯二
結婚十周年
傾訴
茫茫一百日
去年中秋夜
大將軍的小故事
梅林花開
輯三
天地悠悠此生綿綿
附錄
.一部有血有淚的傳記/張其昀
.文學是人類精神糧食/陳紀瀅
.讀《天地悠悠》/馬星野
.寫在《天地悠悠》出版前/穆中南
.要作大丈夫──先父胡宗南將軍逝世三十周年紀念/胡為真
.三分之一──先父胡宗南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感言/胡為...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葉霞翟
- 出版社: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9-01 ISBN/ISSN:978957574922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