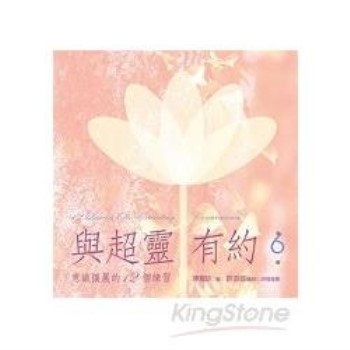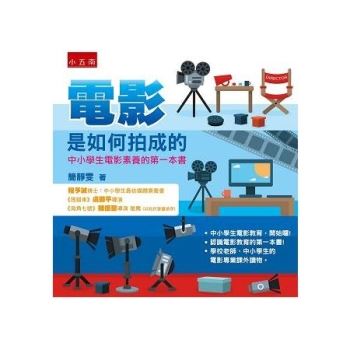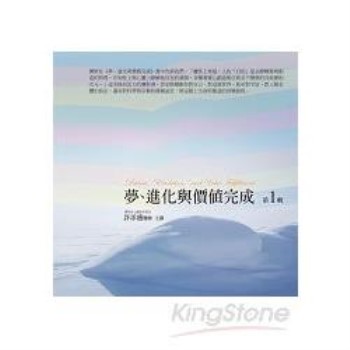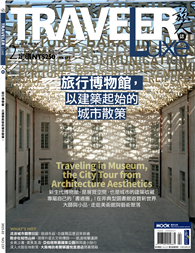芭蕉的散文隨性隨意,像水流遇上頑石,產生浪花是必然的事情。國企破產失業以後,她成了自然人,她的個人生活變得發達起來,和社會的這個隔斷恰恰給了她一個更好的瞭望位置,一個客觀的視角,一段剛好看清人生、找到自己的安全距離。有更多時間體味四季更迭,觀察一個人的心跳和呼吸。
可能一開始她沒想寫給什麼人看,只是用來解悶,或給生活來個備忘。她寫得很鬆弛,想到哪寫到哪,想寫才思奔湧,不想寫並不為難自己,沒有交換與猜忌,沒有逼仄與稱量。有的只是鮮活的個人體驗。你在讀芭蕉文字的同時首先看到的是她作為人的真實真誠和良善,只這一點就讓她撇開了那些做作、矯情、無病呻吟的寫手。這種沒有功利,娓娓道來的口語化寫作讓你倍感親切,她筆下沒經粉飾的人和物顯出原始、粗糙的質感。讀過她的文字,瑣碎、庸常、平面的生活變得明亮、濕潤和豐盈。
芭蕉筆下的人和事看起來信手拈來,仔細研讀會發現她是用了心的,一個芥菜疙瘩,一把馬齒菜,她會把它的前世今生,製作祕笈,藥用價值從裡到外來個活色生香,看完你會想這東西我也見過,原來裡面還有這麼多名堂。對於這個芥菜疙瘩,我們只是路過,芭蕉則把它切絲裝壇,捂成了一道美味。換句話說,我們的取景器是空的,芭蕉的取景器後面是長著眼睛的,所以才能在「無」中找到「有」。表面上好看的東西早已被人拿走,芭蕉給我們的啟示是如何鑿開冰面釣上魚來。
芭蕉的文字之所以有很多聽眾,原因是她寫的都是小情小事,是每天發生在大家身邊的事,觀者很容易帶入產生移情,更重要的是她的小情小事讀後你不感到瑣碎和小氣。她懂寬湯下面,知道以細微搏寬大,能做到這一點要的卻是功夫,芭蕉文字裡散落的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影子是這一切的謎底。由於她有厚重的文化打底,很多時候你會覺得她寫的是一棵蘿蔔,好像又不是一棵蘿蔔。「簡單和質樸從來都是來之不易的。」(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