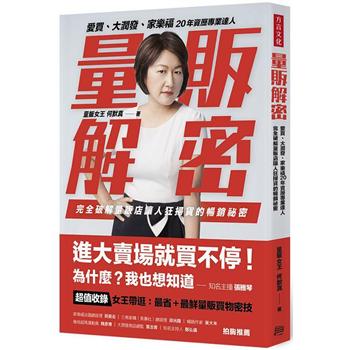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
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
——定盒詩
生命沒有寄託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特別寶貴。這種羅曼蒂克的回憶其實並不是發現了「兒時」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覺到「中年」以後的衰退。本來,生命只有一次,對於誰都是寶貴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眾的裡面,假使他天天在為這世界幹些什麼,那末,他總在生長,雖然衰老病死仍舊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業——大眾的事業是不死的,他會領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夢」的人,從這世界裡拿去的很多。而給這世界的卻很少,——他總有一天會覺得疲乏的死亡:他連拿都沒有力量了。衰老和無能的悲哀,像鉛一樣的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麼短呵!
「兒時」的可愛是無知。那時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學家和大哲學家,每天在發見什麼新的現象,新的真理。現在呢?「什麼」都已經知道了,熟悉了,每一個人的臉部己經看厭了。宇宙和社會是那麼陳舊,無味,雖則它們其實比「兒時」新鮮得多了。我於是想念「兒時」,禱告「兒時」。
不能夠前進的時候,就願意退後幾步,替自己恢復已經走過的前途。請求「無知」回來,給我求知的快樂。可怕呵,這生命的「停止」。
過去的始終過去了,未來的還是未來,究竟感慨些什麼——我問自己。和前一輩做父親的一比,我覺得我們這一輩生命力薄弱得可憐,我們二三十歲的人比不上六七十歲的前輩,他們雖然老的老死的死了,但是他們才是真正的活著到現在到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