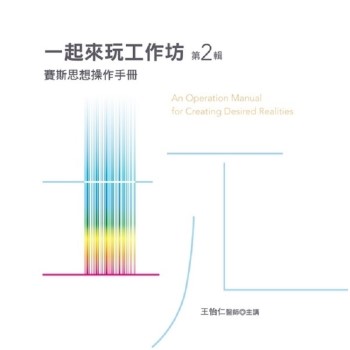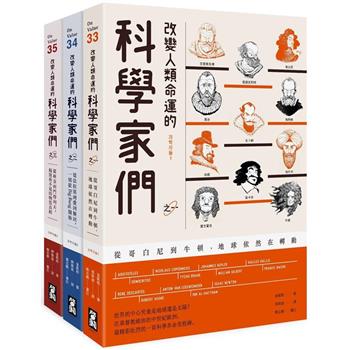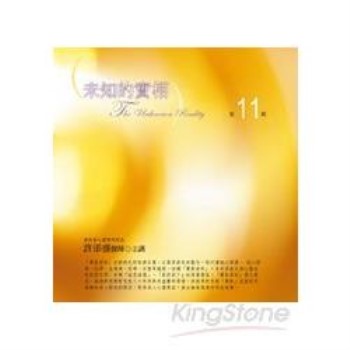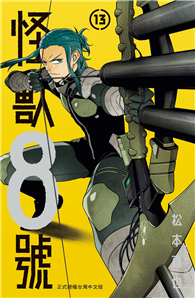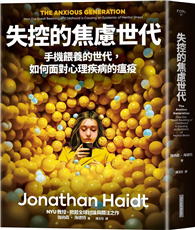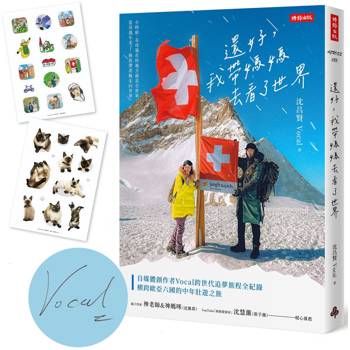如果將人的生活分成現實、智性和想像這幾個層面,詩人牧雨似乎是一個只專注於想像的精靈,他的詩中瀰漫著一種特別的迷離,特別的幻象和唯美。打開這部詩集一路讀下去,猶如跟隨一位泛靈者進行的一場浩大的旅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與人血脈相通,山川草木、蟲鳥花蝶,陽光月色等等,都被詩人的靈性一一喚醒。
對大自然的泛靈化,是萬物有靈階段沉澱於人類集體無意識中的古老基因,許多詩人在創作時都能觸摸到它。如果說美是詩歌的宗教,那麼靈性則是美的發現和呼吸。牧雨的詩歌深得其中要領,你看他寫道: 「早晨,提著雲朵的女人,走得很輕,」「昨夜,丟失的月亮在木船旁邊,等她,」 「今天很寬廣,黎明沒有尖叫/你從夢的皺紋甦醒,八月從表面分離秋意(《故事長滿葉子》)。這是一幅天人合一的畫面,詩人把童話般的顏料和人性的溫暖塗抹其中,讓人體驗到一種恍若隔世的詩意享受。這樣的詩,構成了這部詩集的主調。
詩人是大自然的熱愛者,熱愛得常常讓自己融化,主體似乎消失了。因而在這些詩中,詩人常常是隱身的。我們只看見「瘦下去的陽光」,以及「低谷安寧,螞蟻低調而嚴肅」 等等,這構成了詩人一種獨特的表現方式,他只管寫意畫夢,猶如一個精靈穿梭於大自然之中,非要寫到自己時,也只說是「薄如蟬翼的自己」(《夢境 已峻工》)。這樣的表現方式,達到了一種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對大自然這個三維空間的描述中,詩人還引入了「時間」這個維度,這使大自然流動起來,產生出讓人感懷的無限深意。在《行道遲遲》一詩中,詩人寫道: 「五月,失去水性,朝你眼神吹來/再往前一點,就是你鄉下的夏天,」 「剩下的六月還沒出生,灘塗的雨水已茂盛,」 「眼睜睜看著,天堂從潔白的瓷磚流走。」 (在《行與子逝》一詩中,詩人寫道:「十三點。一枚硬幣掉院子,很輕/輕過雨點敲擊屋頂的回聲,」「十四點。藍色纖薄,有男人淹死心海/有女人被憂慮引入陷阱,」「十五點。?姑的店鋪,稻田被和諧/水窪旁邊是果園,有趕鳥的稻草人。」 這些景物,由於時間的引入而生動,並讓人頓生感概。
從詩中可以看出,故鄉的原形是詩人熱愛大自然的原動力。故鄉的山水草本的靈性,和刻骨銘心的感情融合在一起,使詩人詩思湧動,欲罷不能。在《陽間的牧雨,今天休息》一詩中,詩人對這種情感作了生動的表現, 「四月五日,兩行清淚」, 「用雲朵取代鬥笠,坐在父親身邊/陪他抽煙。」 在這首詩裡,雲朵和雨水變了一種氛圍,詩人的愛和痛融入其中。詩人對時間和生命在大自然中的流逝有著特別的敏感,在《抒情的午後有節奏地老去》一詩中,他寫道: 「看穿一頁九月的水,念想晶瑩的光,你無權反對/欲言又止的種子,跌倒彎曲的呼喚,在模糊不清的方向。」 在《收拾 吹亂的涼意》一詩中,他寫道: 「中秋,寂靜金黃,沒有七月那麼燙手/夜沿溪蜿蜒,覆蓋魚群弄出的響動,鳥放下天空,」 「保持一手臂的距離,與低語的樹,投宿文化邊緣/夢見直立經書的身子,撲滿月光,把你喚醒。」 這樣的詩,在大自然的靈性中突顯出生命的沉重感。讓一幅幅自然的畫面有了重量和質感。
在這部詩集中,靈性的感覺和溫暖的情懷像兩條水流,始終流淌在字裡行間,有著迷離悵然之美。許多詩,單看題目就已詩意盡顯,如《從牆上再次撕下月光》、《陽光 一瘦再瘦》、《風聲 山水的道具》等等。讀這本詩集的過程,就像跟隨詩人走過一片片很美的靈性之地,在享受之餘,有一點點膩的感覺,也就是有些審美疲勞,也許是意象太過密集,在詩意上也有些重複之感吧。不斷超越對任何創造都是件艱難的事,寫詩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