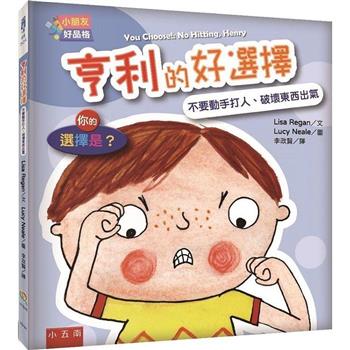初識張鏵是在四年之前,那時他還沒有「桃花詩人」的名號。我們懷化的一干文友,在黃岩開了一次筆會。
張鏵極為純樸靦腆,他在筆會上寫了很多詩,每一首都新巧而空靈,讓人驚訝於他的詩才。
第二次見到張鏵,那是在2008年會同的高椅筆會了。也還是我們這一幫懷化文友,同坐一列火車連夜趕往會同縣。
那時候他已經寫了幾首桃花詩,不記得是哪一個文友突然提到他的桃花詩,誇他的桃花詩寫得好,他就紅了臉笑著。因為當時大家正談到寫系列文章的事情,我就順口對張鏵開玩笑說:「你就寫它100首桃花詩,那也是個好系列呢!」我純粹是戲言,100首桃花詩,對我來講,那同登月球一樣都是天方夜譚。可他想了一下,卻出人意料地說:「100首,我想我也寫得出來呢!」
筆會散了之後,我們就開始各忙各的事情,誰也沒有把張鏵說能寫100首桃花詩的事當真。可他真的就開始寫起了桃花詩。一般來講,同一個題目,最多寫到二三十首,也就成了強弩之末,再無力翻新了。但張鏵似乎總能找到不同的角度,總能翻出新意來,實在讓人驚嘆。
前二天,他突然告訴我,他的100首桃花詩滿數了,他想把這100首桃花詩編成一個集子。我真為他高興,這100首桃花詩,實是張鏵之幸,也是詩歌之幸。
最美的東西,總是最脆弱,比如桃花,比如詩心,我們拼其一生,也難以護住這份美麗。也許只有張鏵,只有他保留住了那一顆未經世事汙染的童心,可以寫出最美的詩,可以養一朵桃花永不凋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