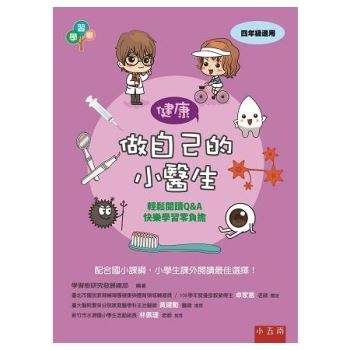我未嘗以禪者自期,亦未嘗以禪師自詡,卻由於教授禪的修行方法,並且主持禪七,故與禪門結下了殊勝因緣。自一九七九年三月以來,若將本書包括在內,我已在臺北及紐約兩地,出版了七種關於禪的中文書籍。
本書的緣起,可分作如下的四個階段:
(一)由於在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了一年多禪七活動之後,參加過的人數已有一百數十位,有人要求,讓這些人仍有適當的機會及道場,集合共修。故自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即假文化館的下院農禪寺,開始了週日禪坐會。會中由我開示,內容則以「禪的生活」為範圍。每次均做錄音,以保存資料。
(二)到了一九八二年八月,已停刊了二十年的《人生》雜誌,以小型報紙方式復刊,每期要登載我的一篇講稿,以補稿源之不足。因此由幾位年輕弟子,陸續將那些錄音帶加以整理。兩年多以來,有一大堆的草稿,送到我的手上。殊不知,我的開示,每都稱性而談,從來不擬大綱,更沒有時間蒐集資料。講話時的用辭遣語,以及次序前後,跟寫文章大不相同。故對每篇講稿的刪改補充,幾乎比另寫一篇文章還要吃力。所以每每到了《人生》的編輯部向我催稿時,才急忙趕出來。急就章的作品,不會太好。同時《人生》是從季刊而雙月刊,今(一九八四)年九月起始改為月刊,對我的需求量也不多,以致迄今為止,修改出來的稿件,僅得三十多篇。
(三)講稿在《人生》逐期刊出後,深受讀者的歡迎,好多人為了專輯我的講稿而向《人生》的發行部索取各期,甚至要求複印了寄給他們。有一家婦女雜誌,來徵求轉載講稿的同意。另有一位出版家,希望我不介意他把那些講稿輯去出版。也有許多讀者,建議我將開示的錄音帶轉錄發行,以廣流通。
(四)由於我的即席開示,資料不夠充分,組織不夠謹嚴,此類的錄音帶,當然不便流通。至於編輯出版,則覺得尚有補充修訂的必要。
這些因緣,使我上回出國之時,順便把三十多篇整理好了的底稿帶在手邊,又花了兩週的時間,重行潤色釐訂,加上這次回國期間在國父紀念館講出的一篇,終於輯成此書。
此書選收了二十五個單篇,除了〈來與去〉、〈真假禪師〉、〈世界和平〉、〈禪與現代人的生活〉、〈禪與人生〉,及附錄的〈述夢〉等六篇,是講於美國及臺北巿的國父紀念館之外,其餘十九篇都是講於北投農禪寺的禪坐會上。
此書的內容,主要是將禪的精神,貼切著現實人間的實際生活來講。一方面疏導人生的苦悶與無奈,並且指出如何達成灑脫自在、積極進取的生活目標。另一方面則分等介紹人生層面,鼓勵每一個人,都應從禪的修行及體驗中,級級提昇身心世界的品質。所以對於一般的禪修現象及其自處與處人的態度,做了分析式的說明。
此書特別注意到禪修及淨土行的會通,教理與實踐之間的調和。因不希望禪與淨土同室操戈;亦不欲見法師跟禪者兄弟鬩牆。
可知,我既寄望此書,能夠成為讀者們在人生修養方面的知音,也祈願此書是伴著讀者們共同修學佛法的益友。
限於原有講稿的格局,一定尚有好多舛誤未是之處,願讀者諸君,有以教我。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序於臺北巿北投農禪寺
日日是好日
一、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你們看過這句話吧?「日日是好日」,每天都是好天。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講: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處處是好地方。人沒有壞人,天氣沒有壞天氣,事情沒有壞事情,隨處都是淨土。那麼可以再加上「心心是好心」、「念念是好念」。「日日是好日」是雲門祖師所講的一句話,但是後來很少有人理解它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在《禪門囈語》的序裡頭用到這句話,我說:如果真正達到「日日是好日」的話,那麼我在禪七期間所講的一些瘋癲話,可以不要忘了。如果沒到達「日日是好日」的程度,那我在禪七中所講的話一定要忘掉,要不然會有麻煩。我在禪七裡講的是什麼話呢?是瘋話。什麼是瘋癲的話呢?應該是看起來、聽起來不合邏輯、不合道理的話,甚至是不合佛法的話。
前天有位日本教授到我們文化館來,看到《禪門囈語》裡有一篇心得報告,題目是〈師父是騙子〉。如果根據一般佛法講,這是大逆不道的話,怎麼可以說師父是騙子?師父騙了誰啦?如果以禪的立場來講,這種騙子愈大愈好,那釋迦牟尼佛也是騙子,而且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典,通通是「胡說」。佛在《金剛經》中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但他又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可見佛也是大騙子。
二、乖牛與笨牛
其實這個「騙」是有安慰、鼓勵、引導、誘導的意思在裡頭。小孩子不肯吃飯,母親會說:「乖乖!你趕快吃,吃過飯後,再買糖果給你吃。」小孩子吃過了飯就忘了,他已經吃飽了,還要什麼東西!所以母親對孩子也是用騙的。不單是騙,而且是哄、嚇、詐、騙。最好聽的話、聽起來最舒服的話,是哄。哄是真的嗎?當然不是。在佛陀的時代,佛看到一個人在罵人,他說不能罵人,不但不能罵人,連牛都不能罵。佛講了一個牛的故事做例子:
過去有兩頭牛,拉著兩輛車子走,一頭牛走得快,一頭牛走得慢,走得快的愈走愈快,走得慢的愈走愈慢。原因何在?原因是駕車的人不一樣。前面那頭牛走得快,因為那駕車的人對牛說:「我的乖牛,你是我的寶貝,你是我最聰明、最好的牛。我就靠你而已,你替我趕快拉,拉到盡頭,我給你好東西吃,好的草、好的糧。」等到這頭牛拉不動了,駕車的人又說:「我不相信你拉不動了,你的力氣比現在更大、更多,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牛,所以我最喜歡、最疼愛你。」於是,那頭牛又拚著老命繼續拉。在後面那頭牛就不一樣了!趕車的人老是罵牛:「你這笨牛、懶牛、壞牛、糊塗牛!怎麼老是休息,又是小便,又是大便,這麼沒出息!你看前面那頭牛,人家跑得多快!你再不走,回去以後,我把你賣掉;再不走,回去後乾脆把你殺掉!」這頭牛想,反正是死,反正是壞,反正是懶,是沒有用,於是牠就蹲下來,索性不走了。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佛法裡面,沒有一句真話,都是講這些哄的、騙的。那麼有沒有詐或嚇呢?《地藏經》中講到:你們不能做壞事;你們如果做了壞事,存了壞心,要做畜生,墮地獄、餓鬼。這是什麼?這就是嚇。禪宗祖師善用詐,詐就是詭計多端,不直接了當跟你講。譬如說,本來希望你向東走,可是曉得你這傢伙不聽話,叫你向東,你一定不向東;所以跟你說:「不要向東走,東邊最不好了,我不希望你向東邊去!」你想一想:「哼!你不要我向東邊去,我偏偏向東去!」這下子便上當了,本來就希望你向東邊去。像這種情況,在經典裡叫它作方便法。方便法不是究竟法,方便法是可以依不同的人而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同樣地希望大家向東邊去,對某甲叫他向東邊去,對某乙則叫他往西邊去,而達到的目的卻是一樣的。比如令一人自臺灣向東走,令另一人自臺灣往西走,最後這兩人可能是在美國的紐約會合。這就是詐、騙。
三、魚在天上飛、羊在海底吃草?
比如「魚在天上飛、羊在海底吃草」,這是沒有意思的話,是不可能的。有時候我說:最高的地方是海底;最深的地方在山上。這是不是相反呢?就常識而言,這是沒有道理。可是,講道理會使你頭腦想得更多。為了叫你不要講道理,祖師們講瘋話,甚至講逢佛殺佛。有的祖師講,念一句佛要漱口三天。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你能達到「日日是好日」的程度,你就可以體會到這些話的真義。「日日是好日」是心中沒有分別,沒有你我、好壞、大小、長短、男女等,這些相對的全部都沒有。那麼是不是有統一的、絕對的呢?統一的時候如果覺得統一了,那麼統一的本身還是分別心。真正的無分別心,是沒有矛盾,也沒有統一。如果執著於統一,表示在統一之外,還有矛盾。自以為:我是在無分別、沒煩惱這一邊,其他的人則是有分別、有煩惱;別人無智慧,我有智慧。
一般宗教、哲學,大致上在追求一個理想,追求超越現實,追求超越我們平凡世界的一個境界。所以有神的世界、有人的世界;有戰爭的世界、有和平的世界。大家追求和平的世界,反對戰爭的世界;又追求聖和靈的世界,希望離開凡夫或人的世界。這是哲學、宗教上的二分法,就是希望從人間、現實的超出,而達成一種理想,或者是從我們的現實生活得到解脫。像這種情況,永遠是追不到的,永遠是沒有的、虛幻的,永遠是假的、不可能實現的。這好比一條狗,背上綁一根桿子,桿子上掛一塊肉,狗要吃這塊肉;狗在跑,知道有一塊肉在牠前面,可是永遠吃不到它。為什麼吃不到?因竹桿子綁在身上,狗跑,竹桿子也被狗帶著跑。所以要追求一個統一的、永恆的、聖靈的,或者是理念的、理想的境界,那是永遠不能實現的。耶穌說天國已經快降臨了,其實天國永遠不會來;如果天國是永恆的,永恆的便不會有來與不來的區別。再說我們所講的無分別心,到達無分別心的時候,現實的世界就是理想的世界,理想世界和我們的現實世界不分,煩惱本身就和智慧一樣,我們凡夫的生活和聖人的生活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就看你的心是不是平了。如果心很平、很穩、很實在,那麼一切本身都是好的,沒有什麼不好。如果自己的心常常在動,那麼一切外在的現象,通通是扭曲的了。
指與月
「以指標月」,在佛典中是一個常用的比喻。
我們至少可以在《楞伽經》卷四、《楞嚴經》卷二、《圓覺經大疏》卷二、《大智度論》卷九、《往生論註》卷下等諸經論中,見到「指月」的比喻,這是將佛所說的經教,及經教所示的義理,比作指與月的關係。如《大智度論》云:「如人以指指月,以示惑者,惑者視指而不視月。人語之言:我以指指月,令汝知之,汝何看指而不視月。此亦如是,語為義指,語非義也。」
語言文字等的符號,是用來標示或表達義理的工具。若藉語文經教得到了佛所表達的義理,便可得月忘指,得魚忘筌,經教亦成為無用之物。所以禪宗祖師,有稱看經為遮眼,有視三藏教典為拭瘡疣紙。
今天,我借這個指與月的比喻,就禪的修行者的修證過程,作如下的討論。
用手指指月亮給人看,這必須有主、客兩體,一個是指月亮給人看的人,就是老師;一個是需要人指月亮給他看的人,就是學生。也就是師徒之間通過手指的動作而達到教人和受教的目的;然而教人和受教的目的本身,並不是手指,而是月亮。
為什麼不直接叫人看月亮呢?因為要看月亮的人,根本不知道月亮是什麼樣子,他也不知道東、西、南、北和上、下的方位,因此需要老師用手把月亮指給他看。老師用種種方便善巧,教你參話頭、參公案,便等於是把手指讓你看。你先看手指,再看這手指指的方向,終於循方向發現了被喻為月亮的自性清淨心,或空性的智慧心。
一、不見廬山真面目
一開始修行的人,當他看到老師的手指,心想,喔!老師的手指是粗的或細的,膚色是黑的或白的。這時他對於手指的作用何在,尚不知道。於是老師叫他不要老瞪著老師的手指看,而是沿著手指一節一節往上看,結果手指尖上面沒有東西,老師說不是看手指尖,而是看指尖所指的最遠方。可是師生所站的角度不一樣,所看到的方向或有偏差;於是老師只有一次一次地修正學生的錯誤,學生也一再地矯正所看的方向,最後終於看到老師所指的那個東西──月亮。
這過程是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修正再修正,考驗再考驗;當然,對於根器猛利的人不需要如此地大費周章,老師只要手一動,學生就立刻見到老師所指的東西。只是這種一點即破的情況難得遇到,除非千里馬遇到伯樂時,所以禪宗只用間接的方法指導人修行,只能用手指標出月亮的方向,沒有辦法直接拿月亮給人看。
很多人求悟心切,希望老師一開始就把月亮從天際摘下來往他面前一擺,說:「你們看,這就是月亮。」可惜老師做不到;因為月亮是佛性的比喻,佛性即空性,沒有具體的形相,不可以言宣,不可以意會,必須你親自去體驗。
有些人認為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方法,見到月亮就是見性、開悟;於是認為手指有,月亮也有,只是在看到月亮以後,忘掉手指,此所謂得月忘指。其實,《心經》中說「無智亦無得」,若在悟後仍有從悟境所得的一種具體的東西,那就不能算是開悟了。真正的開悟,不僅忘掉手指及所指的方向,也忘掉有月亮這可見的目標物,那時你就是月亮。一切的一切,都是月亮的本身,你的自我不見了,月亮當然也不見了。如果尚有月亮可見可得,你與月亮仍是對立的,統一的大我境界尚談不上,何況是解脫自在?諸位可能會發生疑問:修行禪的人是不是要開悟、見性呢?見性以後,是否有個性在那裡?答案是肯定的。不過在沒有見性以前,這性的概念是有的,當你見到了性以後,這個清淨的性就沒有了。性即實相,實相是無相的。
以上所講的,是「指與月」的概論,下面再以三個層次予以剖析;第一,在日常生活中;第二,在精進修行之時;第三,修行成就以後。
安心
二祖慧可(西元四八七─五九二年)見初祖達摩斷臂求法的故事,膾炙人口,千古傳頌;從《景德傳燈錄》所見的一段對話是這樣的:神光(慧可原名)長立雪中經夜,積雪高過膝蓋,達摩問:「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神光答:「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達摩說:「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神光為表明心跡,立即拿一把利刃,將自己的左臂砍了下來,達摩便說︰「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故為更名慧可。慧可又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摩說:「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接著慧可又問:「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摩說:「將心來,與汝安。」慧可找了半天,拿不出他的心來,便說:「覓心了不可得。」達摩說:「我與汝安心竟。」
此故事發生的年代是西元五三二年。《景德傳燈錄》所載的神光立雪斷臂之說,近代學者以為不是事實,求安心之說則頗有根據。在此同時,也有人講到「安心」二字。據敦煌文獻所載,僧稠禪師(西元四八○─五六○年)的〈稠禪師意〉問答,便有:「大乘安心,入道之法云何?」曰:「凡安心之法,一切不安,名真安心。」又說:「夫安心者,要須常見本清淨心。」這是他對大乘禪法的意見。敦煌文獻又載,四祖道信禪師有篇文章的題目,即是〈入道安心要方便門〉。其中說到:「識無形,佛無形,佛無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僧稠禪師涅槃二十年後,道信禪師才出生,兩人都講到關於「安心」的問題,這是早期的禪宗史上對「安心」問題的記載。
「安心」,可分三個層次。
一、不安心
第一個層次是不安心。這又可分為粗、細兩個層面來講:
(一)粗層面的不安心,就是心不安寧,當你處在恐懼、憂慮、焦急、緊張、興奮之中,即是心不安寧。如今的時代是個競爭激烈,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社會經常處於政治、經濟、軍事的壓力之下,尚有社會治安、交通事故、環境汙染等的威脅,隨時都會使得人的生命、家庭和財產毀於一旦。佛陀早已訓示:「世間無常,國土危脆。」自古皆然,而在今日尤為敏感。
(二)細層面的不安心是為修行的問題。今天有兩個人問我有關修行方面的問題,其中一個問:「念〈大悲咒〉、念佛、打坐,哪個好?」我回答他:「你認為哪個好,就選那個好了。」他又問:「我用這些方法修行時,沒有一法能使我沒有妄念,怎麼辦?」我說:「妄念沒關係,不管它。」他說:「我就是希望用種種方法來克服我心理的不平穩和矛盾,才修行的。」我告訴他:「你是應當修行的,但不是為了克服心理的矛盾或不安定。」另外一個人問:「聽說了生死得解脫一定要參禪,沒有他法,是不是?」我回答:「不一定,參禪的人不會參,也不能了生死得解脫。」他問:「那怎麼辦?」我說:「了生死的方法很多,看你用什麼方法。」他說:「那我應該用什麼方法?」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你應該用什麼方法,要開始學習以後,慢慢地跟佛法有接觸,才知道你應該用什麼方法。」
這兩位代表了許多初學佛者的不安心,不是為了生命、生活、家庭、財產的問題,而是考慮到出生死、證菩提等的問題。
二、安下心來──如何安心?
第二個層次:安下心來──如何安心?
(一)普通生活中如何安心: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面對一切的問題──生活、家庭、生命安全、解脫生死等等問題,這些問題時刻縈繞心頭,無法安心地過日子。對修行人而言,這會造成阻礙,因此必須破除身見,破除對身體生命的執著。
現今的工商社會,人人皆汲汲營營於物欲的競逐,倫理淪亡,親情淡薄,家庭組織沒有安全感,離婚率愈來愈高。一對年輕男女準備結婚的同時,也準備著離婚,甚且已開始擔心未來孩子的教養問題,以及離婚時,孩子屬誰的問題,夫妻之間沒有「生同羅帳死同穴」的同生共死的心理準備。很多家庭,更因父母鎮日忙於事業及交際應酬,對兒女疏於管教,而產生許多問題青少年,給社會帶來許多困擾。因此,要挽救家庭,必須從個人自己做起,每個人都盡到了家庭一分子的責任,便能達到「父慈子孝、夫婦和睦、兄友弟恭」的和樂境地。
另外,死亡是人類最恐懼的事了。在混沌初開、茹毛飲血的草昧時期,人類的生命即飽受威脅,要防洪水、防猛獸,跟大自然搏鬥、求生存。接著進入文明社會,又由於利害的衝突,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殘殺,宗族與宗族、部落與部落、種族與種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紛爭頻仍,戰禍綿延。
以個人的生命來說,從出生到死亡,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有絕對的保障,可能生病,也可能因意外而死。「人命危脆,在呼吸間」,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能夠坦然地接受它,也就不必擔心生命的安危與否了。只是在未死之前,一定要設法生存下去,不能自殺,否則就違背了佛法的因果關係。另外一層,如果怕死,也可以藉著努力修行,改變宿業,把壽命延長;而真正的修行者,對死亡是不會恐懼的。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禪的生活(第3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210 |
禪修 |
電子書 |
$ 210 |
佛教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佛教 |
$ 270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禪的生活(第3版)
禪的生活,就是在矛盾中求統一,
在來與去之間超脫自在。
本書將禪的精神,貼切著現實人間的實際生活來講。
藉以疏導人生的苦悶與無奈,
指出如何達成灑脫自在、積極進取的生活目標。
並鼓勵每一個人,都應從禪的修行及體驗中,
級級提昇身心世界的品質。
──聖嚴
作者簡介:
聖嚴法師(1930〜2009年)
聖嚴法師1930年生於江蘇南通,1943年於狼山出家,後因戰亂投身軍旅,十年後再次披剃出家。曾於高雄美濃閉關六年,隨後留學日本,獲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75年應邀赴美弘法。1989年創建法鼓山,並於2005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
聖嚴法師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暨國際知名禪師,曾獲臺灣《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著作豐富,中、英、日文著作達百餘種,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總統文化獎及社會各界的諸多獎項。
聖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主張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推動全面教育,相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文理學院、僧伽大學等院校,也以豐富的禪修經驗、正信的佛法觀念和方法指導東、西方人士修行。
法師著重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陸續提出「心靈環保」、「四種環保」、「心五四運動」、「心六倫」等社會運動,並積極推展國際弘化工作,參與國際性會談,促進宗教交流,提倡建立全球性倫理,致力世界和平。其寬闊胸襟與國際化視野,深獲海內外肯定。
TOP
作者序
我未嘗以禪者自期,亦未嘗以禪師自詡,卻由於教授禪的修行方法,並且主持禪七,故與禪門結下了殊勝因緣。自一九七九年三月以來,若將本書包括在內,我已在臺北及紐約兩地,出版了七種關於禪的中文書籍。
本書的緣起,可分作如下的四個階段:
(一)由於在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了一年多禪七活動之後,參加過的人數已有一百數十位,有人要求,讓這些人仍有適當的機會及道場,集合共修。故自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即假文化館的下院農禪寺,開始了週日禪坐會。會中由我開示,內容則以「禪的生活」為範圍。每次均做錄音,以保存資...
本書的緣起,可分作如下的四個階段:
(一)由於在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辦了一年多禪七活動之後,參加過的人數已有一百數十位,有人要求,讓這些人仍有適當的機會及道場,集合共修。故自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即假文化館的下院農禪寺,開始了週日禪坐會。會中由我開示,內容則以「禪的生活」為範圍。每次均做錄音,以保存資...
»看全部
TOP
目錄
自序
時空與生命
日日是好日
禪詩與禪畫
矛盾與統一
老鼠入牛角
自力與他力──禪與淨土
宗通與說通──禪與教
來與去
真與假
本與末
正與邪
指與月
知與覺
真假禪師
事與心
鍛鍊心
無心
安心
無有恐怖
道不在坐
放下萬緣
世界和平
禪與現代人的生活
禪與人生
附錄:述夢
時空與生命
日日是好日
禪詩與禪畫
矛盾與統一
老鼠入牛角
自力與他力──禪與淨土
宗通與說通──禪與教
來與去
真與假
本與末
正與邪
指與月
知與覺
真假禪師
事與心
鍛鍊心
無心
安心
無有恐怖
道不在坐
放下萬緣
世界和平
禪與現代人的生活
禪與人生
附錄:述夢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聖嚴法師
- 出版社: 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ISSN:978957598755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