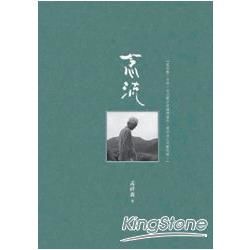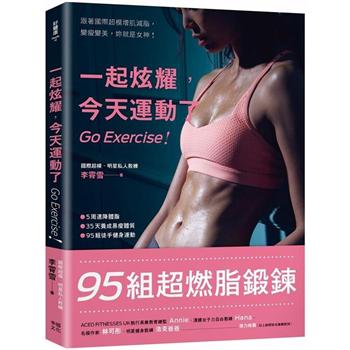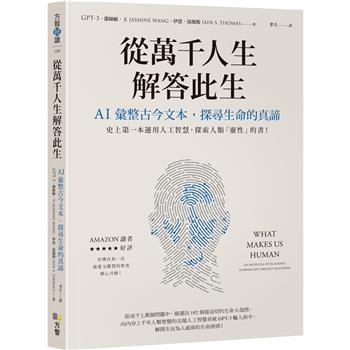當你動了念時,這念便日夜纏繞著你,
使你為之所繫所縛。
作者多年來,出門時,口袋裡總是帶幾張紙、一枝筆,心裡那些摩摩挲挲的念頭一旦形成一個什麼句子的時候,就把它記下來,回到家裡,那紙片就放在桌上,或塞到一個什麼盒子裡。
這些隨筆在謄抄和刊登時,都是未經分類的,摸到哪一張就抄哪一張,可抄的就抄,不可抄的就燒掉。因為對作者來說,其實生活和意念本就是如此交雜的。
※特別收錄: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黃崇憲〈缺席的在場—追憶生活者孟東籬〉
「用一般的看法來衡量孟東籬,錯了,他是非常特殊、非常另類的,要用新的、不同的哲學來看這個人,才能給孟東籬一個正確的詮釋。老孟是屬於山水的、是屬於海洋的、是屬於女性的,也是屬於詩的。」——詩人 瘂弦
「簡約的哲學類似於藝術的創作,都在試圖以最少的表現承載最多的意義。老孟用實際的生活展示了他對人生終極關懷的解讀。」——南華大學專任副教授 明立國
「老孟是我們這個時代特立獨行的人,致力於把日常生活的時時刻刻變成是存有的,感受四季的變化,為春天的到來而欣歡,他書寫,他傾聽,他真正體驗著自己,把生存美學貫徹到生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黃崇憲
王智章、朱天文、朱志學、朱增宏、江日新、何新興、呂學海、李日章、李寶蓮、孟子青、孟心飛、孟瀋之、明立國、林安梧、林倉鬱、林麗雲、洪米貞、紀淑玲、奚淞、徐錫鈺、曹又方、陳大威、陳念萱、陳素香、陳鼓應、黃怡、黃崇憲、瘂弦、齊淑英、蔣素娥、蔣勳、韓良露、藍山靈、羅文嘉、蘇南洲。——攜手懷念.推薦
作者簡介:
孟祥森
筆名孟東籬,一九三七年生於中國河北省,一九四八年來台,就讀鳳山誠正小學,一九五七年考上高雄中學,後進入台灣大學哲學系、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曾任教於台灣大學、世界新專、花蓮師專。
自一九六七年到二○○五年止,孟祥森先後翻譯《齊克果日記》、《沈思錄》、《異鄉人》、《如果麥子不死》等西洋文、史、哲、心理、宗教書籍共計約八十二本,譯作品質與數量為當代少見。
早年以漆木朵為筆名,發表《幻日手記》、《耶穌之繭》。一九八三年起,轉向生活札記體寫作。共計出版《萬蟬集》、《濱海茅屋札記》、《野地百合》、《念流》等十七本自然及禪學著作。
曾在花蓮鹽寮海邊築茅屋而居,被認為是台灣實踐環保生活的作家代表。孟祥森一生特立獨行,具體履行其倡導的愛生哲學,蔣勳曾以「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一個—台灣在生活裡完成自己的哲學家」稱之。
一九九七年,移居台北陽明山平等里磚屋。二○○九年九月,罹患肺腺癌辭世,享年七十二歲;「那花,就那樣兀自開著」,是孟東籬為自己一生,所下的最後註腳。
章節試閱
比賽
人的才華和人的智慧本來都可以是存於天地之間、「唯我獨尊」的(註:佛誕生之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它之所以唯我獨尊,並非它賽過天下,而是由於它是外於比賽的,它的尊貴是越乎比賽的。
高貴的東西一加入比賽,立即就遭到褻瀆、污染,被人作踐。
我們無法想像佛陀參加比賽,孔子參加比賽,耶穌參加比賽。
一個孩子,健康的,快樂的,在父母眼中好看的,如果去參加兒童健美比賽,會突然在他父母眼中、親友眼中,甚至他自己眼中(如果他意識到)變得可疑了,──他真的是那麼健康嗎?真的是那麼可愛嗎?
本然在天地之間「唯我獨尊」的生命變得疑心了,自卑了,虛妄的自傲了。如果敗,他變得不當的自卑;如果勝,他變得不當的自傲。總之,他不要是原本的「他」了。他變成了跟他自己分離了的東西。
「雄心退捲,
俯仰無言。」
有一天,一位好友寫的八個字。
年輕人在我們所認為不能有詩意沉醉的地方都能有詩意沉醉──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心是開的,而我們的心卻鎖閉了,因為他們以環境的現有樣子來接受,我們卻一直在批評,在排斥。──這是心靈老化的現象。
了解心靈,了解宇宙,是人的心靈感到最深邃、最蠱惑的兩件大事。
人的心靈顯然有強烈的自戀。
其實,說不說自戀是沒有什麼特殊意義的;事實是人被自己的心靈所吸引。
其實,他本應被自己的心靈所吸引,這是宇宙的力量被其本身所吸引。
所謂澄靜,就是你的心澄靜下來,動作和緩下來,心隨著動作,而每一處於運用中的官能都活起來、復甦起來;你的手開始親切的撫摸每一樣東西,渴望著把它們擺得好好的。你對樣樣東西都產生了一種愛憐,感到它們是永恆的一部分,而你明日即將逝去……
有些人很有頭腦,卻缺乏「心靈」,而頭腦過於發達或運用過多,似有使心靈萎縮之虞。
心靈生活的絕大努力(如淨土宗)都在殺心。就像英文的to kill time一樣。畢竟心這種東西是很可怕的。
這即是金剛經所說「降伏其心」。
焚香,沐浴,以用心智,這種態度畢竟是對的,因為天下之器,又有什麼比腦更偉大、更浩瀚、更神聖呢?
也許人對人的了解,本身就是目的。
這是一切自我探求的原始解釋。
做為一個人,最大的尷尬之一,是每天早晨醒來都要重新去肯定他生命的意義,重新去肯定他生活與工作的意義。
幸福的意義很難確定,但就精神上而言,可以說是一種沉醉。
沉醉於情,沉醉於美,沉醉於音樂,沉醉於工作或創作,沉醉於內在的清明……
人為什麼要求誠實?因為誠實接近生命。就如同把腐肉刮去,以便新的生機得以生長。
想念,是一種最與永恆相通的情感。它的根在靜默中伸入永恆。
難道唯一不致讓人無聊的就是說人的無聊,不致讓人絕望的就是說人的絕望嗎?
君子遠庖廚。
這庖廚是指一切瑣屑的事物。
如果社會的教育與發展使人失掉了可以感受幸福的心,則任何社會福利所能增進的都不是人的幸福。
其實,你對世界並不真正能了解。你了解世界,只是一個了解過程,只表示了你有這個心。
而只就有這個心,你整個人生就已經因之有了極重大的改觀。
你整個人都變了。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散髮弄扁舟又能稱意嗎?
或許不能吧。問題是,只要人有「意」,便永不能稱。
革命與叛逆
所謂為社會改革而努力的人,如果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的生命可愛,自己的孩子、太太、親人的生命可愛,則如何可能會認為「人民」的生命可愛?若「人民」的生命不可愛,又何須為他們改革社會?
而若「人民」的生命可愛,自己親友、太太、孩子乃至自己的生命不也當是可愛、可貴、可珍惜的嘛?然而一般所謂關懷社會者,似乎很難見到對生命珍惜的影子。不但在他們的視野中沒有「生命」的字眼,而且,如果你用這兩個字,他們還會指你濫情,而他們則「忙於重要的事情」,無暇顧及這等「幼稚」之事。
熱切搞社會理論的人,有些是意淫的野心家。他們雖然不能在實際上左右歷史的潮流,卻要理論上去左右它。
盲動可以有無名的原因做為其後盾,因此,不但是有原因的,而且力量是巨大的。這也可以說為什麼歷史大部分是由人的盲動所鑄成。盲動的根源在「情」,而情是匯眾流而成的茫茫大水。因此盲動可能應合了人的基本需求,成為社會改革的激素。
極端革命份子認為人是為了理想或政策而活。但正確的態度是一切理想或政策都是為了讓人過得更好。
小蒲林尼(Pliny the Younger)致雷圖真的信,說到對基督徒的處理,「……不論他們(基督徒)承認的東西是什麼性質,只他們這種堅持和頑強的態度,就足當受到懲罰。」
這是一切暴政和暴君的本質。它的本質是「只有暴君可以有『我』,可以有『意志』,別人都不可有。」
某些主義的可怕在於它自命為贖世主義,因而自認有權為了贖世而實行大屠殺。
共產主義起於理想,
資本主義起於熱情。
只有理想,是枯乾的;只有熱情,是盲動的。
比賽
人的才華和人的智慧本來都可以是存於天地之間、「唯我獨尊」的(註:佛誕生之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它之所以唯我獨尊,並非它賽過天下,而是由於它是外於比賽的,它的尊貴是越乎比賽的。
高貴的東西一加入比賽,立即就遭到褻瀆、污染,被人作踐。
我們無法想像佛陀參加比賽,孔子參加比賽,耶穌參加比賽。
一個孩子,健康的,快樂的,在父母眼中好看的,如果去參加兒童健美比賽,會突然在他父母眼中、親友眼中,甚至他自己眼中(如果他意識到)變得可疑了,──他真的是那麼健康嗎?真的是那麼可愛嗎...
作者序
序 焚餘集
多年來,出門時,口袋裡總是帶幾張紙、一枝筆,心裡那些摩摩挲挲的念頭一旦形成一個什麼句子的時候,就把它記下來,回到家裡,那紙片就放在桌上,或塞到一個什麼盒子裡。
在家裡的時候,念頭來了,有時隨手記在紙片上,有時記在本子上(當然,有時也沒記,想,這個念頭很重要,我一定不會忘記,但隔不多久,就忘得一乾二淨,甚至連曾經起過念頭也忘了)。
這樣累積久了,就變得很麻煩:零零碎碎的念頭,零零碎碎的本子,有些念頭在自己的生活裡已經屬於過去的了,有些事也是。但寫在那裡卻還留著。常常是覺得留著累贅,丟了可惜。有時看到或聽到別人突然死去,留下一堆日記、書信任人翻弄,把本不願告人之事都無抵抗的攤在別人面前,實在可憐,實在狼狽。警惕之餘,就是及早把這種可能性處理掉。
另一種原因是不願意見到自己以前的一大筆舊帳。我也常常會擔心我的一大堆日記和朋友給我的書信該放在哪裡。因為,放在哪裡都不安全。最安全的辦法是付之一炬。
所以,我的日記(從初中開始)和朋友給我的信,大都這樣隔幾年火祭一次給燒掉了。燒掉了,很乾淨,清清爽爽。
其實,我覺得,生命的不留痕跡,本就是這樣,只是人往往不捨。但不捨會造成累積,累積會變成累贅。文化人現在這麼沉重的負擔就是這樣而來。
最近我又焚一次。而且是一次總清掃:把十幾年前留下來的一些紙片和本子重新看了看,了解一些自己十幾年來走的路(都是重重覆覆繞著圈子走的。但基本上也在緩慢的前行,類如蛇形鐵絲網)另外,我也需要一些稿費,當然覺得也有不少佳句,就耐著性子選抄下來,分寄各報章雜誌。其餘的,大部分都燒掉了。所以,我這次燒得很清爽,留下的東西很少。但燒得還不夠徹底。有些本子仍捨不得燒。
我常有那麼一種想燒東西的衝動,不但想燒自己的東西,而且想燒別人的東西,不但想燒書、燒稿,而且想燒房子──當一個東西成為我的繫累或阻礙時,就想把它燒掉。這或許是一種原始人的本能吧。
以前我在美術雜誌上看過一篇文章,說吳道子(還是梁楷?)常有把自己的畫燒掉的習慣,謂之「滅筆」,我看後大為驚嘆,因為他完全體會了天地的運行之絕決、之無情,但這裡面卻有巨大的腳步在。他把自己的畫消滅,正是體會了、符合了天地的腳步,這種畫家真是偉大。而他這種「滅筆」的行為,正是藝術的極致。
我常常覺得,語言沒有一句是完全對的。語言是人發明出來,用以捕捉事實的,但事實永遠無法被語言所完全捕捉或正確捕捉。所以佛說「有說便錯」。我所說的一切當然也不脫這個範圍。但這一個認識往往也會使人無賴,認為,反正怎麼說都不對嘛,我就不妨亂七八糟說說吧,這就是我的情形。
這些隨筆在謄抄和刊登時,都是未經分類的,摸到哪一張就抄哪一張,可抄的就抄,不可抄的就燒。其實生活和意念本就是如此交雜的。但在收集成書時,又還是覺得這樣不大好──主要的原因是現代讀者太忙,把它分類,讀者看起來、找起來都方便。但這樣卻已不是生活和意念的本來面目。
序 焚餘集
多年來,出門時,口袋裡總是帶幾張紙、一枝筆,心裡那些摩摩挲挲的念頭一旦形成一個什麼句子的時候,就把它記下來,回到家裡,那紙片就放在桌上,或塞到一個什麼盒子裡。
在家裡的時候,念頭來了,有時隨手記在紙片上,有時記在本子上(當然,有時也沒記,想,這個念頭很重要,我一定不會忘記,但隔不多久,就忘得一乾二淨,甚至連曾經起過念頭也忘了)。
這樣累積久了,就變得很麻煩:零零碎碎的念頭,零零碎碎的本子,有些念頭在自己的生活裡已經屬於過去的了,有些事也是。但寫在那裡卻還留著。常常是覺得留著累贅,丟了...
目錄
目次
出版緣起 人生一會(文/羅文嘉)
序 焚餘集
【卷一】心
念流
心之本質
比賽
鄉愁
脫繭
革命與叛逆
【卷二】藝術
詩人
披沙瀝金
暴君讀者優臣作家
讀者
【卷三】生與殺
兩隻巨龜
是與當是
感動
小節與大事
對得起自己
鞋子
「地球」船的甲板呢?
世界將沒
【卷四】人
釀
人的另一個定義
貧與富
兩種人
【卷五】男女
籠子與鳥
芬芳的性
蜜
色素
愛情
對女人幻覺的結束
文明及其不滿
閹
烏托邦
騙
老伴
繩子
挽
不看女人的男人
大劈棺
女人的邏輯
兩種女人──之一
兩種女人──之二
女人和她的愛情
使命
美
恨不能
【卷六】生活
困頓
正與誤
蓮
執著
不可替代
【卷七】生命與真理
學問與智慧
三種智慧
君子不器
虛無之磨
最根本最根本的真實
後記 缺席的在場:追憶生活者孟東籬(文/黃崇憲)
孟東籬/孟祥森著作.譯作目錄一覽
目次
出版緣起 人生一會(文/羅文嘉)
序 焚餘集
【卷一】心
念流
心之本質
比賽
鄉愁
脫繭
革命與叛逆
【卷二】藝術
詩人
披沙瀝金
暴君讀者優臣作家
讀者
【卷三】生與殺
兩隻巨龜
是與當是
感動
小節與大事
對得起自己
鞋子
「地球」船的甲板呢?
世界將沒
【卷四】人
釀
人的另一個定義
貧與富
兩種人
【卷五】男女
籠子與鳥
芬芳的性
蜜
色素
愛情
對女人幻覺的結束
文明及其不滿
閹
烏托邦
騙
老伴
繩子
挽
不看女人的男人
大劈棺
女人的邏輯
兩種女人──之一
兩種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