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紐約客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98 |
二手中文書 |
$ 213 |
小說/文學 |
$ 253 |
中文現代文學 |
$ 272 |
文學作品 |
$ 272 |
現代小說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小說 |
$ 288 |
現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劉俊說:「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從桂林出發,經過上海、南京、香港、臺北、芝加哥,終於停在世界性大都會紐約。《紐約客》的出版意味著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已不只是展現中國的人情歷史、文化處境、政治動盪、精神世界,而有了眾多外國人形象的融入。《Danny Boy》和《Tea for Two》這兩篇小說對愛的涉及,也提升為一種超越種族、性別和文化的大愛,揭示整個人類共同面臨的人間災難。隨著白先勇小說題材、人物和主題的『走向世界』,他觀察世界的角度,已不只是站在國族的立場,而是具有了世界主義的高度??這對白先勇來說,是他創作上的一大豐富和擴張。」
序
從國族立場到世界主義∕劉俊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有幾個城市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們是桂林、上海、南京、臺北、芝加哥和紐約。從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難看出,白先勇小說所覆蓋的地理空間涵蓋了太平洋兩岸的中國和美國,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遷徙中,漸行漸遠,從中國大陸經由臺灣遠走北美。於是,分屬於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的這些城市,不但成為白先勇小說人物活動的場景,而且在這些城市的轉換間,也隱含著一條這些人物「行走」的歷史軌跡。
在已經成為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經典的《臺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眾多從大陸來到臺灣的「臺北人」形象,在從桂林、上海、南京到臺北的空間轉換中,這些身在臺北的「臺北人」揮之不去的卻是桂林記憶、上海記憶和南京記憶,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種「身移」而「心不轉」的錯位,身在臺北卻對桂林、上海和南京難以忘懷,導致這些「臺北人」的心靈痛苦和精神悲劇。
《臺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國共兩黨此消彼長所引發的中國社會的乾坤旋轉,不管小說中的人物怎麼「行走」,這些城市畢竟還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人物雖然在大陸的「前世」和臺北的「今生」之間擺盪撕扯,到底也還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到了《紐約客》,情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不但人物從中國跨到了美國,而且城市也從臺北轉到了紐約,人和城都出了中國的疆界。假使說《臺北人》重在寫臺北的大陸人的故事,那麼《紐約客》則以紐約的「世界人」為描寫物件—這裡所謂的「世界人」既指中國人到了國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時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國人的外國人。
《紐約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著手創作的小說系列,《紐約客》之名或許借自美國著名文學雜誌New Yorker,卻與《臺北人》正好成為一個渾成的佳對。從收錄在《紐約客》爾雅版這個集子中的六篇小說來看,〈謫仙記〉和〈謫仙怨〉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發表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則是最近幾年創作的作品。仔細對照這些分屬不同時期的小說,或許可以發現,體現在白先勇《紐約客》中的創作立場,經歷了一個從上個世紀的國族(中國)立場,到近年來的世界主義的變化過程。
《紐約客》中的六篇小說,活動場景雖然都集中在紐約,但人物的歷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臺北有牽連,仍然割不斷和中國的聯繫。〈謫仙記〉和〈謫仙怨〉兩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黃鳳儀在上海時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離開上海(臺北)到了紐約,卻不約而同地成了「謫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間(紐約),是她們共同的人生軌跡,在紐約她們或在自毀自棄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墮落中沉淪掙扎。李彤和黃鳳儀的身世巨變,固然由國內政治形勢的天旋地轉而來,可是在上海(臺北)和紐約的城市對比中,作者似乎也隱隱然給我們一種暗示:對李彤和黃鳳儀而言,上海的繁華是她們的,而紐約的熱鬧卻與她們無關;她們在上海時是中國(蒙古)的「公主」,到了紐約卻變成了風塵女郎註。從上海到紐約,她們跨越的不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間的界限—在天上她們是主人,到了人間她們卻成為消費品。〈謫仙記〉、〈謫仙怨〉中的李彤和黃鳳儀,在上海(代表中國、東方)和紐約(代表美國、西方)這兩個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運,或許並不是偶然,如果聯繫同時代的吳漢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紐約近郊安樂鄉(《安樂鄉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難看看出白先勇筆下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到了國外成為「世界人」的時候,他們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
這也就是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時候,是持了一種強烈的國族(中國)立場的,站在中國的角度看,那時候來到紐約(芝加哥)這樣的美國大都會的中國人,遭遇的是一種放逐,一種謫仙和一種人生的巨大落差。《臺北人》中的錢夫人們從桂林、上海和南京來到臺北,是國內政治鬥爭的結果,我們從中看到的是同一個國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隨國民黨來台的一群)的命運;到了《紐約客》中的李彤們,她們從上海(臺北)來到紐約,原因可能還是國內政治鬥爭的結果,可反映的卻是同一種人群(中國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運。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臺北人》中的立場,概括為站在失敗者的一邊,同情那些來台的大陸人的話,那麼在〈謫仙記〉和〈謫仙怨〉中,他則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在中西文化夾縫中失魂落魄、沉淪墮落的「謫仙」們,寄予了深深的悲憫。值得注意的是,當〈謫仙記〉中的李彤輾轉在一個又一個外國男人之間,〈謫仙怨〉中的黃鳳儀成為外國男人的性消費品的時候,其中的男女關係,已然隱含了「東方∕女人∕弱勢出賣者對西方∕男人∕強勢購買者」的二元對立框架,這使〈謫仙記〉和〈謫仙怨〉在某種意義上講,成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華文文學中(暗合)文化殖民論述的兩篇作品(李彤和黃鳳儀象徵了東方弱勢文化,而西方男性則象徵了西方強勢文化,男性對女性的佔有,也就帶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對李彤和黃鳳儀的深切悲憫,正體現出他的國族(中國)立場和東方意識。
發表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夜曲〉和〈骨灰〉,是兩篇政治意識強烈的作品。這兩篇小說在反思中國人政治選擇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基礎上,寫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鬥爭所引發的人生的荒誕。〈夜曲〉寫的是一群留學海外的中國人與祖國的關係和由此導致的不同命運,當初沒來得及回國的吳振鐸在國外事業有成,但愛情不幸(和美國猶太人最終分手),學成回國的呂芳、高宗漢、劉偉卻在國內遭遇歷次政治運動,最後高宗漢在「文革」中自殺,劉偉變得學會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自我保護,呂芳則在「文革」後重返紐約。當吳振鐸和呂芳這對戀人二十五年後在紐約重逢時,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吳振鐸的異國婚姻,以失敗告終,而當初呂芳等人「正確」的人生選擇,二十五年後卻因政治的動亂而顯出了它的荒誕性—這種人生的荒誕性到了〈骨灰〉中變得更加令人觸目驚心,當年一對表兄弟,一個是對國民黨忠心耿耿的特工,一個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民主鬥士,為了政治理想,鬥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後,他們卻在紐約重新聚首,此時的特工,已遭國民黨排擠,民主鬥士,也在大陸成了右派,過去的政治對頭,如今到了國外,才又恢復了溫暖的親情。對這些歷劫之後還能倖存的,最深的感觸是當初的政治鬥爭其實是白費了—在波譎難測的政治鬥爭中,他們都不是贏家,最後都沒有好結果,最終只能流落異邦,在紐約以度殘年,乃至終老他鄉。對於〈夜曲〉和〈骨灰〉中的呂芳、大伯和鼎立表伯來說,他們的人生磨難都跟政治相關,而對政治的醒悟卻是以自己的一生為代價換來的。從上海到紐約的路,對他們來說雖然不象李彤和黃鳳儀那樣是從天上落到人間,可是經歷了政治鬥爭的煉獄,這段路無論如何走得實在不輕鬆,且代價慘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白先勇站在國族(中國)的立場,對中國現代歷史中政黨鬥爭的實質所做的反思。在這兩篇小說中,白先勇深懷憂患意識:唯其對中國愛得深,才會對現代史上的中國慘遭政治的撥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對中國人愛得深,他才會對呂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們最後都離開祖國,以紐約為自己最後的人生歸屬地滿懷無言之痛。這兩篇作品連同前面的〈謫仙記〉和〈謫仙怨〉,看上去是在寫紐約客(紐約人),其實倒是在寫中國人—此時的「紐約客」只在「紐約的過客」或「紐約的客人」的意義上才能成立。
白先勇筆下真正的「紐約客」(紐約人)是最近幾年創作的兩篇小說〈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的人物—這不僅是指這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以「過客」或「客人」的身分長居紐約,而是真正地對紐約有一種歸屬感,並且,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限於中國的「紐約客」,而有了外國紐約客(紐約人)的身影。〈Danny Boy〉中的主人公雲哥是個同性戀者,因為愛上了自己的學生,不容於社會,只好遠走美國,來到紐約,在紐約放縱的結果是染上了愛滋病。就在雲哥對人生徹底絕望之際,他卻在照顧另一位因受強暴而染上愛滋病的患者丹尼的過程中,感受到了「一種奇異的感動」—這使他終於從慾的掙扎中升騰而出,生命重新充實,心靈得以淨化。真正的「同病相憐」使雲哥衝破了種族的界限,在一種宗教性的大愛中,尋找到了自己心靈的歸屬,在「救人—自救」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在〈Tea for Two〉中,「我」是華人而「我」的戀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兒,東尼是中國人而他的愛人大偉是猶太人,珍珠是臺山妹而她的伴侶百合是德州人,費南度是菲律賓人而他的「配偶」金諾是義大利裔美國人,這個集聚在「Tea for Two歡樂吧」中由同性戀者組成的小社群,由於來自世界各地幾乎可以構成一個小型聯合國,就戀人間的真情和社群中的友誼而言,他們與異性戀社會其實沒有什麼差別。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現的愛滋病「瘟疫」,使這些同性戀者深受其害,當大偉也染上愛滋病,決心和東尼同赴天國之際,這些同性戀者一起到他們的住處為他們送行,小說最後在倖存者們高唱〈Tea for Two〉的狂歡中結束。
〈Danny Boy〉和〈Tea for Two〉這兩篇小說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就是小說所描寫的內容已不再是單純的中國世界,而具有了世界化的色彩,這不僅體現為小說名稱的英文化,小說人物的聯合國化,而且也是指這兩篇作品所涉及的題材,同性戀和愛滋病,也是一個超越種族、國家和文化的世界性現象。〈Danny Boy〉中雲哥和丹尼的「相互扶持」,以及〈Tea for Two〉中東尼和大偉等人的相濡以沫,同生共死,無疑突顯了人類的一種共相:愛是不分性別和種族的,而愛滋病的蔓延,也不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我們人類今天必須面對的共同現實。小說向人們展示的是,在愛滋病面前,人類已經打破了性別、種族、國家和文化的心靈隔閡和區域界限,在一起共同承擔和面對這一世界性的災難。
如果說在〈謫仙記〉和〈謫仙怨〉中,我們能從作品中感受到隱含的「中」、「西」(文化)不平等的事實,〈夜曲〉中吳振鐸失敗的婚姻,體現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和諧,那麼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小說展示的則是「中」、「西」(族群和文化)的融合(雲哥對丹尼的照顧、眾多同性戀「配偶」的構成,以及大偉和東尼家裡中西合璧的家具布置,都說明了這一點),不論「中」、「西」(民族、國家)都承擔了同樣命運,「中」、「西」(整個世界)實際上已成為難以區隔的命運共同體。很顯然,白先勇在這兩篇作品中,一改他過去以國族(中國)立場來表現中國(人)社會、歷史和政治的做法,而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將世界放在不分「中」「西」的狀態下,描寫世界範圍內的共同問題。這樣的一種轉變,對於白先勇來說,無疑是一次創作上的突破和質變。
於是,我們在《紐約客》中看到,白先勇的筆觸,從表現中國人天上人間的「謫仙」,到中國人對政治的「覺悟」,再到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面對「瘟疫」,其間的變化轉型,其實是在逐步深化和拓展自己的創作空間,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從面對「中國人」時所持的國族(中國)立場(思考中國人的海外命運和中國人的政治歷史),轉而為面對「中國人+外國人」時採取不限於特定民族、國家和文化的世界主義眼光(思考人類不分種族性別文化的宗教大愛和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從中體現出的,是白先勇對人類的觀察視野和包容心,愈見廣闊。
《紐約客》的出版昭示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從桂林出發,經過上海、南京、香港、臺北、芝加哥,終於停在了有大蘋果之稱的世界性都市紐約。與此同時,《紐約客》的出版也意味著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已不只是展現中國(人)的人情歷史、文化處境、政治動盪、精神世界,而有了眾多外國人形象的融入,並且,〈Danny Boy〉和〈Tea for Two〉這兩篇小說對愛的涉及,也提升為一種超越種族、性別和文化的大愛,揭示的問題,也是整個人類共同面臨的人間災難。隨著白先勇小說題材、人物和主題的「走向世界」,他觀察世界的角度,也不只是站在國族(中國)的立場,而是具有了世界主義的高度—這對白先勇來說,應當是他創作上的一大豐富和擴張。
註:李彤在讀書時被美國同學視為「中國的皇帝公主」,黃鳳儀淪落風塵後「蒙古公主」成了她的招牌—這或許可以說明她有「公主」的氣質,而她的過去也當得起公主的稱號。李彤雖然沒有成為風塵女郎,但她最後的行為和處境,事實上已成為高級的風塵女郎。
後記∕白先勇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初到美國第一個落腳的大城便是紐約,因為幾位哥哥姐姐都住在紐約附近。六三、六四年的夏天,我在紐約渡過兩個暑假。我一個人在曼哈頓的六十九街上租了一間公寓,除了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上暑期班外,也在雙日出版公司Double Day做點校對工作,校對《醒世姻緣》的英譯稿,其餘的時間,便在曼哈頓上四處遊蕩,踏遍大街小巷,第五大道從頭走到尾。
紐約曼哈頓像棋盤似的街道,最有意思的是,每條街道個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條街,有時連居民的人種也變掉了,倏地由白轉黑,由黃轉棕。紐約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會,全世界各色人等都匯集於此,羼雜在這個人種大熔爐內,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為紐約是一個無限大、無限深,是一個太上無情的大千世界,個人的悲歡離合,飄浮其中,如滄海一粟,翻轉便被淹沒了。
六三、六四那兩年夏天,我心中收集了許多幅紐約風情畫,這些畫片又慢慢轉成了一系列的「紐約故事」,開頭的幾篇如〈上摩天樓去〉等並沒有一個中心主題,直到六五年的一個春天,我在愛荷華河畔公園裡一張桌子上,開始撰寫〈謫仙記〉,其時春意乍暖,愛荷華河中的冰塊消融,凘凘而下,枝頭芽葉初露新綠,萬物欣欣復甦之際,而我寫的卻是一則女主角從紐約飄流到威尼斯投水自盡的悲愴故事。
當時我把這篇小說定為《紐約客》系列的首篇,並引了陳子昂〈登幽州台歌〉作為題跋,大概我覺得李彤最後的孤絕之感,有「天地之悠悠」那樣深遠吧。接著又寫〈謫仙怨〉,其實同時我也在進行《台北人》系列,把時間及注意力都轉到那個集子去了,於是《紐約客》一拖便是數十年,中間偶爾冒出一兩篇,可是悠悠忽忽已跨過了一個世紀,「紐約」在我心中漸漸退隱成一個遙遠的「魔都」,城門仍舊敞開,在接納許多魚貫而入的飄蕩靈魂。
我的出版人為等待出版這個集子恐怕頭髮都快等白了,目下只有六篇,也只好先行結集。
二○○七年七月五日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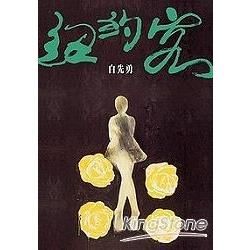
 2007/09/27
2007/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