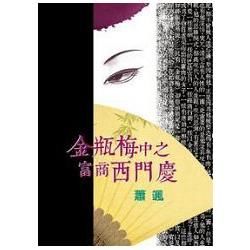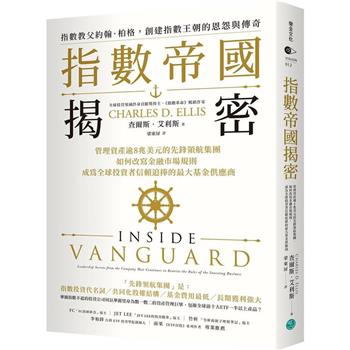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並稱四大奇書之一的《金瓶梅》卻和其他三書的評價相當不同,而今藉由蕭颯之筆,以西門慶為鑰匙,重新開啟解讀此書之路。
經由當時的中國社會來反觀現今的現實,怎不令人驚嘆的相似,無怪乎蕭颯說:「《金瓶梅》所陳述的主題,即使是四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日日在我們四周發生;他所塑造的人物,一樣仍圍繞在我們身邊生活著。」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門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69 |
二手中文書 |
$ 272 |
小說/文學 |
$ 292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15 |
文學作品 |
$ 315 |
金瓶梅 |
$ 325 |
中文書 |
$ 326 |
中國古典文學 |
$ 333 |
金瓶梅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金瓶梅中之富商西門慶
內容簡介
目錄
爾雅出版社特別推薦
蕭颯出入古今 創作、論述並進三
第一章 前言九
第一節 關於金瓶梅九
第二節 成書年代一七
第三節 作者之謎二二
第二章 西門慶人物形象三五
第一節 晚明的商人三七
第二節 西門慶出身與發跡五一
第三節 西門慶之人際關係五八
第四節 西門慶的價值觀七一
第三章 西門慶權力與金錢之追求八五
第一節 不公不義之官場文化八六
第二節 交相互利之官商勾結一 八
第三節 西門慶的豐厚妻財一二八
第四節 西門慶追求權力與金錢形象的意義一三六
第四章 西門慶情愛與肉慾之追求一四七
第一節 與妻妾關係一四九
第二節 與情婦關係一八六
第三節 西門慶的慾海沉淪二 六
第四節 西門慶追求情愛與肉慾形象的意義二一八
第五章 西門慶豪奢生活之追求二三三
第一節 錦衣玉食二三四
第二節 戲曲、散曲二七三
第三節 豪門禮俗二八七
第四節 西門慶追求豪奢生活形象的意義三 五
第六章 結語三一九
主要參考書目三三九
蕭颯出入古今 創作、論述並進三
第一章 前言九
第一節 關於金瓶梅九
第二節 成書年代一七
第三節 作者之謎二二
第二章 西門慶人物形象三五
第一節 晚明的商人三七
第二節 西門慶出身與發跡五一
第三節 西門慶之人際關係五八
第四節 西門慶的價值觀七一
第三章 西門慶權力與金錢之追求八五
第一節 不公不義之官場文化八六
第二節 交相互利之官商勾結一 八
第三節 西門慶的豐厚妻財一二八
第四節 西門慶追求權力與金錢形象的意義一三六
第四章 西門慶情愛與肉慾之追求一四七
第一節 與妻妾關係一四九
第二節 與情婦關係一八六
第三節 西門慶的慾海沉淪二 六
第四節 西門慶追求情愛與肉慾形象的意義二一八
第五章 西門慶豪奢生活之追求二三三
第一節 錦衣玉食二三四
第二節 戲曲、散曲二七三
第三節 豪門禮俗二八七
第四節 西門慶追求豪奢生活形象的意義三 五
第六章 結語三一九
主要參考書目三三九
序
前言
第一節 關於金瓶梅
宋元時期,民間流行說書、講史的娛樂活動,至元代末葉,羅貫中致力于將原先只是以說書形式流傳的三國故事和水滸人物,整理編寫成《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成為我國最早的長篇白話小說。在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對其讚譽備至,認為如果沒有羅貫中,就不可能有後來繼之而起的諸多長篇白話小說。鄭振鐸說羅貫中是:「繼于『書會先生』之後的一位偉大作家。他正是一位繼往承來,繼絕存亡的俊傑;站在雅與俗,文與質之間的。」
因為《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普遍受到世人歡迎和重視,因此帶動了後來長篇白話小說的蓬勃發展。到了明代嘉靖、隆慶、萬曆時,情況更是空前,長篇白話小說《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四遊記》、《封神傳》、《三寶太監西洋記》、《平妖傳》、《隋煬艷史》、《皇明英烈傳》……,一一出現,小說的成就超越以往,已經不能以千里計。而其中最有價值,最受後世稱道的,就屬《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並稱為明代四大奇書。
長篇白話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明代如此蓬勃發展,外在主要因素:一、由於明朝中葉以後,政治上的嚴峻開始鬆緩,自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到天啟,諸皇帝皆不理會朝政,鎮日糜爛嬉戲於皇室後宮,而士大夫也上行下效,渾沌不振。二、因為當時商業日趨興盛,經濟開始活絡,城市繁榮後消費奢靡風氣大開,市民意識亦隨之抬頭。
因為政治鬆緩,平民百姓經濟能力躍昇,開始縱情追逐物慾、娛樂。再有李贄、三袁、馮夢龍等文士的提倡,他們毫不掩飾地反對理學,重視小說、戲曲的創作,這更是推動了長篇白話小說發展的主要動力。另外,當時印刷業興盛,商業販售發達,也為長篇白話小說的出版、流傳,創造了極其良好的條件。
這個時期的長篇白話小說與從前的古代小說,有著明顯的變化,若以小說史的演進而言,先有筆記小說,再是傳奇小說、平話小說,之後才是長篇白話小說,但此一時期的長篇白話小說,更是脫離了從前文人與群眾相結合的話本式小說,開始走向個人創作,並且由說書體的小說,向文人創作小說過渡;從講史、稱頌英雄人物,轉向描寫一般市井小民;從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轉向日常生活的細膩書寫;從類型化的人物典型,轉向個性化的人物;從線形結構,轉向網狀結構;從英雄主義,轉向寫實主義。從此作者的主體意識、思想感情,更多樣的顯現在作品之中,作品的個人風格也就更加鮮明,而其中最具代表的著作,就屬《金瓶梅》。
《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雖然被後世並稱為明代四大奇書,彷彿四者可以等量齊觀,無分軒輊;但是,事實上,《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四百年來得到讚譽、稱頌不斷,從不寂寞,唯獨《金瓶梅》,自明末以來,卻一直遭受著強大的非議和污衊,甚至被當成淫邪之書看待。明崇禎十年,江西學政侯峒曾在「江西學政申曰」中,列有「禁私刻」專條,《金瓶梅》赫然在列,不准民間刻印販售。
明清以來談論《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的文章極多,而論及《金瓶梅》者卻寥寥無幾,而且多隱匿真實姓名,只有少數思想先進開明的文士,才願意以真實姓名公開談論此書,如袁宏道、袁中道、李日華、沈德符、屠本畯、張岱、李漁……等人,但卻也不過寥寥數語帶過而已,並無專門論述文字出現。
五四以後,自由學風漸開,加以西洋文學理論的佐證,《金瓶梅》一書不論是思想上、結構安排、人物描寫、文字敘述……等,都堪稱是一部合于現代意義的長篇白話小說。它寫實的呈現了當時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不同於其他長篇白話小說的內容,或講史、或神怪、或傳奇……。《金瓶梅》是一部絕對純粹的寫實小說,魯迅在其著述之《中國小說史略》中對其誇讚不已,說:
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為非王世貞不能作。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縉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
《金瓶梅》是否王世貞所作,爭議仍多,不過其文學價值,從此得以肯定。除了魯迅外,學者鄭振鐸、吳 、阿英等,都曾對此書多有專文論及,為其平反。從此,《金瓶梅》才勉強得以進入學術殿堂,其藝術價值這才真正得到了認同。
長久以來,海內外研究《金瓶梅》者,多以作者、版本考據為主,成績確實斐然,其次才是思想藝術、人物形象、語言研究……等,著述甚多,但對於文本的研究就稍嫌欠缺,就如專門研究《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的大陸「金學」名家吳敢,便肯定認為「金瓶文化」與「金學」傳播,才是現今新的研究方向,他說:
一九九五︱二○○○年間的『金學』專著,匯編、考證已不多見,思想與藝術研究也已轉平,語言雖然仍有不少研究者留目,『金瓶文化』與『金學』傳播形成新的熱點,社會風俗、時代精神、文化層面、士子心態等越來越進入「金學」同人視野,而世紀之交令人產生難解的歷史情結,一些研究者試圖從不同角度對「金學」進行闡釋和總結。
吳敢的這番話,對想要從事「金學」研究的後學,有著極重要的啟迪。魏子雲教授也在其參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中國古典文學第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研究金瓶梅應走的正確方向」中,提出了「讀通原著」的主張。因此,筆者試圖以「讀通原著」,正視「金瓶文化」,傳播「金學」為目標。
《金瓶梅》在我國小說史上,是一部非常不同於前人的純粹寫實小說,不能說是後無來者,但確實可稱前無古人。不論它的敘事、抒情、寫景、描繪人物,筆筆寫來維妙維肖,佈局完整,文字流暢,最了不起的是風格獨特,不以書寫瑣碎飲食、性事、家常動靜……等為不屑。這種文學藝術觀念,與現代寫實主義文學觀幾乎同出一轍。
《金瓶梅》不但是一部純粹的寫實主義小說,更是一部貼近現代意識的超時代著作,它深具現代意義,與現代的人生觀、現代思潮,多有不謀而合之處。正如鄭振鐸所說:「只有《金瓶梅》卻徹頭徹尾是一部近代期的產品。不論其思想,其事實,以及描寫方法,全都是近代的。」他更說過:「在《金瓶梅》裡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社會。這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早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鄭振鐸就如是說過,《金瓶梅》是合乎近代要求的。事實上,《金瓶梅》甚至更合乎現代開放而且多元化的人生觀。《金瓶梅》所陳述的主題,便是四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日日在我們四周發生;它所塑造的人物,一樣仍然圍繞在我們身邊生活著。《金瓶梅》就是這樣一部以人性為出發,完全符合了近代寫實小說訴求的鉅作,更是一部完全符合了我們現代社會需求的社會寫實小說,它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也值得大家為它的傳播而努力。
唯《金瓶梅》抄本至今未被發現。今日所能見到最早和最接近原本面貌的,只有印著欣欣子序,廿公跋,及記有萬曆丁巳(萬曆四十五年)弄珠客序文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全文百萬字上下,共分十卷,回目一百。
《新刻金瓶梅詞話》目前存世的一共僅餘三部,一部是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省介休縣發現,分裝成二十冊,缺少封面和第五十二回中的七、八兩頁,當時由北京圖書館購藏。一九三三年馬廉等人集資,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出版了一百零四套,缺頁部分則以「崇禎說散本」抄補上。此《新刻金瓶梅詞話》原本,抗戰前夕連同北平故宮文物一起運往了美國保存,一九六五年美方交還臺灣,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另外兩部《新刻金瓶梅詞話》現均存于日本,據校讀《新刻金瓶梅詞話》多年有成的梅節推想:「可能自寶永前傳到日本,也沉埋兩百多年,沒有人看過。」所以是素潔的原刻本,沒有添加任何點改批語。此兩部書,一部藏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一部藏德山毛利氏棲息堂。(另有一部則僅餘二十三回的殘本,藏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三部《新刻金瓶梅詞話》都有少許缺頁,所以均非完本。經過魏子雲和梅節悉心比對後,均認定屬於同一刻版,這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萬曆詞話本」。
「萬曆詞話本」中有著大量詞曲,加上性事描寫過多,又以山東土白寫成,十分不易閱讀。所以後來由一位不能確知姓名的文士加以刪改,將露骨的性事描寫及大量詞曲刪去,全文面目大為不同,詞話說唱氣氛削弱,人物和情節也簡略不少,並以適合南人閱讀的語言代替原先的山東土白,每回結尾不用「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改用一聯或一詩作結。回目雖然仍是一百回,但是改寫得比較工整對仗,並將《新刻金瓶梅詞話》中的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改從「西門慶熱結十兄弟/武二郎冷遇親哥嫂」開始。因為文字容易閱讀,又刪去不雅的性事,崇禎間甚為風行,各種刻版盡出,爭相販售,這便是被一般稱為「崇禎說散本」的《金瓶梅》。只是這個經過文人大量刪改修訂的「崇禎說散本」《金瓶梅》,是否真正成書於崇禎年代?目前仍受著各方學者專家所質疑,不過仍然俗稱其為「崇禎說散本」,以有別於早先的「萬曆詞話本」。
「崇禎說散本」《金瓶梅》,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版本,是《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共二十卷一百回,附有兩百幅刻工精美的圖像。圖上題有刻工姓名,如劉應祖、劉啟先、黃子立等,都是活躍於天啟、崇禎年間的著名木刻名手,所以斷定必刻印於崇禎年間。至於《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究竟是由何人寫定?其中點評文字又是何人所為?雖然至今沒有定論,但其評點文字已經注重作者的寫實手法、人物性格和心理層次等小說必備之重要元素,對於《金瓶梅》的藝術成就,有著開拓性的肯定,對之後的馮夢龍、金聖嘆、李漁、張竹坡等點評家,更有著前導性的啟發作用。
本文的研究,將以「萬曆詞話本」為主。「萬曆詞話本」是目前可見最接近《金瓶梅》原貌,也最能代表《金瓶梅》原本創作主旨,也唯有「萬曆詞話本」能夠真正反映出《金瓶梅》創作的那個時代的真正氛圍,對於西門慶這個人物的描寫,也只有「萬曆詞話本」中的西門慶,才更接近《金瓶梅》原作者塑造的西門慶。所有關於《金瓶梅》小說研究與引文部分,除特別說明,都將依照香港太平書局一九九三年七月第十次印刷之《全本金瓶梅詞話》為本。《金瓶梅詞話》是萬曆年間刊本,目錄頁刻有「新刻金瓶梅詞話」,舊藏北京圖書館,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三三年曾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一百零四套,香港太平書局即用此影印本為底本重印發行,書名改為《全本金瓶梅詞話》。
第二節 成書年代
明、清士人皆認為《金瓶梅》是明嘉靖年間作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鄭振鐸、吳 認為成書是在萬曆年間,魏子雲則根據袁宏道致董其昌的書信中最早出現《金瓶梅》三字為萬曆二十四年,而《金瓶梅》大量見於文獻,是在萬曆三十四年之後,由此斷定《金瓶梅》的成書不可能完成於嘉靖,而可能完成於萬曆或天啟年間。
徐朔方的考定,則認為《金瓶梅》作者多處引用李開先的傳奇《寶劍記》,而《寶劍記》脫稿於嘉靖丁未夏,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所以這才是《金瓶梅》真正成書年代的上限。再根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有:「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弟睹數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劉延伯家有全本……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鈔拏歸。」而《新刻金瓶梅詞話》東吳弄珠客所寫〈金瓶梅序〉中清楚記有萬曆丁巳,也就是萬曆四十五年,所以一般認定成書的下限,自然是不會晚於萬曆丙午,也就是萬曆三十四年;但是,徐朔方又以湯顯祖萬曆二十八年完成《南柯記》以前,曾經讀完《金瓶梅》抄本為證,認為《金瓶梅》成書下限還可再修訂。另外又據《明實錄》記載,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奏酒色財氣四箴;而《金瓶梅》卷首亦有酒色財氣《四貪詞》,認為成書下限該定為萬曆十七年。
劉輝則認為以上皆非,以《新刻金瓶梅詞話》中大量的戲曲描寫,證明此書絕不可能成於萬曆年間。以為書中所描寫的海鹽腔,摘錄的時調小曲,都是盛行於明嘉靖年間,而流傳萬曆年間的崑山腔和「掛枝兒」「打棗杆」,卻是一處也不見,僅此便可認定《金瓶梅》的成書必在嘉靖年間。
許建平則以為作者對嘉靖中後期的社會政治生活極為熟悉,但是書中也寫有許多萬曆初年獨有之事,所以認定《金瓶梅》成書年代為萬曆初年。
《金瓶梅》確實成書年代雖然無法精準確定,但總是不出嘉靖、隆慶、萬曆,這已經是學界公認之事實。嘉靖、隆慶、萬曆可說是明朝政治逐漸進入承平,經濟已是全盛的階段,算得上富裕,而且開始慢慢走向奢靡的年代。黃仁宇在其所著《萬曆十五年》中,如此說及萬曆朝皇宮建築的宏偉、富麗,以及用度的驚人。
和以前的各個朝代相比,本朝的宮廷開支最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哩,各個宮殿上蓋琉璃瓦,前後左右有無數的朱門和迴廊;宮殿下面的臺階都用漢白玉石砌築,真是極盡豪華。皇城環繞紫禁城,占地三方哩有餘。皇城內有馳道和人工開鑿的湖泊,以備馳馬划船和其他遊覽之用。建築物除去皇家別墅之外,還有寺院、高級宦官的住宅。為皇室服務的機構,例如烤餅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馬房以至印書藏書的廠庫也都集中在這裡,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於外。各個廠房、寺廟、坊舍均由專任的宦官掌握,共有二十四個機構,習稱二十四監。到萬曆初年,宦官的總數已逾二萬,而且還在不斷膨脹。……總的說來,萬曆即位以後的第一個十年,即以一五七二年到一五八二年,為本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十年。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承平日久,國家的府庫隨之而日見充實。
皇室富裕,依賴的是民間經濟條件優渥,工商業發達稅收充裕。尤其張居正秉政後,天下大治,經濟高度繁榮,社會日趨奢華,自王公貴族到朝廷權貴,甚至一般士商名流,其生活享樂已經到達了奢侈糜爛的地步。張瀚《松窗夢語》便有如此的描述:
吾杭終有宋餘風,迨今侈靡日甚。……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若事佛之謹,則齋供僧徒,裝塑神像,雖貧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禱懺悔,誦經說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計也。
雖然張瀚記敘的主要是明朝人禮敬事佛之鋪張奢侈,但也正可由此見到當時之人消費風氣如何驚人,凡事講究富麗已經不只是富豪貴族競相追逐,就連一般平民百姓也一樣揮霍無度,一點都不肯相讓於富豪之家。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更是如此描寫晚明富戶奢侈之風:
一個縉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佈著一大堆的隨從;修築花園和精緻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內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三十至四十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晚明政治趨於鬆緩,自由買賣熱絡,經濟空前的興盛,但是否一如大多數大陸學者們認定的,晚明正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黃仁宇就大不以為然,認為稱明末清初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並無理論上的根據。他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寫道:「單是有商人和商業資本,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縱使生產關係超時代的發展,在十四、十五世紀之間,就有了資本家與城市無產階級的對立,也不一定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
然而就算晚明距離真正資本主義社會仍然遙遠,但這是個經濟生產空前進步,富商與城市無產階級並存的黃金時代,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這樣的經濟高度繁榮,自然將為城市生活帶來多樣而且綺麗的變幻,不止是反映在物質生活上,在思想上,宋、明以來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虛偽道學,此時也遭受到開明士人的強烈質疑。除了學術上先有王艮、羅近溪「泰洲學派」的對「人欲」的肯定,再有李贄的「童心說」,之後又有公安三袁的「性靈論」,都是對理學的禁欲,道學的虛偽反對,而更多的覺醒,則反映在文學作品上,譬如《金瓶梅》、《牡丹亭》,便是代表。
《金瓶梅》就是產生在這樣一個富裕、奢靡,但又敢於挑戰傳統的大環境之下。於是《金瓶梅》作者塑造出西門慶這樣一位只知追求權力與金錢、情愛與肉慾,又生活豪奢的反面人物作為主角,如此大不同於前人文學作品的創舉,也就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釋。
正因為嘉靖、萬曆已經脫離了明朝建國初期的艱難,整個社會上至朝廷、官家,下至商戶、百姓,呈現的都是承平富裕的奢靡景象,道德禮教觀念逐漸薄弱,尤其是在如西門慶這樣商戶出身,依靠著裙帶、賄賂關係升官發財之人,自然酒色財氣均沾,再無一點羞恥道德之心。有了這樣的成書背景,自然也就產生了西門慶這樣的一位商人角色,這是《金瓶梅》作者在細膩觀察後,真實的於作品中反映了人生。
第三節 作者之謎
《金瓶梅》的成書年代各家看法大有不同外,對於《金瓶梅》作者的論定,更是眾說紛紜。早在萬曆三十五年,屠本畯便在其《山林經濟籍》中論及《金瓶梅》的作者,說:「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萬曆四十二年袁中道《遊居柿錄》中說:「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萬曆四十四年,謝肇淛在《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中說:「《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年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萬曆四十七年,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金瓶梅」條中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只是眾多說法中,卻都只是相傳、傳聞,無一真正確切知曉作者姓名。就算撰寫《新刻金瓶梅詞話序》的欣欣子也只是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但是,蘭陵笑笑生又到底是何許人呢?
清初宋起鳳和張潮,均云《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但為吳 、鄭振鐸等否定,近人又有許建平著述《金學考論》重申王世貞為《金瓶梅》作者。一九五四年潘開沛則發表論述,認為《金瓶梅》並非個人創作,是由許多藝人集體創作而成的作品。他在〈金瓶梅的產生和作者〉中,說《金瓶梅》道:「不是哪一個『大名士』、大文學家獨自在書齋裡創作出來的,而是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裡的許多藝人集體創造出來的,是一部集體的創作,只不過最後經過了文人的潤色和加工而已。」
一九八 年徐朔方發表了〈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但是在之後所寫〈《金瓶梅》成書新探〉中,探討《金瓶梅》是世代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累積成的集體創作,並以書中大量採用了李開先的詞曲,認為《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或是李開先的崇信者,不再堅持一定是李開先寫定。
魏子雲則依據《別頭巾文》為屠隆手筆,認定《金瓶梅》係南人屠隆所作,並與看法相同的黃霖、鄭潤海峽兩岸相互唱和。劉輝則堅信《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寫定者和評點者是李漁。另外被認為是《金瓶梅》作者的名單中,還有薛應旂、趙南星、湯顯祖、馮夢龍、賈三近、沈德符、金聖嘆、徐渭、李先芳……等,不下二、三十人。
總之,《金瓶梅》的成書年代由嘉靖、隆慶至萬曆,各家均有己見,無法確定。各家所認定的年代,中間間隔又超過半個世紀,要從這麼漫長的時序中尋找出真實作者姓名,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作者之謎,在目前資料不足,沒有充分證據的窘況下,只能說仍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
筆者根據一九三二年山西省介休縣發現的「萬曆詞話本」研判,《金瓶梅》最早應當是供書會才人、說唱藝人表演之用的「話本」,《新刻金瓶梅詞話》是以此「話本」為依據,刊刻問世而成的讀本,並且他與原先表演用的「話本」改變不大,仍屬「詞話本」類型,所以書名仍然沿用了「詞話」二字。一直到了《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問世後,《金瓶梅》才脫離了「詞話本」型態,成為文人刪改修訂成的「說散本」。
宋人羅燁所編《醉翁談錄》中有「舌耕敘引」,說小說者曰:「舉斷模按,師表規模,靠敷衍令看官清耳。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咯嘓萬餘言,講論古今。說收拾尋常有百萬套,談話頭動輒是數千回。說重門不掩底相思,談閨閣難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類,分州軍縣鎮之程途。講歷代年載廢興,記歲月英雄文武。有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術、神仙。自然使席上風生,不枉教坐間星拱。」可知小說者就是說話者,憑三寸不爛之舌,褒貶是非,當堂令看官清耳,使席上風生。宋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中有「京瓦伎藝」,記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霍四就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說的正是小說、講史等,都是在大庭廣眾前的一種表演。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說話人」時,說:「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為『話本』。」認為「說話人」說話時所持底本,就是「話本」,也就是後來「話本小說」的開端。
但是對上述「話本」說法,也有持反對意見者,日本增田涉寫有論文〈論「話本」一詞的定義〉,認為「話本」一詞根本沒有「說話人的底本」的意思,而是指「故事」而言。他說:「『話本』不是『說話人的底本』,而是『說話』,跟『話文』或『小說』具有相同的意思。」但是他也並未反對說話人說話時確有所本,所以文中仍反覆提到「說話人的底本」。
《新刻金瓶梅詞話》是屬於表演用性質的「詞話本」,也就是「說話人的底本」刊刻印製而來,理由最為明顯者有二:一是文內大量採用了現成的詩詞戲曲,甚至他人之作。這在文士創作中屬抄襲行為,是不被允許的,但是作為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的表演,卻無傷大雅,甚至習慣使然。二是《新刻金瓶梅詞話》明白的以「詞話」作為書名,在在證明了它是一部累積型的民間說唱文學,此處的「累積」指的是可以一邊演出,一邊創作,日積月累而成書。就如潘開沛所說,《金瓶梅》不是那個『大名士』、大文學家獨自在書齋裡創作出來的,它是一部為說唱表演而產生的「話本」而已。至於是否如潘開沛所言是集體創作?依全書結構完整,脈絡分明,情節連貫,人物性格分明,語言統一……等看來,絕非集體創作,應當是屬個人創作。
我們再以《水滸傳》第五十一回中一段文字,印證「話本」正是宋、元、明、清以來書會才人,說唱藝人表演時所憑藉的底本:
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著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
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眾人喝采不絕。
白秀英表演的「話本」,正是說了又唱,唱了又說的說唱藝人表演。我們現今所見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也是用來說了又唱,唱了又說的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的表演底本。明末清初丁耀亢作《續金瓶梅》,凡例中說:「小說類有詩詞,前集名為『詞話』,多用舊曲。」第一回又說:「見的這部書反做了導欲宣淫的話本。」這裡的「詞話」和「這部書」,指的就是《金瓶梅詞話》,所以丁耀亢也說《金瓶梅》是話本的一類。
《新刻金瓶梅詞話》內文中,大量引用了可以吟唱的詩詞和散曲,幾乎每一回都有可唱之韻文,或用以勸世或用以說教,或交代情節,甚至與小說情節發展並無關聯的說唱亦多在其中。譬如第二十四回,潘金蓮使人把韓嫂兒叫來,問她為何當街撒酒瘋罵人,韓嫂兒來了,不慌不忙,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為證。」(第二十四回,頁六二四)主人問話,僕婦竟然就這樣當眾唱了起來,這只有在戲劇表演才可能發生。第七十九回西門慶臨終之時,夫妻生離死別悲痛萬分之時,西門慶要吳月娘休哭,聽他囑咐,竟然以〈駐馬聽〉唱詞唱出:「賢妻休悲,我有裡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真心,一妻四妾,攜帶著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吳月娘聽了,亦以唱詞回答:「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分付。」(第七十九回,頁二四三六)《金瓶梅》作者能夠將人物對白寫得暢快淋漓,其實並不需要借助唱詞表達感情,但是他卻在生離死別或是病危的緊要時刻,讓角色一一吟唱,唯一的解釋也就是因為它是屬於說唱表演的「話本」,所以才會出現如此的安排。
另外,第八十九回吳月娘、孟玉樓為西門慶上墳,兩人都唱〈山坡羊〉帶〈步步嬌〉。同樣第八十九回春梅、孟玉樓哭潘金蓮墳,唱的也是〈山坡羊〉。第三十回李瓶兒即將臨盆,產婆蔡老娘趕了來,不急著探看產婦,卻與吳月娘磕頭後報起山門,道:「我做老娘姓蔡,兩隻腳兒能快,身穿怪綠喬紅,各樣狄髻歪戴,嵌絲環子鮮明,閃黃手帕符,入門利市花紅,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貴宅嬌娘,那管皇親國太,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劃,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不管臍帶包衣,著忙用手撕壞,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顧偏多,請的時常不在。」(第三十回,頁七八三)產婆、庸醫出場,都以自報山門的表演方式,先來上一段韻文演唱。第三十回,來保與吳主管押送生辰擔,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其中就插有「評話捷說」字句(第三十回,頁七七二)。第七十回,西門慶前往東京,也用「評話捷說」(第七十回,頁一九九四)。文內又有四十多次用「看官聽說」如何如何之語,另外每回結語,更以「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這些分明都清楚顯示了其為「話本」的本色。
尤其眾所週知的,《金瓶梅》故事是由《水滸傳》衍生而來,現在就以《金瓶梅》的第一回前半「景陽岡武松打虎」,比較之《水滸傳》的第二十三回後半「景陽岡武松打虎」,其中文字大同小異。
《金瓶梅》如是寫道:「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皆落黃葉,刷刷的響。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弔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稍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滿山蒲嶺,盡皆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跨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側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了一聲,把山崗也振動,武松卻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著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稍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著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拏一半在手裡。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卻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著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撾在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撾定那虎,那裡肯放鬆。」(第一回,五五、五六頁)
《水滸傳》寫的是:「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翻將下來,便拿遇條哨棒在手裡,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了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裡攥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跨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了一聲,卻似半天裡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崗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翦,三般提不著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著,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著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枝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拏得一半在手裡。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一只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肐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裡肯放半點兒鬆寬?」
兩段文字詳加比對後,可以發現幾乎大抵雷同,只有少許改動而已。由此可以證明,那些改動只是表演藝人說唱時,因為沒有一字一句的照本宣科,偶爾用了自己的語氣加以增刪潤色,但是所有轉折和細節,則仍屬原來《水滸傳》,並未多改。事實上《金瓶梅》第一回至第十回,幾乎完全抄錄於《水滸傳》的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由此除了可以證明《金瓶梅》確是藉著《水滸傳》武松、潘金蓮、西門慶故事展開情節外,更可以明顯看出,《金瓶梅》當初是以說唱表演《水滸傳》開的端倪。
《金瓶梅》最早是以「話本」形式面市,而「詞話本」也就是「說唱話本」之意。《金瓶梅》正是表演藝人先以念唱《水滸傳》開始,然後敷衍出更多情節和故事,最後集結成為鉅作。此類用以表演的「話本」,內容可以世代累積,但文字卻不一定每一部都屬集體創作,像這樣為了演出所作的「話本」,亦可能由一人獨立寫成,寫定後或用來自己表演,或由其他藝人演出,《金瓶梅》便屬於這樣一種個人創作意味濃厚的「話本」。
既然是應用於表演的「話本」,自然就少了文人創作時的精心講究,所以任意摘取當時現成詞曲,借用其他話本與非話本小說情節穿插文內。又因為是應付演出的底本,所以書寫匆忙,多有疏漏,或情節前後重複或脫節失序,又多處人物年齡和事件年代錯置,除了刊刻時的手民之誤外,若屬作者的疏漏亦是可以理解之事。
只是多數學者專家仍堅信《金瓶梅》作者必為大名士的說法,如徐朔方以為作者是李開先,魏子雲、黃霖認為是屠隆,王汝梅認為是王世貞,張遠芬認為是賈三近,……,他們均不相信一般書會才人、說唱藝人能有此等創作能耐,能夠獨自完成《金瓶梅》如此鉅作。認為《金瓶梅》作者必是王世貞無疑的許建平,言道:「如果假定為下層文人或藝人寫作,該小說構思的完整性,敘事針線之細密,語言之生動鮮活,不失稗官之上乘,又如何解釋?」其實下層文人難道就不能有身懷小說創作之大才者嗎?中國何其大,落第秀才、舉子何其多?既然能「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作為門客的老儒能有這樣大才撰寫《金瓶梅》,那麼自然也會有淪落市井成為下層社會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的潦倒文人,一樣也能身懷大才創作《金瓶梅》。
以校讀《金瓶梅》著稱的梅節,在其〈《金瓶梅詞話》的版本與文本〉中曾道:「編撰者為書會才人一類中下層知識分子,可能與源流久遠的『羅公(貫中)書會』有關。」正因為這位寫作《金瓶梅》的書會才人、說唱藝人只是個一般市井小民、潦倒文人,屬於中下層知識份子,而非什麼大文士大名流,因為他社會地位低落,身份不高,所以不容易名列經傳,這便是《金瓶梅》作者姓名不容易被流傳於世的原因。
既然《金瓶梅》的作者是這樣一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的創作尺度自然較之文人士大夫寬闊,無須受到任何束縛,也因此才能夠創造出西門慶這樣離經叛道的人物,而且以這樣的負面角色作為全書最為重要的靈魂人物。也只有這樣淪落市井的藝人,才能有此悖離了一般所謂傳統正道的勇氣和原創力道,塑造出西門慶這樣的一個負面人物,卻成為數百年來不被遺忘,而且仍然不時的被人們提出討論解析的典型化人物。
總之,《金瓶梅》作者之謎,在目前資料不足,又沒有充分證據的窘況下,仍處於懸而未決狀態。筆者亦認為《金瓶梅》最早為表演用的「話本」,之後才刊行販售,其作者可能正是當時的書會才人、說唱藝人之流,至於真實姓名,就只有等待更新的,更有力的資料出現,再做出詳實、可信之判定。
第一節 關於金瓶梅
宋元時期,民間流行說書、講史的娛樂活動,至元代末葉,羅貫中致力于將原先只是以說書形式流傳的三國故事和水滸人物,整理編寫成《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成為我國最早的長篇白話小說。在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對其讚譽備至,認為如果沒有羅貫中,就不可能有後來繼之而起的諸多長篇白話小說。鄭振鐸說羅貫中是:「繼于『書會先生』之後的一位偉大作家。他正是一位繼往承來,繼絕存亡的俊傑;站在雅與俗,文與質之間的。」
因為《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普遍受到世人歡迎和重視,因此帶動了後來長篇白話小說的蓬勃發展。到了明代嘉靖、隆慶、萬曆時,情況更是空前,長篇白話小說《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四遊記》、《封神傳》、《三寶太監西洋記》、《平妖傳》、《隋煬艷史》、《皇明英烈傳》……,一一出現,小說的成就超越以往,已經不能以千里計。而其中最有價值,最受後世稱道的,就屬《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並稱為明代四大奇書。
長篇白話小說之所以能夠在明代如此蓬勃發展,外在主要因素:一、由於明朝中葉以後,政治上的嚴峻開始鬆緩,自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到天啟,諸皇帝皆不理會朝政,鎮日糜爛嬉戲於皇室後宮,而士大夫也上行下效,渾沌不振。二、因為當時商業日趨興盛,經濟開始活絡,城市繁榮後消費奢靡風氣大開,市民意識亦隨之抬頭。
因為政治鬆緩,平民百姓經濟能力躍昇,開始縱情追逐物慾、娛樂。再有李贄、三袁、馮夢龍等文士的提倡,他們毫不掩飾地反對理學,重視小說、戲曲的創作,這更是推動了長篇白話小說發展的主要動力。另外,當時印刷業興盛,商業販售發達,也為長篇白話小說的出版、流傳,創造了極其良好的條件。
這個時期的長篇白話小說與從前的古代小說,有著明顯的變化,若以小說史的演進而言,先有筆記小說,再是傳奇小說、平話小說,之後才是長篇白話小說,但此一時期的長篇白話小說,更是脫離了從前文人與群眾相結合的話本式小說,開始走向個人創作,並且由說書體的小說,向文人創作小說過渡;從講史、稱頌英雄人物,轉向描寫一般市井小民;從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轉向日常生活的細膩書寫;從類型化的人物典型,轉向個性化的人物;從線形結構,轉向網狀結構;從英雄主義,轉向寫實主義。從此作者的主體意識、思想感情,更多樣的顯現在作品之中,作品的個人風格也就更加鮮明,而其中最具代表的著作,就屬《金瓶梅》。
《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雖然被後世並稱為明代四大奇書,彷彿四者可以等量齊觀,無分軒輊;但是,事實上,《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四百年來得到讚譽、稱頌不斷,從不寂寞,唯獨《金瓶梅》,自明末以來,卻一直遭受著強大的非議和污衊,甚至被當成淫邪之書看待。明崇禎十年,江西學政侯峒曾在「江西學政申曰」中,列有「禁私刻」專條,《金瓶梅》赫然在列,不准民間刻印販售。
明清以來談論《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的文章極多,而論及《金瓶梅》者卻寥寥無幾,而且多隱匿真實姓名,只有少數思想先進開明的文士,才願意以真實姓名公開談論此書,如袁宏道、袁中道、李日華、沈德符、屠本畯、張岱、李漁……等人,但卻也不過寥寥數語帶過而已,並無專門論述文字出現。
五四以後,自由學風漸開,加以西洋文學理論的佐證,《金瓶梅》一書不論是思想上、結構安排、人物描寫、文字敘述……等,都堪稱是一部合于現代意義的長篇白話小說。它寫實的呈現了當時民間社會的日常生活,不同於其他長篇白話小說的內容,或講史、或神怪、或傳奇……。《金瓶梅》是一部絕對純粹的寫實小說,魯迅在其著述之《中國小說史略》中對其誇讚不已,說:
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為非王世貞不能作。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縉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
《金瓶梅》是否王世貞所作,爭議仍多,不過其文學價值,從此得以肯定。除了魯迅外,學者鄭振鐸、吳 、阿英等,都曾對此書多有專文論及,為其平反。從此,《金瓶梅》才勉強得以進入學術殿堂,其藝術價值這才真正得到了認同。
長久以來,海內外研究《金瓶梅》者,多以作者、版本考據為主,成績確實斐然,其次才是思想藝術、人物形象、語言研究……等,著述甚多,但對於文本的研究就稍嫌欠缺,就如專門研究《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的大陸「金學」名家吳敢,便肯定認為「金瓶文化」與「金學」傳播,才是現今新的研究方向,他說:
一九九五︱二○○○年間的『金學』專著,匯編、考證已不多見,思想與藝術研究也已轉平,語言雖然仍有不少研究者留目,『金瓶文化』與『金學』傳播形成新的熱點,社會風俗、時代精神、文化層面、士子心態等越來越進入「金學」同人視野,而世紀之交令人產生難解的歷史情結,一些研究者試圖從不同角度對「金學」進行闡釋和總結。
吳敢的這番話,對想要從事「金學」研究的後學,有著極重要的啟迪。魏子雲教授也在其參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中國古典文學第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論文「研究金瓶梅應走的正確方向」中,提出了「讀通原著」的主張。因此,筆者試圖以「讀通原著」,正視「金瓶文化」,傳播「金學」為目標。
《金瓶梅》在我國小說史上,是一部非常不同於前人的純粹寫實小說,不能說是後無來者,但確實可稱前無古人。不論它的敘事、抒情、寫景、描繪人物,筆筆寫來維妙維肖,佈局完整,文字流暢,最了不起的是風格獨特,不以書寫瑣碎飲食、性事、家常動靜……等為不屑。這種文學藝術觀念,與現代寫實主義文學觀幾乎同出一轍。
《金瓶梅》不但是一部純粹的寫實主義小說,更是一部貼近現代意識的超時代著作,它深具現代意義,與現代的人生觀、現代思潮,多有不謀而合之處。正如鄭振鐸所說:「只有《金瓶梅》卻徹頭徹尾是一部近代期的產品。不論其思想,其事實,以及描寫方法,全都是近代的。」他更說過:「在《金瓶梅》裡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社會。這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曾成為過去。」早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鄭振鐸就如是說過,《金瓶梅》是合乎近代要求的。事實上,《金瓶梅》甚至更合乎現代開放而且多元化的人生觀。《金瓶梅》所陳述的主題,便是四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日日在我們四周發生;它所塑造的人物,一樣仍然圍繞在我們身邊生活著。《金瓶梅》就是這樣一部以人性為出發,完全符合了近代寫實小說訴求的鉅作,更是一部完全符合了我們現代社會需求的社會寫實小說,它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也值得大家為它的傳播而努力。
唯《金瓶梅》抄本至今未被發現。今日所能見到最早和最接近原本面貌的,只有印著欣欣子序,廿公跋,及記有萬曆丁巳(萬曆四十五年)弄珠客序文的《新刻金瓶梅詞話》,全文百萬字上下,共分十卷,回目一百。
《新刻金瓶梅詞話》目前存世的一共僅餘三部,一部是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省介休縣發現,分裝成二十冊,缺少封面和第五十二回中的七、八兩頁,當時由北京圖書館購藏。一九三三年馬廉等人集資,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出版了一百零四套,缺頁部分則以「崇禎說散本」抄補上。此《新刻金瓶梅詞話》原本,抗戰前夕連同北平故宮文物一起運往了美國保存,一九六五年美方交還臺灣,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另外兩部《新刻金瓶梅詞話》現均存于日本,據校讀《新刻金瓶梅詞話》多年有成的梅節推想:「可能自寶永前傳到日本,也沉埋兩百多年,沒有人看過。」所以是素潔的原刻本,沒有添加任何點改批語。此兩部書,一部藏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一部藏德山毛利氏棲息堂。(另有一部則僅餘二十三回的殘本,藏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三部《新刻金瓶梅詞話》都有少許缺頁,所以均非完本。經過魏子雲和梅節悉心比對後,均認定屬於同一刻版,這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萬曆詞話本」。
「萬曆詞話本」中有著大量詞曲,加上性事描寫過多,又以山東土白寫成,十分不易閱讀。所以後來由一位不能確知姓名的文士加以刪改,將露骨的性事描寫及大量詞曲刪去,全文面目大為不同,詞話說唱氣氛削弱,人物和情節也簡略不少,並以適合南人閱讀的語言代替原先的山東土白,每回結尾不用「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改用一聯或一詩作結。回目雖然仍是一百回,但是改寫得比較工整對仗,並將《新刻金瓶梅詞話》中的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潘金蓮嫌夫賣風月」,改從「西門慶熱結十兄弟/武二郎冷遇親哥嫂」開始。因為文字容易閱讀,又刪去不雅的性事,崇禎間甚為風行,各種刻版盡出,爭相販售,這便是被一般稱為「崇禎說散本」的《金瓶梅》。只是這個經過文人大量刪改修訂的「崇禎說散本」《金瓶梅》,是否真正成書於崇禎年代?目前仍受著各方學者專家所質疑,不過仍然俗稱其為「崇禎說散本」,以有別於早先的「萬曆詞話本」。
「崇禎說散本」《金瓶梅》,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版本,是《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共二十卷一百回,附有兩百幅刻工精美的圖像。圖上題有刻工姓名,如劉應祖、劉啟先、黃子立等,都是活躍於天啟、崇禎年間的著名木刻名手,所以斷定必刻印於崇禎年間。至於《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究竟是由何人寫定?其中點評文字又是何人所為?雖然至今沒有定論,但其評點文字已經注重作者的寫實手法、人物性格和心理層次等小說必備之重要元素,對於《金瓶梅》的藝術成就,有著開拓性的肯定,對之後的馮夢龍、金聖嘆、李漁、張竹坡等點評家,更有著前導性的啟發作用。
本文的研究,將以「萬曆詞話本」為主。「萬曆詞話本」是目前可見最接近《金瓶梅》原貌,也最能代表《金瓶梅》原本創作主旨,也唯有「萬曆詞話本」能夠真正反映出《金瓶梅》創作的那個時代的真正氛圍,對於西門慶這個人物的描寫,也只有「萬曆詞話本」中的西門慶,才更接近《金瓶梅》原作者塑造的西門慶。所有關於《金瓶梅》小說研究與引文部分,除特別說明,都將依照香港太平書局一九九三年七月第十次印刷之《全本金瓶梅詞話》為本。《金瓶梅詞話》是萬曆年間刊本,目錄頁刻有「新刻金瓶梅詞話」,舊藏北京圖書館,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一九三三年曾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一百零四套,香港太平書局即用此影印本為底本重印發行,書名改為《全本金瓶梅詞話》。
第二節 成書年代
明、清士人皆認為《金瓶梅》是明嘉靖年間作品。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鄭振鐸、吳 認為成書是在萬曆年間,魏子雲則根據袁宏道致董其昌的書信中最早出現《金瓶梅》三字為萬曆二十四年,而《金瓶梅》大量見於文獻,是在萬曆三十四年之後,由此斷定《金瓶梅》的成書不可能完成於嘉靖,而可能完成於萬曆或天啟年間。
徐朔方的考定,則認為《金瓶梅》作者多處引用李開先的傳奇《寶劍記》,而《寶劍記》脫稿於嘉靖丁未夏,也就是嘉靖二十六年,所以這才是《金瓶梅》真正成書年代的上限。再根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有:「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弟睹數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劉延伯家有全本……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鈔拏歸。」而《新刻金瓶梅詞話》東吳弄珠客所寫〈金瓶梅序〉中清楚記有萬曆丁巳,也就是萬曆四十五年,所以一般認定成書的下限,自然是不會晚於萬曆丙午,也就是萬曆三十四年;但是,徐朔方又以湯顯祖萬曆二十八年完成《南柯記》以前,曾經讀完《金瓶梅》抄本為證,認為《金瓶梅》成書下限還可再修訂。另外又據《明實錄》記載,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奏酒色財氣四箴;而《金瓶梅》卷首亦有酒色財氣《四貪詞》,認為成書下限該定為萬曆十七年。
劉輝則認為以上皆非,以《新刻金瓶梅詞話》中大量的戲曲描寫,證明此書絕不可能成於萬曆年間。以為書中所描寫的海鹽腔,摘錄的時調小曲,都是盛行於明嘉靖年間,而流傳萬曆年間的崑山腔和「掛枝兒」「打棗杆」,卻是一處也不見,僅此便可認定《金瓶梅》的成書必在嘉靖年間。
許建平則以為作者對嘉靖中後期的社會政治生活極為熟悉,但是書中也寫有許多萬曆初年獨有之事,所以認定《金瓶梅》成書年代為萬曆初年。
《金瓶梅》確實成書年代雖然無法精準確定,但總是不出嘉靖、隆慶、萬曆,這已經是學界公認之事實。嘉靖、隆慶、萬曆可說是明朝政治逐漸進入承平,經濟已是全盛的階段,算得上富裕,而且開始慢慢走向奢靡的年代。黃仁宇在其所著《萬曆十五年》中,如此說及萬曆朝皇宮建築的宏偉、富麗,以及用度的驚人。
和以前的各個朝代相比,本朝的宮廷開支最為浩大。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哩,各個宮殿上蓋琉璃瓦,前後左右有無數的朱門和迴廊;宮殿下面的臺階都用漢白玉石砌築,真是極盡豪華。皇城環繞紫禁城,占地三方哩有餘。皇城內有馳道和人工開鑿的湖泊,以備馳馬划船和其他遊覽之用。建築物除去皇家別墅之外,還有寺院、高級宦官的住宅。為皇室服務的機構,例如烤餅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馬房以至印書藏書的廠庫也都集中在這裡,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於外。各個廠房、寺廟、坊舍均由專任的宦官掌握,共有二十四個機構,習稱二十四監。到萬曆初年,宦官的總數已逾二萬,而且還在不斷膨脹。……總的說來,萬曆即位以後的第一個十年,即以一五七二年到一五八二年,為本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十年。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承平日久,國家的府庫隨之而日見充實。
皇室富裕,依賴的是民間經濟條件優渥,工商業發達稅收充裕。尤其張居正秉政後,天下大治,經濟高度繁榮,社會日趨奢華,自王公貴族到朝廷權貴,甚至一般士商名流,其生活享樂已經到達了奢侈糜爛的地步。張瀚《松窗夢語》便有如此的描述:
吾杭終有宋餘風,迨今侈靡日甚。……毋論富豪貴介,紈綺相望,即貧乏者,強飾華麗,揚揚矜詡,為富貴容。若事佛之謹,則齋供僧徒,裝塑神像,雖貧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禱懺悔,誦經說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計也。
雖然張瀚記敘的主要是明朝人禮敬事佛之鋪張奢侈,但也正可由此見到當時之人消費風氣如何驚人,凡事講究富麗已經不只是富豪貴族競相追逐,就連一般平民百姓也一樣揮霍無度,一點都不肯相讓於富豪之家。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更是如此描寫晚明富戶奢侈之風:
一個縉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佈著一大堆的隨從;修築花園和精緻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內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三十至四十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晚明政治趨於鬆緩,自由買賣熱絡,經濟空前的興盛,但是否一如大多數大陸學者們認定的,晚明正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黃仁宇就大不以為然,認為稱明末清初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並無理論上的根據。他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寫道:「單是有商人和商業資本,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縱使生產關係超時代的發展,在十四、十五世紀之間,就有了資本家與城市無產階級的對立,也不一定能構成資本主義的體制。」
然而就算晚明距離真正資本主義社會仍然遙遠,但這是個經濟生產空前進步,富商與城市無產階級並存的黃金時代,則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這樣的經濟高度繁榮,自然將為城市生活帶來多樣而且綺麗的變幻,不止是反映在物質生活上,在思想上,宋、明以來鼓吹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虛偽道學,此時也遭受到開明士人的強烈質疑。除了學術上先有王艮、羅近溪「泰洲學派」的對「人欲」的肯定,再有李贄的「童心說」,之後又有公安三袁的「性靈論」,都是對理學的禁欲,道學的虛偽反對,而更多的覺醒,則反映在文學作品上,譬如《金瓶梅》、《牡丹亭》,便是代表。
《金瓶梅》就是產生在這樣一個富裕、奢靡,但又敢於挑戰傳統的大環境之下。於是《金瓶梅》作者塑造出西門慶這樣一位只知追求權力與金錢、情愛與肉慾,又生活豪奢的反面人物作為主角,如此大不同於前人文學作品的創舉,也就因此有了合理的解釋。
正因為嘉靖、萬曆已經脫離了明朝建國初期的艱難,整個社會上至朝廷、官家,下至商戶、百姓,呈現的都是承平富裕的奢靡景象,道德禮教觀念逐漸薄弱,尤其是在如西門慶這樣商戶出身,依靠著裙帶、賄賂關係升官發財之人,自然酒色財氣均沾,再無一點羞恥道德之心。有了這樣的成書背景,自然也就產生了西門慶這樣的一位商人角色,這是《金瓶梅》作者在細膩觀察後,真實的於作品中反映了人生。
第三節 作者之謎
《金瓶梅》的成書年代各家看法大有不同外,對於《金瓶梅》作者的論定,更是眾說紛紜。早在萬曆三十五年,屠本畯便在其《山林經濟籍》中論及《金瓶梅》的作者,說:「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萬曆四十二年袁中道《遊居柿錄》中說:「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萬曆四十四年,謝肇淛在《小草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中說:「《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年代。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萬曆四十七年,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金瓶梅」條中說:「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只是眾多說法中,卻都只是相傳、傳聞,無一真正確切知曉作者姓名。就算撰寫《新刻金瓶梅詞話序》的欣欣子也只是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但是,蘭陵笑笑生又到底是何許人呢?
清初宋起鳳和張潮,均云《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但為吳 、鄭振鐸等否定,近人又有許建平著述《金學考論》重申王世貞為《金瓶梅》作者。一九五四年潘開沛則發表論述,認為《金瓶梅》並非個人創作,是由許多藝人集體創作而成的作品。他在〈金瓶梅的產生和作者〉中,說《金瓶梅》道:「不是哪一個『大名士』、大文學家獨自在書齋裡創作出來的,而是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裡的許多藝人集體創造出來的,是一部集體的創作,只不過最後經過了文人的潤色和加工而已。」
一九八 年徐朔方發表了〈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但是在之後所寫〈《金瓶梅》成書新探〉中,探討《金瓶梅》是世代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累積成的集體創作,並以書中大量採用了李開先的詞曲,認為《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或是李開先的崇信者,不再堅持一定是李開先寫定。
魏子雲則依據《別頭巾文》為屠隆手筆,認定《金瓶梅》係南人屠隆所作,並與看法相同的黃霖、鄭潤海峽兩岸相互唱和。劉輝則堅信《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寫定者和評點者是李漁。另外被認為是《金瓶梅》作者的名單中,還有薛應旂、趙南星、湯顯祖、馮夢龍、賈三近、沈德符、金聖嘆、徐渭、李先芳……等,不下二、三十人。
總之,《金瓶梅》的成書年代由嘉靖、隆慶至萬曆,各家均有己見,無法確定。各家所認定的年代,中間間隔又超過半個世紀,要從這麼漫長的時序中尋找出真實作者姓名,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作者之謎,在目前資料不足,沒有充分證據的窘況下,只能說仍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
筆者根據一九三二年山西省介休縣發現的「萬曆詞話本」研判,《金瓶梅》最早應當是供書會才人、說唱藝人表演之用的「話本」,《新刻金瓶梅詞話》是以此「話本」為依據,刊刻問世而成的讀本,並且他與原先表演用的「話本」改變不大,仍屬「詞話本」類型,所以書名仍然沿用了「詞話」二字。一直到了《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問世後,《金瓶梅》才脫離了「詞話本」型態,成為文人刪改修訂成的「說散本」。
宋人羅燁所編《醉翁談錄》中有「舌耕敘引」,說小說者曰:「舉斷模按,師表規模,靠敷衍令看官清耳。只憑三寸舌,褒貶是非;咯嘓萬餘言,講論古今。說收拾尋常有百萬套,談話頭動輒是數千回。說重門不掩底相思,談閨閣難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類,分州軍縣鎮之程途。講歷代年載廢興,記歲月英雄文武。有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術、神仙。自然使席上風生,不枉教坐間星拱。」可知小說者就是說話者,憑三寸不爛之舌,褒貶是非,當堂令看官清耳,使席上風生。宋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中有「京瓦伎藝」,記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霍四就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說的正是小說、講史等,都是在大庭廣眾前的一種表演。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說話人」時,說:「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為『話本』。」認為「說話人」說話時所持底本,就是「話本」,也就是後來「話本小說」的開端。
但是對上述「話本」說法,也有持反對意見者,日本增田涉寫有論文〈論「話本」一詞的定義〉,認為「話本」一詞根本沒有「說話人的底本」的意思,而是指「故事」而言。他說:「『話本』不是『說話人的底本』,而是『說話』,跟『話文』或『小說』具有相同的意思。」但是他也並未反對說話人說話時確有所本,所以文中仍反覆提到「說話人的底本」。
《新刻金瓶梅詞話》是屬於表演用性質的「詞話本」,也就是「說話人的底本」刊刻印製而來,理由最為明顯者有二:一是文內大量採用了現成的詩詞戲曲,甚至他人之作。這在文士創作中屬抄襲行為,是不被允許的,但是作為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的表演,卻無傷大雅,甚至習慣使然。二是《新刻金瓶梅詞話》明白的以「詞話」作為書名,在在證明了它是一部累積型的民間說唱文學,此處的「累積」指的是可以一邊演出,一邊創作,日積月累而成書。就如潘開沛所說,《金瓶梅》不是那個『大名士』、大文學家獨自在書齋裡創作出來的,它是一部為說唱表演而產生的「話本」而已。至於是否如潘開沛所言是集體創作?依全書結構完整,脈絡分明,情節連貫,人物性格分明,語言統一……等看來,絕非集體創作,應當是屬個人創作。
我們再以《水滸傳》第五十一回中一段文字,印證「話本」正是宋、元、明、清以來書會才人,說唱藝人表演時所憑藉的底本:
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著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
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眾人喝采不絕。
白秀英表演的「話本」,正是說了又唱,唱了又說的說唱藝人表演。我們現今所見的《新刻金瓶梅詞話》,也是用來說了又唱,唱了又說的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的表演底本。明末清初丁耀亢作《續金瓶梅》,凡例中說:「小說類有詩詞,前集名為『詞話』,多用舊曲。」第一回又說:「見的這部書反做了導欲宣淫的話本。」這裡的「詞話」和「這部書」,指的就是《金瓶梅詞話》,所以丁耀亢也說《金瓶梅》是話本的一類。
《新刻金瓶梅詞話》內文中,大量引用了可以吟唱的詩詞和散曲,幾乎每一回都有可唱之韻文,或用以勸世或用以說教,或交代情節,甚至與小說情節發展並無關聯的說唱亦多在其中。譬如第二十四回,潘金蓮使人把韓嫂兒叫來,問她為何當街撒酒瘋罵人,韓嫂兒來了,不慌不忙,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唱耍孩兒為證。」(第二十四回,頁六二四)主人問話,僕婦竟然就這樣當眾唱了起來,這只有在戲劇表演才可能發生。第七十九回西門慶臨終之時,夫妻生離死別悲痛萬分之時,西門慶要吳月娘休哭,聽他囑咐,竟然以〈駐馬聽〉唱詞唱出:「賢妻休悲,我有裡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真心,一妻四妾,攜帶著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吳月娘聽了,亦以唱詞回答:「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分付。」(第七十九回,頁二四三六)《金瓶梅》作者能夠將人物對白寫得暢快淋漓,其實並不需要借助唱詞表達感情,但是他卻在生離死別或是病危的緊要時刻,讓角色一一吟唱,唯一的解釋也就是因為它是屬於說唱表演的「話本」,所以才會出現如此的安排。
另外,第八十九回吳月娘、孟玉樓為西門慶上墳,兩人都唱〈山坡羊〉帶〈步步嬌〉。同樣第八十九回春梅、孟玉樓哭潘金蓮墳,唱的也是〈山坡羊〉。第三十回李瓶兒即將臨盆,產婆蔡老娘趕了來,不急著探看產婦,卻與吳月娘磕頭後報起山門,道:「我做老娘姓蔡,兩隻腳兒能快,身穿怪綠喬紅,各樣狄髻歪戴,嵌絲環子鮮明,閃黃手帕符,入門利市花紅,坐下就要管待,不拘貴宅嬌娘,那管皇親國太,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劃,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不管臍帶包衣,著忙用手撕壞,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主顧偏多,請的時常不在。」(第三十回,頁七八三)產婆、庸醫出場,都以自報山門的表演方式,先來上一段韻文演唱。第三十回,來保與吳主管押送生辰擔,離了清河縣,一路朝登紫陌,暮踐紅塵,有日到了東京,其中就插有「評話捷說」字句(第三十回,頁七七二)。第七十回,西門慶前往東京,也用「評話捷說」(第七十回,頁一九九四)。文內又有四十多次用「看官聽說」如何如何之語,另外每回結語,更以「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這些分明都清楚顯示了其為「話本」的本色。
尤其眾所週知的,《金瓶梅》故事是由《水滸傳》衍生而來,現在就以《金瓶梅》的第一回前半「景陽岡武松打虎」,比較之《水滸傳》的第二十三回後半「景陽岡武松打虎」,其中文字大同小異。
《金瓶梅》如是寫道:「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皆落黃葉,刷刷的響。撲地一聲,跳出一隻弔睛白額斑斕猛虎來,猶如牛來大。武松見了,叫聲阿呀時從青石上,翻身下來,便提稍棒在手,閃在青石背後。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跑了一跑,打了個歡翅,將那條尾,剪了又剪,半空中,猛如一個焦霹靂,滿山蒲嶺,盡皆振響。這武松被那一驚,把肚中酒,都變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原來猛虎項短,回頭看人教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跨一伸,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側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了一聲,把山崗也振動,武松卻又閃過一邊。原來虎傷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著時,氣力已自沒了一半。武松見虎沒力,翻身回來,雙手輪起稍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枝帶葉,打將下來,原來不曾打著大蟲,正打在樹枝上,磕磕把那條棒,折做兩截,只拏一半在手裡。這武松心中,也有幾分慌了。那虎咆哮性發,剪尾弄風起來,向武松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一跳,卻跳回十步遠。那大蟲撲不著武松把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乘勢向前,兩隻手,撾在大蟲頂花皮,使力只一按,那虎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武松儘力撾定那虎,那裡肯放鬆。」(第一回,五五、五六頁)
《水滸傳》寫的是:「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翻將下來,便拿遇條哨棒在手裡,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了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裡攥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跨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了一聲,卻似半天裡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崗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翦,三般提不著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著,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著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枝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拏得一半在手裡。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一只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肐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裡肯放半點兒鬆寬?」
兩段文字詳加比對後,可以發現幾乎大抵雷同,只有少許改動而已。由此可以證明,那些改動只是表演藝人說唱時,因為沒有一字一句的照本宣科,偶爾用了自己的語氣加以增刪潤色,但是所有轉折和細節,則仍屬原來《水滸傳》,並未多改。事實上《金瓶梅》第一回至第十回,幾乎完全抄錄於《水滸傳》的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由此除了可以證明《金瓶梅》確是藉著《水滸傳》武松、潘金蓮、西門慶故事展開情節外,更可以明顯看出,《金瓶梅》當初是以說唱表演《水滸傳》開的端倪。
《金瓶梅》最早是以「話本」形式面市,而「詞話本」也就是「說唱話本」之意。《金瓶梅》正是表演藝人先以念唱《水滸傳》開始,然後敷衍出更多情節和故事,最後集結成為鉅作。此類用以表演的「話本」,內容可以世代累積,但文字卻不一定每一部都屬集體創作,像這樣為了演出所作的「話本」,亦可能由一人獨立寫成,寫定後或用來自己表演,或由其他藝人演出,《金瓶梅》便屬於這樣一種個人創作意味濃厚的「話本」。
既然是應用於表演的「話本」,自然就少了文人創作時的精心講究,所以任意摘取當時現成詞曲,借用其他話本與非話本小說情節穿插文內。又因為是應付演出的底本,所以書寫匆忙,多有疏漏,或情節前後重複或脫節失序,又多處人物年齡和事件年代錯置,除了刊刻時的手民之誤外,若屬作者的疏漏亦是可以理解之事。
只是多數學者專家仍堅信《金瓶梅》作者必為大名士的說法,如徐朔方以為作者是李開先,魏子雲、黃霖認為是屠隆,王汝梅認為是王世貞,張遠芬認為是賈三近,……,他們均不相信一般書會才人、說唱藝人能有此等創作能耐,能夠獨自完成《金瓶梅》如此鉅作。認為《金瓶梅》作者必是王世貞無疑的許建平,言道:「如果假定為下層文人或藝人寫作,該小說構思的完整性,敘事針線之細密,語言之生動鮮活,不失稗官之上乘,又如何解釋?」其實下層文人難道就不能有身懷小說創作之大才者嗎?中國何其大,落第秀才、舉子何其多?既然能「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作為門客的老儒能有這樣大才撰寫《金瓶梅》,那麼自然也會有淪落市井成為下層社會書會才人、說唱藝人的潦倒文人,一樣也能身懷大才創作《金瓶梅》。
以校讀《金瓶梅》著稱的梅節,在其〈《金瓶梅詞話》的版本與文本〉中曾道:「編撰者為書會才人一類中下層知識分子,可能與源流久遠的『羅公(貫中)書會』有關。」正因為這位寫作《金瓶梅》的書會才人、說唱藝人只是個一般市井小民、潦倒文人,屬於中下層知識份子,而非什麼大文士大名流,因為他社會地位低落,身份不高,所以不容易名列經傳,這便是《金瓶梅》作者姓名不容易被流傳於世的原因。
既然《金瓶梅》的作者是這樣一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的創作尺度自然較之文人士大夫寬闊,無須受到任何束縛,也因此才能夠創造出西門慶這樣離經叛道的人物,而且以這樣的負面角色作為全書最為重要的靈魂人物。也只有這樣淪落市井的藝人,才能有此悖離了一般所謂傳統正道的勇氣和原創力道,塑造出西門慶這樣的一個負面人物,卻成為數百年來不被遺忘,而且仍然不時的被人們提出討論解析的典型化人物。
總之,《金瓶梅》作者之謎,在目前資料不足,又沒有充分證據的窘況下,仍處於懸而未決狀態。筆者亦認為《金瓶梅》最早為表演用的「話本」,之後才刊行販售,其作者可能正是當時的書會才人、說唱藝人之流,至於真實姓名,就只有等待更新的,更有力的資料出現,再做出詳實、可信之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