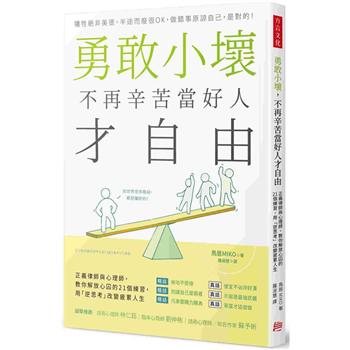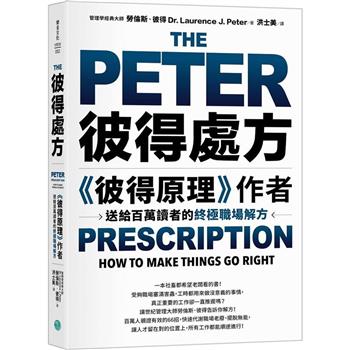作者的老師林谷芳說此書具有吞吐古今的氣象;朱天文感謝作者提供一個以看小說的視角來看《論語》;倪再沁說:「通過薛仁明所看到的那個親切的孔子,再重新看過《論語》,從前認為盡是大道理的『古訓』,竟如此易解,讀來令人神清氣爽、趣味盎然且氣象萬千。」
透過薛仁明清朗的文字來看孔子,不再遙不可及,而對於孔子的語言,也能感到生氣與鮮活,整本《孔子隨喜》正如書名那般親近可喜。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孔子隨喜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哲學 |
$ 323 |
文學作品 |
$ 342 |
中國/東方哲學 |
$ 342 |
儒家思想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孔子隨喜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薛仁明
福建漳州長泰縣山重村薛氏來臺之第十二代。出生于茄萣,民國八十二年起,常居於臺東池上。
年少時,曾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十八歲且因之休學半年。十九歲開始,有心於儒釋道三家。?
目前於臺北書院、北京辛莊師範開設有中國文化的長期課程,也在北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上海恆南書院以及民間多處講授《史記》與《論語》等短期課程,並曾應臺灣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邀請,做過多場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因其與生命相激蕩,與現實相對應,回響甚大。
除講課外,也經常於兩岸報刊發表文章,關心的焦點,是文化之重建與生命之修行。文章長於從淺近之處,推及中華文化的核心。在禮崩樂壞的當下,總能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使人即使面對劫難,仍處處見到生機。尤其能夠將中國文化中的人間興味,在不知不覺中,給挑撥開來,霍地亮出一片寧靜祥和的天地。已經出版的繁、簡體著作,有《胡蘭成.天地之始》、《孔子隨喜》、《教養,不惑》、《進可成事,退不受困—薛仁明讀史記》、《天清地寧》等書。
薛仁明
福建漳州長泰縣山重村薛氏來臺之第十二代。出生于茄萣,民國八十二年起,常居於臺東池上。
年少時,曾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十八歲且因之休學半年。十九歲開始,有心於儒釋道三家。?
目前於臺北書院、北京辛莊師範開設有中國文化的長期課程,也在北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上海恆南書院以及民間多處講授《史記》與《論語》等短期課程,並曾應臺灣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邀請,做過多場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因其與生命相激蕩,與現實相對應,回響甚大。
除講課外,也經常於兩岸報刊發表文章,關心的焦點,是文化之重建與生命之修行。文章長於從淺近之處,推及中華文化的核心。在禮崩樂壞的當下,總能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使人即使面對劫難,仍處處見到生機。尤其能夠將中國文化中的人間興味,在不知不覺中,給挑撥開來,霍地亮出一片寧靜祥和的天地。已經出版的繁、簡體著作,有《胡蘭成.天地之始》、《孔子隨喜》、《教養,不惑》、《進可成事,退不受困—薛仁明讀史記》、《天清地寧》等書。
序
序
學問,惟在氣象
談中國水墨,你可以推崇范寬的巨碑山水,他磊落遒勁,使百家纖巧,喑啞俱廢;你也可以心嚮倪瓚一河兩岸的蕭疏澹泊,逸筆草草,聊寫胸中之氣;而論曲盡其態,筆墨酣暢,「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許多人當推石濤為古今之最;談平淡天真,雅潔遠逸,有些人喜直指黃公望的理意兼顧。而即便八大的意境、筆墨,尤其是他那被大家忽略的山水是如此出格地讓我覺得千古一人,但若要論氣象、論吞吐,怎麼說,也還得從蜀人張大千談起。
朋友問我如何給大千下個斷語,我說「氣象萬千,富貴逼人」。這富貴逼人是張大千極特殊之處,他畫工筆、畫仕女,乃至畫鉤金荷花,再如何富貴,卻無半點俗氣,就如同他過的日子般,令人欣羨,卻不讓人嫉妒,因為居停揮灑,自有一派風光。
風光是禪家語,這裡觸目即是,處處生機,正因禪心是活的。活,所以能出入、能吞吐。不過,要如此,還得先將自己打開,將學問打開。
將自己打開,是不泥於己,如此才能與境相應,眼界一換,所見就有不同;將學問打開,是不受限於法,回眸一望,乃滿目青山。如此,於人於境,不畫地自限,自然開闔自如,寫史論人,對境應緣,就有不同氣象。
氣象是眼界、是格局、是丘壑,但較諸於此,它更有一番吞吐,可以周彌六合,可以退藏於密,無論橫說豎說,總有一番氣度、一番生機。
所以說,「富貴逼人」只是大千有時外顯的相,「氣象萬千」才是他的根本。在畫能不泥於法,從工筆臨摹到潑墨潑彩,從冊頁到通屏,就都能大小無礙,隨意進出。尋常說:人能大氣所以不俗,這大氣不是疏狂,而是開闔的氣象。
論藝,要氣象;看人,更得看氣象。畢竟,藝之一事,盡可舉生命之一端,將之極致,就能奪人眼目。而人,卻必得全體契入,才有真正的生命成就可言。
生命富於氣象,山河大地乃盡是文章;生命缺乏氣象,就只能封閉自持,顧影自憐。一個時光推移,益見豐富圓熟,一個則愈憤世酸腐,總覺老天為何獨薄於己,高低之間,乃愈差愈大。我們看少時同負才情的兩人,其後處境卻有天淵之別,關鍵常就只在這生命氣象的有無之上。
人如此,由人構成的歷史更如此。一個時代能否有其氣象,決定了這時代的成就,不從這入手,巨大的史料就變成永遠的負擔,別說尋章逐句可以累死多數人,即便有所梳理,也早就遠離了那時代的精神,更無益於當下的生命。
可惜的是,多少年來,我們寫人、論史,卻早就忘卻了這氣象。
忘卻氣象,正因早已缺乏氣象,而關鍵,就在宋代。
宋代有高度的文明成就原不待言,它是六朝隋唐以降胡化的終結者,這漢本土文化的復興本非壞事,但可惜走過了頭,走到絕對的夷夏之辨,周之後傳入的東西乃盡歸於須闢而廢之的胡物。於是在宋,你就看到:
雅樂要回復先秦,卻完全忽略了秦火之後,其原貌已難辨析,就一個黃鐘音高為何,可以聚訟千年。
琴家說彈琴一有琵琶音,終生難入古矣!於是以幽微淡遠為宗,最終,連扁舟五湖,一蓑江表,滿頭風雨,以心中之波濤映水雲之翻騰,具現中國式交響的《瀟湘水雲》,在明代最著名的虞山派琴譜中也因其「音節繁複」而不錄。
宋明理學援佛入儒,但罵起佛家,就像批楊墨:「出家,無父也,沙門不敬王者,無君也。無父無君者,禽獸也」,這等罵法,何只粗陋,更已似潑婦無賴之流了。
也所以,日本人比對五代編的《舊唐書》與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乃發覺《舊唐書》中一千一百多筆的佛教資料在《新唐書》中竟就不見,畢竟,面對「無父無君」的佛教,這等刪法還算客氣的呢!
以此,儘管宋有高度的文化成就,但這成就卻可看成在胡化下沉潛待發的奮力一擊,一擊之後,卻就每下愈況了。
每下愈況是因沒了氣象,在此,嚴的何只是夷夏之辨,還是雅俗之辨、正邪之辨,這影響對後世既深且遠,於是:
宋之後,標舉生死事小,失節事大,人須嚴合禮教,由此,除了花燈、秧歌、民俗慶典外,中國人已不能隨意舞動肢體,細膩的舞蹈只能在戲曲中尋,而能有這個出口,還因演員扮演的是別人。
中國的琵琶是歷史中唯一能與琴相頡頏消長的樂器,在唐是橫抱撥彈,至明已直抱手彈,還發展出相信是今曲〈十面埋伏〉前身的〈楚漢〉一曲,其器樂化已臻巔 ,這轉變何其之大!更是胡樂中國化的最好例證,但四五百年間竟無相關的琵琶史料,只因琵琶不僅是胡樂,還是俗樂!
而也就因宋儒的闢佛,即便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千年,民間甚而「家家彌陀,戶戶觀音」,談起佛家,許多儒門中人到今天第一句也還是:「佛教不是中國固有的宗教」。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而就因畫起圈圈,自擬正朔,缺了那吞吐開闔的氣象,所以,於書畫,即便文人多所寄寓,不乏大家,但真能開闔者,也常須於逸於格外者尋;於陶瓷,宋雖顯其底氣,至元明卻僅能但探幽微,到清,則幾乎只餘玩物喪志;於音樂,則宋之前固灰飛煙滅,宋後則雅俗嚴分,難出大氣;於文學,則宋詞、元曲、明之小品文,皆極盡美言,卻都少見酣暢;於思想,則文人之生活,儘管多出入三家,檯面卻只能標舉儒門,此儒門還愈不可親,最後士子就只能完全匍匐於科舉之下,學問也只能死於句中;而中國人不再舞動肢體,居敬最直接的結果竟就是逐漸僵化的身體與想法。
所以說,這氣象的有無、盛衰,才是了解中國千年以降文化變遷、生命轉折的關鍵,但要識得此,卻必須跳開宋文化成就帶給我們的慣性與迷思。換句話說,談人論史,談者的本身就非得具備那吞吐古今的氣象不可。
而老實說,仁明的這本書是有這點氣象的!
這氣象,出現在談儒的孔子九章上,孔子本身就具氣象,他當過大官,門人三千,雖不致三教九流,但來處不一,情性各異,他周遊列國,要面對每次的不可預期,有南子者還相中他,怎麼說,他都不像後世供奉的那種人。
這氣象,直擊宋儒的可敬不可親,但更回歸了做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孔子及其弟子的可能樣貌,使我們讀來,竟覺如 斯人,《論語》、《史記.孔子世家》的每一章句,竟也變得如此可親。
這些篇章量既不多,篇亦不長,但不只內容,文字的本身就體現了一種與孔門直通的氣象,形式論辯幾乎沒有,娓娓道來卻總神氣十足,坦白說,能如此談孔,談得如此直接,如此不死於句下者,怕極難找!而談的是儒,卻及於其他,讀史論學,仁明的文風,相應的正是中國人那具象直抒的風格。
就因這具象直抒,他談宋儒的概念化,乃不致墮在概念裡與之交鋒;而也因此,在全書中,他屢次述及當代知識分子,包含一些誠懇博學,具反思,乃至力圖實踐者其學問及生命的局限時,也特別清朗易讀。原來,雖從古老的中國走出,這些人卻一樣走入了那概念化,那不可親,那只探生命幽微,卻乏趣味、乏江湖、乏活潑乾坤的老路。
這樣的書,從講方法、談概念的看來,既主觀又沒學問,但講方法談概念不正是當前學問最大的異化麼談禪之教學,我總喜歡舉下面的應答: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參投子,問:「祖師言句如家常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麼?」
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
的確,天子下敕,自說即為君命,何須假借權威,反觀當代學界,言必談出處,卻從不問那原典如何產生,既為句下之徒,當然難以言那應緣而發的第一義。
而也正因祖師言句都從自己胸襟流出,所以即便蓋天蓋地,卻總如尋常家飯般親切。同樣,真具氣象者,其言儘管超乎慣性,筆下縱有王者之氣,卻因不假藉權威,不尋章逐句,不撥弄概念,不執著形式,也總令人覺得可親,尋常人乃可在此無隔,在此印證。而離了這親切,不要說難直指那生命學問的大義,首先異化的也就是言說者本人。
原來,學問無它,惟在氣象。你能以生命氣象對歷史氣象,以氣象之筆舉氣象之人,談史論事,為學說藝,何須雄辯再三,何須部繁帙重,平常道來,就有一番自家風光。
林谷芳
序
素看孔子
如果把《論語》當成一部上乘的小說來看,如何?讀完薛仁明《孔子隨喜》,我感謝作者提供了這樣一個視角,可以看小說一樣的看《論語》。
視角一轉換,彷彿取得通關密碼般,突然間,都看懂了。那些原先緘默似石看來全部一個樣的古人突然間,你說我說,連語氣、連舉止、連性格、連身世背景、連他們的命運,一一清晰到像《紅樓夢》裡寫出的百樣人,每一個都難忘。
小時候看《紅樓夢》,看劇情的只關心寶黛戀情。稍長後看熱鬧,挑愛看的章篇看,王熙鳳辦秦可卿喪事的那種場面調度,真好看。晴雯撕扇,病補孔雀裘。講話大舌頭的史湘雲,喝醉了睡在芍藥裀上。有人認同薛寶釵的世故明理,探春爽利有英氣,鴛鴦好蘊藉大方。便是代表儒家堅固系統的賈政,在我們年過半百閱世堪多後,始能明白脂胭齋所批賈政之為人物,「有深意存焉。」李渝一篇文章〈賈政不作夢〉這麼說,「是賈政,扶養寶釵母子;是賈政,攜賈母和黛玉的靈柩歸葬南鄉;是他,送別了寶玉。只有賈政可以撫慰生者,安息逝者,讓離者心安地離去。如果寶玉承盡了愛和哀,賈政擔盡了事和責。」
沒有賈府,不會有大觀園之夢。沒有賈政做為磐石的大觀園,不會有寶黛晴雯這些逆叛之花開出牆外。賈政的存在,是要有點年紀之後才會注意得到吧。
薛仁明寫孔子,眾弟子裡他跟孔子一樣特別鍾愛顏回,不說孔孟,只說孔顏,顏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夠達到的人格狀態。然而顏回,我很介意孔子曾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年輕時候我們受教於胡蘭成,跟妹妹朱天心不同,我對胡老師的一切言行誨喻,無所不悅。這在我,永遠是受益的一方。但對胡老師一方,我於他其實是無所助益的。審視這點,我仍耿耿於懷。
把孔子寫成小說,有日本小說家井上靖。我知道唐諾以前想寫,從子貢的觀點切入(聽聞已經有人這麼做也出版了)。子貢是商人,與孔門最異質,又夠聰明,不出手則已,《孔子家語》裡記載他一出手而亂齊、存魯、強晉、弱吳、霸越,儼然戰國時代縱橫家的先驅。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子貢隨行半程。孔子死後,他廬墓三年,又三年。《史記》寫最後一位見孔子的人是子貢,孔子負杖逍遙於門,看到子貢說:「賜,汝來何其晚也?」接著的一段對話,極為動人。子貢若做為一名敘事者,也許更能看到差異,而揭開的面相因此會更多樣,複雜和豐富。
三十餘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遊淺草觀音寺,胡老師指看寺壇上兩柱字,談起能樂的舞姿猶如此:
佛身圓滿無背相,
十方來人皆對面。
這兩句講修行,修得人事物,照面即見,沒有隔障。當然這兩句也可以拿來說孔子的因材施教,一對一的,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孔子隨喜》,在當代,在兩千五百年後,亦自是一份。
學問,惟在氣象
談中國水墨,你可以推崇范寬的巨碑山水,他磊落遒勁,使百家纖巧,喑啞俱廢;你也可以心嚮倪瓚一河兩岸的蕭疏澹泊,逸筆草草,聊寫胸中之氣;而論曲盡其態,筆墨酣暢,「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許多人當推石濤為古今之最;談平淡天真,雅潔遠逸,有些人喜直指黃公望的理意兼顧。而即便八大的意境、筆墨,尤其是他那被大家忽略的山水是如此出格地讓我覺得千古一人,但若要論氣象、論吞吐,怎麼說,也還得從蜀人張大千談起。
朋友問我如何給大千下個斷語,我說「氣象萬千,富貴逼人」。這富貴逼人是張大千極特殊之處,他畫工筆、畫仕女,乃至畫鉤金荷花,再如何富貴,卻無半點俗氣,就如同他過的日子般,令人欣羨,卻不讓人嫉妒,因為居停揮灑,自有一派風光。
風光是禪家語,這裡觸目即是,處處生機,正因禪心是活的。活,所以能出入、能吞吐。不過,要如此,還得先將自己打開,將學問打開。
將自己打開,是不泥於己,如此才能與境相應,眼界一換,所見就有不同;將學問打開,是不受限於法,回眸一望,乃滿目青山。如此,於人於境,不畫地自限,自然開闔自如,寫史論人,對境應緣,就有不同氣象。
氣象是眼界、是格局、是丘壑,但較諸於此,它更有一番吞吐,可以周彌六合,可以退藏於密,無論橫說豎說,總有一番氣度、一番生機。
所以說,「富貴逼人」只是大千有時外顯的相,「氣象萬千」才是他的根本。在畫能不泥於法,從工筆臨摹到潑墨潑彩,從冊頁到通屏,就都能大小無礙,隨意進出。尋常說:人能大氣所以不俗,這大氣不是疏狂,而是開闔的氣象。
論藝,要氣象;看人,更得看氣象。畢竟,藝之一事,盡可舉生命之一端,將之極致,就能奪人眼目。而人,卻必得全體契入,才有真正的生命成就可言。
生命富於氣象,山河大地乃盡是文章;生命缺乏氣象,就只能封閉自持,顧影自憐。一個時光推移,益見豐富圓熟,一個則愈憤世酸腐,總覺老天為何獨薄於己,高低之間,乃愈差愈大。我們看少時同負才情的兩人,其後處境卻有天淵之別,關鍵常就只在這生命氣象的有無之上。
人如此,由人構成的歷史更如此。一個時代能否有其氣象,決定了這時代的成就,不從這入手,巨大的史料就變成永遠的負擔,別說尋章逐句可以累死多數人,即便有所梳理,也早就遠離了那時代的精神,更無益於當下的生命。
可惜的是,多少年來,我們寫人、論史,卻早就忘卻了這氣象。
忘卻氣象,正因早已缺乏氣象,而關鍵,就在宋代。
宋代有高度的文明成就原不待言,它是六朝隋唐以降胡化的終結者,這漢本土文化的復興本非壞事,但可惜走過了頭,走到絕對的夷夏之辨,周之後傳入的東西乃盡歸於須闢而廢之的胡物。於是在宋,你就看到:
雅樂要回復先秦,卻完全忽略了秦火之後,其原貌已難辨析,就一個黃鐘音高為何,可以聚訟千年。
琴家說彈琴一有琵琶音,終生難入古矣!於是以幽微淡遠為宗,最終,連扁舟五湖,一蓑江表,滿頭風雨,以心中之波濤映水雲之翻騰,具現中國式交響的《瀟湘水雲》,在明代最著名的虞山派琴譜中也因其「音節繁複」而不錄。
宋明理學援佛入儒,但罵起佛家,就像批楊墨:「出家,無父也,沙門不敬王者,無君也。無父無君者,禽獸也」,這等罵法,何只粗陋,更已似潑婦無賴之流了。
也所以,日本人比對五代編的《舊唐書》與歐陽修主編的《新唐書》,乃發覺《舊唐書》中一千一百多筆的佛教資料在《新唐書》中竟就不見,畢竟,面對「無父無君」的佛教,這等刪法還算客氣的呢!
以此,儘管宋有高度的文化成就,但這成就卻可看成在胡化下沉潛待發的奮力一擊,一擊之後,卻就每下愈況了。
每下愈況是因沒了氣象,在此,嚴的何只是夷夏之辨,還是雅俗之辨、正邪之辨,這影響對後世既深且遠,於是:
宋之後,標舉生死事小,失節事大,人須嚴合禮教,由此,除了花燈、秧歌、民俗慶典外,中國人已不能隨意舞動肢體,細膩的舞蹈只能在戲曲中尋,而能有這個出口,還因演員扮演的是別人。
中國的琵琶是歷史中唯一能與琴相頡頏消長的樂器,在唐是橫抱撥彈,至明已直抱手彈,還發展出相信是今曲〈十面埋伏〉前身的〈楚漢〉一曲,其器樂化已臻巔 ,這轉變何其之大!更是胡樂中國化的最好例證,但四五百年間竟無相關的琵琶史料,只因琵琶不僅是胡樂,還是俗樂!
而也就因宋儒的闢佛,即便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千年,民間甚而「家家彌陀,戶戶觀音」,談起佛家,許多儒門中人到今天第一句也還是:「佛教不是中國固有的宗教」。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而就因畫起圈圈,自擬正朔,缺了那吞吐開闔的氣象,所以,於書畫,即便文人多所寄寓,不乏大家,但真能開闔者,也常須於逸於格外者尋;於陶瓷,宋雖顯其底氣,至元明卻僅能但探幽微,到清,則幾乎只餘玩物喪志;於音樂,則宋之前固灰飛煙滅,宋後則雅俗嚴分,難出大氣;於文學,則宋詞、元曲、明之小品文,皆極盡美言,卻都少見酣暢;於思想,則文人之生活,儘管多出入三家,檯面卻只能標舉儒門,此儒門還愈不可親,最後士子就只能完全匍匐於科舉之下,學問也只能死於句中;而中國人不再舞動肢體,居敬最直接的結果竟就是逐漸僵化的身體與想法。
所以說,這氣象的有無、盛衰,才是了解中國千年以降文化變遷、生命轉折的關鍵,但要識得此,卻必須跳開宋文化成就帶給我們的慣性與迷思。換句話說,談人論史,談者的本身就非得具備那吞吐古今的氣象不可。
而老實說,仁明的這本書是有這點氣象的!
這氣象,出現在談儒的孔子九章上,孔子本身就具氣象,他當過大官,門人三千,雖不致三教九流,但來處不一,情性各異,他周遊列國,要面對每次的不可預期,有南子者還相中他,怎麼說,他都不像後世供奉的那種人。
這氣象,直擊宋儒的可敬不可親,但更回歸了做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孔子及其弟子的可能樣貌,使我們讀來,竟覺如 斯人,《論語》、《史記.孔子世家》的每一章句,竟也變得如此可親。
這些篇章量既不多,篇亦不長,但不只內容,文字的本身就體現了一種與孔門直通的氣象,形式論辯幾乎沒有,娓娓道來卻總神氣十足,坦白說,能如此談孔,談得如此直接,如此不死於句下者,怕極難找!而談的是儒,卻及於其他,讀史論學,仁明的文風,相應的正是中國人那具象直抒的風格。
就因這具象直抒,他談宋儒的概念化,乃不致墮在概念裡與之交鋒;而也因此,在全書中,他屢次述及當代知識分子,包含一些誠懇博學,具反思,乃至力圖實踐者其學問及生命的局限時,也特別清朗易讀。原來,雖從古老的中國走出,這些人卻一樣走入了那概念化,那不可親,那只探生命幽微,卻乏趣味、乏江湖、乏活潑乾坤的老路。
這樣的書,從講方法、談概念的看來,既主觀又沒學問,但講方法談概念不正是當前學問最大的異化麼談禪之教學,我總喜歡舉下面的應答: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參投子,問:「祖師言句如家常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麼?」
子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堯舜禹湯也無?」
的確,天子下敕,自說即為君命,何須假借權威,反觀當代學界,言必談出處,卻從不問那原典如何產生,既為句下之徒,當然難以言那應緣而發的第一義。
而也正因祖師言句都從自己胸襟流出,所以即便蓋天蓋地,卻總如尋常家飯般親切。同樣,真具氣象者,其言儘管超乎慣性,筆下縱有王者之氣,卻因不假藉權威,不尋章逐句,不撥弄概念,不執著形式,也總令人覺得可親,尋常人乃可在此無隔,在此印證。而離了這親切,不要說難直指那生命學問的大義,首先異化的也就是言說者本人。
原來,學問無它,惟在氣象。你能以生命氣象對歷史氣象,以氣象之筆舉氣象之人,談史論事,為學說藝,何須雄辯再三,何須部繁帙重,平常道來,就有一番自家風光。
林谷芳
序
素看孔子
如果把《論語》當成一部上乘的小說來看,如何?讀完薛仁明《孔子隨喜》,我感謝作者提供了這樣一個視角,可以看小說一樣的看《論語》。
視角一轉換,彷彿取得通關密碼般,突然間,都看懂了。那些原先緘默似石看來全部一個樣的古人突然間,你說我說,連語氣、連舉止、連性格、連身世背景、連他們的命運,一一清晰到像《紅樓夢》裡寫出的百樣人,每一個都難忘。
小時候看《紅樓夢》,看劇情的只關心寶黛戀情。稍長後看熱鬧,挑愛看的章篇看,王熙鳳辦秦可卿喪事的那種場面調度,真好看。晴雯撕扇,病補孔雀裘。講話大舌頭的史湘雲,喝醉了睡在芍藥裀上。有人認同薛寶釵的世故明理,探春爽利有英氣,鴛鴦好蘊藉大方。便是代表儒家堅固系統的賈政,在我們年過半百閱世堪多後,始能明白脂胭齋所批賈政之為人物,「有深意存焉。」李渝一篇文章〈賈政不作夢〉這麼說,「是賈政,扶養寶釵母子;是賈政,攜賈母和黛玉的靈柩歸葬南鄉;是他,送別了寶玉。只有賈政可以撫慰生者,安息逝者,讓離者心安地離去。如果寶玉承盡了愛和哀,賈政擔盡了事和責。」
沒有賈府,不會有大觀園之夢。沒有賈政做為磐石的大觀園,不會有寶黛晴雯這些逆叛之花開出牆外。賈政的存在,是要有點年紀之後才會注意得到吧。
薛仁明寫孔子,眾弟子裡他跟孔子一樣特別鍾愛顏回,不說孔孟,只說孔顏,顏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夠達到的人格狀態。然而顏回,我很介意孔子曾說:「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年輕時候我們受教於胡蘭成,跟妹妹朱天心不同,我對胡老師的一切言行誨喻,無所不悅。這在我,永遠是受益的一方。但對胡老師一方,我於他其實是無所助益的。審視這點,我仍耿耿於懷。
把孔子寫成小說,有日本小說家井上靖。我知道唐諾以前想寫,從子貢的觀點切入(聽聞已經有人這麼做也出版了)。子貢是商人,與孔門最異質,又夠聰明,不出手則已,《孔子家語》裡記載他一出手而亂齊、存魯、強晉、弱吳、霸越,儼然戰國時代縱橫家的先驅。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子貢隨行半程。孔子死後,他廬墓三年,又三年。《史記》寫最後一位見孔子的人是子貢,孔子負杖逍遙於門,看到子貢說:「賜,汝來何其晚也?」接著的一段對話,極為動人。子貢若做為一名敘事者,也許更能看到差異,而揭開的面相因此會更多樣,複雜和豐富。
三十餘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遊淺草觀音寺,胡老師指看寺壇上兩柱字,談起能樂的舞姿猶如此:
佛身圓滿無背相,
十方來人皆對面。
這兩句講修行,修得人事物,照面即見,沒有隔障。當然這兩句也可以拿來說孔子的因材施教,一對一的,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孔子隨喜》,在當代,在兩千五百年後,亦自是一份。
朱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