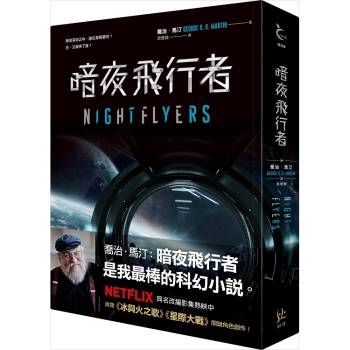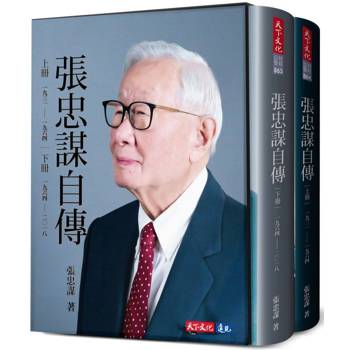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回到五○年代:五○年代的克難生活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187 |
小說/文學 |
$ 198 |
中文現代文學 |
$ 213 |
文學作品 |
$ 220 |
中文書 |
$ 220 |
現代散文 |
$ 225 |
作家傳紀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回到五○年代:五○年代的克難生活
內容簡介
「五○年代」對隱地來說,雖然遙遠,卻是他血液裡難忘的記憶,那段屬於十三到二十二歲的青少年時光。從三、四十年代戰爭烽火中走過來的人們,那些克難歲月的點滴,空氣中飄送著周璇、白光的歌聲……看看隱地如何述說這段既貧乏又豐富的五○年代歷史吧。
目錄
回到五 年代
︱五 年代的克難生活(︱)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代序) 三
輯一
五 年代的克難生活一五
五 年代的臺北二三
一畝文學田二八
五 年代的叫賣聲三一
五 年代之最三四
臺灣文壇的開拓者四一
縫補一個年代四九
輯二
潰敗的一九四九年五七
附錄
一個臺籍美少年的故事六一
一九四九年其他重要紀事六五
輯三
一九五○年,余紀忠創辦《徵信新聞》七三
一九五一年,王惕吾創辦《聯合版》八六
一九五二年,「五陵少年」余光中出新書九三
一九五三年,高雄出現一家大業書店一
附錄
初到臺灣的歲月 吳東權一 七
一九五四年,胡金銓首次當演員一一九
一九五五年,林海音出版第一本書一三
一九五六年,牛哥李費蒙的年代一三五
一九五七年,姜貴出版長篇小說《旋風》一四一
一九五八年,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長一四七
一九五九年,尉天驄開始辦《筆匯》一五五
附錄
回望我的一九五九年一六二
輯四
七○年代接龍一六七
輯外輯
招喚師魂一七九
郭明福 從一篇小說看克難年代的容顏一八五
張小鳳 煤球一八九
附錄
屬於我的年代備忘錄二一
魯雅 小評《回到七 年代》二一二
︱五 年代的克難生活(︱)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代序) 三
輯一
五 年代的克難生活一五
五 年代的臺北二三
一畝文學田二八
五 年代的叫賣聲三一
五 年代之最三四
臺灣文壇的開拓者四一
縫補一個年代四九
輯二
潰敗的一九四九年五七
附錄
一個臺籍美少年的故事六一
一九四九年其他重要紀事六五
輯三
一九五○年,余紀忠創辦《徵信新聞》七三
一九五一年,王惕吾創辦《聯合版》八六
一九五二年,「五陵少年」余光中出新書九三
一九五三年,高雄出現一家大業書店一
附錄
初到臺灣的歲月 吳東權一 七
一九五四年,胡金銓首次當演員一一九
一九五五年,林海音出版第一本書一三
一九五六年,牛哥李費蒙的年代一三五
一九五七年,姜貴出版長篇小說《旋風》一四一
一九五八年,胡適任中央研究院長一四七
一九五九年,尉天驄開始辦《筆匯》一五五
附錄
回望我的一九五九年一六二
輯四
七○年代接龍一六七
輯外輯
招喚師魂一七九
郭明福 從一篇小說看克難年代的容顏一八五
張小鳳 煤球一八九
附錄
屬於我的年代備忘錄二一
魯雅 小評《回到七 年代》二一二
序
|《回到五年代》代序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
人生在世,有誰敢說自己不是一個擺盪者?
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的故事,不管偉大或渺小,在人生大道上,或長或短,誰能逃得過喜怒哀樂?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有亮的時候,而暗,不論暗夜哭泣,或暗自偷笑,暗,經常主宰著人的生命。
人人追求「亮」,只因我們都「暗」著,衝破「暗」,終於見到「亮光」,而繼續往前,怎麼又出現一團「暗黑」?
這就是人生。
人活於世,總是在「要」|要吃、要喝、要錢、要名、要睡,還要愛的撫慰。
是的,愛的撫慰。
索愛的人,經常在獲得愛,或得不到愛的同時,卻露出了厭倦或恨|於是人間永見糾纏不清|糾纏不清的愛與恨。
人在糾纏中,就進入了暗黑中。人的一生,總是失望多,快樂少,因為人的貪欲,人有那麼多七情六慾,不論基督耶穌或釋迦牟尼,無論阿拉或任何一個神,或管你老天爺還是上帝,他們都像頭頂上的太陽,總在給我們光和溫暖,但人,一個希望接連一個希望,即使得到了滿足和滿意,不久,卻又產生了新的希望,新的索求。
索「光」的人,卻不以荷「光」予人。如此貪婪,如此吝嗇,當然,會感覺自己的「光亮」不夠,而「暗黑」之路,卻接連出現……
何況,個人命運又緊緊繫在大時代的神祕運轉之間,人,活一生,能掌控自己命運的又是誰?
書之命運,一如人。
寫《回到七○年代》,是自己的主意。寫完,即一本書的完成。接下去,會寫什麼,或不寫什麼,有時,創作者也迷惘。
就在此時,收到好友文義寄來新書|《夜梟》。打開書,當然先讀主題篇名〈夜梟〉,讀完,立即會心會意,這是他為小說家王定國而寫的文章|兩個夜裡睡不著的寫作者,靠電話說夢的人,穿過友誼光,在許多年許多年後,兩隻夜梟還無比親炙地由心出口,吟詠著川端康成小說開頭名句:
穿過縣境漫長的隧道就是雪國……
接著又讀他為悼念文友黃武忠而寫的〈七葉〉|
一九七六年,作家王鼎鈞因《幼獅文藝》總編輯王慶麟(弦)赴美深造,代其主持「幼獅」編務,其時位於臺北市漢中街萬國戲院斜對面三角街口的紅磚樓大一樓是幼獅書店,三樓編輯部人才濟濟,鼎公帶領的編輯部高人輩出|
沈謙、周浩正、孫小英、詹宏志、黃武忠、何傳馨……
讀畢,突有奇想,寫信向其邀稿,吾兄熟悉文壇,接我《回到七○年代》,來寫一本《回到八○年代》如何?
熱情如他,兩天即收到一張印有中華航空公司飛機的明信片,要我自己續寫,才會有其一貫性……就是這樣,被文義挑起,才有了這本《回到五○年代》。
不是明明說要寫「八○年代」嗎?為何變成了「五○年代」?
噢,「八○年代」爾雅還在高峰上,寫「八○年代」何其容易,可也最難,倒是「五○年代」於我遙遠,卻也是潛伏在血液裡的記憶,那是屬於我十三到二十二歲的青少年時光,不趕快把記憶拉回來,記憶會像傳真紙,放久了,傳真紙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幅圖……顏色都會逐漸消失……最後字跡和影像都不見了……
於是我又展開對五○年代的搜尋,開始重讀所有和五○年代有關的書籍,甚至還因書名的吸引,向應鳳凰借來了葉石濤的《一個臺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書怎麼讀得完,五○年代是貧乏而又豐富的年代,還穿透著自三○年代、四○年代而來的周璇、姚莉和白光的歌聲,戰爭之火毀滅的燒傷,還在許多人的心頭隱隱抽痛,而五○年代末︱一顆對美式物質生活渴望和追求自由的新夢已在每個人心田抽芽,這種時代音貌,我能否以自己手握的簽字筆表達於萬一,就看同樣和我走來以及追步在後的朋友能瞭然於絲毫,就等讀者諸君告訴我了,是為序。
追記
寫完自序,心裡似乎還有幾句話想說:
●本書破了我個人寫作紀錄,從提筆到完成,約三個月。速度讓我自己也難以相信。
●這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只要坐下來,腦海裡就會出現五○年代的畫面,但我以二○○頁上下自我設限,何況我已「入戲太深」,如無止境寫下去,生活無法恢復正常秩序。
●寫作本書有點像答填充題,經常午夜醒來突然想起一條立即添補。一本書就像吹氣球般,每天厚一點胖一點,眼看著五十頁、七十五頁、九十六頁、一三八頁……但日日夜夜活在五○年代,也會迫使人發瘋,趕快收筆,還是讓我返回二○一六年吧!
●一本書前後九校,幸虧是自己的出版社,誰也不可能接我這種邊寫邊發的稿件。龍虎排版公司的朋友不厭其煩的修排,讓我完成一個夢。感恩在心。
●為了營造五年代的氛圍,書中借用兩篇文章,謝謝東權學長和小鳳,同意轉載,為本書增光。
●更要謝謝好友郭明福前後幫我校對兩遍。
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
人生在世,有誰敢說自己不是一個擺盪者?
生是偶然,死是必然。人的故事,不管偉大或渺小,在人生大道上,或長或短,誰能逃得過喜怒哀樂?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有亮的時候,而暗,不論暗夜哭泣,或暗自偷笑,暗,經常主宰著人的生命。
人人追求「亮」,只因我們都「暗」著,衝破「暗」,終於見到「亮光」,而繼續往前,怎麼又出現一團「暗黑」?
這就是人生。
人活於世,總是在「要」|要吃、要喝、要錢、要名、要睡,還要愛的撫慰。
是的,愛的撫慰。
索愛的人,經常在獲得愛,或得不到愛的同時,卻露出了厭倦或恨|於是人間永見糾纏不清|糾纏不清的愛與恨。
人在糾纏中,就進入了暗黑中。人的一生,總是失望多,快樂少,因為人的貪欲,人有那麼多七情六慾,不論基督耶穌或釋迦牟尼,無論阿拉或任何一個神,或管你老天爺還是上帝,他們都像頭頂上的太陽,總在給我們光和溫暖,但人,一個希望接連一個希望,即使得到了滿足和滿意,不久,卻又產生了新的希望,新的索求。
索「光」的人,卻不以荷「光」予人。如此貪婪,如此吝嗇,當然,會感覺自己的「光亮」不夠,而「暗黑」之路,卻接連出現……
何況,個人命運又緊緊繫在大時代的神祕運轉之間,人,活一生,能掌控自己命運的又是誰?
書之命運,一如人。
寫《回到七○年代》,是自己的主意。寫完,即一本書的完成。接下去,會寫什麼,或不寫什麼,有時,創作者也迷惘。
就在此時,收到好友文義寄來新書|《夜梟》。打開書,當然先讀主題篇名〈夜梟〉,讀完,立即會心會意,這是他為小說家王定國而寫的文章|兩個夜裡睡不著的寫作者,靠電話說夢的人,穿過友誼光,在許多年許多年後,兩隻夜梟還無比親炙地由心出口,吟詠著川端康成小說開頭名句:
穿過縣境漫長的隧道就是雪國……
接著又讀他為悼念文友黃武忠而寫的〈七葉〉|
一九七六年,作家王鼎鈞因《幼獅文藝》總編輯王慶麟(弦)赴美深造,代其主持「幼獅」編務,其時位於臺北市漢中街萬國戲院斜對面三角街口的紅磚樓大一樓是幼獅書店,三樓編輯部人才濟濟,鼎公帶領的編輯部高人輩出|
沈謙、周浩正、孫小英、詹宏志、黃武忠、何傳馨……
讀畢,突有奇想,寫信向其邀稿,吾兄熟悉文壇,接我《回到七○年代》,來寫一本《回到八○年代》如何?
熱情如他,兩天即收到一張印有中華航空公司飛機的明信片,要我自己續寫,才會有其一貫性……就是這樣,被文義挑起,才有了這本《回到五○年代》。
不是明明說要寫「八○年代」嗎?為何變成了「五○年代」?
噢,「八○年代」爾雅還在高峰上,寫「八○年代」何其容易,可也最難,倒是「五○年代」於我遙遠,卻也是潛伏在血液裡的記憶,那是屬於我十三到二十二歲的青少年時光,不趕快把記憶拉回來,記憶會像傳真紙,放久了,傳真紙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幅圖……顏色都會逐漸消失……最後字跡和影像都不見了……
於是我又展開對五○年代的搜尋,開始重讀所有和五○年代有關的書籍,甚至還因書名的吸引,向應鳳凰借來了葉石濤的《一個臺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書怎麼讀得完,五○年代是貧乏而又豐富的年代,還穿透著自三○年代、四○年代而來的周璇、姚莉和白光的歌聲,戰爭之火毀滅的燒傷,還在許多人的心頭隱隱抽痛,而五○年代末︱一顆對美式物質生活渴望和追求自由的新夢已在每個人心田抽芽,這種時代音貌,我能否以自己手握的簽字筆表達於萬一,就看同樣和我走來以及追步在後的朋友能瞭然於絲毫,就等讀者諸君告訴我了,是為序。
二○一六年九月十四日莫蘭蒂強颱清晨
追記
寫完自序,心裡似乎還有幾句話想說:
●本書破了我個人寫作紀錄,從提筆到完成,約三個月。速度讓我自己也難以相信。
●這是一本沒有寫完的書;只要坐下來,腦海裡就會出現五○年代的畫面,但我以二○○頁上下自我設限,何況我已「入戲太深」,如無止境寫下去,生活無法恢復正常秩序。
●寫作本書有點像答填充題,經常午夜醒來突然想起一條立即添補。一本書就像吹氣球般,每天厚一點胖一點,眼看著五十頁、七十五頁、九十六頁、一三八頁……但日日夜夜活在五○年代,也會迫使人發瘋,趕快收筆,還是讓我返回二○一六年吧!
●一本書前後九校,幸虧是自己的出版社,誰也不可能接我這種邊寫邊發的稿件。龍虎排版公司的朋友不厭其煩的修排,讓我完成一個夢。感恩在心。
●為了營造五年代的氛圍,書中借用兩篇文章,謝謝東權學長和小鳳,同意轉載,為本書增光。
●更要謝謝好友郭明福前後幫我校對兩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