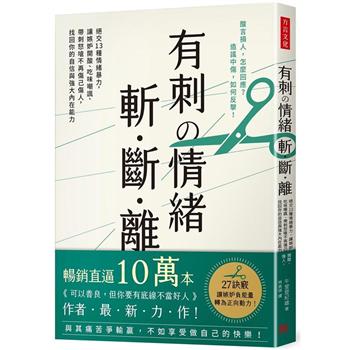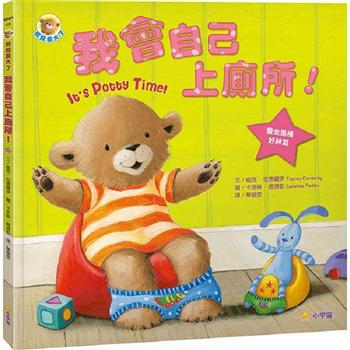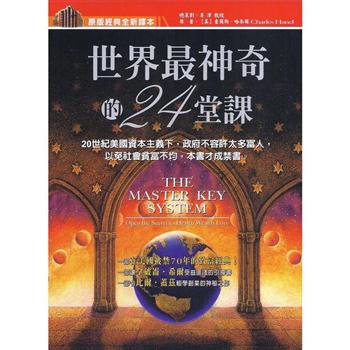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人生畢旅的圖書 |
 |
人生畢旅:照亮我人生旅途的光芒 出版社:爾雅 出版日期:2017-02-0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88頁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0 |
小說/文學 |
$ 182 |
中文現代文學 |
$ 196 |
文學作品 |
$ 202 |
中文書 |
$ 202 |
現代散文 |
$ 207 |
作家傳記 |
$ 207 |
作家傳紀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人生畢旅
內容簡介
一位位耳熟能詳的名字:鄭林鐘、郭泰、蔡志忠、黃明堅、老瓊、高信疆、張敏敏、沈登恩……個個都是奇人異士,在周浩正筆下,成為一個個驚嘆號,難怪被隱地譽為「出版界奇葩」。這本《人生畢旅》不只照亮周浩正的人生旅途,也同時照亮了我們的前方,讓我們在文學花園裡又多了一朵奇花。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周浩正寫編年表
周浩正
筆名周寧,出生於江南小鎮︱南翔。九歲時,因戰亂之故,隨母經香港赴臺與父親團聚,並在臺灣順利完成學業。曾就讀於臺北市中正國小、長安國小(與妻子孫志寧均為第一屆畢業生)、師大附中、文山高中、陸軍官校。
一九七四年自軍中退役後,由楚戈引薦,得結識 弦,進「華欣文化事業中心」,開啟了他文化工作生涯,直到二○○三年四月退休。
近三十年的編輯生涯,停留過的地方不少,計有「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書評書目》、「幼獅文化公司」、「僑聯公司《新少年》」、《臺灣時報》、《中國時報》、《新書月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遠流出版公司」、「正中書局」等十幾個地方。其間,也曾與友朋合資創辦「楓城出版社」「長鯨出版社」和「實學社」。
在職場上,他從最基層的編輯開始歷練,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曾經做過出版社的叢書編輯、報紙副刊及雜誌主編﹔由編輯、主編、總編輯、顧問等不一而足。至於他這一生究竟有些什麼經驗教訓,能寫的,他已全寫入《編輯力初探1.0/寫給編輯人的信》、《企劃之翼》及《人生畢旅》裡了。
一九四一
.出生於江蘇省嘉定縣南翔鎮(現已劃歸上海市)。
一九四九
.因戰亂,隨父母遷臺,就讀於臺北中正國小。
一九七○
.結婚(妻孫志寧)。
一九七四
.自軍中(少校軍階)退伍。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編輯。
一九七五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暨「書評書目」編輯。
.加入新竹「楓城書店」,成立「楓城出版社」。
一九七六
.出版文學評論集《橄欖樹》(書評書目出版社出版)。
.應弦之邀,成為「幼獅文化中心」編輯,與孫小英、朱榮智、詹宏志、劉嵩等人共同籌備《幼獅少年》雜誌創刊事宜。
一九七七
.應唐達聰之邀,參與《王子半月刊》的改版工程。
.成立「長鯨出版社」。
.創辦文學雜誌《小說新潮》(雙月刊,沈登恩出資支持)。
一九七九
.籌備《新少年》創刊。
一九八○
.《臺灣時報》副刊主編。
一九八一
.編選《飛揚的一代》(九歌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二
.因詹宏志引薦,任《中國時報》(美洲版)副總編輯,負責副刊籌劃工作。1
一九八三
.《新書月刊》總編輯。
.主編《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爾雅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五
.應張武順邀請,出任「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副總經理兼總編輯。
一九八六
.「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
一九九一
.主編《七十九年短篇小說選》(爾雅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三
.「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總監。
一九九四
.被金石堂書店《出版情報》選為一九九三年出版界「年度風雲人物」。
.與郭泰、簡媜等十餘人成立「實學社」。
一九九五
.設立「羅貫中歷史小說創作獎」(首獎獎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一
.「實學社」併入「遠流出版公司」。
.出任「正中書局」顧問(楊茂秀推薦予單小琳總經理)。
二○○三
.退休。
二○○四
.四月,開始撰寫〈給編輯人的信〉,初期發表於陳穎青的「老貓學出版」網站。
二○○五
.〈給編輯人的信〉得二十九篇,編成《編輯力初探1.0》數位檔,張貼於「聯合數位閱讀網」、「圖文閱讀網」及「博達版權公司」網站。
二○○六
.十二月,臺北「文經社」將《編輯力初探.》第一至三十一信打散重組,以《編輯道》為書名出版。
二○○七
.《編輯力初探1.0》續寫至三十四篇。
二○○八
.三月,北京「金城出版社」朱策英先生根據《編輯力初探1.0》前三十四信內容,整理成《優秀編輯的四門必修課》出版。
.《編輯力初探1.0》續寫至第四十五篇。
二○○九
.七月十七日,《編輯力初探1.0》寫至第五十一篇,告一段落。
.八月七日,赴「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割除腮腺腫瘤。
.九月,開始撰寫《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
二○一二
.九月,撰寫《編輯檯上的小確幸》。
.十月,《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寫到第十七信。
二○一四
.三月.《編輯檯上的小確幸》寫到第三十二則。
二○一五
.三月,將《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重新整理為《企劃之翼》,分成起、承、轉、合四卷。
二○一六
.四月.北京「金城出版社」將餘信結集成《如何提高編輯力》出版。
二○一六
.六月,開始撰寫「人生畢旅」系列。
二○一七
.二月,爾雅出版《人生畢旅》。
周浩正寫編年表
周浩正
筆名周寧,出生於江南小鎮︱南翔。九歲時,因戰亂之故,隨母經香港赴臺與父親團聚,並在臺灣順利完成學業。曾就讀於臺北市中正國小、長安國小(與妻子孫志寧均為第一屆畢業生)、師大附中、文山高中、陸軍官校。
一九七四年自軍中退役後,由楚戈引薦,得結識 弦,進「華欣文化事業中心」,開啟了他文化工作生涯,直到二○○三年四月退休。
近三十年的編輯生涯,停留過的地方不少,計有「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書評書目》、「幼獅文化公司」、「僑聯公司《新少年》」、《臺灣時報》、《中國時報》、《新書月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遠流出版公司」、「正中書局」等十幾個地方。其間,也曾與友朋合資創辦「楓城出版社」「長鯨出版社」和「實學社」。
在職場上,他從最基層的編輯開始歷練,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曾經做過出版社的叢書編輯、報紙副刊及雜誌主編﹔由編輯、主編、總編輯、顧問等不一而足。至於他這一生究竟有些什麼經驗教訓,能寫的,他已全寫入《編輯力初探1.0/寫給編輯人的信》、《企劃之翼》及《人生畢旅》裡了。
一九四一
.出生於江蘇省嘉定縣南翔鎮(現已劃歸上海市)。
一九四九
.因戰亂,隨父母遷臺,就讀於臺北中正國小。
一九七○
.結婚(妻孫志寧)。
一九七四
.自軍中(少校軍階)退伍。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編輯。
一九七五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暨「書評書目」編輯。
.加入新竹「楓城書店」,成立「楓城出版社」。
一九七六
.出版文學評論集《橄欖樹》(書評書目出版社出版)。
.應弦之邀,成為「幼獅文化中心」編輯,與孫小英、朱榮智、詹宏志、劉嵩等人共同籌備《幼獅少年》雜誌創刊事宜。
一九七七
.應唐達聰之邀,參與《王子半月刊》的改版工程。
.成立「長鯨出版社」。
.創辦文學雜誌《小說新潮》(雙月刊,沈登恩出資支持)。
一九七九
.籌備《新少年》創刊。
一九八○
.《臺灣時報》副刊主編。
一九八一
.編選《飛揚的一代》(九歌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二
.因詹宏志引薦,任《中國時報》(美洲版)副總編輯,負責副刊籌劃工作。1
一九八三
.《新書月刊》總編輯。
.主編《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爾雅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五
.應張武順邀請,出任「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副總經理兼總編輯。
一九八六
.「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
一九九一
.主編《七十九年短篇小說選》(爾雅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三
.「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總監。
一九九四
.被金石堂書店《出版情報》選為一九九三年出版界「年度風雲人物」。
.與郭泰、簡媜等十餘人成立「實學社」。
一九九五
.設立「羅貫中歷史小說創作獎」(首獎獎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二○○一
.「實學社」併入「遠流出版公司」。
.出任「正中書局」顧問(楊茂秀推薦予單小琳總經理)。
二○○三
.退休。
二○○四
.四月,開始撰寫〈給編輯人的信〉,初期發表於陳穎青的「老貓學出版」網站。
二○○五
.〈給編輯人的信〉得二十九篇,編成《編輯力初探1.0》數位檔,張貼於「聯合數位閱讀網」、「圖文閱讀網」及「博達版權公司」網站。
二○○六
.十二月,臺北「文經社」將《編輯力初探.》第一至三十一信打散重組,以《編輯道》為書名出版。
二○○七
.《編輯力初探1.0》續寫至三十四篇。
二○○八
.三月,北京「金城出版社」朱策英先生根據《編輯力初探1.0》前三十四信內容,整理成《優秀編輯的四門必修課》出版。
.《編輯力初探1.0》續寫至第四十五篇。
二○○九
.七月十七日,《編輯力初探1.0》寫至第五十一篇,告一段落。
.八月七日,赴「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割除腮腺腫瘤。
.九月,開始撰寫《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
二○一二
.九月,撰寫《編輯檯上的小確幸》。
.十月,《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寫到第十七信。
二○一四
.三月.《編輯檯上的小確幸》寫到第三十二則。
二○一五
.三月,將《實作編輯心法練習簿》重新整理為《企劃之翼》,分成起、承、轉、合四卷。
二○一六
.四月.北京「金城出版社」將餘信結集成《如何提高編輯力》出版。
二○一六
.六月,開始撰寫「人生畢旅」系列。
二○一七
.二月,爾雅出版《人生畢旅》。
目錄
出版界的奇葩/隱地.
緣起.
〔光芒之源〕貴人隱地
爾雅,文學人嚮往之所.
〔光芒之源〕有他,事就順了。
人人需要的「企劃才」鄭林鐘.
〔光芒之源〕智慧獵人
非等閒人物:郭泰.
附:郭泰訪周浩正.
〔光芒之源〕狂熱分子
與蔡志忠的人生邂逅.
〔光芒之源〕生命,不空過。
「做自己」的黃明堅.
〔光芒之源〕沒人能忘記她
「四格漫畫」開拓者:老瓊.
〔光芒之源〕紙上風雲第一人
「顛覆者」高信疆.
〔光芒之源〕敢先生
「小巨人」沈登思.
〔光芒之源〕那些陽光燦爛的日子!
憶老友姜渝生.
記憶流域之內的人與事
.之一:《幻象》推手
才女張敏敏.
.之二:砌了一個小小台階
與《如何提高編輯力》
作者周浩正一夕談/孟凡.
代跋
如癡、如幻、如戲.
緣起.
〔光芒之源〕貴人隱地
爾雅,文學人嚮往之所.
〔光芒之源〕有他,事就順了。
人人需要的「企劃才」鄭林鐘.
〔光芒之源〕智慧獵人
非等閒人物:郭泰.
附:郭泰訪周浩正.
〔光芒之源〕狂熱分子
與蔡志忠的人生邂逅.
〔光芒之源〕生命,不空過。
「做自己」的黃明堅.
〔光芒之源〕沒人能忘記她
「四格漫畫」開拓者:老瓊.
〔光芒之源〕紙上風雲第一人
「顛覆者」高信疆.
〔光芒之源〕敢先生
「小巨人」沈登思.
〔光芒之源〕那些陽光燦爛的日子!
憶老友姜渝生.
記憶流域之內的人與事
.之一:《幻象》推手
才女張敏敏.
.之二:砌了一個小小台階
與《如何提高編輯力》
作者周浩正一夕談/孟凡.
代跋
如癡、如幻、如戲.
序
出版界的奇葩──為浩正《人生畢旅》而寫
在出版圈四、五十年,我以為有關出版幕前幕後的故事,大概八九不離十,多少都知道一些,但等我先後讀了周浩正寫的幾個和出版界相關的人物,才知自己確實和出版這一行很「隔」──出版界藏龍臥虎,「智」者處處,令人讚嘆目眩。
而浩正就是出版界的奇葩。我雖和他相識四十二年,以他平日給我的印象,永遠無法想像,他後來居然成了編輯「鬼才」,「策略」高手,新點子一個接一個,讓人嘆為觀止,難怪成了許多人崇拜的編輯「周爺」。對於編輯,我只是一個編輯,一個永遠的「純」編輯,他卻突然研究起編輯「道」,而且發展出一套言之有物的「編輯學」。他認識的人五花八門,我則只在小小的文學圈打交道。就出版和編輯來說,我只是一條小小的河流,而周浩正是大洋,他是海。
浩正有一支絕妙好筆,我是老早就知道的。一九七二年編《書評書目》初期,我讀到他評七等生的小說,立即為他的健筆迷倒,一九七六年,他的第一本小說評論集《橄欖樹》,就是由我主編的「書評書目出版社」為他出版的。可惜臺灣始終未建立評論制度,如果有固定的書評園地,周浩正絕對是一把好手。
他和我一樣,都曾為臺灣的文學批評和書評努力過。離開《書評書目》後,他獨立主編由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在幕後支持的《新書月刊》,龍應台的《龍應台評小說》書中一篇篇小說批評,全都先在《新書月刊》刊出,浩正貢獻了一座舞台,讓剛從美國歸來的龍應台大展身手、發光發熱,不久,龍應台有了寫「野火」的構想,仍然是周浩正居中牽線,促成在金恆煒主編的「人間副刊」(中國時報)上大篇幅刊出。
可惜《新書月刊》辦了兩年,仍然不支倒地。從此,周浩正南征北伐,他幾乎在大大小小的雜誌界都進出過,也包括出版社。後來他自己也當了老闆,但不久,蓬勃的出版業走入寒冬;他最後創立的「實學社」,雖然出了許多好書,最後還是走上落幕之路。
在這之前,他曾經是遠流三巨頭之一,詹宏志是總經理,王榮文是發行人,周浩正是總編輯,多麼風風火火的年代,他讓「遠流」幾乎成為臺灣出版業的龍頭。
而直到讀了他新寫的一篇近作──〈敢先生──「小巨人」沈登恩〉一文,才知,當年讓沈登恩成為出版界焦點人物的一套《世界文學全集》,原來也是出自他的構想。說周浩正是出版界的「奇葩」,還真不是蓋的。
臺灣出版圈,就我所知,都屬一掛掛,所謂一掛掛,指的是一個個小圈子,而浩正似乎從來不屬任何一掛。可讀完整本《人生畢旅》,又發現原來浩正可屬出版界的「百搭」,他可搭上任何一掛。也算出版界的奇蹟。
不是嗎?當年《王子半月刊》、《新少年》和《幼獅少年》,這些少年讀物,分屬一掛又一掛,而你會發現周浩正和每一掛都有風風水水的關係,他顯然出自他們的每一個團隊,和一夥對少年讀物充滿理想抱負的人,一起為少年讀物打拚──而新竹的楓城出版社,楓城書店,當年在新竹也都有許多死忠讀者,周浩正照樣是為新竹的閱讀風氣獻出過心力的人;還有「時報集團」,那是臺灣出版業的一個大本營,周浩正在《中國時報》美洲版擔任過副總編輯和副刊主編,他當然也屬《中國時報》這一掛,而南部的《臺灣時報》這一掛,他也當過他們的文藝組主任,並且兼副刊主編;至於從「文星集團」出來的林秉欽,等到他自辦「仙人掌」和「金字塔」出版社,又和周浩正攀上了關係,居然放手讓他創辦一本《小說新潮》,而且豪氣的對他說:
「錢的事,歸我;內容的事歸你。」
此外鄭林鐘、郭泰、蔡志忠、黃明堅、老瓊、高信疆、張敏敏……哪一個不是聰明絕頂的智者,且個個奇人異士,在周浩正筆下,成為一個個驚嘆號。
讀《人生畢旅》其實是讀一本智慧商戰之書,爾雅一向自認是一座文學花園,如今多了《人生畢旅》這本奇書,無疑是開了一朵最奇異之花,值得賞花人慢慢流連,「爾雅花園」亦高舉歡迎之手,迎接嘉賓駕臨。我們要好好重新開放,讓大家都讀得開開心心,並心生歡喜,覺得不虛此行。
周浩正雖口口聲聲自稱老了,從我的觀點看來,他仍幹勁十足,且看來熱力四射,透過他的一支好筆,讀者和出版界都需要他,讓我們高呼讀書萬歲!周浩正萬歲!
隱地
代跋
如癡、如幻、如戲
我從職場退下之後,開始書寫編輯生涯之種種,不知不覺中,累積成《編輯力初探.》、《企劃之翼》、《編輯檯上的小確幸》等數十萬字的內容。好事的朋友,曾摘取部分文字改編成《編輯道》(臺北文經社)和《優秀編輯的四門必修課》、《如何提高編輯力》(以上北京金城出版社)三書出版。但,我依戀的仍然是自己初始的文本。
重新找出這篇是我七十歲那年,擔心不能如願寫完,預先寫妥的〈後記:有開始,就有結束。〉(原題)。細心的朋友,或可在行文字句中,理解所有靠自學成為編輯人的心路歷程。
而今,我的人生舞台上演著最後一幕「人生畢旅」,在生、旦、淨、末、丑的角色扮演中,終於享用了這如癡、如戲、如幻的一生。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徐志摩〈再別康橋〉
「儘管人生漫長,履歷表最好簡短」。
──維斯瓦娃.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親愛的朋友:
老實說,我並不想停筆,還有好多話要說,雖然累積了六十多萬字的經驗談,總覺得自己人拙、筆也拙,老搔不到癢處。
但,隨著馬齒徒增,記憶力一天比一天衰退,剛看過的書,放下就忘;有時候,要寫的字即使搜索枯腸也想不出它的長相;每段文字必須一修再修,才修成通順的句子。整封信挖挖補補二、三十次才是現在看到的模樣,而等到網友來信告知疏漏或筆誤之處,又不得不修訂重寄。如今,情況更趨嚴重,書寫時無法集中精神,三、五分鐘就意志渙散了。我心裡有數,應趁著還沒全面失控之前,自行了結。所謂「見好就收」或「見不好就收」──總之,親愛的朋友,這是你最後一次收到我親自(一對一)發送「寫給編輯的信」。
想當初(二○○四年元月)動念寫下這些「私見」,純屬偶然。
整個事情肇因於天津「新蕾出版社」編輯高彥捎來一封討論出版的e-mail,從最初的兩人互動,到後來面對眾人將個人的編輯生涯進行深刻反省。這六年多來,坐在電腦桌前的思考和書寫,充實了退休生活的每一時刻。我必須滿懷感恩的心,向高彥和其他結緣的朋友說:幸虧遇此機緣,能將過去的得失曝曬於陽光底下,細細檢視。在那年代,打了不少仗,卻不知道「為什麼輸或為什麼贏」。現在,有時間把案例從記憶的洞窟裡拖曳出來,用新吸收的知識予以解讀,才恍然大悟──啊,原來如此!
我願意坦誠,當年行走職場,從沒高瞻遠矚的本領。現在有些看法,是當時沒想過的,年輕的我不懂艱險,拿著鍋蓋當鋼盔,靠著「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二楞子精神,橫衝直撞;別人視為畏途的,我敢咬牙蠻幹。做久做多了,從工作和周圍的好榜樣身上,學到不少自己欠缺的新東西。
這些反省編輯經驗的信能夠成篇,最為感念的當是來自詹宏志先生的啟迪,他從不知道曾影響我如此之深。他的年紀比我至少小一輪以上,可是我對出版現代性的認知,得自他的作為。我在旁靜靜觀察、默默學習,把他獨特的行事法則牢記在心。
有一則只跟很少人說過的故事,我願意公開說一次,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意與謝意。
二○○一年,我退休在家。沒料到塵緣未了,經楊茂秀教授推薦,被「正中書局」總經理單小琳女士延攬到公司幫忙。
有一天,單總非常客氣問道:
「我從事教育工作多年,雖然愛讀書,也買了不少書,交了些出版界的好朋友,可是這次獨當一面做出版,仍屬新手,您建議從哪入手,比較能迅速掌握狀況?」
那段歲月,詹宏志的《數位時代》雜誌創刊一年左右,為了增加雜誌店銷時的吸引力,他曾將談出版的演講實況壓成CD片隨著每期雜誌贈送。
我雖是《數位時代》的長期訂戶,卻未得優遇,為了獲得他的演講CD,只好每次再去店頭購買一本當期雜誌保存下來。我向單總說:
「單總,您和詹宏志也相識,但可能沒時間聽他講出版的事,我手中有些他公開對外演講的CD,聽了之後,對出版的現在與未來一定會有新的理解。」
單總高興地借走CD。
隔了一個多星期,她找我去總經理辦公室。
「周顧問,詹先生的CD聽了,這些內容的確讓我對出版有了新的認識。」
接著,我們交換了一些看法,討論正中書局的未來走向。等我起身離開時,她叫住我:
「顧問,您對詹先生既然如此肯定,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假如在臺灣出版界排序的話,在您心裡,他排在什麼位置?」
這並不是個聰明的問題,她如此發問一定有她的道理。
「第一名。」我幾乎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哈,您可是我們專誠請來的顧問噢!那麼,和他相比,您屬第幾呀!」
我有點明白她的用意了,故意伸出兩指,晃了晃,說:「第二名。」
「哦?」她露出訝異的表情,我一時看不出她是失望還是高興。失望的也許認為請來的人居然不是第一名;高興的也許是僅次於第一名。
她又連續問了很多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我通通回答:「第二名」。
這回,她的好奇心被誘發出來了。她促狹地指指自己,問道:「那我呢?」
「第二。」這次回答的又快、又乾脆。
「我也第二?我可才剛加入出版行列呢!」
「對!您、我、他們都是第二。」
「為什麼?」單總顯然頗不以為然。
「因為,我們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相對於我們,詹先生是全方位觀照。」
這則軼事,有人認真聽進去了,有人把它當笑話聽。假使你讀過我書寫的全部內容,或許會同意我的論斷。不過,若不同意,也十分正確。
因為在近三十年的編輯生涯中,我分別在十七個大大小小的單位做過事,最長的地方待了快八年,最短的一天半。從表象看,我應該認識不少人,其實轉來轉去,都在小池子裡打轉。加上天性木訥,既無文釆、不擅言詞又怯於交際,因此識人有限。我相信臺灣出版界比詹宏志優秀的大編輯不在少數,如純文學林海音、爾雅隱地、九歌蔡文甫、天下殷允芃、遠見高希均、王力行、遠流王榮文、《講義》林獻章、圓神曹又方、時報高信疆、莫昭平、大塊郝明義、聯經林載爵、青林文化林訓民、《創世紀》張默……至少可列出一長串名單,他們全是能打天下、治天下的高手,是我長久欽佩的英雄式人物。有些我只敢仰望,不敢攀交;有些似乎該由他們身邊熟識其貢獻的人,予以宣揚。而我,只能說我知道的──當我回答單總的問話時,答案中有兩個前提:一是有範圍的,不是全稱句;一是純屬個人的主觀。
所以,要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另有名字,也非常合理。
我對編輯工作的認知,是有階段性的。
一九七四年,從軍中退伍,緣於喜歡閱讀,偶爾書寫幾篇類似讀後感的評介文字,知遇於《幼獅月刊》朱一冰先生、《幼獅文藝》瘂弦先生、《書評書目》隱地先生,因此得到發表文字和工作的機會,開始了我的編輯生涯。
那時候的我,熱衷於認識心儀的作家,以能爭取到名家之作刊登在自己參與的雜誌為榮,以為這就是編輯該做的事。慢慢的,隨著接觸面擴大,結識層面逐漸繁複多樣。不久,結交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高信疆先生(高公),目睹他和轉任《聯合報》聯副主編瘂弦先生之間的競合關係,深深震撼了我。那一段臺灣副刊史上的黃金歲月,容許千奇百怪的嘗試,使編輯這行業的內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瘂雙雄對峙的局面以及社會深層剛萌芽的革新意識,突破了傳統思維,激起洶湧波濤。尤其是高公與各個階層密切結合,讓編輯透過工作平台,取得不同面向的發言權,幾乎釀成一場社會改造運動。
高公隱退後,副刊又回歸初始素樸的文學模式,已不復當年站在潮流前沿了。但,隨著「開放社會」來臨,轉戰出版界與雜誌界的編輯,仍延續了已內化為本能的創新意識,投入職場。
我就是從那時代背景走過來的受益者。
那些日子裡,在前輩和同儕那裡,偷學到不少「不足與外人道」的各家優點,譬如:朱一冰的誠懇;瘂弦的睿智、圓融、包容而成其大;隱地的編輯創意;小巨人沈登恩的豪氣;殷允芃的「時時以天下為念」、高希均的「引領潮流」、高信疆不從俗的創新與改革魄力;王榮文的人才策略;林獻章的「但取一瓢飲」;張默捨我其誰的無私奉獻……,人人都是我的老師。
從詹宏志身上見識到的,卻是嶄新的遊戲規則。
他常能放眼天下,跳出框框思索。例如在很早很早,以西門町為臺北消費指標的年代,他便寫了文章,預告臺北東區即將崛起;在一九八六年,臺灣出版界從戒嚴氛圍中甦醒,學習如何伸展手腳時,他想的和所有人不一樣,他的注意力已移向「華文出版的單一市場」。他也曾寫過帶著神奇的、預言色彩的《趨勢索隱》,把當時的臺灣放在蒼穹之上,用大倍數望遠鏡觀察,說出他看見的現象及未來發展的趨向。
他的本事,等我看了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創新與創業精神》之後才恍然大悟,他在眾人眼裡預言式的「創見」,在杜拉克的分析中,都不意外。他和杜拉克一樣聰慧,在人口統計、產業與市場結構、新知識……等變因裡,看到新的機會與新的市場。他不是預言家,全是根據數據與蒐集的資料推斷得來的結論。
他老早感悟到中國必將崛起,臺灣如何因應中國崛起?站在這塊土地上的編輯/出版的未來在哪裡?他在遠流內部工作會報時,一再提示「華文出版單一市場的未來將炙手可熱」,我們必須及早準備好參與競賽。
有一回,他接受訪問時說,面對新情勢要有新的認識,認為臺灣出版社的規模太小,小到沒力量在華文市場攻城略地,所以他大膽建議:合併。把「小」聚合成「大」,才有機會在華文領域以及國際競爭場域發揮影響力。在我印象裡,他把「大」的門檻設定在年營業額新台幣二十億,否則一不小心就邊緣化了。
後來,他登高一呼,以「花園主義」糾合有志一同的朋友組成「城邦集團」,不出幾年,發展成大大小小三十多家各擁特色、戰鬥力特強的出版單位,營業額快速成長,果然一一遂其心願,達成傲人的規模化目標。其間,也得到創投者青睞,紛紛注入資金。可惜,原本支持最力、最欣賞詹宏志才華、出資收購「城邦」的香港「TOM集團」(李嘉誠的事業之一),並不了解出版行業──出版是個需要「長期策略」驅動的產業。
一個好的、充滿未來性的長期策略,需要耐心與時間的,這是一種最終有大回報的「守株待兔的經營藝術」。集團缺乏繪製「未來出版地圖」的想像力,因此失去長遠眼光和耐性,成了美國俚語「Don’t be a bean counter. Count on bean bags. (別做數豆子的人,要數就數一袋袋的豆子)」裡那喜歡數豆子的角色。TOM集團放他離開「城邦」,縱虎歸了山。如今,他在界如龍歸大海,事業規模又更上層樓了。
詹宏志在編輯/出版界(包括所謂的「文創產業」)留下的足跡很廣,我記下的只我所知的「局部」和「片面」,但就傳統、古板、底子淺薄的我而言,已經學得非常吃力。
我辛勤筆耕六年,終於到了軀體不堪負荷的時刻了。年過七十,每天醒來都像多賺了一天,為了做事有始有終,理應未雨綢繆,所以先把〈後記〉寫妥,免得到時懊惱。
既然是收尾感言,有些話便不得不說。
首先要聲明的:縱使我寫成六十萬字,千萬別把我當做「作家」,我不是作家,我此生的定位是「編輯」。你們讀到的,是一個垂垂老去的編輯用餘生記下的一些見聞和心得。我常講「編輯有兩種」:一種是寫而優則編,一種是寫而不優則編︱我是後者。所以,請不要以作家的高度審視這些文字,它們不夠格。
再者,誠懇呼籲編輯們在適當時機,寫下各自的經驗。假使每個編輯都肯不怕嘲笑,記下一得之愚,久而久之,後人一定能從成千上萬的經驗紀錄中過濾出有用的東西(幸好網路容得下恆河沙數般的內容)。
至於我寫的這些,難逃偏、狹之嫌,有些讀友基於敬老或憐憫心,寬容的寫些鼓勵的話,但聰明的讀友立刻看出我的不足。有位叫Rory的讀友,讀了金城出版社朱策英先生根據《編輯力初探1.0》(第一─三十四信)編撰的《優秀編輯的四門必修課》,他下的總評,曰:「很營銷。」他敏銳地點出:「這本書感覺更像市場行銷方面的書,只不過主角是書。處處能遇到作者在引用其他管理書或者其他企業的觀點為己用,比如《長尾理論》、《藍海戰略》、《從優秀到卓越》。他把新加坡的成就,把英華達手機企業的市場成功都拿來作為出版借鑒。他的好多靈感似乎都來自於他當時讀的熱門管理書籍。」親愛的朋友,Rory的話完全正確,的確我如其所言,借用各類書籍中的觀念來解釋我並不真正理解──包括我的(和觀察他人而得到的)經驗。很慚愧,我不是原創型的人,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努力學做「撿拾珍珠」的人。
回頭看自己一生,不得不承認:我太幸運了。
基於幸運,我借了石濤的「一畫」,粗疏地建構自我指導的理論;而孫隆基教授的〈勢力均衡場論〉,居然讓我領會競爭的基礎是「不競爭」(開發無人地帶);尼釆的話「對於整個的組織,美麗乃其餘事」,助我建立做事的準則;讀巴斯卡《沉思錄》,明白了正義的歧義性及追求多元價值的必然──書系概念的豐富性也由此得到滋養;何秀煌教授的《0與1之間》,指出兩極性的專斷,人生所擁有的選擇不只是「0」或「1」;我曾小心翼翼地試著把FUZZY理論置入書系運作,合理化內容的抉擇;發現彼得.杜拉克的秘密,他的影響力源自詮釋「正面的力量」……;得自孔子和老莊思想的啟發,更不在話下了。這種化零碎為整體的「百衲衣式的智慧」,幫我克服過不少挑戰。但我並不感到臉紅,因為連華倫.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美國投資大師)這樣頂尖的聰明人也說:「我通常都靠大量閱讀,學習別人的知識和創意,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有很多原創的觀念,我的許多觀點都是從閱讀來的。你可以從別人的書中學到許多東西,而不需要自己花腦筋創造新知,重要的是要會充分從別人身上學來最好的知識。」
就這樣東讀西讀以及自己前半生的一些實際編輯經驗,拼湊出半生不熟的東西,而最後又「內化」成六十多萬字的篇章。了解這些書稿的始末,就明白我為什麼願意快樂的放棄版權並主張這些文字是「公共財」的緣由了。
經驗告訴我,欠缺經驗時需要經驗,有了成熟的經驗後需要忘掉經驗,因為它會成為「成長的阻力」。所以,若干年後,這些文字若能以位元的形態,倖存在虛擬網路世界,就夠幸運了。
年輕時候,讀張愛玲翻譯的《愛默生選集》,記憶中,愛默生曾說:「每個人都是一個小小的宇宙。」
噯喲,親愛的朋友,我愛死了這句話──既然人不分貴賤、貧富、智愚,都擁有各自的小宇宙,那麼,《編輯力初探1.0》、《編輯力檯上的小確幸》與《企劃之翼》就是我小宇宙的「描紅簿」(它連臨摹都還夠不上)。萬一你不小心接觸它,看到顫抖、歪曲、醜陋的描紅筆法時,請多擔待。
終於,我如願記錄了親歷的人生片斷。你的呢?
謝謝大家多年來的愛護與支持,順祝
平安幸福
周浩正
寫於二○一一.一.十二「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之年
在出版圈四、五十年,我以為有關出版幕前幕後的故事,大概八九不離十,多少都知道一些,但等我先後讀了周浩正寫的幾個和出版界相關的人物,才知自己確實和出版這一行很「隔」──出版界藏龍臥虎,「智」者處處,令人讚嘆目眩。
而浩正就是出版界的奇葩。我雖和他相識四十二年,以他平日給我的印象,永遠無法想像,他後來居然成了編輯「鬼才」,「策略」高手,新點子一個接一個,讓人嘆為觀止,難怪成了許多人崇拜的編輯「周爺」。對於編輯,我只是一個編輯,一個永遠的「純」編輯,他卻突然研究起編輯「道」,而且發展出一套言之有物的「編輯學」。他認識的人五花八門,我則只在小小的文學圈打交道。就出版和編輯來說,我只是一條小小的河流,而周浩正是大洋,他是海。
浩正有一支絕妙好筆,我是老早就知道的。一九七二年編《書評書目》初期,我讀到他評七等生的小說,立即為他的健筆迷倒,一九七六年,他的第一本小說評論集《橄欖樹》,就是由我主編的「書評書目出版社」為他出版的。可惜臺灣始終未建立評論制度,如果有固定的書評園地,周浩正絕對是一把好手。
他和我一樣,都曾為臺灣的文學批評和書評努力過。離開《書評書目》後,他獨立主編由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在幕後支持的《新書月刊》,龍應台的《龍應台評小說》書中一篇篇小說批評,全都先在《新書月刊》刊出,浩正貢獻了一座舞台,讓剛從美國歸來的龍應台大展身手、發光發熱,不久,龍應台有了寫「野火」的構想,仍然是周浩正居中牽線,促成在金恆煒主編的「人間副刊」(中國時報)上大篇幅刊出。
可惜《新書月刊》辦了兩年,仍然不支倒地。從此,周浩正南征北伐,他幾乎在大大小小的雜誌界都進出過,也包括出版社。後來他自己也當了老闆,但不久,蓬勃的出版業走入寒冬;他最後創立的「實學社」,雖然出了許多好書,最後還是走上落幕之路。
在這之前,他曾經是遠流三巨頭之一,詹宏志是總經理,王榮文是發行人,周浩正是總編輯,多麼風風火火的年代,他讓「遠流」幾乎成為臺灣出版業的龍頭。
而直到讀了他新寫的一篇近作──〈敢先生──「小巨人」沈登恩〉一文,才知,當年讓沈登恩成為出版界焦點人物的一套《世界文學全集》,原來也是出自他的構想。說周浩正是出版界的「奇葩」,還真不是蓋的。
臺灣出版圈,就我所知,都屬一掛掛,所謂一掛掛,指的是一個個小圈子,而浩正似乎從來不屬任何一掛。可讀完整本《人生畢旅》,又發現原來浩正可屬出版界的「百搭」,他可搭上任何一掛。也算出版界的奇蹟。
不是嗎?當年《王子半月刊》、《新少年》和《幼獅少年》,這些少年讀物,分屬一掛又一掛,而你會發現周浩正和每一掛都有風風水水的關係,他顯然出自他們的每一個團隊,和一夥對少年讀物充滿理想抱負的人,一起為少年讀物打拚──而新竹的楓城出版社,楓城書店,當年在新竹也都有許多死忠讀者,周浩正照樣是為新竹的閱讀風氣獻出過心力的人;還有「時報集團」,那是臺灣出版業的一個大本營,周浩正在《中國時報》美洲版擔任過副總編輯和副刊主編,他當然也屬《中國時報》這一掛,而南部的《臺灣時報》這一掛,他也當過他們的文藝組主任,並且兼副刊主編;至於從「文星集團」出來的林秉欽,等到他自辦「仙人掌」和「金字塔」出版社,又和周浩正攀上了關係,居然放手讓他創辦一本《小說新潮》,而且豪氣的對他說:
「錢的事,歸我;內容的事歸你。」
此外鄭林鐘、郭泰、蔡志忠、黃明堅、老瓊、高信疆、張敏敏……哪一個不是聰明絕頂的智者,且個個奇人異士,在周浩正筆下,成為一個個驚嘆號。
讀《人生畢旅》其實是讀一本智慧商戰之書,爾雅一向自認是一座文學花園,如今多了《人生畢旅》這本奇書,無疑是開了一朵最奇異之花,值得賞花人慢慢流連,「爾雅花園」亦高舉歡迎之手,迎接嘉賓駕臨。我們要好好重新開放,讓大家都讀得開開心心,並心生歡喜,覺得不虛此行。
周浩正雖口口聲聲自稱老了,從我的觀點看來,他仍幹勁十足,且看來熱力四射,透過他的一支好筆,讀者和出版界都需要他,讓我們高呼讀書萬歲!周浩正萬歲!
隱地
代跋
如癡、如幻、如戲
我從職場退下之後,開始書寫編輯生涯之種種,不知不覺中,累積成《編輯力初探.》、《企劃之翼》、《編輯檯上的小確幸》等數十萬字的內容。好事的朋友,曾摘取部分文字改編成《編輯道》(臺北文經社)和《優秀編輯的四門必修課》、《如何提高編輯力》(以上北京金城出版社)三書出版。但,我依戀的仍然是自己初始的文本。
重新找出這篇是我七十歲那年,擔心不能如願寫完,預先寫妥的〈後記:有開始,就有結束。〉(原題)。細心的朋友,或可在行文字句中,理解所有靠自學成為編輯人的心路歷程。
而今,我的人生舞台上演著最後一幕「人生畢旅」,在生、旦、淨、末、丑的角色扮演中,終於享用了這如癡、如戲、如幻的一生。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徐志摩〈再別康橋〉
「儘管人生漫長,履歷表最好簡短」。
──維斯瓦娃.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親愛的朋友:
老實說,我並不想停筆,還有好多話要說,雖然累積了六十多萬字的經驗談,總覺得自己人拙、筆也拙,老搔不到癢處。
但,隨著馬齒徒增,記憶力一天比一天衰退,剛看過的書,放下就忘;有時候,要寫的字即使搜索枯腸也想不出它的長相;每段文字必須一修再修,才修成通順的句子。整封信挖挖補補二、三十次才是現在看到的模樣,而等到網友來信告知疏漏或筆誤之處,又不得不修訂重寄。如今,情況更趨嚴重,書寫時無法集中精神,三、五分鐘就意志渙散了。我心裡有數,應趁著還沒全面失控之前,自行了結。所謂「見好就收」或「見不好就收」──總之,親愛的朋友,這是你最後一次收到我親自(一對一)發送「寫給編輯的信」。
想當初(二○○四年元月)動念寫下這些「私見」,純屬偶然。
整個事情肇因於天津「新蕾出版社」編輯高彥捎來一封討論出版的e-mail,從最初的兩人互動,到後來面對眾人將個人的編輯生涯進行深刻反省。這六年多來,坐在電腦桌前的思考和書寫,充實了退休生活的每一時刻。我必須滿懷感恩的心,向高彥和其他結緣的朋友說:幸虧遇此機緣,能將過去的得失曝曬於陽光底下,細細檢視。在那年代,打了不少仗,卻不知道「為什麼輸或為什麼贏」。現在,有時間把案例從記憶的洞窟裡拖曳出來,用新吸收的知識予以解讀,才恍然大悟──啊,原來如此!
我願意坦誠,當年行走職場,從沒高瞻遠矚的本領。現在有些看法,是當時沒想過的,年輕的我不懂艱險,拿著鍋蓋當鋼盔,靠著「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二楞子精神,橫衝直撞;別人視為畏途的,我敢咬牙蠻幹。做久做多了,從工作和周圍的好榜樣身上,學到不少自己欠缺的新東西。
這些反省編輯經驗的信能夠成篇,最為感念的當是來自詹宏志先生的啟迪,他從不知道曾影響我如此之深。他的年紀比我至少小一輪以上,可是我對出版現代性的認知,得自他的作為。我在旁靜靜觀察、默默學習,把他獨特的行事法則牢記在心。
有一則只跟很少人說過的故事,我願意公開說一次,來表達我對他的敬意與謝意。
二○○一年,我退休在家。沒料到塵緣未了,經楊茂秀教授推薦,被「正中書局」總經理單小琳女士延攬到公司幫忙。
有一天,單總非常客氣問道:
「我從事教育工作多年,雖然愛讀書,也買了不少書,交了些出版界的好朋友,可是這次獨當一面做出版,仍屬新手,您建議從哪入手,比較能迅速掌握狀況?」
那段歲月,詹宏志的《數位時代》雜誌創刊一年左右,為了增加雜誌店銷時的吸引力,他曾將談出版的演講實況壓成CD片隨著每期雜誌贈送。
我雖是《數位時代》的長期訂戶,卻未得優遇,為了獲得他的演講CD,只好每次再去店頭購買一本當期雜誌保存下來。我向單總說:
「單總,您和詹宏志也相識,但可能沒時間聽他講出版的事,我手中有些他公開對外演講的CD,聽了之後,對出版的現在與未來一定會有新的理解。」
單總高興地借走CD。
隔了一個多星期,她找我去總經理辦公室。
「周顧問,詹先生的CD聽了,這些內容的確讓我對出版有了新的認識。」
接著,我們交換了一些看法,討論正中書局的未來走向。等我起身離開時,她叫住我:
「顧問,您對詹先生既然如此肯定,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假如在臺灣出版界排序的話,在您心裡,他排在什麼位置?」
這並不是個聰明的問題,她如此發問一定有她的道理。
「第一名。」我幾乎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哈,您可是我們專誠請來的顧問噢!那麼,和他相比,您屬第幾呀!」
我有點明白她的用意了,故意伸出兩指,晃了晃,說:「第二名。」
「哦?」她露出訝異的表情,我一時看不出她是失望還是高興。失望的也許認為請來的人居然不是第一名;高興的也許是僅次於第一名。
她又連續問了很多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我通通回答:「第二名」。
這回,她的好奇心被誘發出來了。她促狹地指指自己,問道:「那我呢?」
「第二。」這次回答的又快、又乾脆。
「我也第二?我可才剛加入出版行列呢!」
「對!您、我、他們都是第二。」
「為什麼?」單總顯然頗不以為然。
「因為,我們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相對於我們,詹先生是全方位觀照。」
這則軼事,有人認真聽進去了,有人把它當笑話聽。假使你讀過我書寫的全部內容,或許會同意我的論斷。不過,若不同意,也十分正確。
因為在近三十年的編輯生涯中,我分別在十七個大大小小的單位做過事,最長的地方待了快八年,最短的一天半。從表象看,我應該認識不少人,其實轉來轉去,都在小池子裡打轉。加上天性木訥,既無文釆、不擅言詞又怯於交際,因此識人有限。我相信臺灣出版界比詹宏志優秀的大編輯不在少數,如純文學林海音、爾雅隱地、九歌蔡文甫、天下殷允芃、遠見高希均、王力行、遠流王榮文、《講義》林獻章、圓神曹又方、時報高信疆、莫昭平、大塊郝明義、聯經林載爵、青林文化林訓民、《創世紀》張默……至少可列出一長串名單,他們全是能打天下、治天下的高手,是我長久欽佩的英雄式人物。有些我只敢仰望,不敢攀交;有些似乎該由他們身邊熟識其貢獻的人,予以宣揚。而我,只能說我知道的──當我回答單總的問話時,答案中有兩個前提:一是有範圍的,不是全稱句;一是純屬個人的主觀。
所以,要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名」另有名字,也非常合理。
我對編輯工作的認知,是有階段性的。
一九七四年,從軍中退伍,緣於喜歡閱讀,偶爾書寫幾篇類似讀後感的評介文字,知遇於《幼獅月刊》朱一冰先生、《幼獅文藝》瘂弦先生、《書評書目》隱地先生,因此得到發表文字和工作的機會,開始了我的編輯生涯。
那時候的我,熱衷於認識心儀的作家,以能爭取到名家之作刊登在自己參與的雜誌為榮,以為這就是編輯該做的事。慢慢的,隨著接觸面擴大,結識層面逐漸繁複多樣。不久,結交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高信疆先生(高公),目睹他和轉任《聯合報》聯副主編瘂弦先生之間的競合關係,深深震撼了我。那一段臺灣副刊史上的黃金歲月,容許千奇百怪的嘗試,使編輯這行業的內涵,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瘂雙雄對峙的局面以及社會深層剛萌芽的革新意識,突破了傳統思維,激起洶湧波濤。尤其是高公與各個階層密切結合,讓編輯透過工作平台,取得不同面向的發言權,幾乎釀成一場社會改造運動。
高公隱退後,副刊又回歸初始素樸的文學模式,已不復當年站在潮流前沿了。但,隨著「開放社會」來臨,轉戰出版界與雜誌界的編輯,仍延續了已內化為本能的創新意識,投入職場。
我就是從那時代背景走過來的受益者。
那些日子裡,在前輩和同儕那裡,偷學到不少「不足與外人道」的各家優點,譬如:朱一冰的誠懇;瘂弦的睿智、圓融、包容而成其大;隱地的編輯創意;小巨人沈登恩的豪氣;殷允芃的「時時以天下為念」、高希均的「引領潮流」、高信疆不從俗的創新與改革魄力;王榮文的人才策略;林獻章的「但取一瓢飲」;張默捨我其誰的無私奉獻……,人人都是我的老師。
從詹宏志身上見識到的,卻是嶄新的遊戲規則。
他常能放眼天下,跳出框框思索。例如在很早很早,以西門町為臺北消費指標的年代,他便寫了文章,預告臺北東區即將崛起;在一九八六年,臺灣出版界從戒嚴氛圍中甦醒,學習如何伸展手腳時,他想的和所有人不一樣,他的注意力已移向「華文出版的單一市場」。他也曾寫過帶著神奇的、預言色彩的《趨勢索隱》,把當時的臺灣放在蒼穹之上,用大倍數望遠鏡觀察,說出他看見的現象及未來發展的趨向。
他的本事,等我看了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創新與創業精神》之後才恍然大悟,他在眾人眼裡預言式的「創見」,在杜拉克的分析中,都不意外。他和杜拉克一樣聰慧,在人口統計、產業與市場結構、新知識……等變因裡,看到新的機會與新的市場。他不是預言家,全是根據數據與蒐集的資料推斷得來的結論。
他老早感悟到中國必將崛起,臺灣如何因應中國崛起?站在這塊土地上的編輯/出版的未來在哪裡?他在遠流內部工作會報時,一再提示「華文出版單一市場的未來將炙手可熱」,我們必須及早準備好參與競賽。
有一回,他接受訪問時說,面對新情勢要有新的認識,認為臺灣出版社的規模太小,小到沒力量在華文市場攻城略地,所以他大膽建議:合併。把「小」聚合成「大」,才有機會在華文領域以及國際競爭場域發揮影響力。在我印象裡,他把「大」的門檻設定在年營業額新台幣二十億,否則一不小心就邊緣化了。
後來,他登高一呼,以「花園主義」糾合有志一同的朋友組成「城邦集團」,不出幾年,發展成大大小小三十多家各擁特色、戰鬥力特強的出版單位,營業額快速成長,果然一一遂其心願,達成傲人的規模化目標。其間,也得到創投者青睞,紛紛注入資金。可惜,原本支持最力、最欣賞詹宏志才華、出資收購「城邦」的香港「TOM集團」(李嘉誠的事業之一),並不了解出版行業──出版是個需要「長期策略」驅動的產業。
一個好的、充滿未來性的長期策略,需要耐心與時間的,這是一種最終有大回報的「守株待兔的經營藝術」。集團缺乏繪製「未來出版地圖」的想像力,因此失去長遠眼光和耐性,成了美國俚語「Don’t be a bean counter. Count on bean bags. (別做數豆子的人,要數就數一袋袋的豆子)」裡那喜歡數豆子的角色。TOM集團放他離開「城邦」,縱虎歸了山。如今,他在界如龍歸大海,事業規模又更上層樓了。
詹宏志在編輯/出版界(包括所謂的「文創產業」)留下的足跡很廣,我記下的只我所知的「局部」和「片面」,但就傳統、古板、底子淺薄的我而言,已經學得非常吃力。
我辛勤筆耕六年,終於到了軀體不堪負荷的時刻了。年過七十,每天醒來都像多賺了一天,為了做事有始有終,理應未雨綢繆,所以先把〈後記〉寫妥,免得到時懊惱。
既然是收尾感言,有些話便不得不說。
首先要聲明的:縱使我寫成六十萬字,千萬別把我當做「作家」,我不是作家,我此生的定位是「編輯」。你們讀到的,是一個垂垂老去的編輯用餘生記下的一些見聞和心得。我常講「編輯有兩種」:一種是寫而優則編,一種是寫而不優則編︱我是後者。所以,請不要以作家的高度審視這些文字,它們不夠格。
再者,誠懇呼籲編輯們在適當時機,寫下各自的經驗。假使每個編輯都肯不怕嘲笑,記下一得之愚,久而久之,後人一定能從成千上萬的經驗紀錄中過濾出有用的東西(幸好網路容得下恆河沙數般的內容)。
至於我寫的這些,難逃偏、狹之嫌,有些讀友基於敬老或憐憫心,寬容的寫些鼓勵的話,但聰明的讀友立刻看出我的不足。有位叫Rory的讀友,讀了金城出版社朱策英先生根據《編輯力初探1.0》(第一─三十四信)編撰的《優秀編輯的四門必修課》,他下的總評,曰:「很營銷。」他敏銳地點出:「這本書感覺更像市場行銷方面的書,只不過主角是書。處處能遇到作者在引用其他管理書或者其他企業的觀點為己用,比如《長尾理論》、《藍海戰略》、《從優秀到卓越》。他把新加坡的成就,把英華達手機企業的市場成功都拿來作為出版借鑒。他的好多靈感似乎都來自於他當時讀的熱門管理書籍。」親愛的朋友,Rory的話完全正確,的確我如其所言,借用各類書籍中的觀念來解釋我並不真正理解──包括我的(和觀察他人而得到的)經驗。很慚愧,我不是原創型的人,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努力學做「撿拾珍珠」的人。
回頭看自己一生,不得不承認:我太幸運了。
基於幸運,我借了石濤的「一畫」,粗疏地建構自我指導的理論;而孫隆基教授的〈勢力均衡場論〉,居然讓我領會競爭的基礎是「不競爭」(開發無人地帶);尼釆的話「對於整個的組織,美麗乃其餘事」,助我建立做事的準則;讀巴斯卡《沉思錄》,明白了正義的歧義性及追求多元價值的必然──書系概念的豐富性也由此得到滋養;何秀煌教授的《0與1之間》,指出兩極性的專斷,人生所擁有的選擇不只是「0」或「1」;我曾小心翼翼地試著把FUZZY理論置入書系運作,合理化內容的抉擇;發現彼得.杜拉克的秘密,他的影響力源自詮釋「正面的力量」……;得自孔子和老莊思想的啟發,更不在話下了。這種化零碎為整體的「百衲衣式的智慧」,幫我克服過不少挑戰。但我並不感到臉紅,因為連華倫.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美國投資大師)這樣頂尖的聰明人也說:「我通常都靠大量閱讀,學習別人的知識和創意,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有很多原創的觀念,我的許多觀點都是從閱讀來的。你可以從別人的書中學到許多東西,而不需要自己花腦筋創造新知,重要的是要會充分從別人身上學來最好的知識。」
就這樣東讀西讀以及自己前半生的一些實際編輯經驗,拼湊出半生不熟的東西,而最後又「內化」成六十多萬字的篇章。了解這些書稿的始末,就明白我為什麼願意快樂的放棄版權並主張這些文字是「公共財」的緣由了。
經驗告訴我,欠缺經驗時需要經驗,有了成熟的經驗後需要忘掉經驗,因為它會成為「成長的阻力」。所以,若干年後,這些文字若能以位元的形態,倖存在虛擬網路世界,就夠幸運了。
年輕時候,讀張愛玲翻譯的《愛默生選集》,記憶中,愛默生曾說:「每個人都是一個小小的宇宙。」
噯喲,親愛的朋友,我愛死了這句話──既然人不分貴賤、貧富、智愚,都擁有各自的小宇宙,那麼,《編輯力初探1.0》、《編輯力檯上的小確幸》與《企劃之翼》就是我小宇宙的「描紅簿」(它連臨摹都還夠不上)。萬一你不小心接觸它,看到顫抖、歪曲、醜陋的描紅筆法時,請多擔待。
終於,我如願記錄了親歷的人生片斷。你的呢?
謝謝大家多年來的愛護與支持,順祝
平安幸福
周浩正
寫於二○一一.一.十二「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