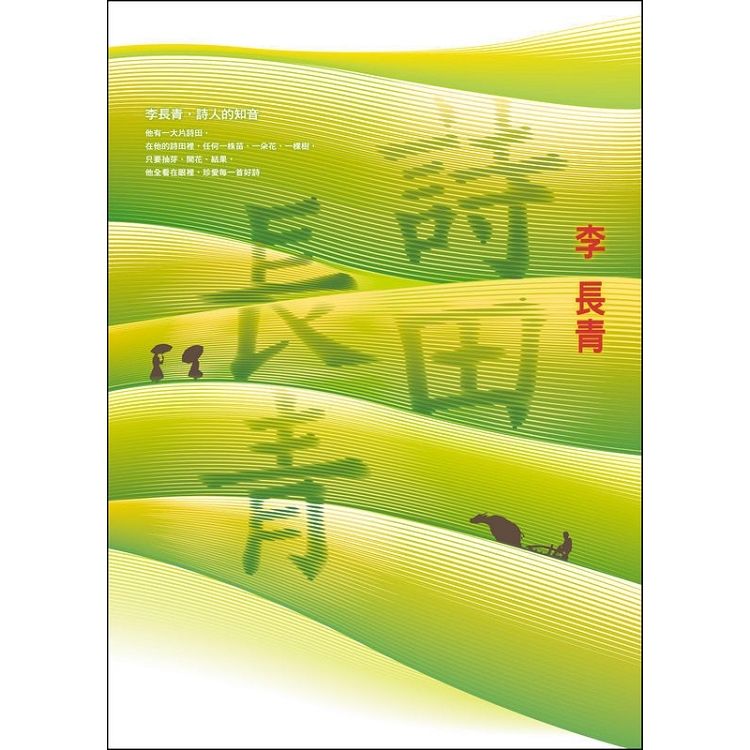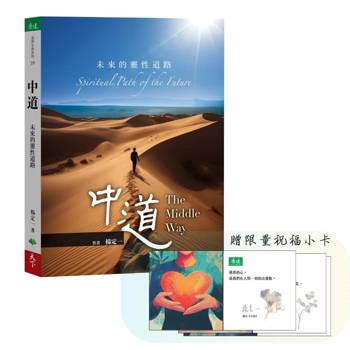李長青,詩人的知音
在出版業如此苦澀的年代,我仍然以快樂如跳舞的心情,為詩人李長青出版其賞詩.品詩.論詩的《詩田長青》。
不僅是長青看到了我的詩,同時也看到了許許多多詩人的詩,他有一大片詩田,在他的詩田裡,任何一株苗、一朵花、一棵樹,只要抽芽、開花、結果,他全看在眼裡,珍愛每一首好詩,他對寫出好詩的詩人總是拍拍手,予以關愛,無論古今中外,不分男女老少,誰寫出了好詩,他總是一一剖析,將一首詩的誕生,詩的特質與藝術性,用他曼妙的筆,為我們細品細說,點出詩的精髓,也深入詩的魂魄,當然,詩人為何能寫出如此佳作,長青總是追蹤詩人所以能產生一首詩的源頭和背景。他是詩的解人,他是詩人的知音。
透過《詩田長青》一書,讓我對詩的認識向前邁進一步,也因細讀本書,讓我更親近詩人,說來,李長青年紀雖比我小許多,而他與詩有關的體悟,遠遠超過我這個老人,對臺灣詩壇歷史的流變,更瞭然胸懷,勝過我不知多少;譬如第一篇分析詹冰的圖象詩〈自畫像〉—讀後不但讓我重新認識一位詩人,而其詩之妙不可言已到拍案叫絕地步—整首詩只有兩個圓圈和三個字—星.淚.花—就能將一位悲憫情懷的詩人,他的生命特質、個性、喜好、人生觀全部表露在讀者面前,真是神來之筆。
詹冰(一九二一—二○○四)認為「詩人的詩心應發揮誠實、高雅、善良、和諧、美感的光芒,並以淺易明瞭的語言書寫,如此讓愛詩的人看得懂才是好詩。」享年八十三歲的詹冰,生前曾於一九六四年和林享泰等十二人合組「笠詩社」,並創辦《笠詩刊》。
李長青說:「許多時候,詩歌應該勇於超脫世俗與現實,儘可能追求藝術的美感,尋找純粹的感動,讓我們的心靈獲得平靜。」所以詩應當像小說,可以虛構,可以幻想,把現實世界揉碎,重新組合,成為自己的創作;「但是有些時候,詩歌也應該『關注』我們生活的環境,了解我們的社會……」李長青認為詩可表達且面對我們的歷史,也應探討認同—譬如性別認同、社會認同甚至國家認同。
李長青的意思,詩不必只是虛的、逃避的、出世的,詩也可以是實的、面對的、入世的,說到認同,他舉了白靈的〈對鏡〉和江自得的〈生物統計學〉兩首詩,來印證他的想法。
「時光」,是詩人永恆的命題。李長青讀一個外省老兵的心情;辛鬱(一九三三—二○一六)的〈六月十八日〉寫他「六十年前來臺的那一天」—
初履高雄港碼頭
年紀輕輕一小兵
裹著一身臭
下船 腳皮發燙
低頭 看不見自己
看不見自己正是茫然所致,他看到的是好辣又好鮮的刺眼陽光,回首前程,辛鬱用詩句告訴我們:「茫茫來時路,一寸寸斷在望眼中」。
原來,「時光」真如另一位詩人席慕蓉所說:「時光是畫在絹上的河流;時光只是空間有限的展示櫃」。
詩可以寫歷史,可以寫地理,可以寫認同,也可寫時光,更可以寫我們的內心,顯然,詩無所不在,詩是小精靈,在門外,在路上,在門內,在內心,明與不明,顯與不顯,均有詩魂,人,只要肯和自己對話,詩心常在。
詩也在野外四周,譬如李長青舉薛赫赫的兩句詩—
黑夜的水田睡在陰影中
睡在自己的寂靜裡
人,只要關心我們的世界,用自己的眼睛,關懷的眼神,立即發現:人世間處處有情,大自然的任何景點,遠望近觀,全是一幅畫,一首詩。
如果你缺少銳利的眼睛,只要敏感度夠,在芸芸眾生裡,無法以詩眼捕捉靈感,不要緊,我們可以靠想像力,請讀李長青以廢名的一首詩為例—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將永遠不愛海了。」
花花微笑道:
「花將長在你的海裡。」
有了這樣豐富的想像力,你怎麼可能寫不出詩?
除了為我們釋詩賞詩讀詩,李長青在《詩田長青》一書,也為我們介紹了幾位頗具特殊風格的詩人,如曾任教育部長的黃榮村,他年輕時候,曾是水田和竹林巷子奔跑的快樂鄉村少年,熱愛閱讀也熱愛文學;還有一位本名溫德生的林野,七○年代曾加入高雄綠地詩社,與一群青年詩人共同創辦「陽光小集」,後因林野赴美攻讀生理學博士,一九九一年學成歸國,繼續在空軍服役,致力於航空醫學的研究與教學,但他並未忘情詩與文學,仍舊持續,至少創作之念從未間斷。
李長青另外向我們介紹的兩位有趣詩人是林德俊和錦連。
一點也不錯,林德俊像極了卡通人物—風趣、突兀並且童言童語。
更妙不可言的是,李長青說林德俊就是一個文建會,而且是文建會個體戶。德俊點子多,為人熱情,樂於助人,自己寫詩,也希望天下人人皆是詩人,後來他愛上咖啡,竟然和妻子韋瑋又開起咖啡館來,這時他又希望人人都能喝杯咖啡,但他不會因為有了自己的咖啡館,就忘了詩,不,如今他不但在他的咖啡館裡推廣詩,推廣閱讀,也在任何一個可能的地方,以擔當一個「文宣兵」為榮,如何讓他居住的霧峰成為文化發射中心,將詩風、文藝風、文化風慢慢擴大,吹向臺中、臺南,當然也要吹回他當初服務的《聯合報》大本營所在地:新北市、臺北市,最後,一定要讓全臺灣都文藝、文學、文化起來,「用文化裝扮」,是詩人林德俊一生的卡通夢啊(只有卡通人物才能達到)!
錦連又是誰呢?
錦連(一九二八—二○一三)是彰化的榮耀。本名陳金連的錦連,少年時代曾北上在鐵道講習所求學,晚年移居高雄養病,他一生都在彰化鐵路局火車站電報房工作,顯然他是一位鐵道詩人。
一生與鐵道為伍,在他心目中,火車像一條蜈蚣,一生在匍匐前進,匍匐到歷史將要湮沒的那一天……
而無論蜈蚣(火車)多麼努力,將一廂廂的旅客送往目的地,火車站最後總是空無一人,只剩長長的兩條寂寞軌道……這樣一生一世的觀察,養成了錦連孤獨的性格,幸虧有文學相伴,能以詩句表達自己內心的憂傷,讓錦連找到了精神寄託。
《詩田長青》書分二輯,輯一為「夏日遠去」,此輯為「甜美篇」,適合一般愛好文學的人閱讀,也可分到易「懂」之部;輯二為「非主題的流連忘返」,是詩的「晉級」版,也屬「苦澀篇」,應列入「不易懂」之部,一般讀者讀後會出現「茫茫然」、「霧煞煞」之感。
以我自己來說,雖為蘇紹連《孿生小丑的吶喊》出版人,但以前讀不懂此書,可以因係臺語詩之故搪塞過去,如今李長青細細分析評介,老實說,仍無法引起我共鳴,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我只能說,趣味無爭辯,各有選擇,一如人和人之間,有人投緣,有人不投緣,讀書、讀文章,有些能神領意會,立即進入狀況,而且越讀越有趣,彷彿擊中我們的胸懷,每一篇每一句都讓我們讚嘆,也另有一些「經典」,儘管專家學者推薦,無論如何我們努力地設法閱讀,就是讀不進去,像一枚硬果,怎麼咬也咬不動,只好望洋興嘆。
這純然是每個人閱讀品味和興趣之迥異,勉強不得,或者說因緣未到,某年某月,忽然開朗,原先讀不懂的突然懂了,原先無感之書,突然讀出了其中的奧妙,說來說去,在於一個關鍵詞—「悟」,無論「自悟」或「他悟」,觸動到我們的「初心」,是謂「開竅」,一旦開了「竅」,我們會拍案大叫,但願有一天,我的「慧根」能從初階晉升,懂得晦澀之妙,那時,我會舞之蹈之。
願以此和許多讀不懂現代詩的朋友共勉。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詩田長青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6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詩 |
$ 253 |
華文詩集 |
$ 272 |
文學作品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現代詩 |
$ 288 |
華文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詩田長青
隱地讚李長青為「詩人知音」,同時提供我們閱讀本書的方式,輯一屬於初階的甜美篇章,輯二則為苦澀篇的晉級版,讓讀者藉由李長青的曼妙筆法,與精闢剖析來進入一首詩,甚至一位詩人的世界。
總有很多讀者抱怨看不懂新詩,現在有了李長青這本《詩田長青》對於新詩的解讀與分析,使得那些無法理解的文字遊戲,提供了入門鑰匙,終於可以一窺新詩堂奧,同時也欣賞到了李長青優美風趣的散文筆法。
推薦序
李長青,詩人的知音
在出版業如此苦澀的年代,我仍然以快樂如跳舞的心情,為詩人李長青出版其賞詩.品詩.論詩的《詩田長青》。
不僅是長青看到了我的詩,同時也看到了許許多多詩人的詩,他有一大片詩田,在他的詩田裡,任何一株苗、一朵花、一棵樹,只要抽芽、開花、結果,他全看在眼裡,珍愛每一首好詩,他對寫出好詩的詩人總是拍拍手,予以關愛,無論古今中外,不分男女老少,誰寫出了好詩,他總是一一剖析,將一首詩的誕生,詩的特質與藝術性,用他曼妙的筆,為我們細品細說,點出詩的精髓,也深入詩的魂魄,...
在出版業如此苦澀的年代,我仍然以快樂如跳舞的心情,為詩人李長青出版其賞詩.品詩.論詩的《詩田長青》。
不僅是長青看到了我的詩,同時也看到了許許多多詩人的詩,他有一大片詩田,在他的詩田裡,任何一株苗、一朵花、一棵樹,只要抽芽、開花、結果,他全看在眼裡,珍愛每一首好詩,他對寫出好詩的詩人總是拍拍手,予以關愛,無論古今中外,不分男女老少,誰寫出了好詩,他總是一一剖析,將一首詩的誕生,詩的特質與藝術性,用他曼妙的筆,為我們細品細說,點出詩的精髓,也深入詩的魂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詩田長青
李長青,詩人的知音隱 地
輯一 夏日遠去
詩的自述一九
詩的歧義二三
詩與歷史二六
詩與認同三一
文本三六
時光:永恆的命題三九
回到我們的內心四四
野薑花飛到天上去四九
得失之間五三
頭髮很重要五七
近日讀詩五九
新年,舊曆,每一天六四
想像練習六九
︱閱讀然靈的散文詩
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七四
海八
最美的黃昏八三
︱訪問「青年詩人」黃榮村
北極星光下的饗宴八七
讀楊風〈夜坐〉九一
當悲傷的卡通人物向你說話九四
解構之必要九八
︱試讀林德俊〈議程表.演〉
崩壞的象徵,前衛的風格一 三
︱試讀錦連鐵路詩兩...
李長青,詩人的知音隱 地
輯一 夏日遠去
詩的自述一九
詩的歧義二三
詩與歷史二六
詩與認同三一
文本三六
時光:永恆的命題三九
回到我們的內心四四
野薑花飛到天上去四九
得失之間五三
頭髮很重要五七
近日讀詩五九
新年,舊曆,每一天六四
想像練習六九
︱閱讀然靈的散文詩
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七四
海八
最美的黃昏八三
︱訪問「青年詩人」黃榮村
北極星光下的饗宴八七
讀楊風〈夜坐〉九一
當悲傷的卡通人物向你說話九四
解構之必要九八
︱試讀林德俊〈議程表.演〉
崩壞的象徵,前衛的風格一 三
︱試讀錦連鐵路詩兩...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