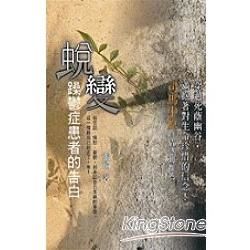重新面對自己
西元二○○六年對我而言,真是充滿了驚奇的一年。這一年,我第一次學習中文電腦的輸入法,我的第一本書《蛻變?躁鬱症患者的告白》出版了!對於一個十多年來飽受疾病糾纏的我而言,真是一個驚嘆號!想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
起初寫這本書時,原稿只有一、兩萬個字,我是為我自己而寫的,像寫懺悔錄般地將自己這一生以來的功與過,作一個總整理並且向上天懺悔。後來,我又將這些文字寄給司馬中原老師。那時,司馬老師就告訴我:「書中的字數太少,出版社是不會發行的。」?此,我開始增加書中的內容,同時,在書寫的過程中,我又開始回憶起在住院期間所認識的無數病患們,想到他們仍然陷於自己的迷思裡,仍然活在社會的邊緣角落中,我又不禁感慨萬千,燃起一絲的悲憫之心。希望藉由我的故事,一方面,能夠喚起病友們的覺醒,另一方面,我希冀著藉由「體制」上的革命,能夠全盤地將精神疾病患者,對於社會所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同時希望藉由「法律」及「教育」雙管齊下的方法,能夠使「精神病」的汙名化畫下一個句點。
在這一本書中,我也一一闡述自己生病的來龍去脈,並將自己個性、心理上的缺點做很深刻的描述,希望藉由我的覺醒與領悟,能夠喚醒更多人對「精神保健」的重視。正如台北縣康復之友協會總幹事劉麗茹女士所說的:「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販夫走卒,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成為下一個不幸罹患精神疾病的人,也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成為下一個無辜的受害者。所以,認識、了解、尊重、接納精神疾病患者,是一門重要的課題,多一分認知,就少一分危險,社會就多一分和諧。」
除了感謝我父母、家人、朋友、醫師們外,我還要向司馬中原老師、師母及其家人們致謝。這幾年來,他們倍受我信件的疲勞轟炸。如果沒有司馬老師鼓勵的話,我也不會傻傻的就寫了這麼多年的小說、散文、遊記、讀書心得、社論等。許多年來,我像一個傻子般地拼命寫,也拼命寄,只不過我寄錯了地方,而司馬老師也像中蠱般地一路讀下去。
直到去年,司馬老師在電話中突然對我說:「我兒子說妳寫的這些東西,已經可以出版好幾本書了。」那時,我才恍然大悟,該是務實地去投稿,賺些稿費了。
在此,我也要感謝華成出版社能夠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將自己攤在太陽底下,並且勇敢地去走人生的道路。希望《蛻變?躁鬱症患者的告白》一書,可以幫助更多在疾病中徬徨無助的病患們,並且走出自己的道路來。
過去的歲月,我除了感激之外,還是感激。對於自己的疾病也不再埋怨說:「?什麼是我呢?」懷疑、困惑、痛哭並不能?我止傷療痛。這本書中的一字一句,已經讓我從痛苦的深淵中解放出來了。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家人,以及仍處在精神疾病中無法自拔的病患及其家屬。
坦然面對現實才是最佳的方法
個人從事文藝教學工作將近一甲子,因畢生自學,毫無學歷可言。多年前,承文化學院張其昀老先生,聘為客座教授,故很多學子都以「教授」稱之。余戲稱「教授」可分三等,一等是既「教」且「授」,二等是既「嬌」且「瘦」,三等即為老愚,實乃「驕」狂之老「叟」也。
猶記二十多年前,余為實踐家專文藝社團授課,認識才女多人,她們來宅拜訪時,帶來一位清秀雅靜的女孩,那就是畢業於實踐家專的張瑜。
人生相遇相知,總離不開一個「緣」字。多年來,受教於余之學子已遍布寰宇,而與余全家均熟悉親近者,為數頗稀,張瑜可算其中之一。緣內子身體單薄,且兒多母苦,常年多病,張瑜總找出時間,陪師母和家人逛古物店,遊陽明山。她是一個樂觀開朗、真誠灑脫的人,隨處都朗笑如鈴,大大減輕了師母的憂煩,我們對她十分感激,視其如家人。
怎麼也想不到,這個聰慧能幹的女孩,竟會成為精神疾病纏身的人?由於出國留學多年,我們對她獨處異鄉的生活景況,僅能從她偶而來函中略有所知。
張瑜已是成年,對其感情生活,我們不便過分關切,總以為如此活潑開朗的女孩,自會有良好的歸屬。她既能帶給我們全家歡樂,日後其婚姻與愛情,必能圓滿處之。
她決定出國留學前夕,余曾登張宅,拜訪其父母,並將小女地址相告,望小女能盡力照顧她。她留美後,幾經轉校,最後落腳於拉斯維加斯,讀了內華達大學研究所。她在美期間,我們也不斷有書信往來。她曾因學習遷延,逼老父售一屋助學。她曾因經濟窘困,倍受病痛折磨。她曾因感情生活的折磨,飽受痛苦,很多幻象始終圍繞著她。我雖萬分憐惜,卻有愛莫能助之感。
我始終認為,張瑜是個天真的好女孩,樂觀、奮進,而確具懷恩報?的仁懷。這樣的人,竟染上嚴重的精神疾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她自美歸國後,事業並不順利,當時我擔任著作權協會理事長,她略有涉及法律事務之問題,我都召喚當時法律事務總幹事陳君代為解決。其後,我發覺張瑜心理上有些難解的鬱結,她顯得徬徨、憂慮,失去了原有樂觀、純潔的笑容。
她對我講起留學後期若干經歷,多與「魔靈」纏繞有關,多少顯示出她精神「恍惚」的現象。一個女孩子,孤獨的處在陌生環境中苦讀,當然會有多方面的壓力,但我始終認為,她是一位確具能力與理想的人,能克服多重艱困讀到碩士學位。但回國後,又遭到多次挫折與打擊,對她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幾年前,在數次聚晤中,我已經覺察到她初期的病徵,不僅是單純的憂鬱,而是多種因素混合而成的,比如幻想、幻聽、幻覺、時空失序、精神分裂,她都多少有那麼一點,我真擔心她一旦病發,將會有嚴重的影響。
我不是醫生,也缺乏醫學界的專業知識,但僅憑直覺,也可判斷出病因:她內在感覺極其敏銳,爭勝心太強,也太重局部得失,有一種永不服輸的叛逆性,即使是「百煉精鋼」,如恆常使用不容休息,也會產生「鋼鐵疲勞」,何況乎血肉之軀?
在現代社會中,人際關係變得尖銳複雜,且爾虞我詐,分秒必爭,絕大多數人均處在緊張狀態中,使精神性疾患暴增,儼然成為時代性的流行病。越是自詡為擁有高度科技文明的工業大國,其發病的比例越高。反而,地處偏遠,遠離塵囂的國度,像北歐諸國、紐澳及大洋洲諸國,生活步調較為悠閒徐緩,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能適度調和,故發病率相對降低。於今之世,早已見不到世外桃源,連大洋洲的大溪地也成為超級精神病患的療養所了。
世界潮流如此洶湧澎湃,張瑜發病後,多次進出療養院,這對她也許是一宗好事,因一般人對精神病患並無正確體認,要不然,「神經病」三個字也不會成為罵人的三字經了!其實,依我國傳統醫學觀點,我們歷史上許多樞紐性的人物,都曾是這類疾病的患者,暴君如桀、紂,多疑如魏武(曹操),宦豎如劉瑾、魏忠賢、李蓮英,凶殘如李闖、張獻忠,有些是「積鬱成痴」,有些是「躁鬱而狂」。再看歐洲古史,暴君尼羅大帝就是典型的躁鬱疾患者,後來的拿破崙、希特勒、史大林無一不是,即使有絕世名醫,也不敢直言,否則一言賈禍,必會像華陀一樣,弄掉了腦袋。
張瑜所患的疾病,原也是這類恐怖的病,她也具有掌握「天下權」的幻想,但那只是「幻想」而已,根本不足為患。許多諱疾忌醫的歷史人物,都以「狂疾」告終,而她竟能成為一隻「浴火重生」的鳳凰,這不能不歸功於她確具靈根慧蒂,能經自省自悟,省察到她得此病的根蒂。她坦承自己有病,也遵守醫囑,按時服藥。她能夠在「杜鵑窩」中,以平靜的心情、堅強的自信,博覽群籍,凡有關精神疾患之書籍,不論是理論或是縷析的,她都收購詳讀。其中精妙之處,她並逐一記錄,或肯定,或品評,主要在鍛鍊她自己認「病」而不認「命」的精神。
在她出入「杜鵑窩」的數年中,她寫給我的信可說是「累篋成筐」,幾乎等於是她精神指標的日記,她狂暴、怨懟、顛倒、訴苦、委屈、自責。萬般情緒,盡納其中。
這種延續數年的信件「大轟炸」,幾可列入金氏記錄,連平素最關心她的師母,都嘖有煩言。但我卻淡然處之,詳閱她每一封信,等於檢閱她的「腦波圖」,觀察她病情的變化,正如每天看溫度計一樣。
張瑜知責己而不怨人了,時空感覺不再錯亂了,正常思考力逐漸恢復了,懂得愛母尊姐了。每一封信,都讓我額手稱慶,俗云:「心病須得心藥醫」,我們不能不感恩於她的主治醫師,適當的醫藥治療是必須的,但徹底的斷根、復原,仍繫於一己的「心靈」,能坦然面對現實才是最佳的方法。
個人深感台灣社會,近年來精神疾患激增,上焉者王公大臣,中焉者各行各業,下焉者升斗小民,憂鬱症、躁鬱症患者急速暴增,?何會這樣呢?說白一點,就是國家這部機器朽爛,運轉不靈,使章制大亂、經濟委頓、百弊叢生、盜匪橫行、人心崩潰,致使精神疾患,發狂的發狂,自殺的自殺,即使是一個正常人,臨到衣食不濟,負債累累,前途茫茫的時刻,也會爆炸。
但這類病患,大多是「隱性」的,病根累積在身並不自知,當其自感不妥時,又諱疾忌醫,連家族也幫其隱瞞,怕丟面子。但面子保住了,裡子卻全丟了,這是最大的錯誤,許多悲劇便是這麼來的。
張瑜以她的靈慧和堅忍,穿過死蔭幽谷,滿抱著對生命珍惜的信念,用精簡平實的筆法,寫出《蛻變?躁鬱症患者的告白》這本書,以其切身的體驗,坦然敘述心路歷程,可說是語語真誠,意義深遠,能夠使這類精神疾患,憑自心參悟,走出魔火煉獄。
司馬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