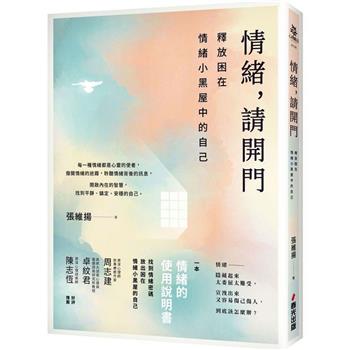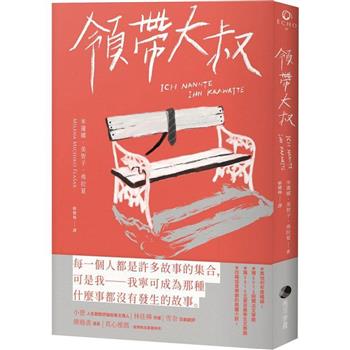在幽靈喚醒我之前,我正舒服地裹著毯子待在壁爐前,身旁滿是文件和卷軸,輾轉反側。
我的手指上沾著墨水和蠟漬。起身後,我環顧四周,試圖回想自己睡著前正在寫些什麼,以及寫給誰。
蟑螂站在通往我房間的祕密通道入口處,一雙如鏡般反射、不帶人性的眼睛望著我。
我的皮膚又溼又冷,我的心怦怦跳著。
我依稀可以嚐到舌頭上的毒藥苦味和令人倒胃口的味道。
「他還是死性不改。」幽靈說。
我不必問他說的是誰。我或許耍了些心機讓卡登戴上王冠,但我還沒學會怎麼讓他表現得像國王那般莊重。
在我外出打探消息時,他便去找洛克。我很清楚他肯定會惹出麻煩。
我揉了揉自己的臉。「我起來了。」
我仍然穿著前一天的衣服。我撣掉夾克上的灰塵,盡量往好處想。我走進臥室,把頭髮往後一梳並束起,用一頂天鵝絨帽子蓋住蓬亂的頭髮。
蟑螂朝我皺起眉頭。「妳真是邋遢。高王陛下不應該和一個看起來像剛起床的總管一塊打理國家大事吧?」
「瓦爾.莫倫十年來不也是用樹枝固定頭髮?」我提醒他,從櫃子裡拿出幾片半乾的薄荷葉放進嘴裡咀嚼,以消除口腔中彷彿腐敗的味道。前任高王的總管和我一樣都是凡人,喜歡聽信一些不可靠的預言,大家都認為他瘋了。「說不定還是同樣那幾根樹枝呢。」
蟑螂發起牢騷。「瓦爾.莫倫是個詩人,詩人向來不講究繁文縟節。」
我不理會他,跟著幽靈進入通往宮殿心臟的祕密通道,只偶爾停下來看看刀子是不是還藏在衣服縐褶裡。幽靈的腳步是如此安靜,以至於當我的視覺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陷入一片漆黑時,總感覺陷入全然的孤單之中。
蟑螂沒有跟著我們。他哼了聲,朝反方向走去。
「我們上哪兒去?」我在黑暗之中問道。
「他的寢宮。」幽靈等我們來到大廳時告訴我,樓上是卡登的寢室。「那裡似乎發生了一些小騷動。」
我很難想像高王在自己的房間裡會遇到什麼麻煩,但很快便水落石出。當我們到達時,只見卡登正在家具殘骸中休息。窗簾從竿子上被扯了下來,畫框斷裂,畫布被踢破,家具也都殘破不堪。角落裡有一小堆火在悶燒,所有東西都散發著煙味,酒味四溢。
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旁的沙發上坐著洛克和兩個長相標緻的精靈──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其中一個精靈頭上長著公羊角,另一個則長著長耳朵,耳朵的尖端有一簇毛髮突起,就像貓頭鷹的耳朵一樣。他們全都褪去身上的衣物,處於酒醉狀態,帶著渙散的眼神望著房間裡燃燒的火焰。
僕人們瑟縮在走廊上,不知道他們是否應該冒著讓國王發怒的危險,進入房間打掃。就連他的侍衛也似乎有些畏懼。他們笨拙地站在門外的走廊上──其中一扇門的鉸鏈幾乎要脫落──使其不受到任何威脅。
「卡登──」我突然想起自己的身分,朝他鞠了一個躬。「陛下。」
他轉過身來,有那麼一刻似乎要看穿我似的,彷彿不知道我是誰。他的嘴角染成金色,瞳孔因醉意而放大。
然後他揚唇,露出熟悉的冷笑。「是妳。」
「沒錯。」我說。「是我。」
他舉著酒袋說道:「來喝一杯。」亞麻狩獵衫的寬袖敞著,他光著腳,我想我應該慶幸他穿了褲子。
「我不會喝酒,陛下。」這話句句屬實。我瞇起眼警告他。
「我難道不是你們的高王?」他問,質疑我怎敢拒絕他?為了不在眾人面前讓他難堪,我只得順他的意。
於是我拿起酒袋,貼在緊閉的嘴唇上,假裝喝了一大口酒。
我能看出來他並沒有上當,但也沒有戳破我的謊言。
「其他人都退下吧。」我指著沙發上的精靈,包括洛克在內。「你們、現在、快點。」
那兩個我不認識的精靈面帶懇求地望向卡登,但他似乎幾乎沒有注意到他們,也沒有反駁我的意思。過了一會兒,他們悶悶不樂地站起來,穿過破損的門走出去。
洛克則拖拉了一些時間才站起身。他一邊走,一邊對我微笑。那微笑帶著暗示,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曾經覺得他的笑容如此迷人。
他看著我,好像我們彼此分享祕密,儘管我們不再分享一切。
我想起洛克與卡登在樓下狂歡時,塔琳正在我的房間等著我。不知道她是否聽到他們喧鬧的聲響。我納悶她是否習慣和洛克一起熬夜,看著事物燃燒殆盡。
幽靈朝我搖了搖頭,眼中閃爍著打趣。他身穿宮廷制服,對大廳裡的騎士和其他任何可能打量他的人來說,他不過是高王私人護衛隊的一員。
「我會確保每個人都待在原地。」幽靈說著,離開了門口,以類似命令的口吻吩咐其他騎士。
「怎麼樣?」我說著,環顧四周。
卡登聳聳肩,坐在剛空出來的沙發上。他從被撕破的布料間挑出一團馬毛。他的舉動顯得百無聊賴似的。我盯著他瞧了一段時間,這麼做似乎太過危險,彷彿他的墮落具有傳染性。「原本還有更多賓客。」他說,似乎想替自己解釋。「不過這下他們都走光了。」
「我想不出來他們離開的原因。」我的語氣極盡挖苦。
「他們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卡登說:「妳想聽嗎?從前,有一個人類女孩被精靈們偷走了,因此,這個女孩發誓要毀掉這些精靈。」
「哇哦,」我說:「這真是證明了你作為一個國王有多糟糕,你讓他們以為精靈王國在你的統治之下會被摧毀。」
話雖如此,這番話聽起來卻令人不安。我不希望別人猜測我的動機。我不該讓他們以為我具有某種影響力。他們根本不應該想到我。
幽靈從大廳返回,把門板靠向門框,盡可能地關上門。他淡褐色的眼睛蒙上一層陰影。
我轉過身,面對卡登。「這個小故事應該不是我被派過來這裡的原因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妳來瞧瞧這個。」他說著,搖搖晃晃地走進房間。裡面有一張床,床頭板上插著兩枝黑箭。
「你之所以生氣是因為其中一個賓客朝你的床射了兩箭?」我對他說。
他笑著說。「他們不是瞄準床。」他拉開襯衫,我看到他的衣服上有個洞,身側劃破了一層皮。
我屏住呼吸。
「誰幹的好事?」幽靈問道。然後,他仔細打量著卡登。「為什麼外面的守衛一副面不改色的模樣?他們似乎並不知道這裡才剛發生過暗殺。」
卡登聳聳肩。「我相信守衛們認為是我在朝賓客們射箭。」
我走近一步,注意到一個凌亂的枕頭上有幾滴血滴,還有一些散落的白色花朵,這些花朵彷彿從布料中生長出來。「有人受傷嗎?」
他點了點頭。「有一枝箭射中其中一個女精靈的腿,她尖叫得有些歇斯底里。因此有人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在沒有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朝她射箭。而真正的殺手則逃回牆後。」他瞇起眼睛望著幽靈和我,歪斜著頭,目光發出熊熊怒火。「這地方似乎藏有一條祕密通道。」
埃爾法默宮殿建在一座小山丘內,高王埃爾德雷的寢宮就在宮殿中央位置,寢宮的外牆上爬滿了樹根和盛開的藤蔓。整個王宮裡的人都認為卡登會入主前任高王的寢宮,不過他卻搬到距離高王寢宮最遠之處,位在山頂上,那裡的地上鑲嵌著像窗戶一樣的水晶。
在他接受加冕之前,這一區住的是在王室中不受歡迎的人。現在,宮殿裡的王公貴族們爭相跟進換房間,以便更接近新任高王。而埃爾德雷的房間就此空了下來,因為沒人敢入住那間太過奢華的王室寢宮。
我只知道有幾條路可以進入卡登的房間──一扇巨大的厚玻璃窗戶因為施了魔法的緣故,永遠打不破,一扇雙開門,顯然還有一條祕密通道。
「我們手上的地圖上並未標示出祕密通道。」我告訴他。
「哦。」他說。我不確定他是否相信我。
「你有看到是誰朝你射箭嗎?你為什麼不告訴守衛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問道。
他氣急敗壞地掃了我一眼。「我只看到一道黑影。至於我為什麼不糾正守衛──那是因為我是在保護妳和暗影宮廷。我不認為妳會希望整個侍衛隊湧入祕密通道吧!」
我無話可說。令人不安的是,卡登為了掩飾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把笨蛋扮演得很好。
床的對面是一座嵌在牆上的櫃子,占據了整個牆面。壁櫃正面是一個彩繪的鐘面,上面用星座代替數字,時鐘的指針指向一組星座符號,像是預示著一個多情的情人。
它看起來只是一個裝滿了卡登衣服的衣櫃。我將掛在衣櫃裡的衣服拉出來,然後將這堆天鵝絨、緞面和皮革材質的衣物堆疊在地板上。卡登倒臥在床上,故意發出沮喪的聲音。
我將耳朵緊貼在衣櫃的木頭壁面上,聆聽風的吹拂,感覺氣流的流動。幽靈在另一邊的衣櫃也做同樣的檢查。他的手指找到了一個門閂,一扇薄薄的門彈開了。
雖然我知道宮殿裡到處都是通道,但做夢也沒想到卡登的臥室裡會有機關。然而……我應該仔細檢查每一吋牆壁才是。至少,我可以要求其中一個密探這樣做。但是我卻避開了,只因為我想避開和卡登單獨在一起的機會。
「別讓高王離開你的視線。」我告訴幽靈,然後拿起一支蠟燭,走到牆後的黑暗中,再次避免和他單獨相處。
隧道內很暗,整個隧道都被金色燭台照亮了,燭台舉著火炬,燒著無煙的綠色火焰。石頭地板上覆蓋著一塊破舊的地毯,對於一條祕密通道來說是個挺奇怪的裝飾。
我在幾呎內找到了一把十字弓。
它不像我隨身攜帶的那種小巧之物。這把十字弓的體積很大,比我半個人還大,顯然是被拖到這裡來──我看到地毯沿著它拖過來的方向一路捲起。
無論是誰,那人便是從這裡出手。
我越過這把十字弓,繼續向前。我以為這樣的地道會有許多分岔口,但這一條沒有,卻是每隔一段距離就向下傾斜,像一道斜坡,然後往內折轉;但它始終只朝著一個方向──筆直向前。我加快步伐,一邊用手護著燭焰,以免火光熄滅。
然後,我走到一塊刻有王家徽章的厚木板前,上面刻有跟卡登戒指上一樣的徽記。
我推了木板一下,木板像是在軌道上移動般地轉開。另一側有一個書架。
截至目前為止,我只聽說過一些關於高王埃爾德雷王宮內部房間的傳說;這些寢宮位處於宮殿中心地帶與精靈王國自治城鎮正上方,以及王位上頭最粗的枝幹如何蜿蜒穿過他的城牆。儘管我從未親眼見識過,然而關於其中的描述仍使我確定自己此刻正親臨現場。
我一手拿著蠟燭,一手持刀,穿梭過老高王埃爾德雷寢宮裡寬敞的房間。
然而此時,我看見一個身影坐在國王的高床上。她的臉上滿是淚水。
這個人正是妮卡莎。
她是奧拉戈女王的女兒,海底王國的公主,作為女王和老高王埃爾德雷幾十年前簽訂的和平條約的一部分,自小便在宮中生活。妮卡莎曾經是卡登那個邪惡四人幫的成員之一,也曾是卡登的摯愛,直到她為了洛克背叛他。自從卡登登上王位以來,她不再像以前那麼頻繁地出現在卡登身邊,然而無視於她的存在似乎並不構成犯罪動機。
這難道是巴勒金與海底女王私底下共謀的協議內容?他們密謀殺害卡登?
「是妳?」我喊道。「是妳射傷卡登?」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語風之靈(II):萬惡之王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語風之靈(II):萬惡之王 作者:荷莉.布萊克 / 譯者:盧相如 出版社: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9-1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語風之靈(II):萬惡之王
王與少女,王座之前,該相殺或要相愛--
命定預言•宮廷權謀•禁忌戀情•強強對決
【國外暢銷佳績/得獎紀錄】
♕全球最大書評網Goodreads 2019年度最佳No.1、全系列吸引近400,000讀者執迷不悔、虐戀深情推薦!
♕環球影業已簽下電影版權,由《社群網站》、《格雷的五十道陰影》製作人監製
♕出版即空降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1名
♕首刷加贈《萬惡之王》珍藏番外〈馬多克〉、〈卡登〉、〈暗殺〉
【各大媒體敲碗推薦】
「一部令人驚豔且引人入勝的續集。」《SLJ》
「《萬惡之王》有令人滿意的劇情轉折、炙熱的激情、殘酷的暴力、勾心鬥角和狂歡——沒有人像荷莉‧布萊克那樣,把錯綜複雜的精靈宮廷及政治表現得如此出色,或者說如此有魅力。」「書架情報網」(Shelf Awareness)
「在《萬惡之王》中,交織著宮廷角力、精靈傳說和吸引力,令人熱血沸騰……布萊克的創作既現代又經典。」《柯克斯書評》(Kirkus)
「難得能夠超越第一集的續集作品。可喜的是,後續還有更多的陰謀和激情。」《書單雜誌》(Booklist)
﹊﹊﹊﹊﹊﹊﹊﹊﹊﹊﹊﹊﹊﹊﹊﹊﹊﹊﹊﹊﹊﹊﹊﹊﹊﹊﹊﹊﹊
英俊墮落的精靈之王,
誓不屈服的人類少女,
爭奪的是權勢、輸贏及生死,還是求而不得的真心?
﹊﹊﹊﹊﹊﹊﹊﹊﹊﹊﹊﹊﹊﹊﹊﹊﹊﹊﹊﹊﹊﹊﹊﹊﹊﹊﹊﹊﹊
出乎意料地登基之後,新任高王卡登開始展現自己的統治手段。
在王座前,茱德是他的心腹總管;在王宮內,兩人間的拉鋸越來越緊繃——卡登不能違抗她的命令,卻能以言語及行為左右她的情緒。他的狡猾與難捉摸讓茱德逐漸懷疑自己的決定,又巧妙地鞏固王權。最令人恐懼的是,即使如此,迷戀依然無法控制地在彼此心中滋長。
於此同時,海底女王奧拉戈突然發難,威逼利誘要求卡登與女兒妮卡莎聯姻,甚至揚言不惜為此發動戰爭!
滴答滴答⋯⋯咒術的時限進入倒數,卡登即將脫離掌控,加上虎視眈眈的海底女王,茱德腹背受敵,但一個她極為親近的人已經選擇了背叛⋯⋯
我們應該停戰。我們早該在此之前就休戰了。
但我們誰也沒有喊停,當時沒有,以後也不會有。
所以--
殺了他。某部分的我在內心說著。在他讓妳愛上他之前。
作者簡介:
全球銷量超過一千兩百萬冊、紐約時報暢銷作者
荷莉‧布萊克(Holly Black)
荷莉‧布萊克著有三十多部兒童和青少年奇幻小說。曾入圍埃斯納獎(Eisner Award)和北極星獎(the Lodestar Award),並獲得星雲獎和紐伯瑞大獎。她的作品被翻譯成全球三十二種語言,並被改編成電影。目前,她和丈夫、兒子以及貓咪住在新英格蘭,家中擁有一間有祕密圖書館。
作者網站:www.blackholly.com
相關著作:《咒術家族》1-3、《魔法學園》1-5、《語風之靈》Ⅰ-Ⅲ
譯者簡介:
盧相如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目前為自由譯者。譯作有《晚安,美人》、《記憶游離》、《QA》(電影「貧民百萬富翁」暢銷原著小說)、《塵世樂園》、《最後的教父》、《語風之靈》系列等多部小說。
章節試閱
在幽靈喚醒我之前,我正舒服地裹著毯子待在壁爐前,身旁滿是文件和卷軸,輾轉反側。
我的手指上沾著墨水和蠟漬。起身後,我環顧四周,試圖回想自己睡著前正在寫些什麼,以及寫給誰。
蟑螂站在通往我房間的祕密通道入口處,一雙如鏡般反射、不帶人性的眼睛望著我。
我的皮膚又溼又冷,我的心怦怦跳著。
我依稀可以嚐到舌頭上的毒藥苦味和令人倒胃口的味道。
「他還是死性不改。」幽靈說。
我不必問他說的是誰。我或許耍了些心機讓卡登戴上王冠,但我還沒學會怎麼讓他表現得像國王那般莊重。
在我外出打探消息時,他便去找洛克。我很...
我的手指上沾著墨水和蠟漬。起身後,我環顧四周,試圖回想自己睡著前正在寫些什麼,以及寫給誰。
蟑螂站在通往我房間的祕密通道入口處,一雙如鏡般反射、不帶人性的眼睛望著我。
我的皮膚又溼又冷,我的心怦怦跳著。
我依稀可以嚐到舌頭上的毒藥苦味和令人倒胃口的味道。
「他還是死性不改。」幽靈說。
我不必問他說的是誰。我或許耍了些心機讓卡登戴上王冠,但我還沒學會怎麼讓他表現得像國王那般莊重。
在我外出打探消息時,他便去找洛克。我很...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