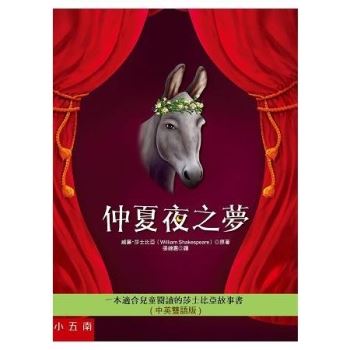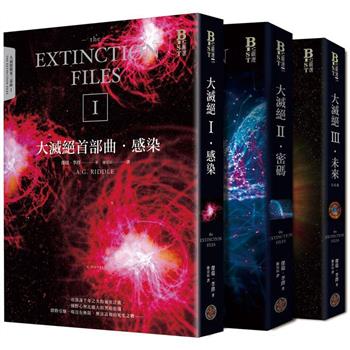★商周集團前執行長 王文靜21年練功心法,暢銷經典增修重出。
★台灣首位「美國艾森豪獎金」女性媒體得主。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被收錄在國、高中、大學6種版本國文教科書。
★7篇全新收錄文章,記錄人生新季節的轉變。
「人生是一場牌局,拿什麼牌,是命中注定;如何出牌,操之在己。」
(Life is like a game of cards. The hand that is dealt you is determinism; the way you play it is free will.)——印度前總理尼赫魯。
我的人生牌局,始於十八歲拿到的一張牌:一顆鴨蛋。
多年之後,我才懂得十八歲的這個鴨蛋,真是我這輩子最大的祝福。
2019年的人生牌局,我在待了近20年的媒體業沒了名片......
重啟一段嶄新的開始,咀嚼人生給予的小啟示。
放心,一切都會更好的!
「人生從沒允諾風平浪靜,但,精彩不會缺席。」
本書獻給所有想要重新學習的人,在經營管理間、工作職場中、人生道路上一些建議、自問與省思。
【經營啟發】當你沒有護航,就要亮出實力,搞定事情,把自己逼到牆角。逼你必須 擁有「搞定事情」的能力。
【職場啟發】沒有靠山,自己就是山;沒有天下,自己打天下。
【人生啟發】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不論是你的沮喪,或者是你的驕傲,其實都沒那麼大,你以為全世界都看到了,但其實沒有。
【挫折啟發】人生有如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不知道你將會拿到那一顆。
【自然的啟發】探索未知之地是人類的天性,唯一真正的失敗是,我們不再去探索。
【智慧啟發】心中有事虛空小,心中無事一床寬。
心的寬度,決定你的高度!
品味私塾總策劃-王文靜,「恐懼禁錮了很多人的狀態,克服它,人生就會很不一樣。」
她,沒有大學文憑,卻在台大教書
她,數學考零分,卻天天看財報
她,英文底子差,卻時常擔任國際論壇演講者
這是一個從「零」開始的鴨蛋人生,每日改變一點點,結果是無限大!
一本寫了二十一年的書,從我三十四歲開始寫,它是我的工作日記,從我的眼睛看台灣與世界,看人物起落與四季更迭;隨我的足跡探索高山與極地,探索富裕國度與貧窮村落。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暢銷珍藏版】的圖書 |
 |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暢銷珍藏版】 作者:王文靜 出版社: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0-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15 |
勵志故事 |
$ 355 |
自我成長 |
$ 355 |
勵志故事 |
$ 356 |
成長/致富 |
$ 356 |
Books |
$ 356 |
Books |
$ 356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96 |
中文書 |
$ 40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暢銷珍藏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文靜
品味私塾總策劃/作家/執教於台大新聞研究所/商周集團前執行長
採訪希拉蕊等一千位政商界領袖。行旅70國,從南極到非洲部落。前商周集團執行長,擔任《商業周刊》總編輯期間,率團隊獲「最佳總編輯」等44座國內外獎項。
獲獎:台灣首位「美國艾森豪獎金」女性媒體得主。
著作:《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被收錄在國、高中、大學6種版本國文教科書。
FB:王文靜 看世界
王文靜
品味私塾總策劃/作家/執教於台大新聞研究所/商周集團前執行長
採訪希拉蕊等一千位政商界領袖。行旅70國,從南極到非洲部落。前商周集團執行長,擔任《商業周刊》總編輯期間,率團隊獲「最佳總編輯」等44座國內外獎項。
獲獎:台灣首位「美國艾森豪獎金」女性媒體得主。
著作:《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被收錄在國、高中、大學6種版本國文教科書。
FB:王文靜 看世界
目錄
作者序 在另一個遼闊,開啟另一故事
01 話成長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
戰敗的孩子
千金難買少年貧
心中伏獅
征服的不是高山,是自己
南威之容,龍泉之利
下台・上台
我是一隻豬
斷腳酒杯
02 聊花草・自然
巨人與侏儒樹
南瓜與鐵絲
香草生死鬥
不與赤陽相遇
風吹柳動・未見柳折
密林養幹
原來是山茼蒿
晨曦木瓜樹
田螺含水過冬
辦公室沒有藍鵲嗎?
十姊妹與胡錦鳥
無翼鳥的滅絕
03 議旅途
古圳重現天日! 一條在台北消失的河(台北)
春天退潮,藻田祕境(基隆)
錯過山毛櫸(宜蘭)
飯包哲學(台東)
沃土種出膚淺的葡萄樹(法國)
如果,海豚真的游回威尼斯(義大利)
貪睡的長頸鹿(尚比亞)
螞蟻高,還是長頸鹿高?(克羅埃西亞)
另一種革命家(馬拉威)
艾森豪隨筆(前進美國)
艾森豪之旅(前進美國)
生氣盎然的驢子,總比死獅子來得好(南極)
沒有電話的飯店(德國柏林)
郵輪上的「仙女」(美國阿拉斯加)
04 論人
餃子露出餡
萊比錫女孩
不能飛高走遠
老闆教我的兩件事
平庸的馬伕主管
將軍的價值
當傑克・威爾許遇上韓非
成功關鍵,90%想失敗
說人話
燈泡或發電機
能大能小
心中之尺
受與擔
包子學
大佛與石階
小三與小四
冒牌貓
危險動作C.C.
失去眼鼻的主管
請問,發票要開統編嗎?
Delete垃圾流程
一顆單純的心
After the Game is Before Game
05 談天地
逢山游山,逢水玩水
菩薩重因,眾生重果
燒柴大小事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流奶與蜜
心中無事一床寬
地上的鹽
掛在樹梢的麵包
蘋果,可以給我嗎?
沒事常吃飯,有事打電話
拖鞋之交
06 過去,成就未來的路
四只鑽戒
被停權的女兒
品味私塾四部曲-春、夏、秋、冬
在夏天,當麵包遇到香蕉(品味私塾.夏部曲)
一座古島的世界四大奇景(品味私塾.冬部曲)
從高山到海洋--我走山海圳(品味私塾.春部曲)
故事一八六九,一條茶金之河的秋日(品味私塾.秋部曲)
01 話成長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
戰敗的孩子
千金難買少年貧
心中伏獅
征服的不是高山,是自己
南威之容,龍泉之利
下台・上台
我是一隻豬
斷腳酒杯
02 聊花草・自然
巨人與侏儒樹
南瓜與鐵絲
香草生死鬥
不與赤陽相遇
風吹柳動・未見柳折
密林養幹
原來是山茼蒿
晨曦木瓜樹
田螺含水過冬
辦公室沒有藍鵲嗎?
十姊妹與胡錦鳥
無翼鳥的滅絕
03 議旅途
古圳重現天日! 一條在台北消失的河(台北)
春天退潮,藻田祕境(基隆)
錯過山毛櫸(宜蘭)
飯包哲學(台東)
沃土種出膚淺的葡萄樹(法國)
如果,海豚真的游回威尼斯(義大利)
貪睡的長頸鹿(尚比亞)
螞蟻高,還是長頸鹿高?(克羅埃西亞)
另一種革命家(馬拉威)
艾森豪隨筆(前進美國)
艾森豪之旅(前進美國)
生氣盎然的驢子,總比死獅子來得好(南極)
沒有電話的飯店(德國柏林)
郵輪上的「仙女」(美國阿拉斯加)
04 論人
餃子露出餡
萊比錫女孩
不能飛高走遠
老闆教我的兩件事
平庸的馬伕主管
將軍的價值
當傑克・威爾許遇上韓非
成功關鍵,90%想失敗
說人話
燈泡或發電機
能大能小
心中之尺
受與擔
包子學
大佛與石階
小三與小四
冒牌貓
危險動作C.C.
失去眼鼻的主管
請問,發票要開統編嗎?
Delete垃圾流程
一顆單純的心
After the Game is Before Game
05 談天地
逢山游山,逢水玩水
菩薩重因,眾生重果
燒柴大小事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流奶與蜜
心中無事一床寬
地上的鹽
掛在樹梢的麵包
蘋果,可以給我嗎?
沒事常吃飯,有事打電話
拖鞋之交
06 過去,成就未來的路
四只鑽戒
被停權的女兒
品味私塾四部曲-春、夏、秋、冬
在夏天,當麵包遇到香蕉(品味私塾.夏部曲)
一座古島的世界四大奇景(品味私塾.冬部曲)
從高山到海洋--我走山海圳(品味私塾.春部曲)
故事一八六九,一條茶金之河的秋日(品味私塾.秋部曲)
序
作者序
在另一個遼闊,開啟另一故事
「王文靜?是不是我們老師說的,學測沒考好但是後來很厲害的那個人?友人就讀國中的女兒讀到國文教科書〈貪睡的長頸鹿〉時發問。那日,在高山工作的我,窗外的雲頓時飄飄入心。這是《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的其中一篇。二○一六年此書出版後,陸續被從國中到大學的六種版本教科書收錄。名字出現在教科書上,比在媒體上更讓人興奮。
而今,在三采出版規劃下,以【暢銷珍藏版】重新上市。
近年,我的生活有些變化,但不變的是依然在說故事。我沒有信手拈來皆經典的才情,但總是好奇。我在好奇中探索世界、發現故事,逐漸形成寫作的風格。不論長途旅行或街頭漫步,一株樹,一種動物,或一位古人都能引發我的巨大好奇,在好奇中探索與思考。
〈貪睡的長頸鹿〉是我至尚比亞,見到巨大長頸鹿的好奇:「四公尺高的大個子怎麼睡覺,長頸鹿的睡眠時間有多長?」當嚮導回答:「長頸鹿只睡三分鐘」。時,徹底掀起我對大自然生物的巨大好奇。這是首次有人以非洲的叢林故事,比喻職場競爭。另一篇收入教科書的文章〈飯包哲學〉,是到池上飯包博物館的旅行,好奇牆上文字的背後:「飯包是做給外出人吃的,一定要用心。」原來,這是一位做了六十年便當,仍一本初衷的阿嬤。
此生,我最大的資產,就是腦子總在想「為什麼」,跳動著無數的「為什麼」,這豐盛了我蒼白的人生。從某一個角度看,我是一名獵人。獵人的訓練──觀察與等待。其境界,不只在槍枝,不只在狩獵技巧,而在能與大自然對話。
帶著「為什麼」這把獵槍,我旅行、我採訪、我閱讀與寫作。從我的眼睛看台灣與世界,看人物起落與四季更迭;隨我的足跡探索高山與極地,探索富裕國度與貧窮村落。形成這本書的大架構:
之一 鴨蛋人生
十八歲數學考零分,以致於沒考上大學,那顆「鴨蛋」影響我對於挫折、文憑、成就的態度。後來長年採訪成功或失敗人物,形成我對於人生路徑的看法。本書收錄的〈萊比錫女孩〉、〈千金難買少年貧〉、〈不能飛高走遠〉、〈南瓜與鐵絲〉、〈螞蟻高,還是長頸鹿高?〉……都是這類的探討。沒有大學文憑,不是我的選擇,是被淘汰的結果。所以,我絕不是主張「文憑無用論」,想說的是,這讓我明白:沒有靠山,自己就是山;沒有天下,自己打天下。逢山過不去,就開路穿去;遇水阻攔,就架橋跨過。
之二 以大自然為師
我生於漁村,從小聽海聲長大。成人後,倚山而居。不論山或海,都讓我有莫名的悸動,我觀察萬物的存活哲學,獲得很多靈感,譬如辦公室的藍鵲、含水過冬的田螺、能矮小能巨大的玉山圓柏、不與赤陽相遇的曇花……從大自然體悟道理,以物喻事,逐漸融入我的文章風格。如果我的生活抽走大自然,肯定無法展現寫作的多面貌。
之三 永不停止探索
我喜歡冒險與旅行,走過七十個國家,去過冰封雪地的南極,拜訪過以老鼠為食的非洲貧窮部落。我探索國家,也探索大時代的精彩人物。譬如希拉蕊
(Hillary Rodham Clinton)、已逝的奇異(GE)集團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Google 前執行長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還有「華人首富」李嘉誠。在〈成功關鍵,九○%想失敗〉一文,我寫道,李嘉誠之所以與眾不同,因為思維不同。他做決策時會花九○%思考失敗,因為:「世上並無常勝軍,所以在風平浪靜時,好好計畫未來,仔細研究可能出現的意外及解決辦法。」
〈另一種革命家〉的主角是「印度矽谷之父」暨「全球最令人景仰的領導者」穆爾蒂(N. R. Narayana Murthy),我問,希望日後人們如何記得他?他回覆:「一個待人公平的人;一個用資料分析得到結論的人;一個心胸開放,樂意接納別人意見的人;一個接受犯錯空間的人。」
有些篇章雖已成文多年,但讀來仍耐人尋味。重新上市的【暢銷珍藏版】在上述外,新增六篇,包括〈春天退潮,藻田祕境〉、〈古圳重現天日!一條在台北消失的河〉、〈在夏天,當麵包遇到香蕉〉、〈如果,海豚真的游回威尼斯〉。
好奇如一對有巨大力量的翅膀,可讓人穿梭時空,打破眼睛的框界,生命瞬間變大、變立體、變活。有些人才日正當中,卻過得蒼白。少數人在白髮蒼蒼時,卻生龍活虎。生龍活虎,不是靠一針興奮劑,而是有一顆想探索的心,成就人生的高潮迭起。
一如我在這本書引用南極探險家薛克頓(Ernest Shackleton)的話:「一隻生氣盎然的驢子,總比一隻死獅子來得好。」四度到南極的他說,探索未知之地是人類的天性,唯一真正的失敗,是我們不再去探索。
如今,我離開原任職的商周,創立「品味私塾」。在另一個遼闊,展開新旅程與新的人生故事。遼闊,也代表未知。人生風景,時有不同,很幸運的是,不論繁華或荒涼,這些年,有一個人總默默地支持我。他,是我先生。言語不多但讀書甚多的他,簡直就是一座圖書館,文采亦勝我。人生,難能得此鐵粉。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頭號粉絲與家人,
是你們讓我在荒涼中,走出繁華風景。
在另一個遼闊,開啟另一故事
「王文靜?是不是我們老師說的,學測沒考好但是後來很厲害的那個人?友人就讀國中的女兒讀到國文教科書〈貪睡的長頸鹿〉時發問。那日,在高山工作的我,窗外的雲頓時飄飄入心。這是《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的其中一篇。二○一六年此書出版後,陸續被從國中到大學的六種版本教科書收錄。名字出現在教科書上,比在媒體上更讓人興奮。
而今,在三采出版規劃下,以【暢銷珍藏版】重新上市。
近年,我的生活有些變化,但不變的是依然在說故事。我沒有信手拈來皆經典的才情,但總是好奇。我在好奇中探索世界、發現故事,逐漸形成寫作的風格。不論長途旅行或街頭漫步,一株樹,一種動物,或一位古人都能引發我的巨大好奇,在好奇中探索與思考。
〈貪睡的長頸鹿〉是我至尚比亞,見到巨大長頸鹿的好奇:「四公尺高的大個子怎麼睡覺,長頸鹿的睡眠時間有多長?」當嚮導回答:「長頸鹿只睡三分鐘」。時,徹底掀起我對大自然生物的巨大好奇。這是首次有人以非洲的叢林故事,比喻職場競爭。另一篇收入教科書的文章〈飯包哲學〉,是到池上飯包博物館的旅行,好奇牆上文字的背後:「飯包是做給外出人吃的,一定要用心。」原來,這是一位做了六十年便當,仍一本初衷的阿嬤。
此生,我最大的資產,就是腦子總在想「為什麼」,跳動著無數的「為什麼」,這豐盛了我蒼白的人生。從某一個角度看,我是一名獵人。獵人的訓練──觀察與等待。其境界,不只在槍枝,不只在狩獵技巧,而在能與大自然對話。
帶著「為什麼」這把獵槍,我旅行、我採訪、我閱讀與寫作。從我的眼睛看台灣與世界,看人物起落與四季更迭;隨我的足跡探索高山與極地,探索富裕國度與貧窮村落。形成這本書的大架構:
之一 鴨蛋人生
十八歲數學考零分,以致於沒考上大學,那顆「鴨蛋」影響我對於挫折、文憑、成就的態度。後來長年採訪成功或失敗人物,形成我對於人生路徑的看法。本書收錄的〈萊比錫女孩〉、〈千金難買少年貧〉、〈不能飛高走遠〉、〈南瓜與鐵絲〉、〈螞蟻高,還是長頸鹿高?〉……都是這類的探討。沒有大學文憑,不是我的選擇,是被淘汰的結果。所以,我絕不是主張「文憑無用論」,想說的是,這讓我明白:沒有靠山,自己就是山;沒有天下,自己打天下。逢山過不去,就開路穿去;遇水阻攔,就架橋跨過。
之二 以大自然為師
我生於漁村,從小聽海聲長大。成人後,倚山而居。不論山或海,都讓我有莫名的悸動,我觀察萬物的存活哲學,獲得很多靈感,譬如辦公室的藍鵲、含水過冬的田螺、能矮小能巨大的玉山圓柏、不與赤陽相遇的曇花……從大自然體悟道理,以物喻事,逐漸融入我的文章風格。如果我的生活抽走大自然,肯定無法展現寫作的多面貌。
之三 永不停止探索
我喜歡冒險與旅行,走過七十個國家,去過冰封雪地的南極,拜訪過以老鼠為食的非洲貧窮部落。我探索國家,也探索大時代的精彩人物。譬如希拉蕊
(Hillary Rodham Clinton)、已逝的奇異(GE)集團前執行長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Google 前執行長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還有「華人首富」李嘉誠。在〈成功關鍵,九○%想失敗〉一文,我寫道,李嘉誠之所以與眾不同,因為思維不同。他做決策時會花九○%思考失敗,因為:「世上並無常勝軍,所以在風平浪靜時,好好計畫未來,仔細研究可能出現的意外及解決辦法。」
〈另一種革命家〉的主角是「印度矽谷之父」暨「全球最令人景仰的領導者」穆爾蒂(N. R. Narayana Murthy),我問,希望日後人們如何記得他?他回覆:「一個待人公平的人;一個用資料分析得到結論的人;一個心胸開放,樂意接納別人意見的人;一個接受犯錯空間的人。」
有些篇章雖已成文多年,但讀來仍耐人尋味。重新上市的【暢銷珍藏版】在上述外,新增六篇,包括〈春天退潮,藻田祕境〉、〈古圳重現天日!一條在台北消失的河〉、〈在夏天,當麵包遇到香蕉〉、〈如果,海豚真的游回威尼斯〉。
好奇如一對有巨大力量的翅膀,可讓人穿梭時空,打破眼睛的框界,生命瞬間變大、變立體、變活。有些人才日正當中,卻過得蒼白。少數人在白髮蒼蒼時,卻生龍活虎。生龍活虎,不是靠一針興奮劑,而是有一顆想探索的心,成就人生的高潮迭起。
一如我在這本書引用南極探險家薛克頓(Ernest Shackleton)的話:「一隻生氣盎然的驢子,總比一隻死獅子來得好。」四度到南極的他說,探索未知之地是人類的天性,唯一真正的失敗,是我們不再去探索。
如今,我離開原任職的商周,創立「品味私塾」。在另一個遼闊,展開新旅程與新的人生故事。遼闊,也代表未知。人生風景,時有不同,很幸運的是,不論繁華或荒涼,這些年,有一個人總默默地支持我。他,是我先生。言語不多但讀書甚多的他,簡直就是一座圖書館,文采亦勝我。人生,難能得此鐵粉。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頭號粉絲與家人,
是你們讓我在荒涼中,走出繁華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