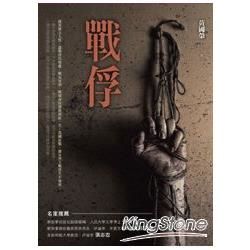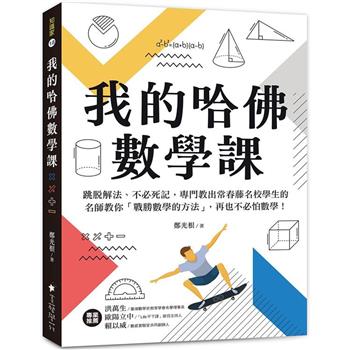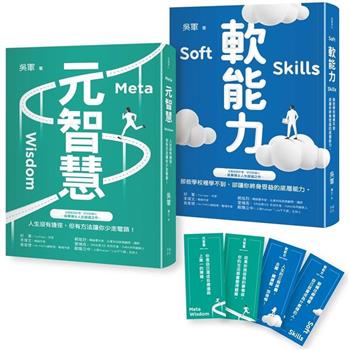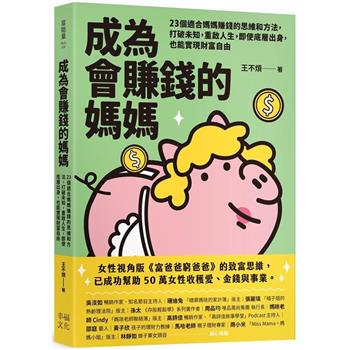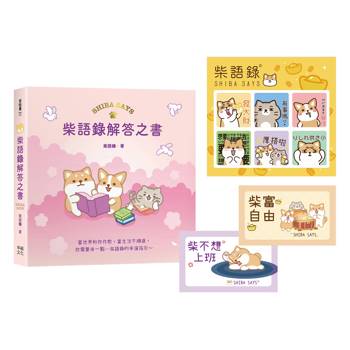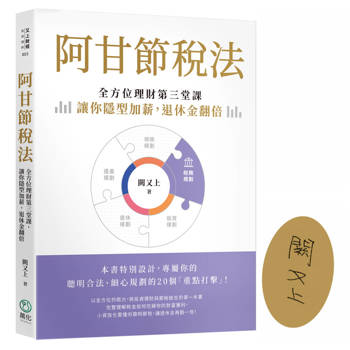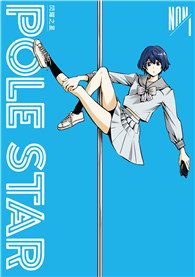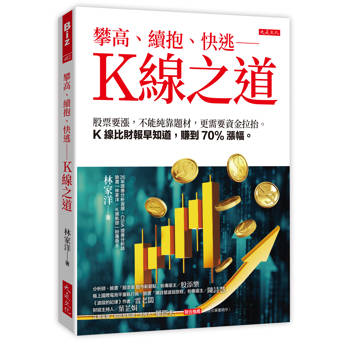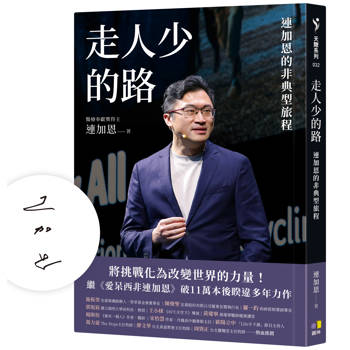自序
與魔共舞
清晨,當你從舒坦的酣睡中自然醒來,翻身起床,打開大門,門口一隻東北虎正張著血盆大口等著你。意外威脅讓你產生的恐懼、失態與慌亂,與突然遭遇戰爭有某些相似。戰爭小說的魅力或許就在它的驚悚恐怖、險象環生、懸念跌宕、曲折緊張、大悲大喜。
去年發表在《文學報》上的那篇《文學的聲音》裡,我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我不贊同顧彬先生「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這說法。但是,我非常欣賞顧彬先生近期與李雪濤先生《對談》中表達的一個觀點。他說:「我認為: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應該有一個聲音,這個聲音是一位作家。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聲音。所以我要問,中國有這樣一個聲音嗎?……一九四九年以前好像有過,就是魯迅。而這之後呢?還有嗎?還需要嗎?」
我一直以為,戰爭小說才是軍事文學的正宗,好的戰爭小說很有可能會說出國家和民族的聲音。做為一名軍人寫作者,一輩子寫不出一部真正的戰爭小說,似乎有點枉頂了軍旅作家這個頭銜。當然,不是說我的這部小說代表了國家和民族的聲音,也不是說我為了這才寫這部小說,只是認為社會和讀者需要好的戰爭小說。寫這部小說的真實動因還是生活,要沒有親自把自己一百零八個部下送上戰場這個經歷,我絕對想不到要寫也絕對寫不出這部小說。內心的追求與生活的切合促成我寫出了這部小說。
每一個作家寫一部作品,都把他想要表達的東西隱含其中,讓讀者在閱讀中感悟而產生共鳴,這是作家寫作的根本目的,也是文學的力量。
我想讓大家認識戰爭是個魔鬼。這是一部虛構作品,寫了一場虛擬的戰爭,
小說也許有歷史中戰爭的影子,但小說中戰爭的對象是虛擬的,戰爭在這裡僅僅是小說中人物的生存環境。雖然是虛擬的戰爭,但我想要大家認識到,戰爭所導致的血腥屠殺和反屠殺不只致使雙方死亡,甚至要連帶無辜遭受厄運;不僅塗炭生靈,還會破壞大自然;不僅毀滅生命,還會給活著的人們留下無盡的痛苦與創傷。精神正常的人絕不願與這魔鬼為伍,只有利令智昏的瘋子狂人才會與它結伴同行。作家寫戰爭小說,讀者喜愛讀戰爭小說,並不是嚮往戰爭,而是試圖瞭解戰爭、研究戰爭、認識戰爭、學習戰爭、制止戰爭,以至消滅戰爭。
我還想讓大家認識戰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只要世界上存在國家和民族,它就不可能消亡。至今,家庭仍然是人類社會的細胞,人類還是以群落居住方式相互依存。有家庭便有家庭利益,有群落就有群落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家庭利益、群落利益的最高形式。有利益必有紛爭,有紛爭必導致戰爭。對戰爭無法逃避,只有拿起武器,用戰爭消滅戰爭。
我更想要告訴大家,英雄首先是人,軍人也是人。沒有人對戰爭不懼怕,也沒有一個英雄生來就想犧牲當英雄。邱夢山和他的戰友們同樣是父母所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同樣有七情六慾。面對戰爭這個魔鬼,他們同樣恐懼,誰都不願意無故犧牲。在戰場他們跟敵人作戰,同時也在跟自己作戰,他們要把七情六慾擰合成一個意念--愛國、愛民族、愛人民。邱夢山他們令人敬愛,不只是他們英勇作戰,收復失地,讓祖國領土完整,拯救邊疆人民於水火,更感天動地的是他們同時在孝敬父母,摯愛妻子和孩子,渴望享受人間的美好生活。這種孝敬、摯愛和渴望客觀自然地融合在為國家和民族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行為之中,但集體英勇行動中,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差異,英勇行為中包含著種種個人的意念,作家和文學的任務就是要真實地再現戰爭中各色人物的這種差異和個人意念。邱夢山和荀水泉都是英雄,但他們是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石井生和倪培林都非常英勇,但他們的英勇卻有很大區別;彭謝陽的懼戰與倪培林面對死亡突然的膽怯性質也不相同。儘管邱夢山和他的戰友們在戰場上思想各異,有一點卻是一致的,他非常清楚軍人的職責,戰爭的正義性要靠軍人用犧牲來捍衛。他們不願意無故犧牲,但他們絕不允許敵人橫行,不能眼睜睜看著百姓遭受欺凌,不能讓國家喪失尊嚴,不能叫民族蒙受恥辱,於是他們穿槍林、過彈雨、蹚雷陣,赴湯蹈火,義無反顧。他們明白,勝利之路是用軍人鮮血鋪成;犧牲三個戰友,消滅五個敵人,就是勝利;犧牲自己,守住陣地,就是勝利。在魔鬼面前,要麼戰勝魔鬼,要麼被魔鬼吞噬,別無選擇。軍人的職業就是與魔共舞,無論他們是英雄,還是戰俘,他們都在為國家與民族而戰,社會和人們對軍人應該多一些理解,多一點愛。
我還想告訴大家,英雄主義是國家之魂,是民族之魂,是軍隊之魂,是軍人之魂。戰爭絕不是遊戲,是你死我活的相互殘殺,非常慘無人道(當下的敘利亞戰亂,已有兩萬餘人喪生)。和平生活是人類生存的常態,戰爭是人類生存的非常態。作家對戰爭的思考是多方位的,思考最多的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無論軍人還是普通老百姓),從和平生活的常態,突然捲入戰爭生活的非常態,發生的是怎樣的逆轉;再從戰爭生活非常態轉入和平生活的常態,又是怎樣的一種恢復。在這兩種狀態轉化的環境下,國家、民族和人如何生存?該怎樣生存?這正是作者藉以小說中人物想要表達和告訴廣大讀者的東西。我想讓大家明白,一個不崇拜英雄的國家,不可能是英雄的國家;一個不崇拜英雄的民族,也不可能是英雄的民族;一個不崇拜英雄的軍隊,更不可能是英雄的軍隊;一個不崇拜英雄的人,他不可能成為英雄。邱夢山是這兩種狀態轉化下的一個典型。戰前戰中,他無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連長;戰後,他成了戰俘,他從你死我活搏殺的戰場走進了另一個「戰場」,他一直在以軍人的身分,為自己的尊嚴在與世俗觀念抗爭,在與歧視他的人抗衡,在與自我爭鬥。用邱夢山的話說:「軍人可以承受流血犧牲,絕不蒙受恥辱;軍人可以丟腦袋,絕不丟尊嚴」。「真英雄不只是戰勝敵人打勝仗,而且在經受失敗挫折時還能像個男人活著!」
我還想要大家明白,軍隊赴戰場作戰,人民是後盾靠山。正義的戰爭都是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戰爭更離不開人民的支持。邱夢山和他的戰友們在戰場流血犧牲,岳天嵐、曹謹、依達就是他們的精神支柱,一想到她們,他們就無所畏懼,英勇無比。他們有一個心念,為祖國而戰,為民族而戰,也是為自己的親人而戰。可世俗中的人們,相當多的人並沒能真正明白這個道理,有一些人的情感有點麻木,邱夢山他們犧牲也好,流血也罷;痛苦也好,鬱悶也罷,似乎一切都與自己毫無關係。
我在第十章「天道」裡寫到邱夢山去邊界烈士陵園給犧牲戰友祭典,看墓老人發感慨說,咱中國人現在不缺吃,不缺穿,也不缺錢,只缺一樣東西,缺心。中國年輕人缺不忍心,缺羞恥心,缺辭讓心,缺惻隱心,缺感恩心,快成空心人啦。邱夢山離開烈士陵園時,心裡非常鬱悶。他孤寂地走在山野裡,對著空曠而荒涼的山野悲憤地喊,沒有心哪!都成空心人啦!空心人啊……
乾隆在穹覽寺碑文中寫道:「萬機偶暇即窮經史,性理諸書,臨池揮翰,膳後即較射觀德,以安不忘危之念,此乃大略也。」乾隆避暑之中尚且不忘習武練射,居安思危。假如讀者讀了這部小說,在國泰民安的幸福日子裡,還能想到有些國家對我國崛起始終心存敵意,我們的釣魚島還被人佔著,春曉油田常常受別國飛機、軍艦的騷擾,周邊國家對南沙群島居心叵測,巴拿馬運河還不是我們的安全國際通道,我們的同胞剛剛在湄公河上無辜遭人搶殺,這就算我沒白費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