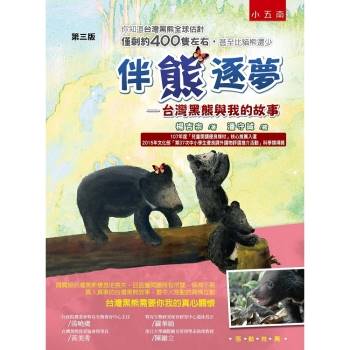南國的鄉下,
一個神秘的老人,
一個機智的少年,
溝通陰陽兩界,
以鬼為敵,以鬼為友。
通鬼靈,說鬼語,每個午夜背後都有一個不可告人的虧心事,心中有鬼,鬼就來了……
水潭裡的長毛髮,
峽谷裡的嬰兒哭,
房梁上垂掛的紅嫁衣,
荒野裡行走的綠屍體,
沒有呼吸的活人,
燒不掉的紙錢……
一個個謎團讓村民不斷陷入精神恐怖的極限,在坊間流傳的恐怖傳聞一次次侵擾著村民的內心,是的,它們,隱藏在仍然未知的恐懼中,步步逼近。
而現實中,卻只有一對爺孫能夠洞察詭異的秘密……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真的有鬼?零時與鬼有約的圖書 |
 |
真的有鬼? 零時與鬼有約 作者:童亮 出版社: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7-24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34 |
推理/驚悚小說 |
$ 148 |
中文書 |
$ 149 |
驚悚/懸疑小說 |
$ 152 |
華文驚悚/恐怖小說 |
$ 1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真的有鬼?零時與鬼有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