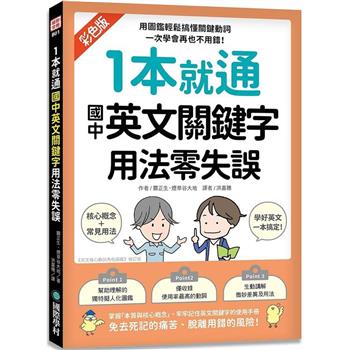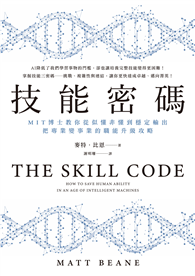午後,程貴從縣衙回到程宅,陰著一張臉直接進了內院。
他將程安玖的那封告訴書直接砸到柳氏的臉上,喝道:「妳是瘋了嗎?竟遣人去打砸玖娘在安陽坊的舊屋!」
到了晌午還等不到楊嬤嬤的回稟,柳氏開始懷疑是否事情不順,但她以為是楊嬤嬤辦事不力,或是被那些從市井僱來的幾個潑皮纏磨要價脫不開身,沒想到那死丫頭片子竟會去衙門告她。瞧程貴臉色不善,她眼珠子轉了轉,這會兒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
柳氏撿起落在地板上的告訴書,快速看完後做出一副驚嚇狀,眼眶通紅,淚水撲簌,哽咽辯解道:「老爺,這到底是誰在陷害妾身?這告訴書上所言妾身完全不知情,讓人去打砸安陽坊舊屋,妾身沒有做過這事,絕不能任人如此栽贓!老爺,你我夫妻多年,難不成你寧願相信別人也不相信我?」
程貴最怕柳氏這副哭哭啼啼的模樣,不耐煩的擺了擺手道:「妳也不用巧言強辯,若是沒影兒的事,玖娘不會憑空誣告妳。妳身邊侍候的那個楊嬤嬤還有上門打砸的四個潑皮早讓玖娘拿下送去衙門,他們已經作供畫押,指證是受妳指使行事。」
程貴看著柳氏那張變了顏色的臉,冷哼一聲瞪著她道:「若非周大人與我有些交情,私下知會我去處理,否則這事兒要是鬧開了,妳我顏面掃地不說,角逐北境供糧的生意也將化為烏有,白白便宜了其他人,妳看妳做的好事!」
柳氏這才知道自己險些壞了大事,只是她完全沒想到,那程安玖看著不聲不響的,竟敢去衙門告她,俗話說得好,不叫的狗會咬人。
她心頭憤恨,腮幫子繃得鼓鼓的,一口銀牙幾乎要咬碎,可眼前這攤子還是得收拾。她低下頭,淚如雨下辯白道:「老爺,妾身委實不知情啊,多半是楊嬤嬤陽奉陰違,拿妾身的名頭胡作非為,妾身根本不知道程安玖回榮成縣的事,且她又沒來招惹妾身,妾身怎會做出給老爺臉面抹黑的事情呢?」
程貴豈聽不出她這是在推卸責任,他這些年對柳氏縱容,是因為有高人指點柳氏八字旺夫,有她在自己身邊,他的生意才能越做越大,順風順水。本來他一開始也是半信半疑,可自打柳氏被扶正後,家裡生意果然是一帆風順。而柳氏私下的那些手段雖然上不得檯面,可還算是無傷大雅,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她去了。
可這次事情若是鬧大了,他的對手肯定會拿此事大做文章攻擊他,萬一處理不好,極有可能會被取消角逐皇商頭銜的資格。一想到後果的嚴重性,程貴便不打算這般輕易的饒了她。
「事實真相如何,我心中自有尺度。從今日起,妳就待在家裡哪兒也別去。我可把話放這兒,日後妳要是膽敢對玖娘使這些手段,可別怪我不念這些年的夫妻情分。柳氏,人心不足蛇吞象,這些年我待妳如何,妳自個兒好好掂量掂量。」程貴沉著臉警告道。
柳氏睜大眼睛,不敢置信的看著程貴揚長而去,腦袋裡嗡嗡作響,不明白程貴為何突然會對她說出這樣的話?這些年來,她說的話程貴多半會聽,也從來沒有對她這般冷漠無情過。她是這個家的功臣,不只為程貴生了鵬哥兒繼承香火,還辛苦操持內宅、為他打點應酬交際,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可到頭來竟得來這樣的警告,八成是程安玖那個小賤人灌了什麼迷湯,程貴才會這樣對待自己。
柳氏越想越氣,對程安玖的怨恨更深了。
◎
程貴到來,趙嬤嬤並沒有給他好臉色。她心裡對他有怨恨,若非他這樣縱容柳氏,柳氏焉敢如此肆意妄為?
程安玖卻是早料到程貴會來,所以也不讓趙嬤嬤收拾屋子,反倒帶他四處觀光。
「程老爺看到了,我這屋裡頭的傢俱都不能用了,該怎麼辦,程老爺是聰明人,不必我把話講透吧?」程安玖微笑的說道。
程貴一張老臉黑沉如墨,他這輩子最討厭被人抓著把柄威脅,這會兒還是被自己的閨女威脅,別提心裡有多嘔了。
「這件事其實只是誤會,咱們一家人怎麼解決都行,何必拿到外面招惹人笑話?」程貴是個好面子的人,哪肯讓家醜傳揚出去,自然是要私下裡解決的。他掃了一圈屋裡頭破敗不堪的擺設,道:「一應所需的傢俱,我會派人送新的過來。」
「就這樣?」程安玖嗤笑一聲問道。
「不若妳還想如何?」程貴穩住情緒反問道。
程安玖「呵呵」笑了兩聲,道:「看來程老爺是壓根兒沒有解決事情的誠意啊,我家原本好端端的,無緣無故被人強行上門打砸一通,且不說身心所承受的驚嚇和傷害,單就我母親留下來的這些傢俱,那都是有紀念意義、有市無價的東西,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那麼,我就明確表明一下我的立場和態度吧。」
她繞著程貴走了一圈,然後停下腳步,輕咳了兩聲,迎著程貴憤怒的目光含笑道:「這事程老爺您得處理得讓我們滿意,否則我就上告州府衙門,請州府大人稟公辦理。據我所知,程老爺最近在角逐什麼北境供糧的生意,不曉得會不會造成影響?」
「妳!」程貴哪裡料到程安玖會拿這件事威脅他,氣得眼睛都綠了,拔高音罵道:「不孝女!妳這是在向自己的父親敲詐勒索嗎?」
程安玖掩嘴輕笑,像調皮的孩子翻了翻白眼,道:「我可沒拿刀子逼柳氏遣人來我家打砸,讓我抓住把柄敲詐勒索你。再者,程老爺沒有盡到撫養我長大的義務,怎麼倒好意思怪起我不孝了?」
程貴感覺自己的五臟快要氣炸了,有種七竅生煙的感覺。
「妳到底要如何?」他有氣無力的問道。
「這個嘛……」
直到程貴氣呼呼的甩袖走人後,趙嬤嬤還感覺自己好似踩在雲端,暈乎乎的恍然置身夢境裡。她愣愣的看著程安玖,不敢相信的問道:「玖……玖娘,妳爹剛剛答應妳,願意付什麼精神損失費,給我們一千兩銀子?」
程安玖點點頭,微笑道:「他不答應也得答應,再說一千兩銀子對他而言委實不多,他當年霸占林家米業的家底,可遠不止這個數。」
「這倒是。」趙嬤嬤終於找到安撫自己的理由。
她是老實人,從沒想過要在柳氏派人砸屋的事情上做文章,當她聽見程安玖獅子大開口向程貴索討賠償時,她心裡惶惶,有些不安,如今轉念一想,心裡踏實了許多。
程安玖從來不是投機取巧、不講道理之人,如今這般藉機威脅,並非眼紅程貴的萬貫家財。程貴早年拋棄妻女,給林氏和原主姐妹倆造成的傷害是不可估量的。她不清楚當年林氏為何要將所有家業都拱手讓給程貴,這其中程貴有沒有威脅迫害她不知道,她只是從局外人的角度為林氏和原主姐妹感到不平,這些年她們過得如此悽苦潦倒,始作俑者程貴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程安玖分析過他們家如今的現狀,未來幾年都會過得辛苦拮据,她當捕快的那點俸祿只能勉強養活一家子,若有突發情況根本無法應付。誠如此次為林氏遷墳便在程安玖計畫之外,她身上帶的那點盤纏遠不夠買東山頭的那塊墓地。
柳氏讓人上門打砸對她而言是個機會,程安玖不是聖母,自然不會顧忌此舉是否有趁火打劫、乘人之危的嫌疑,所謂的道德公義也是要看人而論的。
「咱們收拾一下吧,一會兒就去六福客棧住。」程安玖對趙嬤嬤說道。
趙嬤嬤點頭道好,收拾衣物去了。
「娘,剛剛那人是誰?」文哥兒伸手拉住母親,噘著小嘴兒問道。
程安玖想起方才程貴對兩個孩子置若罔聞的態度,以及那不經意間看到時流露出來的厭惡眼神,心頭一陣疼痛。小孩子的心思單純,可誰對他好、誰對他不好,他們也有自己最直觀的感受。她將文哥兒摟進懷裡,儘管不願意承認,還是要告訴他們事實。
「他是你們的外公。」
「娘,外公好像不喜歡娘,也不喜歡我和武哥兒。」文哥兒眨著眼睛委屈道。
武哥兒聞言也鑽進程安玖的懷裡,像小大人一樣的勸道:「娘,沒關係的,外公不喜歡我們,我們也不喜歡他就是了。」
程安玖失笑,認真無比的點頭道:「是,對不喜歡我們的人,我們無視他就行了。」
等趙嬤嬤將衣物整理妥當後,程安玖就帶他們去程貴經營的六福客棧暫住。
四人才在客房安置下來,程貴就找上門來了。
「一千兩的銀票我帶來了,不過需要妳跟我去衙門走一趟,妳呈遞縣衙的告訴書要自個兒去撤回來。等事情辦完後,我就把銀票給妳。」程貴對程安玖說道。
面對一個如此精明算計的渣爹,程安玖委實無力吐槽,點了點頭,跟趙嬤嬤和孩子們交代一聲,隨著程貴去了一趟衙門。
周縣令將他們迎進縣衙內堂,經過一番了解,才知道原來程貴與苦主程安玖竟是父女。骨肉之間鬧到公堂對簿,說出去並不是什麼有臉的事,能私下解決自然是好的,也省得他左右為難。
周縣令秉著父母官的職責從中勸了幾句,讓師爺將告訴書取出來還給程安玖。而後,程貴又請周縣令當見證人,就柳氏這次僱潑皮上門尋釁打砸之事擬了一份賠償說明,與程安玖雙方各自簽署姓名,達成賠償協議。
這是家醜,還鬧到外人面前,程貴覺得很沒面子,將銀票交給程安玖後連多餘的寒暄都沒有,馬上起身與周縣令拱手告辭,領著程安玖一塊兒出了縣衙。
待兩人走了,師爺才在周縣令的呼喚下回過神來。他方才一直盯著程安玖看,越發覺得程貴的這個閨女,與池東海給他看過的那張畫像十分相似。
「看什麼呢?」周縣令問道。
師爺瞇著眼睛賠笑,找了個藉口應付道:「卑職是在想程老爺怎麼會與自個兒的閨女鬧到這個分上呢?」
周縣令也笑了笑,道:「可不是?這位程姑娘是程貴與先前和離的先夫人林氏生的,不得他喜愛。和離後林氏便帶著程姑娘遠走遼東府,鮮少回來。」
「原來是這樣。」師爺眸子轉了轉,尋思著要不要將這個消息告訴池東海,讓他確認一下這個程姑娘是不是他們要找的人。
◎
翌日清晨,程貴遣人去六福客棧告訴程安玖,林氏的新墳已經日夜趕工修繕妥當,明日一早要請一塵道長去新墳做法事,讓程安玖和趙嬤嬤明日卯時上山祭奠。至於祭拜的三牲果品,他自會命人買辦張羅,讓程安玖不必擔心。
這事兒讓趙嬤嬤好一陣詫異,想那程貴莫不是轉性了,突然這樣面面俱到,反而讓人心頭難安。
趙嬤嬤哪裡想得到,程貴這麼周到,也是希望林氏遷墳的事儘早處理完畢,好讓程安玖一行人早早回去遼東府,別在他競爭北境供糧期間再出什麼岔子。
原來程貴參選北境供糧的競爭已經進到最後階段,入選的名額有三個,都是附近州府數得上名號的米業大亨,而其中最具實力、有望奪得最後勝利的人當屬錦州府榮成縣的程貴,以及遼東府安東縣的何燦實,兩人底蘊沉厚,人脈關係也相當,實力不分伯仲。
程貴原本並不懼何燦實這個敵手,榮成縣是錦州府的中心縣,最後選拔在此舉行,論起優勢還是他略勝一籌。然而不怕狼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柳氏這個蠢婦竟在這個當口給他添亂,他若不顧全大局忍氣吞聲,這事萬一鬧大了,連參選資格都要被取消,這才是他如此小心翼翼選擇妥協的緣故。
由於遷墳祭奠的三牲果品被程貴承包了,程安玖倒是省下一番麻煩。左右無事,她便帶兩個孩子和趙嬤嬤去東市,打算在錢莊開個戶,將程貴賠償的那一千兩銀票存進去,再買些錦州府的土產帶回去送人。
四人在外頭用過午膳後,提著滿滿的東西回到六福客棧。
趙嬤嬤一進客棧的大門就覺得不對勁,狐疑的問道:「怎麼今日客棧這般安靜?」
程安玖也發現了,昨日她帶趙嬤嬤和兩個兒子搬進來住的時候,客棧內往來人流絡繹,熙熙攘攘儼如鬧市,與此刻的冷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見掌櫃從樓道口走出來,程安玖上前詢問因由,才知道原來這是程貴的意思。
北境供糧最後一輪的角逐,三日後就要在榮成縣商會舉行,由於何燦實和高宏遠這兩位米亨是外地人氏,在榮成縣沒有下榻的地方,程貴做為東道主,便主動向商會兜攬招待競爭對手的一應事宜,打算將兩人安置在自家經營的六福客棧。
因客人今晚就要住進來,為了保證環境清幽不受干擾,掌櫃便將客棧暫時清場,待選拔落幕後再重新開張做生意。
程安玖聽罷,心裡也暗讚程貴是個精明有手段的。他此舉肯定會引來外界的一片讚賞,順便拉一些人氣票。再者,將兩個競爭對手安置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也方便探知他們的底細、與什麼人接觸過,這招可謂是一舉兩得。總體而言,比起經營客棧每日得到的盈利,這背後帶來的連續效益才是巨大的,程貴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盤。
「那我們也要搬走嗎?」趙嬤嬤皺著眉頭問道。
掌櫃忙擺手,笑著說:「老爺交代過了,您幾位還是住在客棧二樓。」
「這便好。」程安玖淡笑,領著兩個孩子和趙嬤嬤上樓去了。
夜幕徐徐降臨,客棧門前升起兩排彩燈,燈光將門前的石階和近鄰的商鋪屋舍映上了斑駁的色彩。
隱約有喧囂聲傳來,程安玖走到窗前,推開一扇窗探頭往下看。兩輛奢華的馬車一前一後停在客棧門前,掌櫃和小廝都迎了出去,將馬車上已然喝得微醺的客人攙扶下來。
「這位是何老闆吧?小的已經命人將房間收拾好了,知道何老闆喜歡沉香,一早就燃上了。」掌櫃堆著滿臉笑意對何燦實道。
何燦實是個高大壯碩的中年人,四十來歲,留著八字鬍,衣著打扮通身貴氣。他捏著眉心的大拇指上戴著一枚扳指,玉質碧綠通透,映著門前的彩燈,隱約能看到其內緩緩流轉的光澤。掌櫃暗暗咋舌,他略通玉石,曉得何燦實戴著的那枚扳指是價值連城的寶貝。
何燦實今晚在宴會上喝多了,此刻酒意上湧,人醉得厲害,只嗯啊的隨意應和兩聲,整個人就像一灘泥,軟軟的趴在隨侍身上。
隨侍吃力的扶著主子,點點頭對掌櫃道:「有勞了。」
掌櫃回過神來,忙讓一個小廝幫忙攙扶,另一個小廝在前頭帶路,之後再去迎第二個貴客——高宏遠。
高宏遠是仙居府婁通縣人氏,也是這次最終競選三人中實力略顯薄弱的一個,比較年輕,體型修長精瘦,約莫只有三十歲出頭。
比起何燦實華麗的穿戴,高宏遠則是內斂低調許多,暗紋團花錦緞的寶藍色直綴,腰間繫著一條嵌著羊脂玉石的黑色腰帶,頭頂沒有戴冠,只簪著一支水頭極好的玉簪,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裝飾。
他似乎也喝了不少,狹長的眸子半瞇著,瞳孔透出迷離的光,笑著對掌櫃道:「程老闆就是客氣,好酒好菜的宴請不說,還如此周到為我們安排住宿的地方。」
掌櫃笑著接話:「我家老爺也只是略盡地主之誼,只望貴客不要嫌棄。」
高宏遠大笑:「豈敢豈敢。」
程安玖看到此處便收回目光,順手帶上窗戶,將一切喧囂吵雜隔絕在外,明日還要趕早上山祭奠,替兒子們洗漱後,一家四口上炕歇下。
後半夜的時候,程安玖睡夢迷糊間嗅到一股濃濃的焦臭味,而後被趙嬤嬤劇烈的嗆咳聲吵醒,一個激靈,翻身坐了起來。
屋子裡一片混沌晦暗,藉著透過窗櫺的月光,依稀能看到白色的煙霧從房門下的縫隙鑽進來。煙霧裊裊,如同婉約飄渺的輕紗,又似少女婀娜輕盈曼妙起舞的倩影,慢慢的在整個房間裡飄蕩繚繞起來。
程安玖暗叫不妙,剛要出聲喊趙嬤嬤和兒子們起身,就聽門外長廊傳來「匡匡」的鑼鈸聲,還有一聲聲劃破夜空的尖厲喊叫。
「著火了!著火了!」
「嬤嬤、文哥兒、武哥兒,快起來,客棧著火了!」程安玖大聲喊道。
趙嬤嬤坐起來,頭腦一陣昏沉,愣愣的看著程安玖將睡眼惺忪的孩子抱下炕,又聽外頭緊張急促的喊叫,這才回過神來。
「怎麼了?著火了?」趙嬤嬤心頭一跳,又低頭劇烈的咳嗽起來。
「嬤嬤快起來,咱們得趕緊撤離。」程安玖怕來不及,連衣裳都來不及穿,匆匆給孩子們披上外衣後,一手一個拉著他們出門。
趙嬤嬤不敢耽誤,抓起放在炕頭的包袱,趕緊下炕趿上鞋履緊跟出去。
整條迴廊通道都被濃濃的煙霧包圍,燻得人嗆咳不止,眼淚直流。文哥兒和武哥兒到底還是孩子,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嚇得直哭。程安玖顧不得安撫他們,彎下身子,一左一右將兩個兒子攔腰抱起,一邊喊著身後的趙嬤嬤跟上。
憑著直覺,程安玖尋到下樓的樓道口,一鼓作氣跑出客棧。
儘管是子夜,喊叫聲和鑼鈸聲將附近留守商鋪的夥計招了出來,長街頓時一陣騷動。臨街圍觀的商鋪夥計們同樣焦慮,此時有風,他們生怕火會向左右蔓延,殃及池魚。
「怎麼回事?好端端的六福客棧怎麼就著火了?」
「誰知道,趕緊滅火救人啊!」
「快!打水滅火!」
場面一時亂糟糟,有些夥計們拔腿跑回自家商鋪,提了水桶衝出來,不由分說就往六福客棧潑去。
「火看起來像在三樓,這樣潑沒用。」
「裡面的人都逃出來了嗎?」
「不知道,火勢越來越大,要是再不出來,就要葬身火海了!」
「有人出來了!快幫忙!」
程安玖沒有多餘的心思去看客棧的火勢,她把兩個兒子和趙嬤嬤領到長街對面的商鋪門前,蹲下身子認真檢查孩子們的情況。好在及早發現逃了出來,除了臉被煙霧燻得有些黑之外,一家四口都沒有什麼損傷。
「娘,我怕……」武哥兒皺著一張花貓臉,眼淚撲簌而下,鑽進程安玖的懷抱。
程安玖摟住他,輕輕拍了拍他的脊背,安慰道:「不怕不怕,有娘在呢,娘一定會保護你們的。」
文哥兒也是害怕極了,可他想到自己是個小男子漢,還曾經對母親說過要保護她,當即就上前一步,用自己那雙微涼的小手握住程安玖的手,堅強的看著她說道:「娘,文哥兒不怕,文哥兒會保護您。」
「真乖。」程安玖微笑,摸了摸文哥兒的小臉,也將他摟緊。
趙嬤嬤被六福客棧的火勢嚇呆了,她隔著救火的人群看著漫天的濃煙,喃喃祈禱道:「南無阿彌陀佛,但願客棧裡面的人都能平安脫險,別出人命才好。」
六福客棧半夜起火的事,在榮成縣引起極大的騷動。
天甫微亮,程安玖一家與其他生還者們來到榮成縣縣衙。這一夜實在驚心動魄,眾人看上去皆無精打采,神色黯然。周縣令讓衙差們將他們安置在會客的偏廳內,並差人送上熱茶,一會兒讓他們錄口供。
有好幾人被火燎傷,傷勢輕重不一,雖然周縣令請來大夫為他們進行清創包紮,可呻吟聲還是不絕於耳。看到這一幕,程安玖越發慶幸自己一家住在二樓,且發現得早,他們老弱婦孺未必能逃過這一劫。
程安玖在梨木高椅上坐下,兩個孩子一左一右依偎在她身旁。
「娘,我口渴。」武哥兒撅著小嘴道。
「來,喝口熱茶,小心燙。」程安玖將茶盞端起來,吹了吹,送到武哥兒嘴邊。
就著母親的手,武哥兒小心翼翼的喝了幾口,道:「娘,我喝夠了,您餵大哥喝吧。」
程安玖笑著道好,換到另一邊餵文哥兒喝茶。
趙嬤嬤神色依然惶惶,雙手擱在膝蓋上不停揉搓,昭示她此刻內心不安。
「玖娘,聽說那個何老闆被燒死了,這可是真的?」趙嬤嬤問道。
程安玖點頭,雖然具體情況她並不清楚,可方才聽衙門裡的人說起,起火點是在客棧的三樓,而昨晚來自遼東府的米業大亨何燦實被安置在三樓歇息。何燦實昨晚在接風宴席上喝了不少酒,睡得沉實,著火後沒能在第一時間逃生,且後來火勢太猛,他的隨從小廝也不敢闖進火場,結果自然是葬身火海了。
原先程貴將人安置在自個兒的客棧,想藉此搏些名聲拉點兒票,不料意外發生,這下子只怕是好處撈不著,反倒要惹一身腥了。
沉吟間,周縣令進來了,隨同在他身後的是衙門的師爺,還有同在火場生還的婁通縣米亨高宏遠。他低著頭,鬢髮微亂眼瞼低垂,讓人看不清楚表情,一隻手打著石膏,用繃帶纏著吊在胸前。
「見過大人。」所有人從座椅上起身,躬身朝周縣令行了禮。
周縣令點了點頭,掃了人群一圈,目光最後落在程安玖身上,略顯意外。
「程捕快也在?」周縣令寒暄道。
「是。」程安玖回以淡淡微笑,「昨晚在下和家人正好住在六福客棧內。」
周縣令「哦」了一聲,雙眸裡有一閃而過的疑惑,他下意識的看了師爺一眼,師爺朝他搖了搖頭。
周縣令之所以會有疑惑,是因為方才高宏遠告訴他,昨晚客棧的火災委實有些蹊蹺。雖然高宏遠沒有明說什麼,可周縣令哪裡聽不出來他意有所指。客棧是程貴開的,要是在平時倒也沒什麼,可偏偏在競爭北境供糧最後一輪角逐的當口出了這樣的意外,教人不免要多想。
何燦實和高宏遠是程貴角逐皇商頭銜的最大競爭對手,而他們會入住六福客棧是受程貴所邀,又碰巧在入住的第一晚就出事,若是何燦實和高宏遠意外葬身火海,那麼坐收漁利的會是誰?如此一想,程貴確實有足夠的縱火動機和理由。
只是周縣令看到了程安玖,程貴和程安玖是嫡親血脈相連的父女,虎毒尚且不食子,程貴應該不會為了區區一個皇商的頭銜,黑心冷血的置自己閨女於不顧吧?
周縣令有些動搖,他看師爺的那一眼,是想詢問師爺是否與他想法一致。師爺朝他搖頭,讓他不要先入為主,案情還要進一步調查方能確認。
周縣令掩下心頭的猜想,揚手請高宏遠坐下,自己在上首落坐,開口道:「你們都受驚了。昨晚六福客棧的火災事故,究竟是意外還是人為,本官會做進一步的調查,希望各位安心靜神,配合衙門工作,將昨晚在客棧的行蹤交代清楚。」他說到此處突然頓了頓,語氣有些嚴肅:「對於縱火行凶者,本官也在此奉勸一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切莫作僥倖心理。」
「大人明鑒,事發的時候已經是後半夜了,小的都已經上床歇下了,不曾做出這等傷天害理之事啊!」
「是啊大人,您瞧小的都被燒成這樣了,要行凶也斷不會搭上自己,請大人明察。」
「就是啊,我等可都是受害者啊!」
一時間,偏廳裡為自己辯解的聲音紛紛響起,生怕被當成這起事故的替罪羔羊,場面頓時亂轟轟的,最後還是師爺扯著大嗓門制止,才讓眾人安靜下來。
「大人剛剛只是勸行凶者自首,若你們不是縱火者,不必著急害怕,只管好好交代昨晚自個兒做過的事情就成,大人明察秋毫,絕不會冤枉任何一個人。」師爺說罷,回頭請示周縣令,見他點頭,擺手讓候在偏廳外的幾名衙役進來,讓他們領人去審訊房錄口供畫押。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與子偕刑(卷二)霧裡看花花非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言情小說 |
$ 228 |
中文書 |
$ 234 |
穿越文 |
$ 234 |
華文羅曼史 |
$ 234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與子偕刑(卷二)霧裡看花花非花
穿越古代的女刑警與有著驚人奇技的帥仵作當了同僚,
一同上刀山下火海這樣那樣東奔西跑我辦案你驗屍之後……
她拍拍他的肩膀,肯定的道:「帥哥,你……來自遠方啊。」
帥哥笑而不答。
案件更多、手法更五花八門,驚悚程度絕對挑戰你的想像──
如何透過逝者之聲尋得真凶、覓得真愛(?),就看兩人怎麼攜手破案!
程安玖與原主爹的鬥法正式展開序幕,她用精明的頭腦和(粗暴)有力的威脅成功讓渣爹吃癟吃不停還得吐著銀兩來供著她一家,正感到十分滿意的時候──
卻被捲入了她老爹和其他米亨競爭供糧、即將決定誰勝出前卻有對手被燒死在自個兒客棧的案子!
屍體一旦焦黑,屍檢難度便節節上升,現場勘驗難度也是不同以往。
幸好辦案經驗頗豐的程安玖配上(已被她認定也是穿越的)容徹,
從最細微之處找到了關鍵性的線索。
原以為殺人縱火案就該到此結束,可是他們卻發現幕後真凶另有其人,
能真正從這場陰謀中獲利的人到底是誰?
明明答案已十分明顯卻沒有決定性證據,
正當苦惱之際,才剛被抓到的凶手竟然死在了監牢裡……?
作者簡介:
唐寧
出生在中國廣東潮汕地區的一個熱愛生活的普通姑娘,平凡上班族,業餘寫手,也是一個寶媽!
信奉人性至善至美,喜歡以筆編織夢想,喜歡溫馨的故事,喜歡有一技之長果敢陽光的女主!
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有閃光點,希望能夠不斷的進步,超越自己,帶給大家更多好的作品!
▌繪者
殼中蠍
微博:殼中蠍
LOFTER:sasora
暱稱是蠍子~喜歡畫畫、看劇和玩遊戲的認證宅女,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夠睡到自然醒。目前古風作品比較多。如果你喜歡我的畫,我會感到很榮幸,你也可以通過上述社交網站找到我的更多作品(=・ω・=)
TOP
章節試閱
午後,程貴從縣衙回到程宅,陰著一張臉直接進了內院。
他將程安玖的那封告訴書直接砸到柳氏的臉上,喝道:「妳是瘋了嗎?竟遣人去打砸玖娘在安陽坊的舊屋!」
到了晌午還等不到楊嬤嬤的回稟,柳氏開始懷疑是否事情不順,但她以為是楊嬤嬤辦事不力,或是被那些從市井僱來的幾個潑皮纏磨要價脫不開身,沒想到那死丫頭片子竟會去衙門告她。瞧程貴臉色不善,她眼珠子轉了轉,這會兒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
柳氏撿起落在地板上的告訴書,快速看完後做出一副驚嚇狀,眼眶通紅,淚水撲簌,哽咽辯解道:「老爺,這到底是誰在陷害妾身?這告訴書上...
他將程安玖的那封告訴書直接砸到柳氏的臉上,喝道:「妳是瘋了嗎?竟遣人去打砸玖娘在安陽坊的舊屋!」
到了晌午還等不到楊嬤嬤的回稟,柳氏開始懷疑是否事情不順,但她以為是楊嬤嬤辦事不力,或是被那些從市井僱來的幾個潑皮纏磨要價脫不開身,沒想到那死丫頭片子竟會去衙門告她。瞧程貴臉色不善,她眼珠子轉了轉,這會兒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
柳氏撿起落在地板上的告訴書,快速看完後做出一副驚嚇狀,眼眶通紅,淚水撲簌,哽咽辯解道:「老爺,這到底是誰在陷害妾身?這告訴書上...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一章 砸屋
第二章 敲詐
第三章 追究
第四章 痕跡
第五章 凶器
第六章 祕密
第七章 認罪
第八章 舊部
第九章 線索
第十章 試衣
第十一章 綁架
第十二章 佩服
第十三章 線索
第十四章 自白
第十五章 遊街
第十六章 染病
第二章 敲詐
第三章 追究
第四章 痕跡
第五章 凶器
第六章 祕密
第七章 認罪
第八章 舊部
第九章 線索
第十章 試衣
第十一章 綁架
第十二章 佩服
第十三章 線索
第十四章 自白
第十五章 遊街
第十六章 染病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唐寧 繪者: 殼中蠍
- 出版社: 可橙文化工坊 出版日期:2018-12-04 ISBN/ISSN:9789576627569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8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8mm \ 高:16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