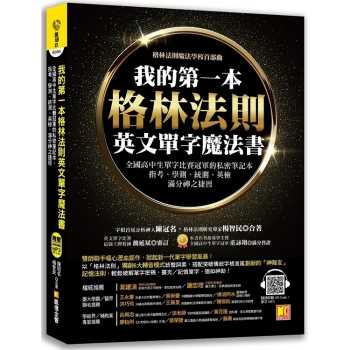廣陵城外多山,山不高,盡是些或近或遠的大小丘陵,連綿起伏。
這個季節剛剛入秋,風還不算涼,只是捲起落葉的時候顯得有些蕭瑟。
官道上,自北向南的幾匹輕騎疾馳而來,踏著地面常年累月形成的車轍,一路煙塵滾滾。騎馬的皆是一色青布勁裝的男子,身形如松,氣宇軒昂。
馬是好馬,卻也禁不住日夜奔波的折騰,眼看快到城郊,楊晉便略略放慢速度,因他領頭,身邊的幾人亦隨其收緊韁繩。
寶駒成陣,無數馬蹄落地,凌亂中,敲擊聲沉沉的在四周林間迴盪。
那一點異樣的動靜便是在此刻出現的。
叮鈴鈴,叮鈴鈴。金屬相互叩擊的聲響,旋律頗有節奏,像是鈴鐺搖晃。
楊晉不自覺循聲望去,前方斜伸出來的樹幹上,一抹象牙白的衣袂在風裡翻飛,海浪般滾動。仔細看時,竟是有人在其中起舞,手臂高揚的瞬間,白皙的腕子上露出掛有銀鈴的鐲子,正叮噹作響。
沒有任何樂曲相伴,那人的每一個動作卻緊隨鈴聲,與之契合得天衣無縫。
等離得近些了,才瞧清是個年輕女子,黑髮高高束成馬尾,在風中飛捲。
荒郊野外,又日落西山,這一幕情景陡然出現在視線中,換作是誰都會忍不住背脊發涼,偏偏她身姿有種難以言喻的和諧之美,一時間竟讓人來不及多想。
隨著人群漸近,那雙纖細的手腕翻得越來越快,鈴聲也越來越急,彷彿要和馬蹄的節奏相合。她腳下的樹幹並不是很粗壯,可她的步伐依然輕盈,綴著蒼青色繡紋的裙裾拂在腿邊,隱約能看見裙下白生生的足面。大概是裸足,否則也不便於在此處跳舞。
馬匹從樹下一晃而過,帶起的煙塵與疾風讓樹枝輕輕搖動,女子的足尖隨即一點,蝴蝶般躍然旋轉。
楊晉前行一段距離後忽地回過頭,夕陽的餘暉剛好打在枝葉間。
年輕女子從始至終目不斜視,眼神專注的盯著手腕。被風吹起的髮絲和衣襬不停的在她唇邊拂動,遮住了大半張臉。除了那雙眸子,別的沒能看清。
日頭還未下山,楊晉一行人在城郊附近的茶攤旁勒馬歇腳,裹了油布的繡春刀擱在手邊,一面落坐一面叫上茶。
小二甩著巾子顛顛兒的跑來了,倒過水,擦完桌,滿面笑容的問:「幾位爺要吃點什麼?這會兒城裡人多,難免上菜慢,趕路還有一陣子,倒不如先墊墊肚子。」
他話說得很實在,楊晉還未放下茶杯,施百川已張口要了幾盤點心,頭回出任務,他是最不禁餓的。小二忙喜孜孜的應了,回頭朗聲衝內廚報菜名。
楊晉一行人沒穿官服的時候,三教九流的百姓待他們會親和很多,若放在平時,光是端盤子,手都抖得像是得了癲癇。
楊晉抬眼,隨口打聽:「小二,這段時間廣陵城裡可有什麼閒談八卦沒有?」
小二還在給他斟茶,聞言笑道:「能有什麼新鮮事,咱們這兒又不是北京城,天大的事也不過柴米油鹽,您幾位一看就是大地方來的人,聽了多半也覺得沒意思。」
施百川丟了幾粒花生米進嘴,仍舊不死心:「難道就沒發生點不一樣的?比方說……命案?捉姦?誰家女人、小孩走丟也行。」
小二端著茶壺,還當真思索了片刻,「命案捉姦是沒有。」他笑了笑,「不過這附近鬧鬼倒是有些日子了。」
他神色如常,語氣隨意,像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似的。
「鬧鬼?」
「對。」小二抬手一指,西北方向正是一片鬱鬱蒼蒼的榕樹林,「就在那林子裡,挺大一個的,白天看不到,晚上才會出來。」
楊晉奇道:「你見過?」
小二啊了聲,「我們好幾個人都見過,一聽到人聲,那鬼就走遠了。」他聳聳肩,「不然怎麼說是『神出鬼沒』呢?」
小二提起茶壺轉身進去了,楊晉手裡還端著茶杯,目光注視樹林,若有所思的晃兩下。
微風掠過,傳來幾波遙遠的沙沙聲。
◎
八月立秋。
廣陵城的歷史長到能追溯至春秋了,幾朝更替,屬南宋時最繁華,而今雖早已遷都北平,但一晃眼又是錦繡成堆,海晏河清。
江南水鄉盛產楊柳,一條清河從城內橫貫而過,倒映出兩岸碧青的草木,以及岸上彩綢高掛的雕梁畫棟。此地的勾欄瓦肆都是大江南北數一數二的,青樓妓院、歌館樂坊,修得比大戶人家還奢華雅致。
在一干秦樓楚館中,最拔高的那棟是聽雨樓,進門兩邊挑起的牌子,一塊寫「妙指微幽契」,另一塊書「繁聲入杳冥」,來往者進進出出,絡繹不絕。
戲臺很大,樓足有三層之高。坊主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姓曹,留著兩片小鬍鬚,生得滿臉和氣,一天到晚負手在樂坊中巡視,不時囑咐小二添茶送水,不時讓小丫頭往後院跑跑腿,沒事找事幹。
琵琶聲響,花鼓敲得歡快又輕揚,這是時新的小曲兒《明月秋霜》,出自上年的新科狀元之手,在坊間很是有名。
四周一群客人推杯換盞,臺上飛袂如虹,舉手投足將節奏掐得分毫不差,綾紗的袖襬下露出的五指,蝴蝶似翻飛。曹坊主瞇著眼睛偏頭瞧,忍不住一聲輕嘆,感慨自己老了。
就在這周遭氣氛正好之時,門邊迎來送往的小二忽被人大力推開,一隊身著玄青色長身罩甲的官差魚貫而入,剎那間,肅殺之氣襲面而來。
人很快將整個樂坊團團包圍,不甚客氣的開始呵斥趕客。
場面登時一片混亂,曹坊主立在原地驚疑不定,待看清這幫人的裝束,心裡一個咯登,當即暗道不妙,忙衝著面前的錦衣衛哈腰:「幾位大人、幾位大人,這是所為何事啊?」
他辨不出這幾尊佛的官階大小,但見中間那位眉目疏朗、星眸深沉幽暗,氣度不凡,便下意識朝對方作揖。
戲臺上的歌聲已止,可跳舞之人並沒停,素手抬腕,能聽到清脆的銀鈴響。
楊晉不經意看了一眼,很快的又收回視線望向曹坊主。
「錦衣衛辦案,無關人等不得停留!」
曹坊主聽完一頭霧水,還得斟酌著賠笑:「大人,咱們這地方太太平平的,沒出什麼案子呀。況且,即便有點雞零狗碎之事,那不是還有衙門嗎?怎麼好勞您大駕呢……」
眾所周知,尋常百姓犯事,錦衣衛是不會插手的,除非,這裡頭涉及的是朝廷命官。
果不其然,他話音才落,旁邊那個稍顯年輕的男子已踏前一步,伸手指道:「查的就是你這聽雨樓!數日前,錦衣衛王總旗曾來此處飲酒,結果徹夜未歸,昨天卻被人發現死在城郊,死狀蹊蹺,慘不忍睹。你們這樂坊裡的人……」
說話間,他目光往旁側上上下下一掃,冷聲道,「都脫不了干係。」
死誰不好,偏偏死的是錦衣衛,知道此事是輕易揭不過去了,曹坊主抬袖擦汗,「大人,我們都是良民,而且手無縛雞之力,哪有這個膽子敢對您的人下手。」
「是與不是,查過才知道。」楊晉偏頭示意左右,「挨個兒問。」
眾人領命行動。
楊晉說完,又轉目看向曹坊主,一字一頓,「就勞煩曹坊主,多多配合了。」
此話很有分量。曹坊主只好自認倒楣,連連稱是,無奈的轉過身去對一幫不明真相的樂師、舞姬示意:「大夥兒,可有誰當天見過這位王總旗的?說過什麼話、吃過什麼東西、喝過什麼水酒,事無鉅細,趕緊上來告訴大人。」
樂坊裡的少女們莫名其妙的面面相覷。每日來來往往那麼多人,臉熟的,常光顧的倒罷了,突然沒頭沒腦的冒出一個王總旗,誰知道他幾個鼻子幾隻眼?何況姓王的人滿街跑,不見得逛樂坊還要穿官袍,萬一人家是便服又不肯暴露身分,豈不是更難找?
私下裡,少女們竊竊私語。
「錦衣衛是見過不少,有姓王的嗎?」
「有吧……」
一旁的少女推了跟前的粉衣女孩一下,「上回不是有個王大人送妳金簪子嗎?人長得白嫩嫩的那個。」
「什麼呀。」粉衣少女嗔怪道,「人家明明姓劉……」
饒是官差在前,少女們也不見有多少慌亂之色,和滿頭冷汗的曹坊主相比,心態可見一斑。一群女人嘰嘰喳喳,儘管輕聲細語,連成片也是海浪滔天。
錦衣衛雖行事專橫,但畢竟全是大老爺們,面對這些穿紅戴綠的美貌姑娘一時也頗為頭疼,勉強扯著嗓子喊了幾句「閉嘴」,總算開始了例行盤問。
幾問幾答,間或夾雜著此起彼伏的抱怨,場面居然比先前還熱鬧幾分。
方才在戲臺上跳舞的女子已下來了,正靠在雕花欄杆旁專心致志的把玩自己塗了蔻丹的指甲,十指纖纖,被嬌豔的胭脂紅襯得分外細嫩。
錦衣衛裡有個年紀尚小的,瞧著還不到二十歲,遲疑一會兒,握住刀壓著嗓音走上去。
「妳,說妳呢……叫什麼名字?」
女子終於抬起頭,妝容精緻的眉眼,顧盼生輝,自成風流,「我嗎?」
她把垂下的秀髮撥開,甜甜一笑,「我叫聞芊。」
曹坊主對錦衣衛是唯恐避之不及,只盼著這群大爺們查完案子能早點離開。然而對方卻用行動證明聽雨樓的這場飛來橫禍絕對不是一日兩日的走過場。上到掌櫃、老闆,下至伙夫、小廝,從祖宗十八代問到街坊鄰里、腹中胎兒,詳細得令人瞠目。
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天時間顯然不夠,於是錦衣衛把守,日夜巡視,聽雨樓迫不得已只能暫時閉樓,就這麼折騰了兩天。
還未享受夠微雨帶來的涼爽,秋老虎便如期而至,早起時燦爛的陽光直透過紗帳,照得人無心懶睡。聞芊打著呵欠起床梳洗,等坐在妝奩前把胭脂餅拿出來,才想起樂坊這幾日不開張,難得清閒,實在是有些不習慣。
她想了想,仍舊擺正銅鏡,畫了個精緻的壽陽妝,眉尾處貼上一朵月白色花鈿,左右看了半晌,覺得很滿意,推門出去了。
清晨的樂坊別有一番風味,露水浸過的吊腳樓散發出淡淡的木料香氣,樂班唱曲的小姑娘們在屋外站著吊嗓子;院子裡,戲班的女孩兒正在拉筋,滿眼花團錦簇,衣袂飛舞。
「反正也沒客人,練來做什麼,都閉館三天了。」翻觔斗的玩累了,停下來衝著那邊穿堂努嘴。
有人笑她:「妳就懶吧,平日不用功,臨時抱佛腳,難怪班主不讓妳上臺,活該!」
另一人戲謔道:「是想她的『柳公子』吧?哎呀,昨晚上睡覺,迷迷糊糊唸了一夜。」
四周笑聲不斷。
「要我說,妳也別惦記什麼柳公子了,咱們現在抬頭低頭全是錦衣衛,這裡面俊朗英武的可不少呢,妳挑一個?」
那女孩朝地上呸了口,「誰稀罕,一群粗人,還搜姑娘家的閨房,不知羞,叫他們討不著老婆。」
「能耐啊,有本事再大聲點?」
女孩們嘻嘻笑笑,玩得正開心,人叢中忽然冒出個怯怯的聲音:「錦衣衛這麼查下去,會不會……把咱們樂坊給抄了啊?」
此話一出,周圍立馬安靜了。樂坊畢竟是所有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來這裡唱曲兒跳舞的大多是無家可歸、父母雙亡的孤兒,若是聽雨樓倒了,這吃飯的碗必然難以保住。
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眾人不禁憂鬱起來,再無心玩鬧。
「妳們啊,真是閒不得。」樓梯上傳來輕笑,繼而便是一串不緊不慢的腳步聲,「好不容易休息幾日,還整天愁眉苦臉的。」
聞芊從樓上下來,少女們紛紛圍到她跟前,一迭聲的叫「師姐」。
整個樂坊,除了當初創立霓裳班的白芍以外,眼下就屬她資歷最老。白芍幾年前奉旨入京,現在早就嫁人了,因此聞芊也算是聽雨樓的頂梁柱之一。
「師姐。」方才那翻觔斗的少女喚作游月,拉著她胳膊搖了兩下,「妳看看那些錦衣衛,占著咱們的地方耀武揚威,明明什麼也審不出來,還要天天審,天天問,外頭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樂坊惹了官司呢。」
「就是呀,曹坊主不管事,再不開張,大家都快沒飯吃了。」
聞芊掃了她們一眼,手指拈起胸前的青絲,勾唇淺笑:「虧得妳們還唱曲唱戲,話本子上那麼多法子,也不知道學著使嗎?」
眾人頗為惆悵的互相對視,提醒她:「師姐,那可是錦衣衛啊,鬧不好會丟小命的。」
聞芊伸手在那說話的少女臉上捏了兩下,嘖道:「硬的不行,妳可以來軟的呀,別忘了自己是幹什麼吃飯的,看家本領拿出來,不愁他不中招。做大事要學會軟硬兼施,把耳根子吹軟了,最後再……」她五指一收,捏成拳,關節處咯咯作響。
眾人聞言嚥了口唾沫,隨即又滿眼欽佩,一臉「師姐果然好手段」的表情。
不過崇敬歸崇敬,敢不敢做是另一回事。
聞芊也不為難她們,摸了摸師妹們的頭髮,吩咐道:「好好練,記得要用早飯。」
眾師妹依言點頭,吊嗓子的繼續吊嗓子,翻觔斗的繼續翻觔斗。
聞芊走到穿堂門前停下腳,回眸看了幾眼,才轉身往外走。這會兒庖廚裡大概已經準備好吃食,她沒急著去,例行公事的先到小偏院去看慕容海棠。
慕容海棠是樂坊的老人了,從聞芊來的時候她就一直住在小院,而今過花甲,據說年輕時也是傾國傾城的人物,現在一把年紀了,跳舞怎麼樣不知道,不過跳大神很有一套,興致一起就要來上兩段。
聞芊茶還沒喝兩口,慕容海棠便指尖沾水衝她面門一彈,鄭重其事的扯淡:「芊丫頭,我瞧妳今日紅鸞星動,印堂發紅,怕是喜事將近!」
聞芊靜靜放下茶杯,抹了一把臉,掏出胭脂盒補妝。
「棠婆,您這句話快唸三年了,在您嘴裡我天天紅鸞星動,怎麼至今還沒嫁出去?」
慕容海棠咧著一口缺牙的嘴咯咯笑:「好飯不怕晚,今天我這籤保管靈……來!」她說著,啪的一聲把聞芊眉尾的花鈿換成了桃花,美其名曰:「桃花運,討個好綵頭!」
聞芊最後頂著個妖豔的妝容出了院子。
辰時的聽雨樓比較熱鬧,因為正值飯點,早起晚起的都聚在底樓用點心,她行至樓梯口,二樓的聲音便傳了下來。
「大人,我就是個送茶水的,唱曲兒又輪不到我,怎麼可能認識那些大人物啊。」
「除了他呢?妳既然送茶送水,前些日子沒發現樂坊裡有什麼異樣嗎?」
「沒有啊……」
迴廊處站了一個錦衣衛,正在盤問一個小丫頭。聞芊收回視線,漫不經心的甩著腰間玉墜的流蘇。
這宗案子查得沒完沒了,她喝了碗粥,從樂坊的戲臺一路逛到後園,巡邏的守衛隨處可見,不難看出,這地方已經裡裡外外被人監視起來了,大有不找到真凶絕不罷休的架式。
「王總旗……」
聞芊自言自語的低吟兩句,不經意看到拐角處滿懷心事的曹坊主,四目交會,她唇邊若有似無的噙了點笑,仍甩著流蘇,目不斜視的走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蛇得拿七寸,這些錦衣衛雖大部分不是地方官,個個面生,但從服飾上的細微差別,能明顯看得出哪個是官階最高的。
銀製革帶、鏤花、綬環銀中鍍金,不是副千戶也是個百戶了。
聞芊觀察了半日,聽底下人叫他「趙大哥」,於是挑了個四下無人的好時機,整了整衣襟,狠命往手臂上一掐,愣是擠出點「梨花帶雨」來,細步纖纖的踱過去。
趙青才啃完手裡的油餅正在翻卷宗,冷不丁聽到啜泣聲,抬頭便看見個貌美如花的姑娘,哭得我見猶憐,還明顯是朝他這邊來的,整個人登時一愣。
「姑……姑娘,妳,沒事吧?」
聞芊擦著眼淚,欲語還休:「大人,您們錦衣衛辦案,咱們樂坊從來沒有不配合過,這些天,您也都看見了……」
趙青一頭霧水,只好跟著頷首。
「我知道各位大人平日辛苦,問什麼自然答什麼,半分不敢逾越。可大家雖賣藝為生,也不是自輕自賤之人,您們……總不能隨隨便便的欺負人呀。」
趙青總算咂摸出點味道來,多半是自己那幫兄弟沒管住手腳,幹了點出格的事。雖說都是正值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一時衝動可以理解,但姑娘都告上門來了,的確有失分寸。
「姑娘受委屈了,此事是我管教不周……這樣,是何人欺負妳?我立刻嚴懲……」
話未說完,便嗅到一股淡淡的脂粉香氣,撩人心弦。
聞芊湊近他,哭得更加傷心了,「大人,您們這些天把樂坊圍得水洩不通,防賊似的,鬧得我們人心惶惶。」
趙青頓覺歉疚:「辦案需要,我們也是不得已,還望姑娘體諒。」
她借勢問下去:「那位王總旗的案子到底怎麼樣呢?都三天了,大人查出什麼沒有?」
趙青也未多想就道:「姑娘不必慌張,其實吧,這案子……」
瞧著有門兒,聞芊瞬間提起精神,可還沒等到下文,耳畔卻聽得一聲輕咳,有人開口打斷對話。
「趙大人,廣陵知府那邊已經把案卷調過來了,事不宜遲,煩請大人前去看看。」
好好的氣氛被人打亂,聞芊暗自齜牙,滿心不悅的轉頭,想瞧瞧是誰壞了她的好事。
來者是個身形高挑的年輕男子,五官清俊,星眸蘊光,劍眉微微擰起。他人比趙青高,居高臨下的望過來,那模樣不像是下屬,反倒更像是趙青的頂頭上司。
一見是他,趙青頓覺尷尬,忙磕磕巴巴的應了,抄起手裡的卷宗匆匆離開。
臨行前還沒忘關心一下聞芊,朝她介紹道:「姑娘,這位是楊……楊大人,妳若有什麼委屈大可同他說,他能給妳做主。老楊,你幫幫人家……我一會兒回來。」
楊晉淺淡的笑了笑,點頭算是答應了。
儘管心裡在罵娘,聞芊面上仍保持著感激的神色,甚是有禮的欠身目送他。
待人走遠,楊晉的目光才落在她身上,「聞姑娘,是吧?既然趙青有吩咐,我不會坐視不理。」
他表情淡淡,「說說吧,錦衣衛欺負妳,姓甚名誰,是何相貌,我去找他當面對質。」
聞芊察覺到此人不太好對付,笑容裡漸染上些許嬌媚,「大人,您們人這麼多,臉上又沒寫字,我哪會知道姓名,這不是為難我嗎?」
楊晉不以為然:「不知姓名,那總該記得相貌。」
她張口就來:「我記得啊,四方臉,濃眉毛,鼻子略挺,嘴唇略厚。」
他語氣輕蔑:「照妳這個說法,整個廣陵城我能找出數百人。」
聞芊歪頭一笑:「楊大人這是不信我呀。」
「不是不信。」楊晉低頭直視她,忽然漸漸湊近,「是懷疑。」
聞芊眨眨眼,顧左右而言他:「既不信,又何必壞人家的好姻緣呢,會遭雷劈的。」她說得無比真誠。
楊晉雙目陰沉,聲音壓得極低,帶著警告:「我告訴妳,不該招惹的人,不要去招惹;不該問的,也別多問。」
儘管聽出話裡的威脅,聞芊倒也不甘示弱,看他靠那麼近,反而作勢抬起胳膊搭在他肩頭,一臉無辜,「招惹?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誤會?莫非……楊大人是在吃醋?早說啊,我就該來找您的。」
不習慣與人有這般親密的舉動,楊晉握住她手腕欲推開,然而一觸之下,他發現這女子的力道竟不小,兩人一來二去的在這狹小空間內拆了幾招,誰也沒占到便宜,楊晉抬掌封住她小臂,聞芊便也停下來與他對視,各自手上互相較勁。
「大人,要憐香惜玉啊。」
楊晉力道未減,似笑非笑的說:「憐香惜玉是對弱女子的,姑娘只怕不算吧?」
這話可不愛聽了啊。聞芊忍著想翻白眼的衝動,看著楊晉近在咫尺的眉眼忽而心生一計,抬手以兩掌與他一掌拚力氣。
楊晉微微顰眉,腳步邁開幾寸穩住身形,就在他準備全力以赴時,聞芊冷不丁踮腳湊上來,在他臉頰處親了一下,動作太快,竟引出「啵」的一聲響。
楊晉整個人都懵住了。
被鉗制住的力道驟然散開,聞芊立刻抽手退出數步,等看清他此時的模樣,沒憋住笑出聲,「楊大人,您看您的臉!」她伸出手指在唇邊刮了幾下。
楊晉黑著臉拿手背狠狠一擦,赫然是一抹淡淡的胭脂。
聞芊且退且行禮,和適才朝趙青欠身的動作不同,她抱拳拱手,笑得明媚:「多謝大人賜教,改日得空了再好好招待您。今天有事在身,就不打擾了。」
說完幾步上了臺階,很快跑沒了影。
楊晉皺眉,在臉上擦了半天,轉目瞧見路過的幾名錦衣衛衝他露出訝然的表情,便知道痕跡還在,立時沒好氣,「有什麼好看的?」
幾人趕緊收斂神情,強忍著笑,低聲從他身邊匆匆走過。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姑娘請自重(卷一)不是冤家不聚頭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8 |
古代小說 |
$ 220 |
中文書 |
$ 225 |
古代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225 |
文學作品 |
$ 225 |
言情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姑娘請自重(卷一)不是冤家不聚頭
他追逃犯,她追他;逃犯追到了,他也被她追到了。
被求著迫著壓榨著答應了一個又一個的要求和請託,楊晉才猛然驚覺──
他怎麼,就被帶著一塊兒跳坑了呢?
坑不是不好,但坑坑相連著,這姑娘的祕密……也恁多了點!
這是一段從暗中捉拿逃犯開始的孽緣。
首輔大人之子楊晉為錦衣衛試百戶,押解犯人的途中讓人給逃了,一路追到廣陵城,一處充滿江南風情、令人眼花撩亂的水鄉之地。
聞芊是城內第一舞姬,嬌嬌媚媚的姑娘卻總帶著一絲痞氣,把正經工作的楊晉玩弄於手掌心,成天以逗他為樂,讓人總搞不清這個八面玲瓏的女子到底在想些什麼?
她所屬的樂坊看似單純,卻曾經莫名的起落數遍,直至如今,已經更迭了好幾代的頭牌個個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聞芊是否也是呢?楊晉查著查著,感覺似乎被帶入了某個神祕的坑,也把自個兒的心也賠了進去……
作者簡介:
賞飯罰餓
心懷浪漫的90後雙子座,住在爬坡上坎,九曲十八彎的巴蜀。語速風馳電掣,寫文烏龜慢爬……儘管酷愛虐男主,但內心深處依然嚮往甜蜜的愛情故事,並努力描繪一個貫徹愛與真實的美好世界~
在臺灣出版的作品有《追夫小廚娘》、《三朝書》、《美人不識君》等。
▌繪者
棠燁
擅長古風與日系風格的水彩,沉迷於美食和遊戲的禿頭畫手。很開心能為《姑娘請自重》繪製封面圖,讓我能有這個機會將自己腦海中的楊晉聞芊通過紙筆展現給讀者們。日常於新浪微博、LOFTER平臺發表個人作品。
章節試閱
廣陵城外多山,山不高,盡是些或近或遠的大小丘陵,連綿起伏。
這個季節剛剛入秋,風還不算涼,只是捲起落葉的時候顯得有些蕭瑟。
官道上,自北向南的幾匹輕騎疾馳而來,踏著地面常年累月形成的車轍,一路煙塵滾滾。騎馬的皆是一色青布勁裝的男子,身形如松,氣宇軒昂。
馬是好馬,卻也禁不住日夜奔波的折騰,眼看快到城郊,楊晉便略略放慢速度,因他領頭,身邊的幾人亦隨其收緊韁繩。
寶駒成陣,無數馬蹄落地,凌亂中,敲擊聲沉沉的在四周林間迴盪。
那一點異樣的動靜便是在此刻出現的。
叮鈴鈴,叮鈴鈴。金屬相互叩擊的聲響,旋律...
這個季節剛剛入秋,風還不算涼,只是捲起落葉的時候顯得有些蕭瑟。
官道上,自北向南的幾匹輕騎疾馳而來,踏著地面常年累月形成的車轍,一路煙塵滾滾。騎馬的皆是一色青布勁裝的男子,身形如松,氣宇軒昂。
馬是好馬,卻也禁不住日夜奔波的折騰,眼看快到城郊,楊晉便略略放慢速度,因他領頭,身邊的幾人亦隨其收緊韁繩。
寶駒成陣,無數馬蹄落地,凌亂中,敲擊聲沉沉的在四周林間迴盪。
那一點異樣的動靜便是在此刻出現的。
叮鈴鈴,叮鈴鈴。金屬相互叩擊的聲響,旋律...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錦衣衛
第二章 美人計
第三章 擺一道
第四章 周娘子
第五章 回憶傷
第六章 中秋宴
第七章 海棠豔
第八章 嘗胭脂
第九章 懷心事
第十章 抓山鬼
第二章 美人計
第三章 擺一道
第四章 周娘子
第五章 回憶傷
第六章 中秋宴
第七章 海棠豔
第八章 嘗胭脂
第九章 懷心事
第十章 抓山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