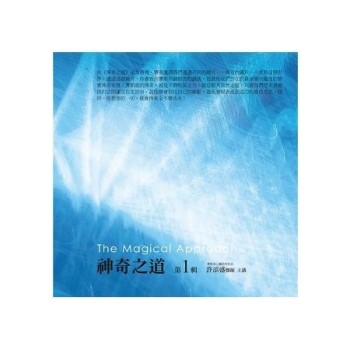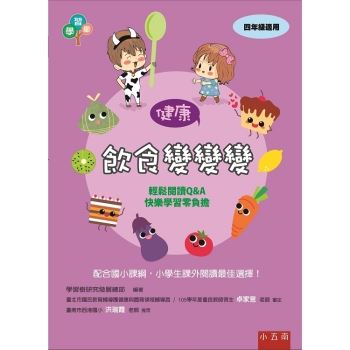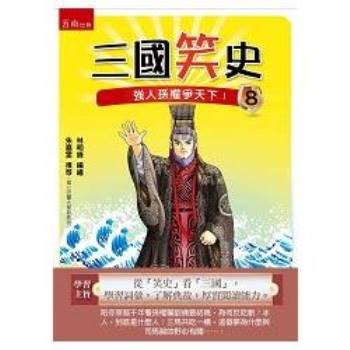臨近淮河,沿途的旅人便多了起來,地界還處於江浙,兩場雨一下,滿地濕氣,走在路上便有種說不出的黏糊感。
這季節氣候反覆,極容易得病,時常有馬車從身邊經過,遙遙便是一個拖長的噴嚏。
兩隊人一前一後的照常趕路,楊晉也依舊同聞芊保持著距離。
白日停車休息,聞芊在道旁的小攤上百無聊賴的翻揀水果,耳畔恰聽到楊晉在不遠處說話,偶爾掩嘴輕咳。
「哥,是不是昨晚沒睡好?今天要不我守夜吧。」
「沒關係,只是剛好嗆到了……」
她心裡一計較,彎腰揀了幾顆新鮮的梨。
一整天風塵僕僕,傍晚照例找地方歇腳。官道上的客棧賺的都是流水錢,飯菜很不走心,最初兩天的新鮮勁過去後,游月幾人也沒那麼愛蹦躂了,終於感受到長途跋涉的疲憊,差不多吃過飯便早早上床就寢。
等樓上樓下的客人都已回房休息,聞芊才輕手輕腳的走到廚房。
那個年輕的廚子正蹲在灶前看火,瞧她進門來便趕忙起身,聞芊擺擺手,繞過他掀開鍋蓋,白氣刷刷的往外冒,帶著一股清甜的香氣。鍋裡的雪梨肉白如雪,盛到碗中與紅棗、枸杞相映,顯得越發甘甜可口。
她把冰糖雪梨裝好,給了廚子一把銅錢的封口費:「不能告訴別人這是你煮的。」
她隨即拎著食盒出門找楊晉去了。拿甜食哄人這種法子是她六歲前玩剩下的,乍一看有些單薄無力,不過一個蘿蔔一個坑,對不對症還得看人。
聞芊在客棧尋了一圈,房間內不見人影,等繞到後院才發現他在那裡練刀。
記憶裡,似乎很少看見楊晉拔刀,他不太愛沾血,多數情況下能不動手就不動手。
冰涼如水的清輝中,雪亮的刀光像是流星閃電,不經意落下的月華在刀口起勢時擦過一絲細細的光芒,但很快都隱沒在那漫天飛雪似的一招一式裡。
楊晉不穿官服的時候,總是偏愛箭袖,墨色的上衣束在玉帶之中,腰身緊窄,隨著刀風繃出結實的肌肉來。耳畔聽到腳步聲,他周身的鋒芒倏地一收,整個人像手中那把寒光遍隱的繡春刀,眸色冷凝的看過去。
聞芊背著手在後面,正慢悠悠的走過來。
一見是她,楊晉眼底的戾氣瞬間淡去不少,抬頭望了一眼天色。深更半夜,她挑了個最清淨的時間來找自己,會是為了什麼?他心中莫名生出些微弱的期待。
荒野裡的小店連蠟燭錢也要省,牆外紙糊的燈籠在夜風中輕晃,那抹不甚明亮的昏黃與銀白的月光交織,她的臉從晦暗不明的陰影裡浮出,眉目間有妍麗的笑。
這樣的神情,並不陌生。認識這麼久以來,除了他跑樂坊之外,聞芊倒也不是沒有主動上門拜訪過,但仔細想了想,她的每一次笑臉相迎好像都帶了目的。
初遇時是為了讓錦衣衛撤出樂坊,第二次是為了上清涼山莊,第三次是為了青梅竹馬……這麼一推算,楊晉先前生出的那絲期待便很快平復下去,只沉默著垂首收刀入鞘。
「楊大人。」聞芊不自覺放輕腳步,眉眼上端著笑意,「在練刀呀?我是不是打擾到你了,不然你再練會兒?」
不著痕跡的將她的表情打量一遍,楊晉把刀放在石桌上,終究還是開口:「有事嗎?」
見他出聲,聞芊已覺事成功了大半,「別這麼提防我,又不會吃了你,來,你先坐。」
她硬生生把他摁在凳子上,這才將藏在身後的食盒拿到身前,擺在他手邊,笑靨如花,「是好東西。」
然而,楊晉卻在看到那食盒時,目光明顯的暗了一暗。
聞芊並未察覺,俯身打開蓋子,雪梨的甜香猶在,盡職盡責的撲出來,「怎麼樣?冰糖雪梨。瞧你似乎染了風寒,吃這個正好清肺止咳。」
瑩白瓷碗中的梨肉映入眼簾,他心情不自覺的往下沉。
聞芊仍忙活著往裡面灑杏仁碎,取出勺子放到他手中,「嘗嘗看,照你的口味做的,味道應該不差,若是不夠鍋裡還有,我去給你盛。」
話音剛落下,楊晉便將湯匙輕擱入碗內,匡噹一聲脆響。
他眉峰皺起深深的紋路,低聲道:「這一次,妳又打算要什麼?」
一瞬間,徐徐的北風戛然而止,四周的空氣像是凍結一般,帶著冷意。
聞芊聽到這句話怔了怔,又不在意的眨眼笑道:「一碗糖水而已,我還能要什麼呀?」
「是啊。」楊晉神色不變,口氣卻略陰鬱,「一碗糖水而已,我怎知道妳想要什麼?」
她總是如此。沒來由的示好、獻媚,一路避重就輕,等最後才道出有所求,然後自己就心甘情願的替她鞍前馬後。他是不是太好說話了?才放任她一而再,再而三這樣……
到這個分上,聞芊也覺察出他的語氣並非玩笑,一時間唇邊的弧度漸漸凝滯。
短暫的寂靜後,她盯著他的眼睛,「你什麼意思?莫非我對你好就一定有所圖?」
他避開視線:「是與不是,妳心裡清楚。」
「我不清楚。」她反駁,「覺得我對你有企圖?那當初你查唐石利用我的時候呢?」
楊晉強壓著情緒,「這一路上,誰利用誰還說不準呢。」
聞芊被他這態度弄得一肚子無名火,拍桌道:「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們錦衣衛平時是不是都是這麼斷案的?也難怪詔獄裡出那麼多冤假錯案!」
「我小人之心?」楊晉跟著拍桌而起,四平八穩的瓷碗愣是被他掌力震得彈了起來。
「好,那妳倒是說說。妳不是放不下樂坊嗎?妳不是不打算上京授藝嗎?眼下突然改主意又是為什麼?」言罷,他自嘲的一笑,「可別說妳是因為捨不得我。」
聞芊竟難得被他問得一陣語塞,半晌吭不出一聲來。
她這般表情顯而易見,不用質問就知道被自己言中,楊晉胸口沉重無比,一把握住她手腕往身前拽了拽,「妳平日裡不是千方百計的勾引我,吵著嚷著要以身相許嗎?」他星眸如刀鋒般刺人,簡直帶了些殺氣騰騰,「我給妳這個機會,妳許啊!」
這番言語滿是挑釁,又含著分明的嘲諷與戲弄。
聞芊被他拉了個趔趄,腦中像是炸開了煙花,她原就禁不起激怒,現下聽了這話,越發將那股不服輸給逼出來,當下毫無猶豫,伸手揪住他脖頸處的衣襟,猛地往下一拽,仰頭狠狠吻了上去。
楊晉本在氣頭上,冷不防被她咬住嘴唇,思緒驟然一片空白。聞芊發起瘋來像是收不住勢,狂風驟雨似的在他口中席捲,甚至貝齒磕在他齒間也渾不在意,雙唇覆在舌尖上用力吮舔,又來回撩撥,時鬆時緊,彷彿想將他最原始的欲望一併牽出。
在愣過片刻後,楊晉回過神來,怒火把他所有的吃驚和遲疑全數焚毀,他驀地扣住聞芊的雙肩,轉身將她壓在牆上,毫不示弱的吻回去。
從咬到舔再到吮,她怎麼做的他也一個不落的依樣反擊,唇齒間的血沿著嘴角滑下,此刻也顧不得這麼多了,索性破罐子破摔,他不自覺將力道放大,再放大,手指兜著她的頭,發狠般的將聞芊整個人壓在懷中。唇齒追逐,互不相讓。
此刻如有外人,大概得被如此凌厲霸道的「以口相噙」驚住。
那些逢迎躲避時傳出的碎吟和吮吸聲,糾纏出令人心蕩神馳的熾熱。
周遭的氣息終於在這個無比「認真」的吻裡沸騰起來,饒是互相較勁,那些異樣的呼吸聲也一寸寸的撥動著神經,他口中越發潮濕,身上的溫度不可抑制的滾燙,周遭的血液似乎都湧向同一處,四肢酥麻……
男子遠勝女子的耐力到底讓楊晉占上風,聞芊在呼吸耗盡前反守為攻,伸手把他反推到牆上,來去如風似的猝不及防又鬆開唇。
兩人相顧無言的各自喘息。楊晉目光灼灼的看她,抵著冰冷的石牆,抬起手背擦去唇下的血跡與水漬。聞芊卻突然拉住他的手,猛地摁在自己胸上,甚至還引著他揉捏兩下。
楊晉微微一怔,指尖傳來的綿軟讓後背不可抑制的起了一層細慄。
近在咫尺的那雙嫵媚桃花眼中帶著從容不迫的神情。
「不就是以身相許嗎?我聞芊說到做到。」她一字一頓的挑釁,「你隨時來我房裡,我隨時奉陪,就看楊大人你自己敢不敢了。」說著,將他的手往旁一甩,頭也沒回的走了。
石桌上的雪梨湯早已放涼,微風吹不起半點漣漪。
原地裡,楊晉收回視線,垂目用拇指抹了抹嘴唇。
隱約的疼痛還在其中蔓延,他發現手抖得有些厲害,攤開五指在眼前看了,才覺得掌心燙得像是躥起了火……他無言的緊緊合攏五指,最後又頭疼的摁住眉心。
另一邊,走得趾高氣昂的聞芊回了房,倨傲的插上門閂,倨傲的掩上窗戶,再倨傲的卸完妝,最後直挺挺的仰面倒在床上。年深日久的木床當即發出哀鳴,好似下一刻就要分崩離析。餘音尚未斷絕,就見她拿起軟枕罩住頭,在背面上狠搥兩下,心煩意亂的嚎了兩聲。
這叫什麼事啊!她明明是去送甜湯,怎麼搭上一個「以口相就」不說,倒頭來還多添了個「以身相許」!
尚未從方才的混亂中走出來,這一夜簡直過得亂七八糟,細想更是不堪回首。
實在不願面對現實,聞芊索性把被子一蓋,決定天大的事等睡完再說。
一晚上風聲疏狂,惡夢連連,好像有無數個楊晉在輪番踹她的門,場面很是可怖,且一幕接著一幕,沒完沒了。
好不容易睡醒了,總以為已經躺了三天三夜,她趴在床頭去看更漏,竟不過辰時而已。
做了整夜的夢,再加上受驚不小,聞芊疲憊得四肢無力,骨頭縫裡都泛著酸水,她眼底下兩圈青黑,草草拿脂粉遮住,才拖著雙腿推開門。
「吱呀」一聲響。偏不巧,對面也有人將門打開,許是出於本能,聞芊抬起頭,不經意與那人對了個正著。眉眼俊逸的青年,眸中帶著分明的倦意,乍然望向她時好似沒反應過來,目光有些怔怔的。彷彿劈頭打了個雷似的,聞芊匆匆別過臉,暗自朝著地上齜牙。
到這會兒了才知道他們兩人的房間是相對的。
經歷了昨晚的「衝動亂性」,她實在是不想和楊晉同行,便刻意放慢腳步,等他先下了樓,自己方慢條斯理的走出去。
樓下,早食已經擺好,游月一行不知幾時和這幫錦衣衛攀上交情,將桌子拼成一張,正其樂融融的坐在一塊兒用飯,見她下來,揚起筷子招呼道:「師姐,就等妳啦,快來吃飯!」
十來個人圍桌而坐,當中何其扎眼的空了一個椅子,兩邊的人自不知他倆剛吵完一架,很貼心且理所當然的給她留了個緊挨著楊晉的位子。
「咱們這行哪有你們想的那麼好混。」施百川嗓門大,猶在侃侃而談,「幹的都是體力活,逮人、審人,從北往南來回跑,光是這樣還不夠,連審人都是有講究的。」
清晨人少,滿客棧就他們一行,因此他才敢肆無忌憚。
「什麼講究?」菱歌捧碗好奇的問。
一見有人搭理,施百川更來了勁,「單拿廷杖來說吧,上頭下旨要打多少大板,妳可不能掄棍子就幹,有的人打得了,打死算完;有的人打不得,只能意思意思兩下。還有那些平日裡有仇的,正好能藉此機會出口惡氣。碗口大的棍子,要做到一棍下去,表皮無傷,筋骨寸斷……難吧?所以眼下啊,最吃香的還是那幫東廠的閹人。」
聞芊不便開口,一聲不吭的坐下。饒是四周不算擁擠,靠得這麼近,手肘也若有似無的擦到了。楊晉坐在那兒沒事人似的埋頭吃飯,她看在眼中,立時生了不悅,手端起碗,毫無胃口的拿筷子在米飯裡戳了一陣。
最後,她將筷子往上一擱,放回桌上,賭氣道:「我不吃了。」
周遭吃得正歡的眾人皆不明所以的面面相覷,紛紛停了動作看她。
楊晉嚼著嘴裡的菜,目光有意無意的斜過去,半晌似也覺得味同嚼蠟,面無表情的在她面前把碗擱了,「匡噹」一聲響,很有點旗鼓相當的意思。
這情形,哪怕再遲鈍的人也多少發現出其中的微妙來。
原在嘻嘻哈哈的眾人當即止了聲,各自捧著碗安分的扒飯。
施百川小心翼翼的嚥下一口粥,試探性的小聲問道:「哥,你也不吃啦?」
楊晉沒說話。聞芊悄悄橫了他一眼,覺得這人居然模仿自己,好不要臉!
她把碗端起,張口叫朗許:「小朗!和我換位子,我不要坐這兒。」
朗許正扒了口飯,聞言自無二話,順從的起身來讓她。中間隔了人,還是個身形龐大的人,登時就像是隔了一座大山,讓聞芊瞬間覺得心情好多了,也有了心思肯喝幾勺粥。
繃成一根弦的氣氛到此才有所緩和,見她開始用飯,楊晉在心中暗嘆,重新提起筷子。
飯桌上被這一段暗潮洶湧的經過捲得鴉雀無聲,一時沒人再開口插科打諢,只聽到碗勺相撞的脆響,文靜得像是大戶人家的「食不言,寢不語」。
聞芊心不在焉的吃了兩根鹹蘿蔔,旁邊的游月大概是此前聽施百川說了些什麼,忽然湊過來:「師姐,咱們這是要去徐州落腳啊?」
聞芊低低嗯了聲。
「可上京不是應該走鳳陽府那條道更快嗎?怎麼繞了遠路?」
一直以來聞芊只想著隨錦衣衛總能進京,倒沒留意過路程的問題。聞芊被她問住,轉過頭本欲去找楊晉,但轉念想到他估摸著又不會搭理自己,只好在桌下踢了踢對面的施百川。後者衝她聳聳肩,示意自己也不清楚,聞芊顰眉努努嘴,讓他去問楊晉。
施百川無奈了好一會兒,鑒於腳實在是被她踹得退無可退,他只能哼哼兩聲,「……哥,聞姑娘問你,咱們為什麼去徐州不去鳳陽。」
楊晉連頭也沒抬,「走徐州那條道主要是為了去濟南,臨行前接到趙大哥的書信,楊千戶現在人在濟南,我必須過去一趟,返京倒是不急。」
說完,似是想起什麼,他面對著施百川:「皇后娘娘大壽是什麼時候的事?樂師要在多久前進宮?」
施百川一頭霧水,正打算說不知道,回頭才意識到他是在問聞芊,心下更鬱悶了,不情不願的又把話朝對面重複一遍。
聞芊想了想:「皇后壽辰是在明年三月,但樂師正月底就得入京,來得及嗎?」
儼然被當成信使的施百川白眼直翻,眼見楊晉半天沒反應,只能道:「哥,聞姑娘問你來得及嗎?」
「來不及。」楊晉淡淡喝粥,「趁早改道吧。」
施百川很盡職的轉頭:「聞姑娘,我哥讓妳趕緊走。」
雖知曉楊晉是故意這麼說,聞芊還是忍不住咬咬牙,固執的哼了聲,「我偏不改道。」
就猜到她會如此回答,楊晉也不意外,繼續吃他的飯,然而剛把筷子伸出去,斜裡有人先他一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他面前盤中所有的包子全數夾到朗許碗裡。
視線裡的包子快疊成了山,朗許簡直不知要如何下筷,側頭去看聞芊。她不在意的給他盛了碗粥,笑容燦爛,「你每天趕車多辛苦,吃得飽點才有力氣呀。」
朗許忙伸手比劃:我已經吃飽了,妳問問楊大人餓不餓?
聞芊想也沒想便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哦,你說這點不夠啊?」言罷就將楊晉手邊的麻醬燒餅給他端過來。
朗許:「……」
見他還想比劃,聞芊把他抬起來的手摁下去,施施然起身,「你慢慢吃,我消消食。」
頂多也就喝了一碗清湯似的米粥,實在看不出她到底有什麼消食的必要。
看著手邊空空如也的餐盤,楊晉默了片刻後,嘆了一聲,無奈的撂筷,「你們慢用。」
隨著這兩個人的相繼離席,幾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的鬆了口氣。
施百川目送他倆從相反方向走遠,瞧見朗許眼中的茫然,伸手過去在他肩頭拍了拍,一副過來人的口氣:「他們倆吵架是這樣的,習慣了就好。」
聞芊有個不錯的優點,就是無論臉皮撕得有多破,在正事上她都不會感情用事。
所以,哪怕和楊晉都快鬧到天上去了,該上路還是得上路。
坐在馬車中,車廂搖搖晃晃,從偶爾掀起的簾子能看到車外蒼茫的天空,入冬了,又向著北,江南的溫柔如水只能在記憶裡勾畫。因為起得早,又被這車子晃得昏昏欲睡,菱歌和游月坐得東倒西歪,腦袋一點一點的,像是隨時能睡過去。
一連住了兩三天的驛站,今天應該可以尋個鎮子好好的休息一下。聞芊正這麼想著,車子忽地一頓停了下來。等了片刻也不見動作,聞芊打起簾子看出去——
青山掩映的二十道灣間,一條河阻了去路。南邊山多水多,有河並不奇怪,只是那河上架著的木橋卻被前幾日下雨而暴漲的急流沖垮,現下正攔了道在修繕中。
橋邊的小酒肆裡站著個年輕的老闆娘,比聞芊大不了幾歲,身段婀娜,體態風騷,大冷天還拿把團扇輕搖,乍一看去,很有些姿色。
施百川問她橋還要修幾日,她卻蓮步一轉走到楊晉跟前,倒也是個會挑模樣的。
「前天斷的,昨天才來人攔路,怕是要修個十天半月了。」
言罷,她身子往他胳膊上一靠,勾著梅花妝的鳳眼瞇起來,嫵媚的笑道:「怎麼樣,幾位小哥要不要在我這兒住下?東西什麼都有,價錢好說。」
同樣是女人,脂粉味卻大不相同,胭脂這種東西,若不精心調製會帶著礦石的氣息……其實並不好聞。聞芊素來在脂粉上很下工夫,哪怕是尋常的頭油也要讓人千里迢迢的從京城帶來,因此她身上的味道從不違和,甚至有些渾然天成。
而現下乍然和這山野間的女子如此親密接觸,楊晉自然而然有些不太習慣。
「這附近可有別的路?」
馬車內,發現聞芊在車窗邊看得認真,游月忍不住湊過去。
映入眼簾的便是這幅欲拒還迎的畫面,風情萬種的賣酒老闆娘半倚半靠的挨在楊晉身邊,兩人聊得甚是投機的模樣,她手指還時不時在他臉上撩幾下,好似恨不能把「勾引」兩個字插在腦門兒上。
不知是不是多想了,聞芊總感覺楊晉很有些享受其中,甚至不經意閃過來的目光裡還帶了不少輕蔑。
好了不起的樣子。她裝作不在意似的忿忿把簾子丟下,偏在這時,前去詢問的小廝折返回來,仰頭巴巴兒的叫聞姑娘。聞芊只好又掀了上去。
「楊大人那邊說,因為漲水斷橋的緣故,咱們可能要繞道。」
她輕飄飄的應了一聲,「那就繞吧。」說著,她招呼朗許繼續趕路。
過不了河,一群人沿著河岸而行,在傍晚來臨前抵達了最近的一個小鎮。
比起沿途那些老舊的水馬驛,鎮上的客棧簡直溫馨可愛,久違的叫賣聲惹得人心頭蠢蠢欲動。游月放下包袱便拉著朗許準備去街上逛逛。朗許因為身形高大,走出店門時不得不勾著頭,引得路人頻頻回顧。
施百川正開門叫小二打熱水,就看到楊晉穿戴整齊似乎準備外出。
「哥,你去哪兒?」
楊晉答得簡短:「去寄封信。」
知道是要寄往濟南的信,施百川瞬間會意,也沒再多問。
畢竟濟南府裡有個對楊晉而言十分重要的人物,此人非常追求規整與細節,因此哪怕是繞道多耽擱幾日,也要事無鉅細的向他回稟。
眾人收拾好行李,各有目的地的自行散開。
今年正是科舉之年,幾個月前秋闈結束,眼下到處都是返鄉的秀才,連這小小的鄉鎮也不例外,遍地彌漫著一股酸腐氣。聞芊在雜貨攤前閒逛時就遇上一個,端著把折扇滿口酸詩,她揀一樣東西他就唸叨一句,一路形影不離,弄得人煩不勝煩。
「綺羅嬌容,佳人如玉……我瞧這玉鐲挺配姑娘,姑娘若是喜歡,不如我買給姑娘?」
平日裡樓硯嘰嘰歪歪已經很讓人火冒三丈了,眼下聽了這位天賦異稟的嘮叨方式,兩相一對比,聞芊才發現自家人的可愛之處。
正想找個由頭把這話癆打發掉,眼角餘光突然看到楊晉走來,她心頭一琢磨,覺得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乾脆換了笑顏柔聲道:「公子這樣大方,叫小女子如何受得?」
嘴皮子磨了快一炷香,連口都說乾了總算得佳人青睞,折扇公子有點受寵若驚,連聲道:「受得,受得,以姑娘這樣的人品容貌,當然受得。」他一雙眼睛盡在聞芊臉上打轉,一面往懷裡掏銀子。
瞧準那人走近,聞芊秀眉一挑,忽然扶著額頭,重心不穩似的靠在一邊,折扇公子愣了愣,立時伸手抱住她,「姑娘,沒事吧?」
「沒事……就有些頭暈。」她不著痕跡的朝旁瞥了瞥,「可能是白日裡趕路太累,休息會兒便好了。」
「那怎麼行。」美人在懷,折扇公子不免神魂飄蕩,「姑娘身子這般單薄,倘若受了寒可怎麼是好,還是隨我看大夫要緊。」
「這……哪敢這般勞煩公子。」
「不麻煩,不麻煩。」折扇公子扶起她,「自然是姑娘妳要緊了。」
言語間,身側的楊晉正目不斜視的走過去,從始至終沒轉過眼。
幾乎是在人拐進小巷的一瞬,聞芊驀地掙開折扇公子的手站起身,回眸衝著人離開的方向冷冷哼了哼,像是扳回一城,不由得通體舒暢。
「姑娘……」眼見聞芊要走,折扇公子伸手去拉她,「妳不看大夫啦?」
指尖還未碰到,她猛然拔了簪子,動作極快的抵在他咽喉處,似笑非笑的開口:「再跟著我,我就讓你去看大夫。」
好好的一個美人,怎麼說翻臉就翻臉!折扇公子雖好色,但也知道惜命,尖刃當前立馬規矩了,兩手抬起來,忙討好的笑道:「不敢,不敢。」
聞芊自鼻中發出一聲不屑輕哼,把人往前狠狠一扔,這才轉身離開。
回到客棧時,天已經黑盡,小二在麻利的上菜,菱歌擺好碗筷,乖巧的叫了聲師姐。
她低低應了,頭也沒抬,讓小二把熱水送來,抬腳上樓準備沐浴換衣裳。
因為察覺她與楊晉不和,飯桌又很微妙的拉開一段距離,各自分開落坐。但儘管是這樣,菱歌還是很懂事的給兩邊都盛上熱飯。
小客棧的招牌菜是豆花,一幫大老粗對調料一竅不通,她便一小碟一小碟的準備好,到施百川身邊時,聽他道了句謝,又補充:「先別給我哥盛,他可能要晚些時候回來。」
她把調料的小勺放下,這才發現缺了個人:「楊大人不在?他去哪兒了?」
想起走前同自己說的寄信一事,施百川自是一臉正經:「當然去辦正事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姑娘請自重(卷二)道是無晴卻有晴的圖書 |
 |
姑娘請自重(卷二)道是無晴卻有晴 出版日期:2019-02-2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5 |
Literature & Fiction |
$ 198 |
言情小說 |
$ 198 |
古代小說 |
$ 220 |
中文書 |
$ 225 |
古代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22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姑娘請自重(卷二)道是無晴卻有晴
他追逃犯,她追他;逃犯追到了,他也被她追到了。
被求著迫著壓榨著答應了一個又一個的要求和請託,楊晉才猛然驚覺──
他怎麼,就被帶著一塊兒跳坑了呢?
坑不是不好,但坑坑相連著,這姑娘的祕密……也恁多了點!
與楊晉同路北上,聞芊原本安的就不是什麼單純的心,卻沒想到先沉不住氣和他攤牌的是自己,把自己的過往吐得一個子兒也不剩的,也是自己。
人稱強買強賣小霸王的聞芊,好像遇上對手了?
意外與錦衣衛一同被困在徐州參與偵辦飛賊殺人案,聞芊才驚覺楊晉這人真是不簡單的體質,到哪兒都能把人推坑下獄,霉運不是一般的重啊。
但這人的奇妙氣場還是比不上她走到何處都有人千方百計的不讓她上京授藝這件事來得稀奇,到底是誰在費盡心思的阻撓她?聖上明令的御旨,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敢挑戰呢?
作者簡介:
賞飯罰餓
心懷浪漫的90後雙子座,住在爬坡上坎,九曲十八彎的巴蜀。語速風馳電掣,寫文烏龜慢爬……儘管酷愛虐男主,但內心深處依然嚮往甜蜜的愛情故事,並努力描繪一個貫徹愛與真實的美好世界~
在臺灣出版的作品有《追夫小廚娘》、《三朝書》、《美人不識君》等。
▌繪者
棠燁
擅長古風與日系風格的水彩,沉迷於美食和遊戲的禿頭畫手。很開心能為《姑娘請自重》繪製封面圖,讓我能有這個機會將自己腦海中的楊晉聞芊通過紙筆展現給讀者們。日常於新浪微博、LOFTER平臺發表個人作品。
章節試閱
臨近淮河,沿途的旅人便多了起來,地界還處於江浙,兩場雨一下,滿地濕氣,走在路上便有種說不出的黏糊感。
這季節氣候反覆,極容易得病,時常有馬車從身邊經過,遙遙便是一個拖長的噴嚏。
兩隊人一前一後的照常趕路,楊晉也依舊同聞芊保持著距離。
白日停車休息,聞芊在道旁的小攤上百無聊賴的翻揀水果,耳畔恰聽到楊晉在不遠處說話,偶爾掩嘴輕咳。
「哥,是不是昨晚沒睡好?今天要不我守夜吧。」
「沒關係,只是剛好嗆到了……」
她心裡一計較,彎腰揀了幾顆新鮮的梨。
一整天風塵僕僕,傍晚照例找地方歇腳。官道上的客棧賺的都...
這季節氣候反覆,極容易得病,時常有馬車從身邊經過,遙遙便是一個拖長的噴嚏。
兩隊人一前一後的照常趕路,楊晉也依舊同聞芊保持著距離。
白日停車休息,聞芊在道旁的小攤上百無聊賴的翻揀水果,耳畔恰聽到楊晉在不遠處說話,偶爾掩嘴輕咳。
「哥,是不是昨晚沒睡好?今天要不我守夜吧。」
「沒關係,只是剛好嗆到了……」
她心裡一計較,彎腰揀了幾顆新鮮的梨。
一整天風塵僕僕,傍晚照例找地方歇腳。官道上的客棧賺的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別廣陵
第二章 鬧性子
第三章 春山案
第四章 燕姑娘
第五章 揭真相
第六章 賞花宴
第七章 心頭亂
第八章 千佛山
第九章 見故人
第十章 尋出路
第二章 鬧性子
第三章 春山案
第四章 燕姑娘
第五章 揭真相
第六章 賞花宴
第七章 心頭亂
第八章 千佛山
第九章 見故人
第十章 尋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