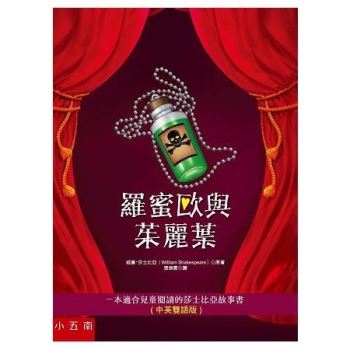莘國。
京郊。
景德二十一年,仲秋,八月初八。
月夜,朔風乍起,稀疏的幾點星光將一長一短兩個身影拉得極長。
「東東,我們倆這種行為,可稱得上私奔?」
「……」
「你為什麼不把翠花也帶上?這樣咱們三人一道私奔,路上也熱鬧些。」
「……」
「你老實跟我說,你是不是喜歡翠花?」
「……」
「你既愛慕她,又為何要跟我走?」
「……」
「你有沒有想過,被抓回去有什麼後果?」
「……」
「沒想過?你居然沒想過!做狗,豈可如此不顧後果,隨心所欲。」
「……」
「你怕不怕?」
「……」
「我有些怕的。」
「……」
「你最怕誰?」
「……」
「小師弟?東東,你果然跟我是一條心啊。老爹是隻紙老虎,沒甚用處;師姐心最軟,我只要朝她哭兩聲,她保管心疼死;就那廝最是陰險狡詐,表裡不一,被他逮到,咱們倆都沒有好果子吃!」
「……」
「說到吃,東東我餓了,你餓不餓?」
「……」
「哎!若不是他們逼咱們分開,咱們也不用離家出走,連頓熱飯也吃不上。」
「……」
「你說老爹他怎麼想的?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非要我去相府做丫鬟,他腦袋不是被驢踢了,就是被門夾過了。」
「……」
「東東啊,你可知道大宅門做丫鬟有多難。那些個色鬼老爺、色鬼少爺專門喜歡朝丫鬟下手。」
「……」
「這世上,哪有做父親要賣了女兒的,莫非,我不是他親生的?」
「汪!汪!汪!」
被喚作東東的黑狗突然站起來衝四周叫喚幾聲,十分警惕的擋在紅衣女孩的身前。
「小妹妹,聲音這麼好聽偏偏跟隻狗說話,嘖嘖嘖,太冷清了,哥哥們來陪妳如何?」
不知何時,面前站了四名黑衣男子,為首的男子從懷裡掏出個火摺子。
「喲,還是個小美人啊,長得不錯!」
「大哥,還是個丫頭片子,身子還沒長開,能不能吃啊?」
「哈哈哈!老四,你不知道咱們大哥最喜歡的就是丫頭片子嗎,那滋味……吃著才帶勁啊!」
「老大,悠著點,細皮嫩肉的,可禁不起你折騰!」
「你,想吃我?」女孩的聲音不大,卻極為清脆動聽。
「小妹妹,若不想我吃,妳來吃我,也是一樣的。」
「大哥,真有你的!」
「大哥,人家還是個小姑娘!」
女孩臉上絲毫沒有一點害怕,小手撫了撫東東的腦袋,「東東,擒賊先擒王,你意下如何?」
東東被女孩撫摸得極為舒服,嗚嗚幽吠兩聲,正要撲過去,一道寒光閃過,耳邊傳來四記悶聲。
抬頭一看,四個賊人突地已成四具屍體,橫陳在路中間。
女孩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看著夜色中慢慢靠近的熟悉身影:「完了,要沉塘了!」
「妳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
景德二十五年,初冬。
京城南四牌樓。
一夜寒雪在清晨時分將將止住。
林西手捧著白玉手爐,髮髻上沾著些許白雪,不停的跺著雙腳,吸著鼻涕,探頭探腦的立於暖閣後的梅樹下。
時間一點點的流逝,暖閣彷彿已沉睡千年,並無一絲動靜。
林西狠跺了幾下腳,終是後知後覺的明白了,為什麼給小姐送手爐這麼體面的差事,會落到她這個灑掃庭院的粗使丫鬟身上。
門「吱呀」一聲突然打開,一個目光如炬的中年婦人陰沉著臉,手持戒尺,朝林西輕輕一點。林西此時正咧著嘴,用力吸著剛滴下來的清水鼻涕。
婦人轉過臉,對著暖閣裡四位小姐幽幽道:「妳們說,這丫鬟如何?」
「譚嬤嬤,依我看,這丫鬟愚笨至極。」
林西耳尖,聽出說話的是大小姐高茉莉,羞愧的把頭深埋在胸前。
「哦,何以見得?」譚嬤嬤深邃的眼睛裡無一絲波瀾。
「說此人愚笨,原因有二。」高茉莉不緊不慢道:「其一,凡我們姐妹院裡的人,都知嬤嬤授課共兩個時辰,每半個時辰休息一刻。偏這丫鬟一無所知,可見她日常並未把主子的事情擺在心上,這樣的僕人要來何用?」
「其二?」譚嬤嬤抬眉。
高茉莉輕蔑的向暖閣外看了一眼,「其二,即便她事先一無所知,總有眼睛,總有嘴巴,偏她一不打聽,二不觀察,只一味在寒風底下傻等。手爐已冷,是一重罪;擾了嬤嬤授課則為二重罪。由此可見,這丫鬟愚笨之至!」
美人蛇吐信子般的言語,讓立於寒風中的林西似有種進了盤絲洞的幻覺。她壓低了身子,大氣都不敢出,眼睛透過門縫,偷偷往暖閣裡瞧。
毫無意外,她看到自家小姐冷著臉,微不可察的搖了搖頭。林西渾身哆嗦了一下,身子又蜷縮下去一寸。
譚嬤嬤如箭的目光掃了四位小姐一眼,眼中的銳利似暖閣外的寒風,讓人遍體生寒。
「下人分兩種,精明和愚笨。精明的,保不准奴大欺主;愚笨的,保不准奴笨累主。妳們做主子的該如何取捨?」
高府的四位小姐睜大了眼睛,安安分分的靜聽下文。
譚嬤嬤嘴角微微下垂,眼中的深色一閃而過,「妳們只要記得一點:若為忠奴,兩者皆可用;反則棄之不用。」
話及一半,譚嬤嬤的貼身丫鬟匆匆進來,在她耳邊輕語幾句。
譚嬤嬤目光如電,嗓音冰冷:「今日我派人給四位小姐院裡傳話,其餘三人在湖邊的小廂房裡吃茶聊天,只等著我下課再把手爐給主子送來。只這個丫鬟在寒風底下站了足足半個時辰。笨是笨了些,卻是忠心耿耿。這樣的人,方堪大用!」
「嬤嬤此言,我有異議。」
依舊是高茉莉盈盈而立,「嬤嬤怎知,那其餘三人心裡頭對主子沒有忠心?」
譚嬤嬤嘴角輕挑,素來陰沉的臉上不知為何帶了一絲譏笑。
她朝林西招了招手,和煦道:「我來問妳,妳是哪個院裡的丫鬟?妳可知道我上課的規矩?」
林西眼觀鼻,鼻觀心,正靜聽譚嬤嬤講課。據她所知,譚嬤嬤在高家一年授課的費用是一千二百兩,劃到每個月就是一百兩。
而做為高府三小姐身邊的一名粗使丫鬟,林西一個月月錢僅僅五百錢,連個小零頭都比不上。林西正盤算著,剛剛聽到的譚嬤嬤這幾句話,換算成銀子該值多少錢。
冷不丁被人問話,林西慢慢的抬起頭,不想凍得久了,連鼻涕落下來都了無知覺。
就這樣,林西無知無覺的拖著兩條清水鼻涕,諾諾道:「奴婢是平蕪院裡的粗使丫鬟,奴婢來之前,打聽過嬤嬤上課的規矩。」
譚嬤嬤瞳孔驟然一縮,「那為何還站在這風口上?那邊廂房裡暖和,既有熱茶,又有點心,何不在那裡頭歇歇,等我下了課再給妳家小姐把手爐送來也不遲。」
臥槽,居然有廂房可以避寒!爺爺的,怎麼不早說?害得我在這湖邊吹了半天的冷風,連骨頭都是冰的。
林西暗中問候一聲老天爺祂母親,剛張嘴,似有什麼冰涼的液體落到了唇上。
她背過身迅速的抬起袖子擦了擦鼻涕,含糊道:「奴婢以為小姐急著要用,怕耽誤了小姐的正事……」
譚嬤嬤滿意的點了點頭,「人活世上,無非是兩件事:一是做事,二為做人。做事容易,做對事不易;看人容易,看清人不易。做人比做事難,看清身邊的人比對付外人難。」
譚嬤嬤如願的看到府上四位小姐收了嬉笑之色,目光炯炯的看向她。
「高家鐘鳴鼎食,詩禮傳家,小姐們身邊的人都是府裡精挑細選而出,若論忠心,必不會差。然凡事總不能只看表面。小姐們順風順水時,誰都會是忠奴;然小姐們一旦陷入泥潭……」
譚嬤嬤戒尺一伸,直直的指向門外的林西,聲音驟然拔高了幾分。
「所謂的忠奴只有像她那樣,不問緣由,不聽是非,不偷奸耍滑,唯主子之命是從。所以小姐們既要用人所長,又要用人所短……」
暖閣的門驟然被關上,譚嬤嬤的聲音化作了一陣寒風,肆意暴虐的吹走了林西身上的最後一絲溫度。
她有些猶豫不定,到了這個分上,她是該繼續在寒風裡哆嗦呢?還是到譚嬤嬤手指的廂房裡歇上一歇?
就在林西天人交戰的時候,門再度打開,譚嬤嬤目不斜視的從她身邊走過,臉上一絲多餘的表情也無。
高家詩禮官宦人家出身,府裡不管是少爺還是小姐,都得斷文識字。因此,但凡是高家的女兒,年滿六歲,都必須坐在學堂裡,跟著夫子上學。
高家女子的讀書與男子不同。男子讀書無非是些四書五經之類的,為的不過是功名。
女子則不然,詩書也讀,女則也讀,琴、棋、書、畫各有一位先生養在府裡,甚至還有專門的教養嬤嬤教導規矩。
譚嬤嬤便是專門負責教導府裡四位小姐的教養嬤嬤。
譚嬤嬤的來頭很大,有宮廷第一嬤嬤之稱。有人說她曾服侍過先太后,又有人說她是當今皇后的教養嬤嬤,林林總總,也不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林西朝譚嬤嬤欠了欠身,低著頭退至一旁。
這時,一雙紅色鹿皮小靴陡然出現在林西的視線範圍內,她緩緩抬起頭。
入眼的少女穿著桃紅色對襟褙子,粉色主領中衣,蛾眉緊蹙,香肌若雪,含笑盯著她看。
林西嚥了口口水,慌忙把懷裡的白玉手爐奉到少女眼前。
「小……小姐,臘梅姐姐讓我把手爐給妳送來。」
高鳶尾接過已經微涼的手爐,柔聲道:「妳叫什麼?多大了?什麼時候到我院裡來的?」
「回小姐,奴婢姓林,單名一個西字。過了年便十四歲了。半個月前剛剛到的平蕪院,負責灑掃庭院。」
高鳶尾輕輕一嘆,「倒和我同歲。妳是哪家的?」
「回小姐,奴婢是劉嬤嬤從外頭買來的。」
「大姐,劉嬤嬤如今這眼色也是平常,像這樣的人也配買進府伺候咱們,瞧瞧那臉,又黃又醜,也就眼睛長得像模像樣些。」
空氣如膠凝一般,冷了下來。
林西下意識把像模像樣的眼睛睜得更大些,見說話的是二小姐高錦葵,不由得又瞇成了一條線。
高府有四朵金花:大小姐高茉莉、二小姐高錦葵、三小姐高鳶尾、四小姐高紫萼。
說來也奇怪,頭三朵金花竟是一年中開放,唯獨紫萼花開遲了兩年,林西很是佩服她們老爹傲人的生育本事。
高茉莉走到林西面前,從下到上打量了她幾眼,「論規矩,倒還過得去,只這長相……好歹是個忠奴,想必三妹是不會在意的。」
「三姐當然不會在意。有了這丫鬟,才能襯著咱們三姐越發的好顏色。」四小姐高紫萼跟上來,挽著高茉莉的手,似讚非讚道。
高鳶尾恍若未聞,伸手握住林西冰涼的小手,「劉嬤嬤看人的眼光豈會是差的?她調教出來的丫鬟,連夫人都親口誇過。大姐,我看這丫鬟雖長相平常,卻是難得的忠僕,越發證明劉嬤嬤的眼光出眾,回頭我倒要好好謝謝她。」
輕描淡寫的一句話使得大小姐高茉莉心下頗為熨貼。
她掙脫開了高紫萼的手,得意一笑道:「劉嬤嬤是母親從崔家帶來的,眼光自不必說。」
高紫萼手裡落了空,看向高鳶尾的目光便有了幾分不善,「三姐,既然是忠僕,做那灑掃庭院的粗活可真真是埋沒了,妹妹看,倒不如放在身邊更妥當些!」
林西心頭一驚,磕磕巴巴道:「四小姐,萬萬不可。奴婢長得醜,又笨手笨腳的,做個粗使丫鬟已是劉嬤嬤抬舉,奴婢……」
「喲,三妹,妳這丫鬟不僅人忠實,倒還有幾分自知之明。這樣的人不擺在身邊,實在是可惜啊!」高錦葵笑容滿滿,一身胭脂紅襖子襯得她嫻靜溫和。
林西不知何故,總覺得二小姐渾身上下透著一股子寒氣,讓她忍不住想遠遠的避開。
高鳶尾噗哧一笑,「二姐,妹妹正有此意。林西,從今往後,妳便在我書房裡伺候。天冷,妳先回去吧!」
書房伺候?為什麼要到書房伺候?
林西心頭的悲哀如同冬日掛在天空的那一抹淡日,淒淒慘慘戚戚。
高鳶尾如願以償的看到姐妹們微變的臉色,笑道:「大姐、二姐、四妹,這裡風大,著了寒氣可不是玩笑的事,咱們往暖閣裡說話吧。」
高紫萼剛剛落了下乘,不由出言譏諷道:「三姐不僅琴棋書畫首屈一指,這小嘴也像抹了蜜似的,怪不得討母親喜歡。回頭也教教妹妹,省得妹妹笨嘴笨舌的,連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高鳶尾身子一顫,笑容卻不減半分,恍若未聞的挽著大姐高茉莉的胳膊一同進了暖閣。
高紫萼一口惡氣堵在胸口不上不上,正欲反唇相譏,卻見二姐高錦葵玉手一指,只見譚嬤嬤的身影遠遠走來。
「四妹這心直口快的毛病也該改一改,母親跟前也能……」
「二姐!」高紫萼冷冷的打斷,「我可不是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整天裝神弄鬼的往母親跟前湊。」
高錦葵似漫不經心道:「也難怪,咱們都是有兄弟可依靠的人,獨她孤零零的一個。走吧,該上課了!」
林西看得目瞪口呆。我的個親娘哎,句句含沙射影,字字飛沙走石,果然是姐妹情深啊。
灑掃庭院的粗使丫鬟,突然變成了小姐書房裡的二等丫鬟,林西所受的驚嚇不小,她決定走小路回去和同屋的好姐妹柳丁商議商議。
一夜寒雪,園子裡的小道上已積了厚厚的一層,很是打滑,她走得小心翼翼。
窸窸窣窣似有什麼聲音從不遠處傳來,林西打了個激靈,貓著身子四下打量,卻見樹叢邊的牆角下,立著兩個人。
只見一新月籠眉、春桃拂臉的女子酥胸半露,露出白花花的一片雪膚,倚在牆角,神情迷離,不時發出囈語般的呻吟。
一錦衣少年正埋在其胸前作狗啃狀。
有姦情?
林西頓時羞得面紅耳赤,兩眼放出狼一般的光芒,渾身的毛孔散發著八卦的氣息。
錦衣少年一口封住了女子的櫻唇,似馬上就要溺水而亡的兩人,扭在了一處。
林西瞇著眼睛,一邊觀賞,一邊連連搖頭。
妖精打架這事,果然還是脫光光比較好,不僅方便當事人有手感,也方便像她這樣偷窺的人有觀感。像這般穿著厚厚棉襖辦事……真是隔靴騷癢啊!
「嗯……二少爺……奴婢……被人瞧見了……嗯……不好……奴婢還有事,等天黑了……」
「小妖精!」
女子戀戀不捨的往二少爺臉上親了又親,待他如痴如醉時又一把推開。她迅速的理了理衣裳,飛快的閃過樹叢,如那展翅的蝴蝶一般,三兩下沒了蹤影。
林西未料到這姦情戛然而止得這般神速,女子走了另一條小路離去,那男子勢必向她走來。
不妙!心裡一慌,沒留神腳下,她摔了個四仰八叉。
似有一道目光落在她的背後。
林西悚然一驚,咕咚幾下爬了起來,一邊用髒手抹了把臉,一邊自言自語道:「好好的,走個路也能摔一跤,真倒楣!」
轉過身,卻見一俊朗少年面無表情的看著她,一襲錦袍端的是風流俊雅,氣度萬千。
林西硬生生扯出個笑臉。
高家的基因真真不錯。府上三位少爺、四位小姐,男的英俊,女的貌美,果然是龍潛鳳采,委實令人羨慕啊!
她狗腿的跑上前行禮,衝來人一笑,「二少爺安好。」
高子眈定睛一瞧,原是個黃臉醜丫鬟,鼻子裡哼嗤出一股子冷氣。
「怎麼又是妳?果然是個蠢貨,連個路都不會走。這劉嬤嬤的眼睛是瞎了嗎,這種貨色都買進府?」
林西上前兩步,乾笑幾聲,「二少爺,奴婢蠢是蠢了些,卻是忠心耿耿,任勞任怨。剛剛三小姐還誇過奴婢呢!」
「別過來!」
高子眈連連後退兩步,嫌棄的看著她已經花了的臉,掩鼻繞道而走。
果然是一個娘生的,這二小姐與二少爺毒舌的本事如出一轍。只二小姐擅長在一旁搧陰風點鬼火;二少爺則對狗嘴裡能不能吐出象牙更有研究。
林西入高府四年來,統共與這二少爺只見過兩回,頭一回還得追溯到三年前。
她剛入府一年,還在劉嬤嬤手下學規矩,被人差去辦個什麼事,因為想偷懶,走了小路,一不留神摔了個狗吃屎,好巧不巧的遇到了高二少。
林西一邊掏出帕子擦了擦臉上的泥巴,心道:小路走多了,總能遇見鬼!還是個色鬼!
平蕪院位於高府內宅的東面,是個坐北朝南的二進院子。
兩邊抄手遊廊從兩扇朱漆大門起圍著院子一周,上面三間大正房連著左右耳房,東西各兩側廂房,均是粉牆青瓦,雕梁畫棟。
院子極為寬敞,東南角一池薄冰掩映在幾叢翠竹下,西南角兩株臘梅掛滿了白雪。
林西的屋子,便是在這西邊的廂房內。
屋子裡沒人,她在角落裡找到了自己的床鋪被褥,默默的打了盆冷水,粗粗的洗了把臉。
想著這一早上的境遇,林西喪氣的撲倒在自己的被褥上。
被褥半舊不新,料子倒是極好,因前幾日剛剛曬過,上頭還有一股子陽光的味道。
林西凍僵的身子漸漸有了絲熱氣。她從枕頭底下拿出面小手鏡,趴在床上細細的照了半天。
手輕輕撫上臉龐,微有粗糙感。
又快七天了,這面皮也該換一張了。
看著鏡子裡的這張臉,林西覺得二小姐的話雖然刻薄了些,卻生動形象的道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張臉作為醜丫鬟的典範,實在是太成功了。
林西看向鏡子的目光漸漸出神……
簾子被掀起,一個容長臉兒,白淨皮膚,約莫十四五歲的少女突然進屋來。
林西迅速的把鏡子塞回枕頭底下,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柳丁姐姐,妳回來了!」
「大白天的,挺什麼屍啊?妳這小蹄子,越發的懶了。小姐的手爐送過去了?」
柳丁倒了杯茶,一口氣喝下,「渴死我了,這院裡怎的連個人影也沒有?人都死哪去了?」
林西接過空杯子,殷勤的替她續滿了水,「聽說都往夫人院裡去了。」
柳丁面色一沉,眼眸閃了閃,叉著腰冷笑。
「我說怎的把我支到了何姨娘那兒討要什麼繡花樣子,原是為了這一樁。哼,也不撒泡尿照照,都是些什麼德性。這毛還沒長齊呢,便要飛上枝頭做鳳凰。我呸!做他娘的春秋大夢!」
柳丁的祖上三代都是這個府裡的家生子。其祖父母因是老實人,不會來事,在高府裡只弄了個小管事當當。哪知祖墳冒青煙,生了個小兒子容貌出眾,勾搭上了當時夫人身邊一個得用的丫鬟。
這個得用的丫鬟,便是劉嬤嬤。
劉嬤嬤閨名劉芳,伺候了夫人崔氏三十多年,與夫人的情分非比尋常,管著府裡採買丫鬟一事,最是油水豐盛的差事。
林西能進高府做丫鬟,除了劉嬤嬤慧眼識珠外,醉仙居半罈上好的竹葉青可謂功勞不小。
醉仙居一壺上好的竹葉青為紋銀十兩,半罈子竹葉青怎麼著也得過百兩。而她在高府整一年,連著主子的賞賜統共存下十兩銀子。
賣身做丫鬟要做到倒貼的分上,天上地下也只她林西是頭一個。
柳丁罵了半天,也沒個應聲的人,回頭一看,見林西正對著剛剛遞到她手裡的茶盞痴痴的傻笑,氣不由消了一半。
「別說我沒提醒妳,少往夫人那院裡跑,做好自個兒的本分就是!」
「柳丁姐姐,妳放一百個心,我就是一天往夫人院裡跑個十七八趟,夫人也看不上我。便是夫人看得上我,大少爺也看不上我。」
「死妮子,妳這話倒是實在。」
林西想著大少爺那一院的鶯鶯燕燕,笑得越發歡實,「柳丁姐姐,大少爺院裡那幾個,也不知道誰能入了夫人的青眼,放在大少爺屋裡。」
高府大少爺高子瞻早已年滿十七,身體與心理都已經發育到了可以與女子進行床上交流活動的時候。
做為高府唯一嫡出的少爺,交流活動的對象當然不能隨便,須得由其母親,高府的當家夫人崔氏為他精挑細選。
如今這項選秀活動發展得如火如荼,吸引了高府各房各院無數懷春丫鬟們的前仆後繼。當然鹿死誰手,勝負暫時尚未揭曉。
柳丁笑得一臉神祕:「聽我娘說,左不過大少爺院裡那容色好的大丫鬟們。咱們這院裡的,想都別想。」
林西猛眨了幾下眼睛,頓時來了精神。
都道肥水不流外人田,與自己熟悉的侍女進行床上交流活動,既不用擔心染了什麼髒病,又沒有陌生感,再說以那幾個丫鬟對大少爺的垂涎程度,說不定連前戲都能省下不少。
「柳丁姐姐,其實放在屋裡也沒什麼好的,萬一將來大少爺娶個厲害的少奶奶回來,還不知道是生是死呢。」
柳丁臉上浮現一抹可疑的紅色,「大少爺那般人品的人,將來配的少奶奶必不會差。」
林西心頭咯噔一下。
完了,完了,看情形這姑奶奶已是動了芳心,劉嬤嬤算計了半天,到底沒算計過異性相吸這條鐵的規律。
為了防止眼前的少女胡思亂想,她忙岔開了話題道:「柳丁姐姐,有件事情我得跟妳說,妳幫我出出主意。」
柳丁斂了神色,「又出了什麼夭蛾子?」
「柳丁姐姐,妳看我這個樣子,怎麼配到小姐書房伺候?妳幫我在小姐跟前說說好話,就說我大字不識幾個,笨手笨腳的,是扶不起的阿斗。」
柳丁俯首盯著她瞧了半晌,直看得林西心頭起了毛,才幽幽道:「也不知道妳走了什麼狗屎運,居然入了譚嬤嬤的法眼。罷了,既然小姐讓妳到書房伺候,自然有她的用意,妳只管照小姐的吩咐去做吧。」
林西哭喪著小臉,「柳丁姐姐,我怕……」
「妳怕什麼怕?這份差事又不是妳湊到小姐跟前哭著喊著求來的,憑她是誰,這閒話也說不出口。」 柳丁一臉的恨鐵不成鋼。
林西感動得眼眶含淚。
「林西,林西!劉嬤嬤叫妳去一趟!」
「哎,來了!」林西乾笑道:「柳丁姐姐,妳娘叫我去呢!」
「去吧,去吧,長點眼力勁兒。」柳丁沒好氣的擺擺手。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極品丫鬟(卷一)一葉輕舟入高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5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言情小說 |
$ 246 |
中文書 |
$ 252 |
古代小說 |
$ 252 |
華文羅曼史 |
$ 25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極品丫鬟(卷一)一葉輕舟入高門
人生如戲,全靠演技。林西暗嘆:我真是個人才啊!
相府生存的必備條件:
要巧言如蜜,要變臉神技,要心思縝密,要一身武藝……這有必要?
林西從父之命來到相府當丫鬟,兢兢業業的過了四年,眼見約定的期限快到,她仍是沒能找到父親臨終囑託的東西……真真是天要亡她!
想著最後一年定要安全度過的林西,被暗中安排進了三小姐的院,卻意外惹了大少爺的眼,遭了姨娘的恨和其他婢女的妒。林西覺得人生沒有比無奈更無奈的事了,她一個小小的醜丫鬟,不小心承蒙大家關注,還怎麼低調尋寶啊?
偏偏此時遇上高老爺正妻病危,妾室們群起作亂的時刻,一片腥風血雨中,林西該如何在大宅門裡明哲保身,卻又能不著痕跡的潛入那間「最神祕的院落」一探究竟呢?
---------------------------------------------------------------
千年老妖王氏出山了;
朱姨娘哭天喊地的在院子外頭替二少爺喊冤;
何姨娘滿臉春色的朝高老爺拋媚眼;
高老爺一邊與小妾眉來眼去,一邊對正室情深款款;
夫人拖著將死的身體,欲說還休,欲拒還迎。
我的娘哎,這是何等詭異啊!
作者簡介:
包子才有餡
處女座宅女一枚,性散漫。
生於江南水鄉,居於六朝金陵,嗜文學,愛音樂,喜旅遊,貪美食,微有潔癖。
為人胸無大志,四平八穩,不拘雅俗。
養一懶狗,喚名巧克力。
常常一人,一狗,一書。
此生,唯願所愛之人喜樂平安。
《繪者》
棠燁
喜歡古風,熱愛遊戲,沉迷美食,執著畫畫,最享受用紙筆顏料表達內心的過程。很高興能為《極品丫鬟》系列繪製封面圖。希望大家能通過我筆下的人物更加喜愛這部作品。
歡迎關注我的微博/LOFTER:棠燁
章節試閱
莘國。
京郊。
景德二十一年,仲秋,八月初八。
月夜,朔風乍起,稀疏的幾點星光將一長一短兩個身影拉得極長。
「東東,我們倆這種行為,可稱得上私奔?」
「……」
「你為什麼不把翠花也帶上?這樣咱們三人一道私奔,路上也熱鬧些。」
「……」
「你老實跟我說,你是不是喜歡翠花?」
「……」
「你既愛慕她,又為何要跟我走?」
「……」
「你有沒有想過,被抓回去有什麼後果?」
「……」
「沒想過?你居然沒想過!做狗,豈可如此不顧後果,隨心所欲。」
「……」
「你怕不怕?」
「……」
「我有些怕的。」
「……...
京郊。
景德二十一年,仲秋,八月初八。
月夜,朔風乍起,稀疏的幾點星光將一長一短兩個身影拉得極長。
「東東,我們倆這種行為,可稱得上私奔?」
「……」
「你為什麼不把翠花也帶上?這樣咱們三人一道私奔,路上也熱鬧些。」
「……」
「你老實跟我說,你是不是喜歡翠花?」
「……」
「你既愛慕她,又為何要跟我走?」
「……」
「你有沒有想過,被抓回去有什麼後果?」
「……」
「沒想過?你居然沒想過!做狗,豈可如此不顧後果,隨心所欲。」
「……」
「你怕不怕?」
「……」
「我有些怕的。」
「……...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引子
第一章 高家大院
第二章 內宅暗鬥
第三章 少爺小姐
第四章 家中醜事
第五章 崔家來人
第六章 林家村莊
第七章 荷花姑娘
第八章 王家姑娘
第九章 忍辱負重
第十章 萬花初見
第一章 高家大院
第二章 內宅暗鬥
第三章 少爺小姐
第四章 家中醜事
第五章 崔家來人
第六章 林家村莊
第七章 荷花姑娘
第八章 王家姑娘
第九章 忍辱負重
第十章 萬花初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