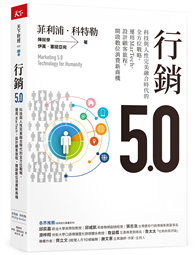一次意外的邂逅,在無預警的狀態下,讓葉慈觸及一份死去愛情的餘溫。
那是思念的幽靈?抑或只是葉慈的幻覺?
葉子,一個在唱片業能力極受肯定的唱片宣傳。她擁有旁人稱羨的工作,也擁有深情體貼的戀人。但在她內心深處隱藏的「他」,卻隨著每次思念來襲,越來越清晰,連呼吸都是一種折磨…。
在漫天白雪的日本溫泉鄉元箱根,她遇見了「他」,雖然只是長相神似的陌生人,但卻深深勾起她內心的悸動,五年前深愛的記憶如同電影,一幕幕在眼前放映…
當那男人向她走近,她會做出什麼選擇?她該如何找回獲得幸福的能力?
本書特色
愛是一種原生的能力,無庸置疑!
但往往,我們卻會用許許多多的偽裝,把愛,從「有能」愛成「無能」!
於是,幸福才會一直呈現「不能」的狀態!
一對約定彼此不問姓名的男女,
二個在幸福中各自藏著迷惑的困境,
一段意外中帶著寂寞與宿命的北國之旅…
用笑容與眼淚相互取暖並肩逃亡,當雪花飄落,
他們該怎麼面對無力反擊的人生,找到平行線的交叉點?找回幸福的能力?
作詞達人嚴云農,將擅於觀察兩性間的情愫變化與心理微妙互動,
化成細膩的文字與銳利的筆鋒,
獨創出洗練的寫作風格,
在上本短篇小說集《想你的離人節》,發揮得淋漓盡致。
此次即將推出的《愛 無能,幸福不能》,
幾乎是嚴云農的半自傳長篇小說,
書中從事填詞工作的男主角李耕一所經歷的愛情、親情、工作的點點滴滴,
即是源自於作者每一次實實在在的呼吸,
以及那些切膚的迷惑、煩惱、期待與反省。
你也許會好奇在他的小說中,到底有哪些是真實,哪些是虛構?
但這一點都不重要!
當你看著書中角色被工作、愛情、親情、友情各種複雜的成分攪和在一起,
產生了各種連鎖反應時,能回頭想想…對於你的生命,你是否也夠『誠實』?
『誠實』面對自己對『愛』的無能為力!
作者簡介
嚴云農
我不帥,但我知道自己長的是怎麼的一個樣子。
我不沈默,但有時我覺得再多話語也說不清我真正的心思。
我不悲傷,但我也還不能理解什麼是絕對的快樂。
我不難相處,但似乎少有人可以完全突破我的防備。
我喜歡看你笑,但我更希望你有能力誠實地哭。
我寫很多東西。寫歌、寫小說、寫劇本。
寫呀、寫呀…
我總覺得我是在文字與文字之間拼拼湊湊,
想搞清楚自己真正的輪廓…
而且僅是輪廓,就已經讓我累的半死了…
我操縱著自己的RPG GAME,
現在才開始準備進入序章而已!
我是這麼跟自己說的!
嚴云農的部落格anoyen.pixnet.net/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