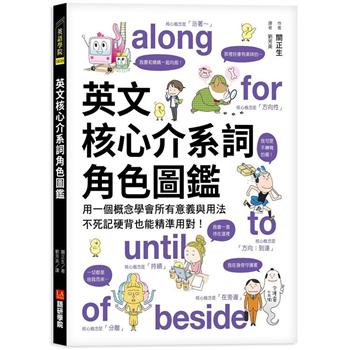序函
林泠
雅雯:
在歲晚的壓縮下,我再次細讀了你的詩卷。第一次是依照你設定的目次進行,另一次則是順著你創作的時序,也許就是你某段生命中,情思的流程。這樣縱橫地閱讀,是為了讓我在一個狹窄的時窗裡,迅速地感受這本詩稿特有的觸鬚。
你的詩,無論語言、內涵,或整體的設計,都清晰地展現了年輕一代詩人少有的含蘊、優雅,以及對於抽象視野的重視。你耳中的風聲絕不是嘶鳴,而是「微涼的草鼾」;你看到的秋色,則是「老藤縫隙間……破碎的蟬翼」。讀你的詩,我能感到它沉靜而不喧嘩的獨立性,來自你對某種時尚語言││或稱之為感官語言││蓄意的疏離;讀你的詩,往往被它轉折的意象吸引,而不期然地進入你隱喻的幽冥,卻又處處置身於現實之中。這樣細緻的詩,作序的人唯有採用微觀處理,方能公允地向讀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引示,而這絕不是一兩千字的草章所能涵蓋的。
況且,你詩的語言正在蛻變之中。我初步的印象是:你收在集裡的、上世紀寫的作品,依稀有「尋詩」的痕跡;但是下半部、尤其在二○○三年後期完稿的幾篇,就儼然是「詩來尋你」的產物了││簡約、自在、流動││展現了青年詩人敏銳、愈趨圓熟的基調和姿勢。這是相當重要的轉軸。詩人的你,對此當會有高度自覺的。
瑣碎地說了一大堆,祇想以最大的誠意說服你:你的自序或後記將遠勝我能提供的序言;何況我已預知,緊迫的時間實不容許我做理想的微觀評議。(哪,我可不是傳說中的完美主義者,祇不過留存了些科學的後遺症罷了!)往後若有機會,我盼望能為這集子寫一篇稱職的讀後感。
而此時,是大海嘯後的第七日,北半球風雪連連,你的詩帶來冬夜少有的愉悅和暖意。我窗上的積雪像是溶化了……卻在我掩卷遙思的那一刻,又結成了冰。
二○○五年‧元月
一四七巷(代後記)
Dear林泠:
我想好好地解釋自己為什麼寫出這樣的東西,為什麼喜歡隱藏、又忍不住喃喃地說。越是想好好解釋,越是覺得困難重重。百般思索,我想那終究還是根源於我成長的場所吧。
那是一條有時喧噪、有時安靜的長巷。白天,它聯絡台北市兩條東西向的主要幹道;每天每天,許多人車在此迴轉,從東西向轉為南北向,或者由奔馳轉為遊蕩。然而,我的巷子又不是多麼繁華的。從幹道轉進長巷,此岸是我們靜默的鄰里,彼岸是一所以蔚藍天空自傲的學校,它們都簡淨樸素,顯露於外的只有磚灰的外牆和報時的號聲。一旦入夜,距離各種吃食或市集都有段距離,車燈很快地掃了過去,未曾特別盤桓逗留。不論長巷如何在朝九晚五的時段身負重任,只要卸下光線、卸下外來的聲色,它都只是一條簡單,筆直,不言不語的巷子。
影響巷子氛圍最深的應該是那所學校,或者說,是那所學校決定了我眼中巷子悠藍的色調。在地圖上,學校會被標示於四條重要幹道的中心,這樣的區塊本該是層層密密的辦公大樓或住宅、把人們框進無數柵欄中,可是因為遼闊的校地,城市上方那一大片天空得以日升月落、風往雲來。我在這裡長大,沿著天空的邊緣行走,遭遇了最初的離合聚散,花費無數時間體會種種情緒,縱容自己想像一些憤怒和感慨。即使後來到了我們都熟悉的綠色四方城,我還常常想念這個藍色校園:許多人的青春記憶是在高中時代開始奔騰縱放,我卻是在那之前就擁有過太豪華的旅程,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有流浪的欲望。
至於與校園相望的一側,在我年幼時曾是一大片眷村。說是一大片,如今也不太能估量了,因為眷村遷移之後,裡面蜿蜒曲折的小徑已然不存。眷村深處曾經有個防空洞,漆黑的岩石、厚厚地刷抹上瀝青、任憑石縫間雜草竄生。我曾經在防空洞前的空地貪看一隻大蝸牛、好奇牠究竟要去哪裡,以至於延誤了回家的時間,讓媽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責罵。神奇的是,像我這種外人是找不到防空洞的真正入口的。所有的洞口都僅有窗戶大小,而且滿是亂七八糟的荊棘與蔓生植物,成人怎麼鑽得進去?唯一看起來比較像神秘入口的,是一個靠近地面的半圓形洞穴,但還是黑漆漆的,分不出是深不可測、抑或是死路的偽裝。而且,在兒童的腦袋裡,沒有一或兩扇門戶,怎麼能夠算是入口呢?出口又該如何安排?
因為一座神秘的、蹲踞在一個村鎮內心深處的防空洞,我隱約感受到長巷的矛盾和欲言又止:它細長幽深、每天走也走不到盡頭,同時又空闊舒朗、裝得下天空與時代的秘密;它安靜到彷彿多年前撤守了的戰線,同時也是一條人事與時間共喧囂的河流。
那個眷村以及其中的防空洞,可能是很多小孩彼此分享的秘密基地。對我而言,那裡面卻有一套難以掌握的邏輯。我曾經在放學路上和同學追逐遊戲,跑不過人家就既沮喪又狀似自得地鑽進某條小徑,進去之後才知道恐慌 ── 小徑中還有小徑,每條小徑都只容一個成人牽著一輛腳踏車通行;所有的小徑兩側都是住家,或者是廚房、或者是廳堂,或者是晾衣服的竹竿、或者是在小藤椅上懶洋洋曬著滿臉皺紋或國旗刺青的老人。我並不害怕,卻因為迷途而恐慌:怎麼每個廚房的排煙管、每扇門的老舊春聯、每根竹竿上的衣被,甚至每個老人,都長得一模一樣?小徑越鑽越多分岔,越鑽越見曲折,我到底在哪裡呢?我想放聲大哭,但是「哭」可能比迷路更能造成恐慌,內在真實情緒的發洩不見得請來救兵,反而會讓人輕易逮到弱點,若有歹徒聽到哭聲,馬上知道這小孩迷路了可以一騙……所以我無論如何忍著不哭,繼續鑽進鑽出,佯裝自得自在,不時停下腳步看地上滾落的七彩玻璃珠。
我已經不記得怎麼走出了迷宮。只記得走出來的那一刻,驀然發現原來還身在自己日來日往的長巷,距離鑽進小徑的起點,也不過隔著兩三戶人家。那時陽光忽然很刺眼,我還是想哭,但在簡單的、筆直的、熟悉至極的路上哭泣實在無謂,眼淚將落未落之際,也許就自行蒸乾了。
或者人生就是這樣吧。以一條長巷作為隱喻,幾度鑽進鑽出,各種歡欣挫折不斷重疊複製,想要放聲大哭、又刻意自我壓制,等到事過境遷,眼淚還在,哭泣卻沒有意義了。以這樣的人生為基礎,時時追想回溯,進而形成一種自我認知與要求:我恍惚認識了時光的侷限及其所選擇的視野;恍惚明白,由焦急徬徨的內在望出去,這世界竟可能是無聲的煉獄;並且明確地記得我曾經非常珍視一些偶然的遇合和知契,記得自己曾經以為得到又終於失去、並因而多麼喜悅又多麼絕望。那些都是地上滾落的七彩玻璃珠,被我東西南北的腳步隨處踏落,又一一拾起。
既然哭泣沒有意義,那也無須讓人看到我曾經的迷途或進退失據吧?所以,親愛的林泠,我來了個小小惡作劇:刪除了每一首詩的寫作日期。我仍然在旅途中、仍然會恐慌,沒有了時序的線索,或者僅僅擁有一份經我刻意編排調整過的時序;情感的流轉、人生重心的變遷,乃至於那些眼淚已經掉下來卻不願承認的事件,就可能在刺眼的陽光下模糊漫漶。
讀者不會知道我心中的小徑何時被移除,緩緩爬過防空洞的蝸牛可能躲在什麼地方 ── 把讀者視為綁架小孩的歹徒是有點莫名其妙,然則我另外提供了線索。「抒情考古學」可能是線索之一,若有人擅長考古,則技藝生澀程度當可做為鑑別依據,他會知道我尋詩的歷程,也可能願意寬容地認可詩來尋我的鼓勵。此外,更重要的也許是這條巷子:我以一條巷子描繪生命的執著或弛放,騁縱或迂迴,茂美或清冷 ── 那是我反覆沉吟、反覆抒情的核心。
雅雯
二○○五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