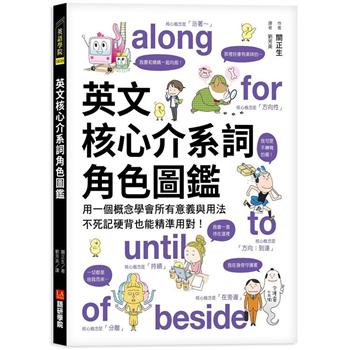簡媜筆下搖曳恣縱,其作品莫不使讀者如享盛宴,餘味無窮。本書內容包括尋常生活、懷鄉、旅行、閱讀等多種題目,其中約三分之一取自絕版多時的《浮在空中的魚群》,餘皆未嘗結集,但都經重新檢視增修,精緻投射,展現盎然之新意。
作者簡介
簡 媜
宜蘭冬山人,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當代散文名家,筆下搖曳恣縱,言人之所不能言,但謹守紀律,輕易不逾越文法尺度,收放之間看得出旺盛過人之血色,卻始終維持著一種從容的學院氣息;出版有《水問》、《只緣身在此山中》、《私房書》、《下午茶》、《女兒紅》、《舊情復然》、《密密語》等散文集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