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城正年輕(馬世芳)
「過了許多年之後,他們也可以想當年了。當年是一段歷史,當年是時間的過去,但值得一個人回想,那一定是多姿多采的事情。所以,生活得燦爛,並非沒有意思。」
──〈想當年〉
當時只道是尋常。多年後回望,那時活得多燦爛,多有意思啊。
《試寫室》是西西一九七○年在《快報》寫的專欄,每天一則,每則八百字,前後寫了幾個月。當時西西三十二歲,寫過不少影話、藝評、隨筆,編了兩齣電影劇本,也發表過幾篇小說和現代詩,在香港算是小有文名了。當時的西西,主要是一位專欄作家,也是一位剛起步的小說家。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城》,要到四年後才落筆。
這批四十多年前的專欄文字,連作者自己都遺忘了,卻生動地留下了當時香港青年人的生活側寫,以及一位始終好奇觀看這一切的作者形象。這裡的香港,是一座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城。西方青年文化大潮東來,從電影、時尚到搖滾樂,愈來愈多青年懂得追求更豐富的文化生活,也都願意費心讓自己活得更有風格。那也是經濟起飛的時代:「人們嘩啦啦的跑到四面八方去,紙幣流來流去,臉們到處出沒,而這樣子,一個城市就蓬勃起來,市面就繁榮起來。」
許多事情變得很快。比方青年人的時尚:「這幾年來,這裡的男孩子女孩子可樂了,因為男孩子既不用穿父親那樣的西裝,女孩子又不用穿母親那樣的旗袍。……忽然的,香港居然也有條加納比街(倫敦青年時尚重鎮)那樣的街了。」不太久以前,若在雜誌看到一襲好衣服,只能自己依樣畫葫蘆裁一件(所以許多女孩都會踩縫衣機做洋裁),或者找裁縫照著做一件。
是的,那年頭時尚男孩穿闊腳褲(喇叭褲)梳長頭髮,女孩夢想一件瑪麗鄺的迷你裙,一雙狄奧的鞋。不只這樣,西西還寫到當年的「喜僻士(嬉皮)」青年,一針見血:「快樂的喜僻,祇是一個神話……真正的喜僻士少,做到的也難」── 真正的喜僻士「插足高貴的場合,穿得像個乞丐而毫不在乎;別人把手指指上臉,自己依然微微笑;永遠不生氣,不妒忌,不憎恨,不報復;永遠和和平平,那就是冷。喜僻士的哲學乃是冷的哲學。」多麼生動!這個「冷」,便是後來我們說的「酷」了。
西西告訴我們當時最「潮」的文藝青年模樣是這樣的:漂亮時髦讀很多書的女孩子,竟然流行講粗口,一群姊妹穿戴講究坐在咖啡室,「嬌聲滴滴,抑揚頓挫地媽的媽的起來」。在書店裡徘徊的男青年呢,「一窩蜂,人人抽煙斗。那些讀書的青年,抽得最起勁。」至於真正聰明的新時代女孩,「她自己賺錢,賺很多。她自己住一層樓,自己煮飯,飯煮得出色,房子又打理得乾淨……她喜歡好東西,自己一件一件買回來,買來北平的地氈,買來聲音兩邊走的錄唱機。過幾天,要買一輛跑車。她說,當然是積架E。要是早已考到了車牌,現在她已經在街上一小時六十哩了。」而且「很早很早就知道卡夫卡的《變形記》,又把《紅樓夢》背得很熟……她知道十萬塊錢該怎麼享用,如果祇有兩塊錢,也可以美麗地度一個週末。」唉呀,誰不想認識這麼一位似曾相熟的女孩呢。可是西西告訴我們:她並不快樂,朋友給她的建議,竟是「把武功廢掉」。
那段時間,也是後來西西自謂「看電影的黃金時代,上『第一影室』像上學」。那些歐陸新浪潮的名導名片:高達、安東尼奧尼、維斯康提、路易馬盧,猶是新鮮熱辣的當下,種種驟臨新世界的新鮮興奮,紛紛留在了這個專欄 ── 那還是「舉世對彩色片寄以最高期望的時刻」呢。
後來寫起小說汪洋恣肆、博學博聞的西西,那驚人的閱讀胃口,也在這裡讓我們窺見一二:她可以一面寫胡蘭成、阿保里奈爾、貝克特和喬易斯(喬伊思),一面慨歎「經史子集四大類,單是廿四史,就可以讀五年」,於是「買了神話的《山海經》。選了《詩經》、《左傳》、《國語》、《戰國策》。周秦諸子的是《論語》、《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另加一部《楚辭》。由於怕古文太古,所以,同時插以清代小說梅花間竹讀,找來了曹雪芹《紅樓夢》,特別看脂批,又找來金聖歎批水滸」,繼而筆鋒一轉,又介紹起麥魯恒(麥克魯漢)《瞭解媒介》時新的「冷媒介、熱媒介」觀念,也很明白青年人愛讀的時尚雜誌《十七歲》。即使在這些早期的隨筆,西西的觀影筆記、閱讀筆記也已經自成一格。除了閱讀、電影,她也寫劇場,從前衛劇《毛髮》寫到馬素(馬歇馬叟)的啞劇。她就像一個天真的孩子,對人間一切藝術、知識與智慧始終抱著無窮無盡的好奇心。
且翻開這本書,跟著這位興味盎然的文藝女青年,借她那雙慧黠靈動的眼,探望這座猶然青春的城。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試寫室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中文現代文學 |
$ 255 |
現代散文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270 |
現代散文 |
$ 270 |
文學作品 |
$ 323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試寫室
「《試寫室》是西西1970年在香港《快報》寫的專欄,每天一則,每則八百字,前後寫了幾個月。當時西西32歲,寫過不少影話、藝評、隨筆,編了兩齣電影劇本,也發表過幾篇小說和現代詩,在香港算是小有文名了。當時的西西,主要是一位專欄作家,也是一位剛起步的小說家。
這批四十多年前的專欄文字,連作者自己都遺忘了,卻生動地留下了當時香港青年人的生活側寫,以及一位始終好奇觀看這一切的作者形象。這裡的香港,是一座年輕的、朝氣蓬勃的城。西方青年文化大潮東來,從電影、時尚到搖滾樂,愈來愈多青年懂得追求更豐富的文化生活,也都願意費心讓自己活得更有風格。」(馬世芳)
《試寫室》一書,由西西於1970年為香港《快報》專欄「我之試寫室」所撰文章,收輯而成;其他在《快報》的散文及閱讀專欄,已結集為《剪貼冊》、《花木欄》、《耳目書》、《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我之試寫室」借自西西喜愛的日本漫畫家久里洋二的專欄「僕の試写室」,書名亦由此而來。其中見之當時三十初的西西,爽朗瀟灑的明快筆風,迭有「現在的我遇上以前的我」之趣。
作者簡介:
西西
原名張彥,廣東中山人,1938年生於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香港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曾任教職,為香港《素葉文學》同人。1983年,她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榮獲《聯合報》小說獎推薦獎,正式開始了與台灣的文學緣。著作極豐,包括詩集、散文、長短篇小說等近三十種,形式及內容不斷創新,影響深遠。2005年獲《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2011年為香港書展「年度文學作家」。
TOP
推薦序
那時我城正年輕(馬世芳)
「過了許多年之後,他們也可以想當年了。當年是一段歷史,當年是時間的過去,但值得一個人回想,那一定是多姿多采的事情。所以,生活得燦爛,並非沒有意思。」
──〈想當年〉
當時只道是尋常。多年後回望,那時活得多燦爛,多有意思啊。
《試寫室》是西西一九七○年在《快報》寫的專欄,每天一則,每則八百字,前後寫了幾個月。當時西西三十二歲,寫過不少影話、藝評、隨筆,編了兩齣電影劇本,也發表過幾篇小說和現代詩,在香港算是小有文名了。當時的西西,主要是一位專欄作家,也是一位剛起步的小說家。...
「過了許多年之後,他們也可以想當年了。當年是一段歷史,當年是時間的過去,但值得一個人回想,那一定是多姿多采的事情。所以,生活得燦爛,並非沒有意思。」
──〈想當年〉
當時只道是尋常。多年後回望,那時活得多燦爛,多有意思啊。
《試寫室》是西西一九七○年在《快報》寫的專欄,每天一則,每則八百字,前後寫了幾個月。當時西西三十二歲,寫過不少影話、藝評、隨筆,編了兩齣電影劇本,也發表過幾篇小說和現代詩,在香港算是小有文名了。當時的西西,主要是一位專欄作家,也是一位剛起步的小說家。...
»看全部
TOP
目錄
那時我城正年輕(馬世芳)
何不說不
保守秘密
語言有趣
瀟灑男孩子
許願的時候
給教訓一頓
嘻哈恐怖劇
過去的過去
雜誌上的遊戲
鄉下人去打仗
愛麗絲之餐室
金童玉女
阿保里奈爾的家
有涯隨無涯
靜土何處
一屋子擠滿人
冬眠過
大家到廚房去
星期日是家庭日
不用做家課
認字十大個
啦啦歌
店有黑有不黑
現代詩
怪模樣瓶罐
書的衣服
想當年
熱鬧音樂節
難題
大家都是
恭喜恭喜你
這樣說
東西試寫室
玻璃杯等等
鬍子鞋子其他
甚至有趣的鬼
溫暖洋娃娃
大嬰孩
貝克特說貝克特
動物園故事
有創造力...
何不說不
保守秘密
語言有趣
瀟灑男孩子
許願的時候
給教訓一頓
嘻哈恐怖劇
過去的過去
雜誌上的遊戲
鄉下人去打仗
愛麗絲之餐室
金童玉女
阿保里奈爾的家
有涯隨無涯
靜土何處
一屋子擠滿人
冬眠過
大家到廚房去
星期日是家庭日
不用做家課
認字十大個
啦啦歌
店有黑有不黑
現代詩
怪模樣瓶罐
書的衣服
想當年
熱鬧音樂節
難題
大家都是
恭喜恭喜你
這樣說
東西試寫室
玻璃杯等等
鬍子鞋子其他
甚至有趣的鬼
溫暖洋娃娃
大嬰孩
貝克特說貝克特
動物園故事
有創造力...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西西
- 出版社: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8-05 ISBN/ISSN:978957674339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4頁 開數:25K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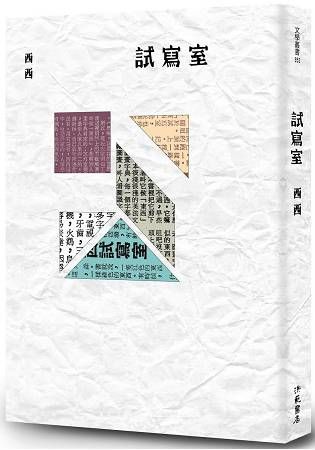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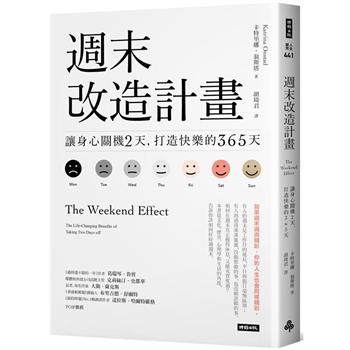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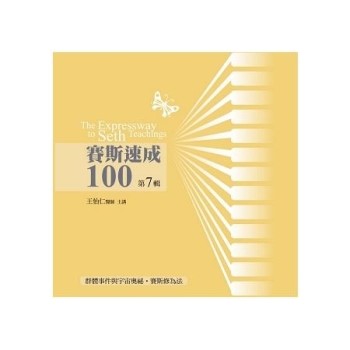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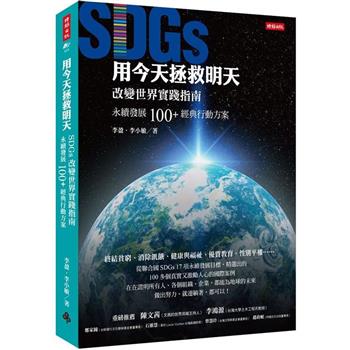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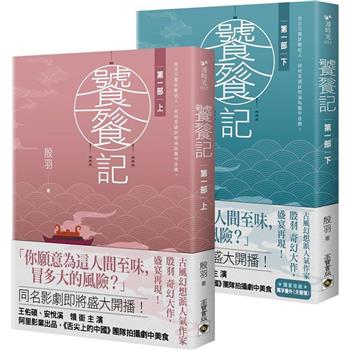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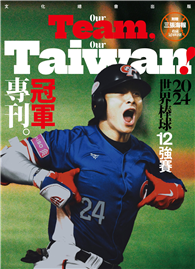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