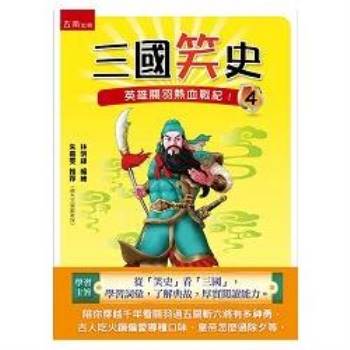在紀弦先生左右
我是紀弦先生的「私淑弟子」,從文藝青年時代開始,我就是他熱情的崇拜者、追隨者。「瘂弦」這個筆名,是在我十九、二十歲時就取定了,裏邊有個「弦」字,可見我當時潛意識裏對紀弦先生就敬佩、景仰。我的第一首詩〈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一九五三),經紀弦先生發表在他主編的《現代詩》第五期(一九五四年二月)上,這對我的鼓勵很大,紀弦先生就是從這首詩對我有了初步的印象。
林海音女士曾為紀弦先生和我拍了一張合照,應該是一九六八年吧,林先生稱為「二弦」,一個是大弦、一個是小弦,這張照片裏紀弦先生拿著他的菸斗,我站在旁邊狀至恭謹,當時心裏不知道有多高興可以與老師輩大詩人合照。
我永遠不會忘掉我第一次到他任教的成功中學去看他的印象,他站在校園的椰子樹下跟我說話,那樣子活脫脫就是《暴風雨》詩集封面上的自畫像,書上的樣子竟然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動得渾身發燙,好像看到情人一般。之後很多年,我對他的追隨、嚮往與崇拜,有增無減。
紀弦先生晚年,我們時常通信,一個月總有兩三封信吧,信中談詩談畫談家常。有封信他在信的第一句話寫著「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後來我查了查這兩句詩的出處,是杜甫寫給李白的一首詩的頭兩句,當然我知道紀老是把它當作普通的問候語來用的,但這也說明了老先生是把我當作很親的朋友來看待。因此,在他年事漸高以後,沒有精神氣力去做的事就交給我來做,比如他與胡蘭成在三十年代交往頻繁,但手頭已沒有相關資料,就要我代為尋找,我到處蒐集,終於整理了一套資料寄給他,他收到後非常高興。
在很多信裏邊,我最常提到的有兩件事情,一是請他保重身體,做文壇最長壽的詩人;二是「鼓勵」他寫回憶錄,每封信都提到這件事。在我聲聲催促之下,皇皇三大卷的《紀弦回憶錄》終於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呈現在世人面前。回憶錄寫得非常好,這部書曾得到文化部部長龍應台(時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經費上的支持,在出版的過程中張默也出了很大的力氣。錢鍾書說「自傳就是他傳」,像紀弦先生這樣重要的人物,他的自傳就彷彿是整個詩壇的歷史,具有文獻的意義。
紀弦先生很重視養生之道,有很好的生活習慣,他曾告訴我他長壽的祕訣就是,吃飯定時定量,兩餐之間絕對不吃任何東西。他年輕時常飲酒,但到了晚年就保持在微醺狀態,所以我覺得他的身體本錢夠,因此我在每封信最後的問候語,不是「文安」、「保重身體」之類,都是「祝您向人瑞進軍!!!」關於這兩件事,我們的大詩翁都做到了,他把回憶錄寫出來了,也活到一百零一歲。
紀弦先生一向多產,晚年仍然寫作不輟,二○○四年時他已經九十多歲了,他告訴我他很想出一本詩集,把九十歲以前的詩彙集在一起,他要我替他取個書名,我建議他能不能用「年方九十」?意思是說我才九十歲,還年輕呢!他很喜歡這個書名,也直說「很絕、很絕」。其實中國畫家在畫上題字時,常寫「年方」幾歲,我只是借用而已,紀老滿意就好了。詩集成書前,紀弦先生對我說,過去文壇的習慣,都是年輕作家請前輩作家撰序,咱們來個逆向思考,我這次是老前輩請年輕作家寫序,你寫序挺認真的,你就幫我寫序吧!我一想,這可折煞我了,實在不敢當,就勉力為之吧。我寫序有個習慣,為了慎重起見,執筆之前,一定與作者做個紙上訪問,作為參考之用。我就出了十二道題目請教他。老先生的回答十分詳盡,告訴我們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情,是珍貴的文學史料。後來出書時,因為他身體狀況不太好,延宕了一些時日,文史哲出版社發行人彭正雄先生就把這篇問答放在書後,作為跋文。這篇訪問記雖然篇幅不長,比較簡要,卻是紀老在世最後一次接受訪問,實在是彌足珍貴。
紀弦、覃子豪、鍾鼎文三位先生,文壇稱之為「來臺三老」,他們都是留日的,皆為詩壇的重鎮,我們這一代都是在他們的培育薰陶下成長的。紀弦先生熱情、奔放,有一點神經質,對臺灣詩壇而言,他是名副其實的「點火者」,他點的火把我們當年這群小伙子統統燃燒起來,他的作風是火我點著了,至於能燒多久、能燒多旺就各憑本事了;覃子豪先生則屬實戰派,他是親手教我們如何把詩寫好,每篇習作他都仔細修改,尤其是當年參加文藝函授學校的同學,如向明、麥穗、我等等,都是受惠者;鍾鼎文先生是位溫文爾雅的紳士,對年輕人雖然不像上述兩位這麼熱絡,但在發表和出版上也常常給我們很多幫助,他的作品對我
們產生了很大的示範作用,也是我們尊敬的長者。
如今,三位老師皆已辭世,我們這些學生輩的也都八十多歲了,已至耄耋之年,執筆的當下真是覺得無限感傷。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老師們對創作的執著和對年輕人的關愛,將永遠銘刻在我們的心版之上。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聚繖花序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5 |
二手中文書 |
$ 276 |
中文書 |
$ 277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8 |
現代詩 |
$ 315 |
近代文學 |
$ 315 |
近代文學 |
$ 31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聚繖花序Ⅲ
瘂弦是現代詩壇大家,以洪範版《瘂弦詩集》行世,為現代詩經典之作,影響深遠。詩人曾主編《創世紀》、《幼獅文藝》及聯合報副刊等重要期刊雜誌近四十年,文學經驗豐富,觀察入微,長期維持優越而精緻的品味,體現在歷年來撰寫的文論及序跋文章之中,思維深刻、人情練達,是瘂弦文學論述詮析的精闢之作,這些文章總題《聚繖花序》,2004年曾輯成二冊出版,2018年再新編一冊行世。
作者簡介:
瘂弦
本名王慶麟,一九三二年生於河南南陽,青年時代於內戰中隨軍來臺,後在復興崗學院戲劇系畢業,曾服務於海軍;六十年代應邀參加愛荷華大學(lowa)國際創作計劃中心,並自威斯康辛大學(Wisconsin)獲碩士學位。
TOP
章節試閱
在紀弦先生左右
我是紀弦先生的「私淑弟子」,從文藝青年時代開始,我就是他熱情的崇拜者、追隨者。「瘂弦」這個筆名,是在我十九、二十歲時就取定了,裏邊有個「弦」字,可見我當時潛意識裏對紀弦先生就敬佩、景仰。我的第一首詩〈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一九五三),經紀弦先生發表在他主編的《現代詩》第五期(一九五四年二月)上,這對我的鼓勵很大,紀弦先生就是從這首詩對我有了初步的印象。
林海音女士曾為紀弦先生和我拍了一張合照,應該是一九六八年吧,林先生稱為「二弦」,一個是大弦、一個是小弦,這張照片裏紀弦先生拿著他的菸...
我是紀弦先生的「私淑弟子」,從文藝青年時代開始,我就是他熱情的崇拜者、追隨者。「瘂弦」這個筆名,是在我十九、二十歲時就取定了,裏邊有個「弦」字,可見我當時潛意識裏對紀弦先生就敬佩、景仰。我的第一首詩〈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一九五三),經紀弦先生發表在他主編的《現代詩》第五期(一九五四年二月)上,這對我的鼓勵很大,紀弦先生就是從這首詩對我有了初步的印象。
林海音女士曾為紀弦先生和我拍了一張合照,應該是一九六八年吧,林先生稱為「二弦」,一個是大弦、一個是小弦,這張照片裏紀弦先生拿著他的菸...
»看全部
TOP
目錄
卷一:詩與詩論
《朱湘文選》校訂跋
在紀弦先生左右
覃子豪先生的遺音
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
── 論商禽《夢或者黎明》
大哉問,大哉想,大哉寫!
── 《坐六》賞讀
一壺老酒,一小碟時間
── 讀丁文智時間意識與詩友聚談作品之聯想
一株胡楊的成長
── 汪文勤的詩
青春的反顧
── 林婉瑜作品賞讀
張堃詩美學的三個向度
從抒情到詠史
── 洪書勤的學思歷程與新感覺結構
詩是一種自牧,一種修行
── 王露秋《白描時間風景》賞析
《詩學》創刊號弁言
天上人間俱悵望,經聲佛火兩淒迷
── 懷念詩人盧飛白
詩美學的大磁場
── 《...
《朱湘文選》校訂跋
在紀弦先生左右
覃子豪先生的遺音
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
── 論商禽《夢或者黎明》
大哉問,大哉想,大哉寫!
── 《坐六》賞讀
一壺老酒,一小碟時間
── 讀丁文智時間意識與詩友聚談作品之聯想
一株胡楊的成長
── 汪文勤的詩
青春的反顧
── 林婉瑜作品賞讀
張堃詩美學的三個向度
從抒情到詠史
── 洪書勤的學思歷程與新感覺結構
詩是一種自牧,一種修行
── 王露秋《白描時間風景》賞析
《詩學》創刊號弁言
天上人間俱悵望,經聲佛火兩淒迷
── 懷念詩人盧飛白
詩美學的大磁場
── 《...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瘂弦
- 出版社: 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8-03 ISBN/ISSN:978957674346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04頁 開數:25K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