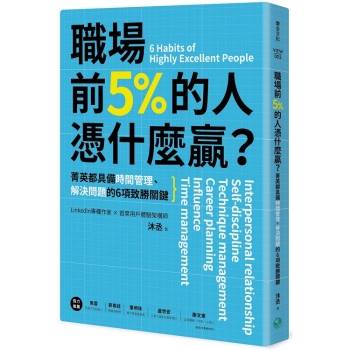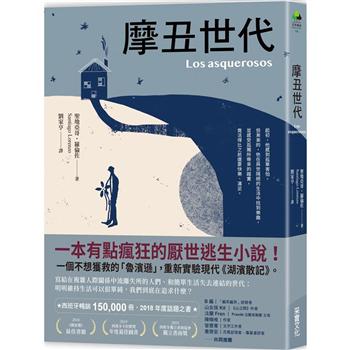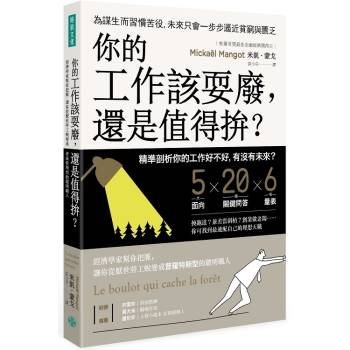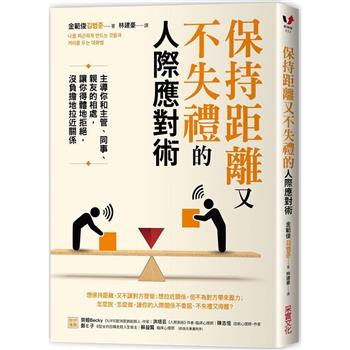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質疑克里希那穆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3 |
二手中文書 |
$ 261 |
西方哲學 |
$ 290 |
中文書 |
$ 297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質疑克里希那穆提
‧五百年來第一人克里希那穆提與當代引領思潮者的對話錄。
克里希那穆提是二十世紀最受敬仰的心靈導師之一。
本書蒐羅了克氏生平最後二十年的十四篇對話。參與討論者包括科學家、佛學家、哲學家、藝術家和天主教耶穌會教士。
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稱得上是克氏的「信徒」,而是前來討教、請益和挑戰的人。這是克氏在有生之年,一直督促他的聽眾和讀者去做的事。
克氏始終熱烈地主張,我們所面臨的一切問題,需要人類意識的徹底轉變才得以解決。他不斷地教誨生命的愛、美與無限價值,使許多人深受啟發。
至今,美國已有百餘所大學院校,在哲學、心理學、宗教、教育等領域研究他的著述。
你可以把克里希那穆提所說的話,解釋成一種無止境地探究人類的狀態。但是所有解釋的價值,不一會兒便煙消雲散。就如克氏所說:「到目前為止,你可以自己探索。」本書提供了這樣的一趟旅程。
商品資料
- 譯者: 繆妙坊
- 出版社: 方智出版 出版日期:1998-02-09 ISBN/ISSN:957679532x
-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西方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