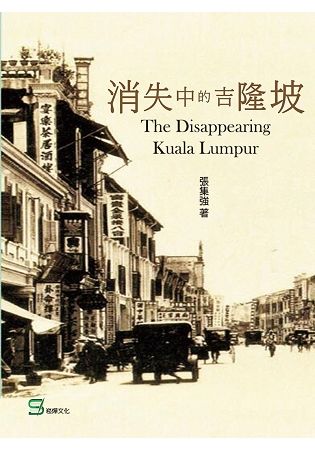在時代的巨輪下,許多老建築就好像摩登林立的大廈之間的一縷幽魂,寄居在城市一隅,任由歲月在身上踐踏出斑駁不堪的痕跡。這些看來破舊、礙眼、再也發揮不了本身最大經濟效益的老建築,也許背後曾有過一段輝煌的過去,也許其建築型式具有獨特的意義,卻無法覓得知音人而面臨了終究要被拋棄淘汰的命運。這看在內行人如集強者的眼裡,不免要連連惋惜,大聲疾呼,不僅透過文章,如為歌梨城、坤成四合院、蔡正木故居……發聲,也坐言起行,透過文章和行動,參與雙溪毛糯痲瘋病院、富都監獄圍牆、蘇丹街……的搶救工作。
本書作者以建築為經、歷史為緯,為這個時代的一座城市銘刻身世傳記,自1980年代至21世紀,當那些可以追索憑藉的實體都已不在,將來的人又要到哪裡去發掘先輩一路走來的痕跡?如果那些先輩遺留下來的文物遺產到最後再也無法傳承下去,後人似乎也只能一廂情願的寄望文字能將那一磚一瓦、一梁一柱、一窗一門的價值給記錄了下來,權供後人憑弔而已。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消失中的吉隆坡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消失中的吉隆坡
內容簡介
目錄
序:用建築說故事的哀悼之書/001
自序:吉隆坡的前世與今生/005
第一輯:前世/011
茨廠街的百年變遷/012
兩朝國都遷徒錄/015
吉隆坡中央市場/019
舊市場廣場/023
重建吉隆坡/027
從牛車路到鐵路/032
雪蘭莪鐵路的開幕慶典/036
蘇丹街火車站/040
吉隆坡第一次自來水供應/043
電力供應時代的來臨/046
十五碑/049
Brickfield/053
新政府大樓開啟吉隆坡新時代/057
從甲必丹管理到市政成形/061
半山芭──吉隆坡重建的推手/065
半山芭路的老建築/068
第二輯:今生/073
消失中的吉隆坡文化/074
老吉隆坡的故事/077
茨廠街不見了茨廠/081
吉隆坡發展的窘境/085
守護老吉隆坡社區的歷史與記憶/088
走進茨廠街的時光隧道/092
茨廠街社區藝術計劃/096
捷運,劫運!/100
為了誰而犧牲?/103
蘇丹街的保存意義/107
關乎全民利益的公共議題/111
文化保存運動及公民社會醒覺/114
獨立遺產大樓 VS 百年遺產老店/117
蘇丹街的危機解除了嗎?/121
聚石能改道/125
永別了,蔡正木故居/128
後蔡正木故居時代來臨/131
陸佑故居/135
不那麽光彩的富都監獄/140
歌梨城/144
《黑眼圈》與吉隆坡/147
半山芭社區文化成形/150
獨立廣場不是集會場所/153
自序:吉隆坡的前世與今生/005
第一輯:前世/011
茨廠街的百年變遷/012
兩朝國都遷徒錄/015
吉隆坡中央市場/019
舊市場廣場/023
重建吉隆坡/027
從牛車路到鐵路/032
雪蘭莪鐵路的開幕慶典/036
蘇丹街火車站/040
吉隆坡第一次自來水供應/043
電力供應時代的來臨/046
十五碑/049
Brickfield/053
新政府大樓開啟吉隆坡新時代/057
從甲必丹管理到市政成形/061
半山芭──吉隆坡重建的推手/065
半山芭路的老建築/068
第二輯:今生/073
消失中的吉隆坡文化/074
老吉隆坡的故事/077
茨廠街不見了茨廠/081
吉隆坡發展的窘境/085
守護老吉隆坡社區的歷史與記憶/088
走進茨廠街的時光隧道/092
茨廠街社區藝術計劃/096
捷運,劫運!/100
為了誰而犧牲?/103
蘇丹街的保存意義/107
關乎全民利益的公共議題/111
文化保存運動及公民社會醒覺/114
獨立遺產大樓 VS 百年遺產老店/117
蘇丹街的危機解除了嗎?/121
聚石能改道/125
永別了,蔡正木故居/128
後蔡正木故居時代來臨/131
陸佑故居/135
不那麽光彩的富都監獄/140
歌梨城/144
《黑眼圈》與吉隆坡/147
半山芭社區文化成形/150
獨立廣場不是集會場所/153
序
序
用建築說故事的哀悼之書
擁有同樣在1980年代成長經歷的同輩應該不難體會,在那個閉塞、匱乏的小鎮,少年慘綠生活的苦悶滋味。我一直想要回顧,我們這一代的人文素養究竟是如何養成的呢?
書店裡賣的是文具、參考書,學校圖書館裡的藏書大部分陳舊過時、八股乏味,除了偶爾巡回至鎮上,在會館、校友會會所舉行的書展,大概就是唯一能夠獲得額外心靈糧食的管道了。
但那也選擇不多,勵志、食譜、命理、歷史、古典或翻譯的經典小說等,往往是翻版的暢銷書,而且也不是常有,一年最多也就那麽兩三次的機會而已,平時就只能到出租言情、武俠、科幻小說,以及漫畫、八卦雜誌的租書攤尋找寄托,聊勝於無。
那時的零用錢也不多,買不起,更捨不得花費去租,只能向朋友同學調借傳閱,《龍虎門》、《天下》漫畫有一期沒一期斷斷續續地看,三毛的散文、余光中和鄭愁予的詩,《椰子屋》、《天蠍星》雜誌,以及港臺流行歌曲的卡帶,都是別人看完、聽過不再聽的二手、三手,有時甚至是七手、八手傳播,也是聊勝於無。
但我不記得這些互通有無的朋輩中有張集強這一號人物。
我和他同樣來自霹靂州的太平後廊新村,先後念過同一所中學、在陳源興老師的畫室學過畫,但我較他癡長三歲,這些共同經驗並不併行在同一條時間軌道上,唯一的交集,就是我媽那時在巴剎賣經濟炒粉,他家好像是經營家庭式理髮生意,印象中,我媽有幾次為參加親朋的喜宴去燙過頭髮,他也許也吃過我媽炒的米粉,如此而已。1994年他赴臺升學,我已大三,淡出大馬留臺生的圈子,平日多與當地臺生廝混,對這位同鄉的學弟並不熟稔。
他2005年回國,彼時我從〈星洲廣場〉編輯調任副刊副主任,又從副刊回巢主編〈星洲廣場〉多年,我們也許曾在什麽聚會上碰過面,但我已不記得。一直到2006年,我負責的刊物需要一個新作者,頂著中原大學建築所碩士頭銜,曾在臺北建築事務所擔任建築設計師、擁有參與古蹟與歷史文物保存實務經驗的他自然成了我的目標,我們的往來才頻繁密切起來。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閱讀興趣集中在與建築有關的題材上,當然並不是十分專業的研究,只是零散隨性的入門涉獵,讀得也不多,大概與自己三分鐘熱度的性格有關,但已足以累積一些心得。這些專業的知識,在林會承的《傳統建築入門手冊》、漢寶德的《透視建築》、《為建築看相》的書寫中一點也不艱澀難懂,反而讀來興味盎然。那時候我就在想:我們是否能夠擁有聚焦於馬來西亞題材的本土書寫?以集強的專才和經驗,其實不難寫出類似知性與感性兼具的文章,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告訴馬來西亞讀者,我們的建築擁有哪些特色?
集強先後在〈星洲廣場〉撰述的兩個專欄取名「街巷語絲」、「漫步五腳基」,就是要通過街巷走道去觀察一個城市的文化景觀,主要的重心還是集中在建築文物上,頗受好評。那時與集強在〈星洲廣場〉上同場的還有寫民俗野趣的李永球「田野行腳」、古城話古的歐陽珊「明日遺書」、掠影檳城的陳耀威「張圖寫意」,也都引起讀者追讀的興趣,這大概與當時大環境的氛圍有些關係: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走來,整個社會在物質上雖已不再匱乏,人們在寬裕之後尚有餘力關心起身邊看似無關緊要的人文事務。但同時人們的內心深處卻彷彿有一道永遠也填補不了的欲望缺口,追求發展的步伐從未鬆懈。建設和破壞,保存和阻滯,永遠是一道相互拉鋸的難題,找不到並存的兩全之道。
在時代的巨輪下,許多老建築就好像摩登林立的大廈之間的一縷幽魂,寄居在城市一隅,任由歲月在身上踐踏出斑駁不堪的痕跡。這些看來破舊、礙眼、再也發揮不了本身最大經濟效益的老建築,也許背後曾有過一段輝煌的過去,也許其建築型式具有獨特的意義,卻無法覓得知音人而面臨了終究要被拋棄淘汰的命運。這看在內行人如集強者的眼裡,不免要連連惋惜,大聲疾呼,不僅通過文章,如為歌梨城、坤成四合院、蔡正木故居……發聲,也坐言起行,通過文章和行動,參與雙溪毛糯痲瘋病院、富都監獄圍牆、蘇丹街……的搶救工作。
如今他把專欄中關於吉隆坡的文章整理成冊,結集成這本《消失中的吉隆坡》,書名正正宣告了那些枉然的努力,始終挽不回一個時代遺留的身影,神傷之餘,亦不無哀悼的意味。那些失去的再也回不來,亦無法複製,不懂的人還是不懂,繼續盲目無知的製造遺憾;而懂得的人無能為力,只能望著手中的一枝禿筆,徒呼負負。
在這本書中,集強以建築為經、歷史為緯,為這個時代的一座城市銘刻身世傳記,那是我們的故事,即使匱乏,畢竟是曾經滋養我們一代人成長的人文空間;從小鎮到都市,自1980年代至21世紀,我們那一代人已屆中年,往事不堪回首,如今我比較想追問的是,我們下一代的人文素養又是如何養成的呢?當那些可以追索憑藉的實體都已不在,將來的人又要到哪裡去發掘我們一路走來的痕跡?如果那些先輩遺留下來的文物遺產到最後再也無法傳承下去,我們似乎也只能一廂情願的寄望文字能將那一磚一瓦、一梁一柱、一窗一門的價值給記錄了下來,權供後人憑弔而已。但說句消極不中聽的話,如果沒有更多人的覺悟,那終究也只是吹皺一池春水罷了。
有趣的是,集強的第一本書叫《英參政時期的吉隆坡》,第二本卻取名為《消失中的吉隆坡》──從莽荒草創的生機勃勃,一下子就來到了毀滅消逝的終結篇章,這中間跳過的一大段環節,時間凍結,無異是對一個有機生命體漠視的最大諷刺。如果將來我們的後輩有怨,今人方知後悔,那也是應得的活該。
但真的會有那麽一天到來嗎?我很懷疑。
黃俊麟
(作者為星洲日報〈星洲廣場〉主編)
用建築說故事的哀悼之書
擁有同樣在1980年代成長經歷的同輩應該不難體會,在那個閉塞、匱乏的小鎮,少年慘綠生活的苦悶滋味。我一直想要回顧,我們這一代的人文素養究竟是如何養成的呢?
書店裡賣的是文具、參考書,學校圖書館裡的藏書大部分陳舊過時、八股乏味,除了偶爾巡回至鎮上,在會館、校友會會所舉行的書展,大概就是唯一能夠獲得額外心靈糧食的管道了。
但那也選擇不多,勵志、食譜、命理、歷史、古典或翻譯的經典小說等,往往是翻版的暢銷書,而且也不是常有,一年最多也就那麽兩三次的機會而已,平時就只能到出租言情、武俠、科幻小說,以及漫畫、八卦雜誌的租書攤尋找寄托,聊勝於無。
那時的零用錢也不多,買不起,更捨不得花費去租,只能向朋友同學調借傳閱,《龍虎門》、《天下》漫畫有一期沒一期斷斷續續地看,三毛的散文、余光中和鄭愁予的詩,《椰子屋》、《天蠍星》雜誌,以及港臺流行歌曲的卡帶,都是別人看完、聽過不再聽的二手、三手,有時甚至是七手、八手傳播,也是聊勝於無。
但我不記得這些互通有無的朋輩中有張集強這一號人物。
我和他同樣來自霹靂州的太平後廊新村,先後念過同一所中學、在陳源興老師的畫室學過畫,但我較他癡長三歲,這些共同經驗並不併行在同一條時間軌道上,唯一的交集,就是我媽那時在巴剎賣經濟炒粉,他家好像是經營家庭式理髮生意,印象中,我媽有幾次為參加親朋的喜宴去燙過頭髮,他也許也吃過我媽炒的米粉,如此而已。1994年他赴臺升學,我已大三,淡出大馬留臺生的圈子,平日多與當地臺生廝混,對這位同鄉的學弟並不熟稔。
他2005年回國,彼時我從〈星洲廣場〉編輯調任副刊副主任,又從副刊回巢主編〈星洲廣場〉多年,我們也許曾在什麽聚會上碰過面,但我已不記得。一直到2006年,我負責的刊物需要一個新作者,頂著中原大學建築所碩士頭銜,曾在臺北建築事務所擔任建築設計師、擁有參與古蹟與歷史文物保存實務經驗的他自然成了我的目標,我們的往來才頻繁密切起來。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閱讀興趣集中在與建築有關的題材上,當然並不是十分專業的研究,只是零散隨性的入門涉獵,讀得也不多,大概與自己三分鐘熱度的性格有關,但已足以累積一些心得。這些專業的知識,在林會承的《傳統建築入門手冊》、漢寶德的《透視建築》、《為建築看相》的書寫中一點也不艱澀難懂,反而讀來興味盎然。那時候我就在想:我們是否能夠擁有聚焦於馬來西亞題材的本土書寫?以集強的專才和經驗,其實不難寫出類似知性與感性兼具的文章,以深入淺出的手法告訴馬來西亞讀者,我們的建築擁有哪些特色?
集強先後在〈星洲廣場〉撰述的兩個專欄取名「街巷語絲」、「漫步五腳基」,就是要通過街巷走道去觀察一個城市的文化景觀,主要的重心還是集中在建築文物上,頗受好評。那時與集強在〈星洲廣場〉上同場的還有寫民俗野趣的李永球「田野行腳」、古城話古的歐陽珊「明日遺書」、掠影檳城的陳耀威「張圖寫意」,也都引起讀者追讀的興趣,這大概與當時大環境的氛圍有些關係: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走來,整個社會在物質上雖已不再匱乏,人們在寬裕之後尚有餘力關心起身邊看似無關緊要的人文事務。但同時人們的內心深處卻彷彿有一道永遠也填補不了的欲望缺口,追求發展的步伐從未鬆懈。建設和破壞,保存和阻滯,永遠是一道相互拉鋸的難題,找不到並存的兩全之道。
在時代的巨輪下,許多老建築就好像摩登林立的大廈之間的一縷幽魂,寄居在城市一隅,任由歲月在身上踐踏出斑駁不堪的痕跡。這些看來破舊、礙眼、再也發揮不了本身最大經濟效益的老建築,也許背後曾有過一段輝煌的過去,也許其建築型式具有獨特的意義,卻無法覓得知音人而面臨了終究要被拋棄淘汰的命運。這看在內行人如集強者的眼裡,不免要連連惋惜,大聲疾呼,不僅通過文章,如為歌梨城、坤成四合院、蔡正木故居……發聲,也坐言起行,通過文章和行動,參與雙溪毛糯痲瘋病院、富都監獄圍牆、蘇丹街……的搶救工作。
如今他把專欄中關於吉隆坡的文章整理成冊,結集成這本《消失中的吉隆坡》,書名正正宣告了那些枉然的努力,始終挽不回一個時代遺留的身影,神傷之餘,亦不無哀悼的意味。那些失去的再也回不來,亦無法複製,不懂的人還是不懂,繼續盲目無知的製造遺憾;而懂得的人無能為力,只能望著手中的一枝禿筆,徒呼負負。
在這本書中,集強以建築為經、歷史為緯,為這個時代的一座城市銘刻身世傳記,那是我們的故事,即使匱乏,畢竟是曾經滋養我們一代人成長的人文空間;從小鎮到都市,自1980年代至21世紀,我們那一代人已屆中年,往事不堪回首,如今我比較想追問的是,我們下一代的人文素養又是如何養成的呢?當那些可以追索憑藉的實體都已不在,將來的人又要到哪裡去發掘我們一路走來的痕跡?如果那些先輩遺留下來的文物遺產到最後再也無法傳承下去,我們似乎也只能一廂情願的寄望文字能將那一磚一瓦、一梁一柱、一窗一門的價值給記錄了下來,權供後人憑弔而已。但說句消極不中聽的話,如果沒有更多人的覺悟,那終究也只是吹皺一池春水罷了。
有趣的是,集強的第一本書叫《英參政時期的吉隆坡》,第二本卻取名為《消失中的吉隆坡》──從莽荒草創的生機勃勃,一下子就來到了毀滅消逝的終結篇章,這中間跳過的一大段環節,時間凍結,無異是對一個有機生命體漠視的最大諷刺。如果將來我們的後輩有怨,今人方知後悔,那也是應得的活該。
但真的會有那麽一天到來嗎?我很懷疑。
黃俊麟
(作者為星洲日報〈星洲廣場〉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