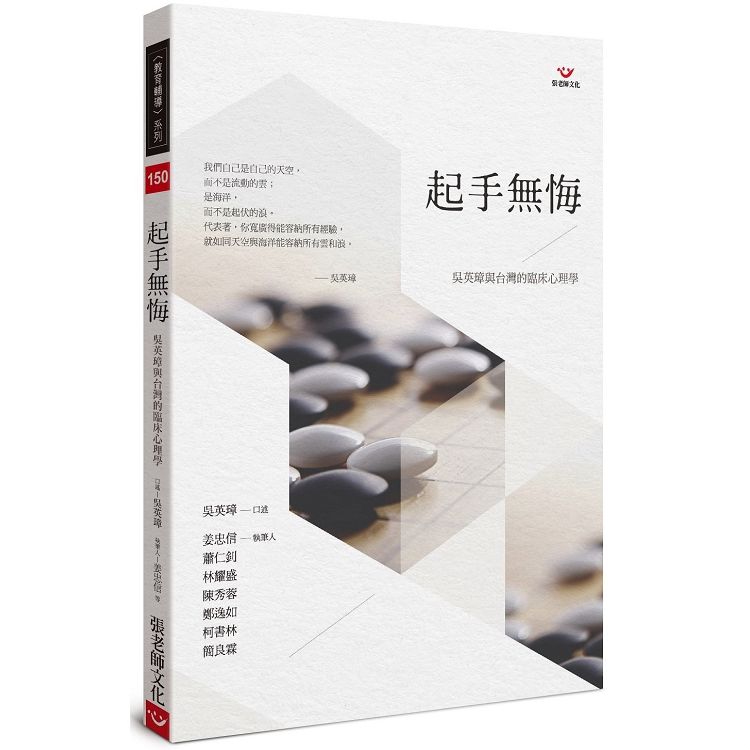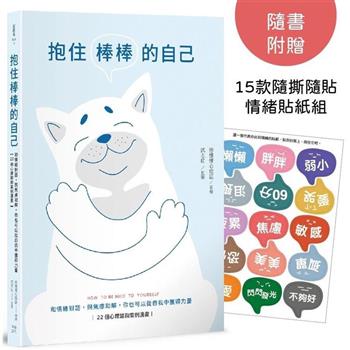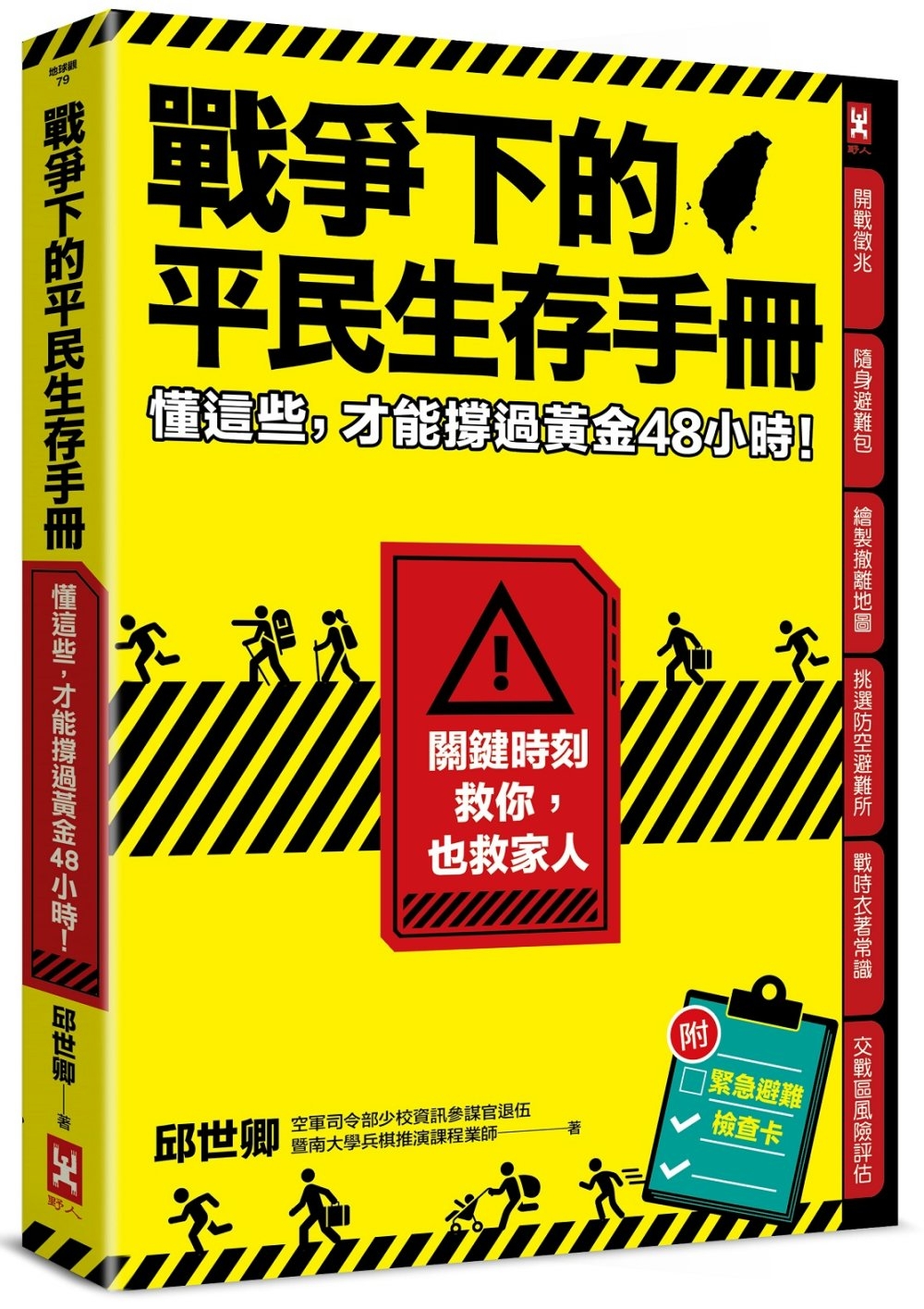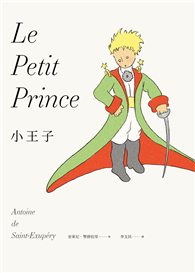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起手無悔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起手無悔
本書由吳英璋口述,姜忠信、蕭仁釗、林耀盛、陳秀蓉、鄭逸如、柯書林、簡良霖等人執筆撰寫,記錄台灣第一代臨床心理學家吳英璋的發展軌跡。內容涵括其投身精神科系統的部分,關於自殺防治、青少年輔導工作與後來在台北市教育局工作的紀錄,九二一震災後的心理復健工作,以及將臨床心理學從精神科走向更大的醫療領域,亦即健康心理學的發展過程。
本書非一般的編年傳記,而是生命經驗的鍛造過程,以吳英璋在重要領域的開創深耕敘事為橫斷面,交叉刻描出其成為一位台灣重要臨床心理學家的學思踐行紀錄。
作者簡介
吳英璋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研究所博士,致力於臨床心理學、健康心理學與心理病理等臨床實務教學與研究。曾任台北市立療養院臨床心理室主任、台大心理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及教授兼系主任。學術團體中,曾擔任中國輔導學會理事、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監事、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台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理事長、中華心理衛生學刊主編、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在台大心理學系任教期間,曾借調出任台北市教育局局長、考試院秘書長。2013年在台大退休,目前為台大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