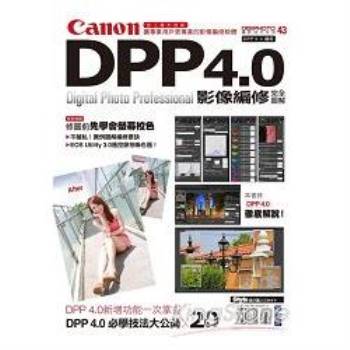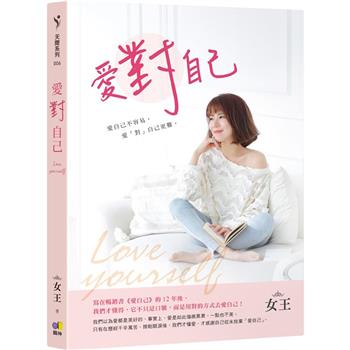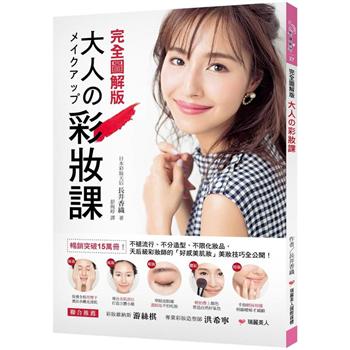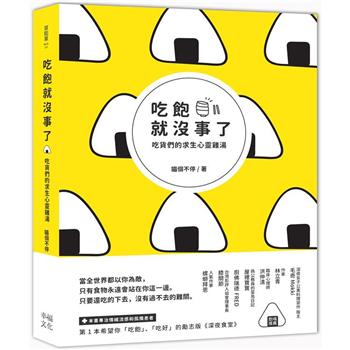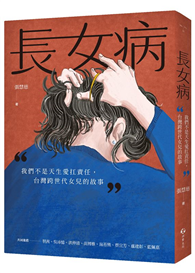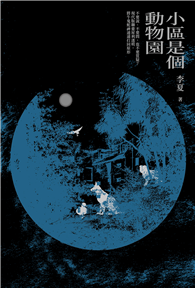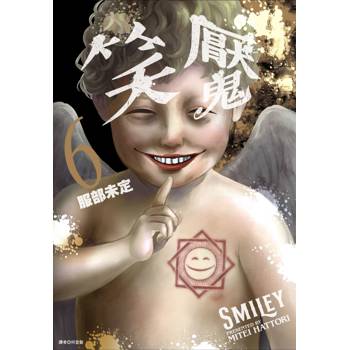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解密自卑情結的圖書 |
 |
解密自卑情結:阿德勒心理治療歷程解析 作者:曾端真 出版社: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3-0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解密自卑情結
從自卑到自在,成為人生的主人。
阿德勒心理學是一門解開心理活動的謎題,照亮心底的暗處,揭開潛意識自卑情結的面紗,並且找到解決方法的心理學。阿德勒心理治療的宗旨在於幫助案主從原本是潛意識衝動的玩物,轉而成為意識和感覺的主人。
曾端真教授(古典阿德勒學派深層治療師)在本書中,累積其二十餘年在阿德勒心理治療上的鑽研經驗,將理論概念、心理治療的邏輯思維、和治療的藝術貫穿起來。作者用理論與實務交織說明的模式,以個案晤談逐字稿,解析作者在治療歷程中的後設思考,不藏私地呈現其在實務工作上的概念和操作歷程,是學習阿德勒心理治療的寶典。對於一般讀者,藉由案例的心路歷程,和作者的解析,看到人性的生命力,也能夠有療癒效果。
作者簡介
曾端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諮商心理師高考及格,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及副校長。
鑽研古典阿德勒學派歷二十餘年,師事Henry Stein(西北華盛頓阿德勒中心主任),為亞洲首位獲得「古典阿德勒學派深層治療師」證照(Certification in Classical Adlerian Depth Psychotherapy, CADP)的心理治療師。迄今仍持續和Stein討論個案。
專長於阿德勒學派心理治療、家庭諮商、親職教育。相關著作有《鼓勵孩子邁向勇氣之路》、《傾聽生命故事與敘說的療癒力》、《教出有勇氣與行動力的孩子》。目前從事教學、督導,以及阿德勒學派心理治療的專業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