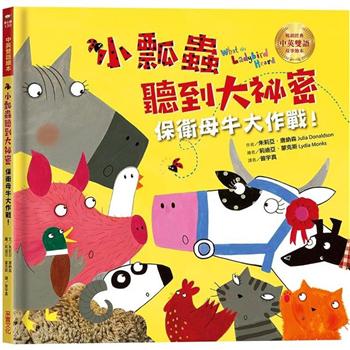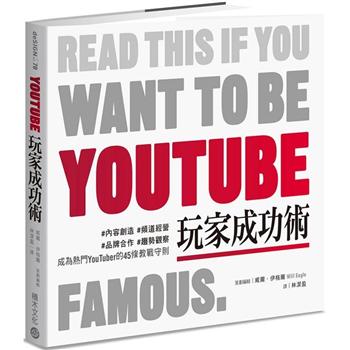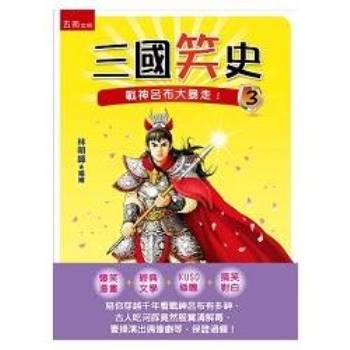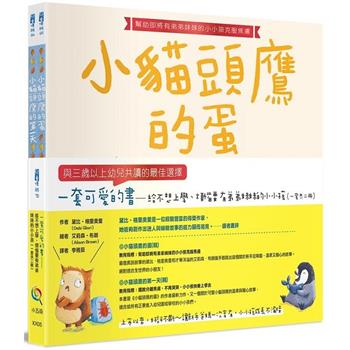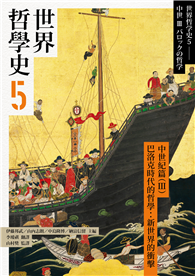運用比較史學的技巧,
對唐與日本的人物交流,以及禮俗、法制施行狀況、變化過程,
有深入的分析探討。
唐日間曾有頻繁的人物與文化交流。本書選定於八、九世紀間為歷史背景,運用比較史學的技巧,對唐與日本的人物交流,以及禮俗、法制施行狀況、變化過程進行分析探討。
上篇透過珍貴史料,探討人物交流後所帶動的文化現象及影響,下篇深入追索唐的法制禮俗文化對日本從皇室到民間造成的影響,說明唐朝先進文化的影響力,以及日本古代國家自主性的特色,藉此了解彼此的文化在歷經時光的洗禮後,如何融合為一,成為後世日本的文化傳統。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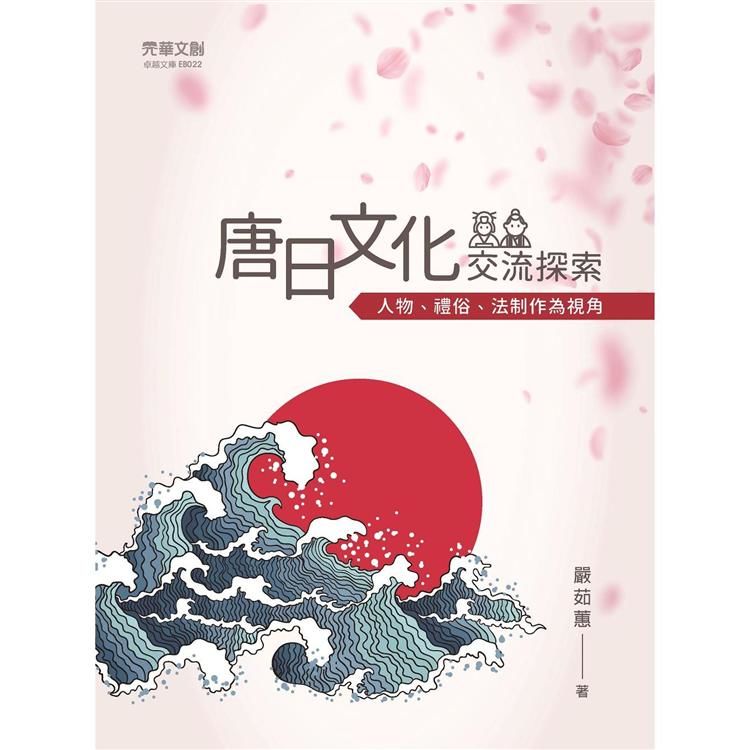 |
唐日文化交流探索: 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 作者:嚴茹蕙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11-0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63 |
文化評論 |
$ 414 |
中國歷史 |
$ 414 |
中文書 |
$ 414 |
文化研究 |
$ 414 |
社會人文 |
$ 414 |
Social Science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嚴茹蕙
學歷
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大學院人間文化創成科學研究科比較歷史學/國際日本學博士後期課程研究留學生
教職
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所)、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苗栗縣立大同高中等校
現任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民商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著作
期刊論文:
〈《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中所見唐人樂郃——兼論九世紀後半渡日唐人於唐日交流中所扮演角色〉 、〈禮俗法制的交融──日本《服忌令》探源兼論與唐令關係〉、〈試論「化外人」與文化認同──以八世紀的渡唐日本人為例〉等篇
專書:《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2018年8月獲科技部專書出版補助)
嚴茹蕙
學歷
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大學院人間文化創成科學研究科比較歷史學/國際日本學博士後期課程研究留學生
教職
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所)、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苗栗縣立大同高中等校
現任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民商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著作
期刊論文:
〈《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中所見唐人樂郃——兼論九世紀後半渡日唐人於唐日交流中所扮演角色〉 、〈禮俗法制的交融──日本《服忌令》探源兼論與唐令關係〉、〈試論「化外人」與文化認同──以八世紀的渡唐日本人為例〉等篇
專書:《唐日令中所見節假生活初探》(2018年8月獲科技部專書出版補助)
目錄
宋德熹教授序
古瀨奈津子教授序
緒論
一、問題意識的提出
二、研究史介紹與述評
三、研究課題、章節架構與研究方法
上篇 唐日人物交流
第一章試論「化外人」與文化攝取── 以八、九世紀的代表性渡唐日人為例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化外人範圍
第三節「化外人」文化攝取舉隅─以、八九世紀日本為例
第四節小結
第二章 《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徃反傳記》中所見唐人樂郃 ──兼論九世紀後半渡日唐人於唐日交流中所扮演角色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慈覺大師入唐徃反傳記》諸版本簡介
第三節 從圓仁、樂郃事例探討唐人赴日的境遇
第四節樂郃的《慈覺大師入唐徃返傳記》史料價值 ─兼論渡日唐人在文化交流中所扮角色
第五節小結
附錄:1813年真超抄本錄文
下篇 唐代禮令對日本的影響
第三章唐日喪禮的異同──以挽歌、遊部為例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日本喪服制度與唐代禮令
第三節橫跨俗禮法之間的唐代挽歌
第四節日本令的抉擇
第五節小結
第四章清和天皇為祖母服喪禮儀── 唐《喪葬令》對日本的影響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日本古代史中呈現的法制禮俗問題── 以清和天皇為太皇太后服喪問題為線索
第三節小結
第五章禮俗法制的交融── 日本《服忌令》探源兼論與唐令關係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 喪服制與忌、穢、假
第三節服忌與給假天數的結合── 以《養老.假寧令》「職事官遭父母喪解官」條為線索
第四節小結
結 論
引用書目
後 記
古瀨奈津子教授序
緒論
一、問題意識的提出
二、研究史介紹與述評
三、研究課題、章節架構與研究方法
上篇 唐日人物交流
第一章試論「化外人」與文化攝取── 以八、九世紀的代表性渡唐日人為例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化外人範圍
第三節「化外人」文化攝取舉隅─以、八九世紀日本為例
第四節小結
第二章 《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徃反傳記》中所見唐人樂郃 ──兼論九世紀後半渡日唐人於唐日交流中所扮演角色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慈覺大師入唐徃反傳記》諸版本簡介
第三節 從圓仁、樂郃事例探討唐人赴日的境遇
第四節樂郃的《慈覺大師入唐徃返傳記》史料價值 ─兼論渡日唐人在文化交流中所扮角色
第五節小結
附錄:1813年真超抄本錄文
下篇 唐代禮令對日本的影響
第三章唐日喪禮的異同──以挽歌、遊部為例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日本喪服制度與唐代禮令
第三節橫跨俗禮法之間的唐代挽歌
第四節日本令的抉擇
第五節小結
第四章清和天皇為祖母服喪禮儀── 唐《喪葬令》對日本的影響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日本古代史中呈現的法制禮俗問題── 以清和天皇為太皇太后服喪問題為線索
第三節小結
第五章禮俗法制的交融── 日本《服忌令》探源兼論與唐令關係
第一節前言
第二節 喪服制與忌、穢、假
第三節服忌與給假天數的結合── 以《養老.假寧令》「職事官遭父母喪解官」條為線索
第四節小結
結 論
引用書目
後 記
序
古瀨 奈津子教授序
為了締結唐和日本的關係,日本於舒明二年(630)派遣犬上御田鍬為遣唐使入唐,直至菅原道真於寬平六年(894)被任命為遣唐大使,基於唐國混亂等理由,建議停派遣唐使為止,其間約二百六十年,日本派遣遣唐使赴唐。舒明年間的遣唐使在舒明四年(632)歸國,當時唐的送使高表仁來到日本。唐的使節來到日本非常罕見,一般認為,唐和日本的關係,建立在日本對唐朝朝貢之上。於此同時,留學於隋的僧旻也一起返日。
遣唐使派遣次數約二十次(因研究者觀點不同,次數有異),七世紀的遣唐使,因為是與朝鮮半島上的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爭奪霸權的時期,主要目的為解決外交問題,派遣的使節約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分乘二船,沿朝鮮半島的西海岸,也就是所謂北路前往中國。另一方面,八世紀以後的遣唐使,常被譽為文化使節,由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分乘四船,從博多經五島列島,橫越東中國海,直接抵達長江沿岸地區,取南路派遣中國。
如此,日本遣唐使因時期而目的稍有不同,七世紀的遣唐使不僅是為了外交問題而被派遣至中國,也為了要帶回唐先進的法律、制度、文化、技術做為範本,使日本能夠形成律令國家。
嚴茹蕙小姐的作品《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主要是基於八、九世紀唐日文化交流的背景,闡明人物、禮俗、法制的層面。在上篇,嚴小姐取人物為主體,首先對渡唐的日本人:粟田真人及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普照等為鑑真赴日盡力的僧侶們、最澄及空海、橘逸勢這些於平安時代初期延曆年間的遣唐使一同赴唐的僧侶們,以及圓仁、圓珍、圓載這些與最後的遣唐使一起渡唐的僧侶們,是如何渡唐、在唐學習什麼,逐一進行檢討。
接著,嚴小姐注意到以往不太為人所知的日本史料《慈覺大師入唐往反傳記》,前往叡山文庫進行史料調查,對寫本進行檢討,並對從該史料中出現的渡日唐人樂郃,進行了令人興味盎然的考察。
在下篇,嚴小姐檢討了唐的禮令對日本的影響。首先運用新史料天聖令和日本令的喪葬令,對唐宋和日本的喪葬禮儀,取挽歌和遊部進行比較檢討,取得了令人興味盎然的研究成果。此即澄清了日本喪葬禮儀在以唐為模範的過程中,並未完全模倣唐朝,而是有其獨自性。
再者,嚴小姐以九世紀日本清和天皇為祖母服喪禮儀對《日本三代實錄》的內容進行檢討,對律令制展開期吸收唐禮的經過進行考查。關於此時期日本如何受容唐禮的研究罕見而貴重。
另外,選擇了禮與令的交點──服忌令,溯源其與唐的關係。
如以上,嚴小姐本來是中國史的專家,本書的研究方法,特色是透過唐日文化交流的過程,探尋日本史中的特徵,但是採用這樣的研究方法,卻也可說反過來映射出了唐的特徵。
嚴茹蕙小姐於台灣大學畢業後,在研究機構中擔任行政工作,在高明士教授身邊協助舉行國際研討會等事務,我就是在當時與嚴小姐初識。其後嚴小姐進入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就讀,繼續進行研究。至她通過博士課程的資格考後,得到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單位補助,於2013年4月至2014年10月期間,以研究留學生身分,在御茶水女子大學大學院的博士後期課程進行研究。研究課題是「八、九世紀入唐日本人所見唐朝法制禮俗研究──兼論對日本的影響」。嚴小姐在日本,繼續研究中國史的同時,也同時收集日本史史料,密集學習日本史。她獨自一人前往叡山文庫調查史料,並且至出雲參加木簡學會研究集會等活動,對於她在學問上的行動力,本人至為感佩。此外其研究成果在國際研討會及日本的研究會上發表,我認為對於研究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經驗。嚴小姐回到台灣後,以留學時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再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完成本書。
嚴小姐留學日本時,採用中國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發現的新出史料──北宋天聖令抄本,以及嚴小姐自己注意到的罕見史料《慈覺大師入唐往返傳記》等史料進行研究,能夠置身於可以使用這些史料的環境,堪稱幸運。要深入進行唐日關係史及比較歷史的研究,唐日雙方的史料都能閱讀是必要的。我認為嚴小姐確實是適合進行唐日關係史及比較歷史的研究者。本書今後當可以成為這個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而長久流傳。
古瀬 奈津子
2019.07.18
為了締結唐和日本的關係,日本於舒明二年(630)派遣犬上御田鍬為遣唐使入唐,直至菅原道真於寬平六年(894)被任命為遣唐大使,基於唐國混亂等理由,建議停派遣唐使為止,其間約二百六十年,日本派遣遣唐使赴唐。舒明年間的遣唐使在舒明四年(632)歸國,當時唐的送使高表仁來到日本。唐的使節來到日本非常罕見,一般認為,唐和日本的關係,建立在日本對唐朝朝貢之上。於此同時,留學於隋的僧旻也一起返日。
遣唐使派遣次數約二十次(因研究者觀點不同,次數有異),七世紀的遣唐使,因為是與朝鮮半島上的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爭奪霸權的時期,主要目的為解決外交問題,派遣的使節約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分乘二船,沿朝鮮半島的西海岸,也就是所謂北路前往中國。另一方面,八世紀以後的遣唐使,常被譽為文化使節,由一百至一百二十人分乘四船,從博多經五島列島,橫越東中國海,直接抵達長江沿岸地區,取南路派遣中國。
如此,日本遣唐使因時期而目的稍有不同,七世紀的遣唐使不僅是為了外交問題而被派遣至中國,也為了要帶回唐先進的法律、制度、文化、技術做為範本,使日本能夠形成律令國家。
嚴茹蕙小姐的作品《唐日文化交流探索─人物、禮俗、法制作為視角》,主要是基於八、九世紀唐日文化交流的背景,闡明人物、禮俗、法制的層面。在上篇,嚴小姐取人物為主體,首先對渡唐的日本人:粟田真人及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普照等為鑑真赴日盡力的僧侶們、最澄及空海、橘逸勢這些於平安時代初期延曆年間的遣唐使一同赴唐的僧侶們,以及圓仁、圓珍、圓載這些與最後的遣唐使一起渡唐的僧侶們,是如何渡唐、在唐學習什麼,逐一進行檢討。
接著,嚴小姐注意到以往不太為人所知的日本史料《慈覺大師入唐往反傳記》,前往叡山文庫進行史料調查,對寫本進行檢討,並對從該史料中出現的渡日唐人樂郃,進行了令人興味盎然的考察。
在下篇,嚴小姐檢討了唐的禮令對日本的影響。首先運用新史料天聖令和日本令的喪葬令,對唐宋和日本的喪葬禮儀,取挽歌和遊部進行比較檢討,取得了令人興味盎然的研究成果。此即澄清了日本喪葬禮儀在以唐為模範的過程中,並未完全模倣唐朝,而是有其獨自性。
再者,嚴小姐以九世紀日本清和天皇為祖母服喪禮儀對《日本三代實錄》的內容進行檢討,對律令制展開期吸收唐禮的經過進行考查。關於此時期日本如何受容唐禮的研究罕見而貴重。
另外,選擇了禮與令的交點──服忌令,溯源其與唐的關係。
如以上,嚴小姐本來是中國史的專家,本書的研究方法,特色是透過唐日文化交流的過程,探尋日本史中的特徵,但是採用這樣的研究方法,卻也可說反過來映射出了唐的特徵。
嚴茹蕙小姐於台灣大學畢業後,在研究機構中擔任行政工作,在高明士教授身邊協助舉行國際研討會等事務,我就是在當時與嚴小姐初識。其後嚴小姐進入國立中興大學研究所就讀,繼續進行研究。至她通過博士課程的資格考後,得到台灣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單位補助,於2013年4月至2014年10月期間,以研究留學生身分,在御茶水女子大學大學院的博士後期課程進行研究。研究課題是「八、九世紀入唐日本人所見唐朝法制禮俗研究──兼論對日本的影響」。嚴小姐在日本,繼續研究中國史的同時,也同時收集日本史史料,密集學習日本史。她獨自一人前往叡山文庫調查史料,並且至出雲參加木簡學會研究集會等活動,對於她在學問上的行動力,本人至為感佩。此外其研究成果在國際研討會及日本的研究會上發表,我認為對於研究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經驗。嚴小姐回到台灣後,以留學時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再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完成本書。
嚴小姐留學日本時,採用中國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發現的新出史料──北宋天聖令抄本,以及嚴小姐自己注意到的罕見史料《慈覺大師入唐往返傳記》等史料進行研究,能夠置身於可以使用這些史料的環境,堪稱幸運。要深入進行唐日關係史及比較歷史的研究,唐日雙方的史料都能閱讀是必要的。我認為嚴小姐確實是適合進行唐日關係史及比較歷史的研究者。本書今後當可以成為這個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而長久流傳。
古瀬 奈津子
2019.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