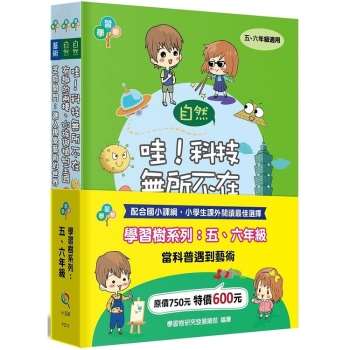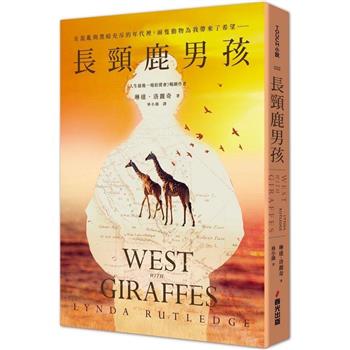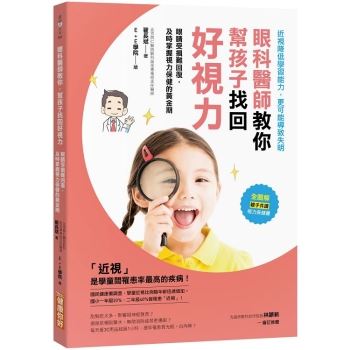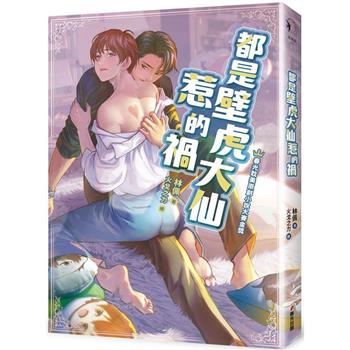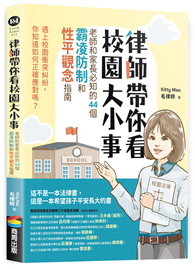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三尺春秋:法史述繹集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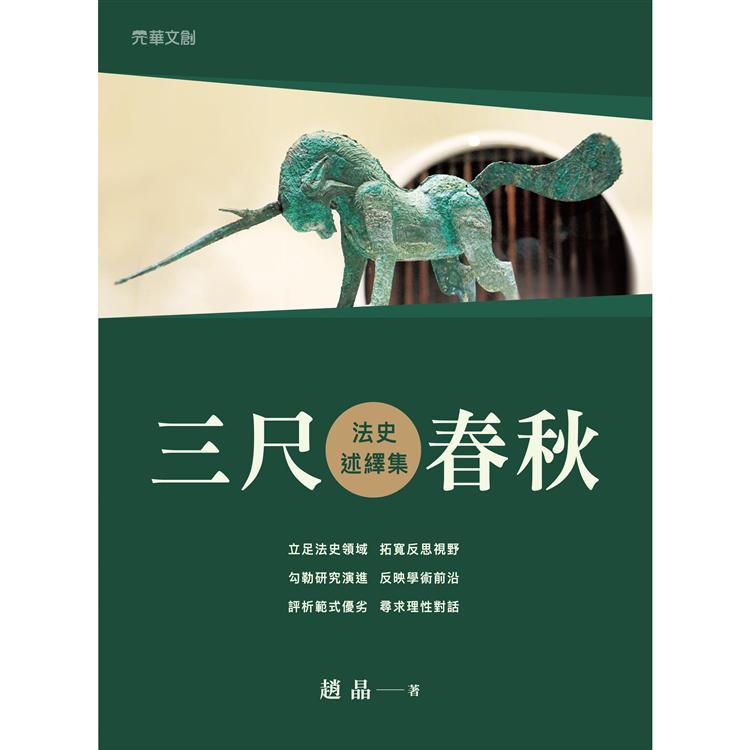 |
三尺春秋:法史述繹集【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趙晶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1-11 規格:382頁/23*17cm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68 |
法學總論 |
$ 468 |
歷史 |
$ 468 |
中文書 |
$ 468 |
軍事 |
$ 468 |
社會人文 |
$ 468 |
歷史 |
$ 468 |
Others |
電子書 |
$ 520 |
人文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三尺春秋:法史述繹集
本書以「法律史」為論域,以學術評論為體裁,除「序言」、「附錄」外,收錄二十篇文章,共分三編。
第一編「學術史述評」立足文獻(敦煌吐魯番法律文獻、《天聖令》、《至正條格》)、方法(歷史書寫、古文書學)與特定主題(公司形態),搜羅海內外相關研究業績,呈現研究演進,評析個中得失;第二編「學術書評」擇定七本專書,廣涉刑罰、法源、司法官群體、訴訟社會、法律知識傳播、區域社會等領域,呈現最新動態,積極尋求學術對話;第三編「讀書心得」以四本著作為楔子,延伸討論法史教科書編纂、教學課程設計、近代中日學者交流、法學經典重刊等話題,借鑒域外經驗,思考教學與研究的改進之策。
本書特色
立足法史領域,拓寬反思視野,
勾勒研究演進,反映學術前沿,
評析範式優劣,尋求理性對話。
作者簡介
趙晶
【學歷】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學士、法學碩士、法學博士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
【教職】
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講師,現任該研究所副教授
【訪學經歷】
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客座副教授、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系暨東亞研究所洪堡學者
【著作】
期刊論文
〈唐令復原所據史料檢證——以令式分辨為線索〉、〈唐令復原における典拠史料の検証——《大唐開元禮》を中心に〉、 〈文書運作視角下的「東坡烏台詩案」再探〉、〈宋太宗的法律事功與法制困境——從《宋史‧刑法志》說起〉等
專書論著
《〈天聖令〉與唐宋法制考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