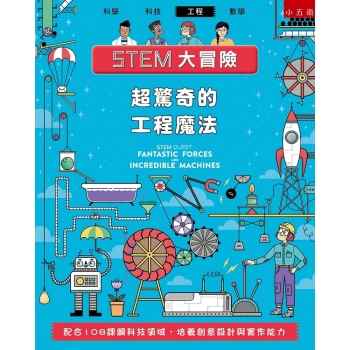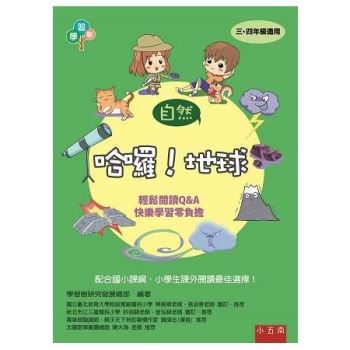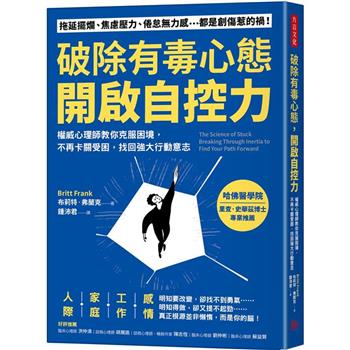推薦序:漫漫歷史長夜中的守更人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陳建忠
一、大河小說的命名與研究
眾所皆知,錢鴻鈞教授是鍾肇政文學史料最忠誠的守護人。十多年來,除了整理百萬字的書信,他更鉅細靡遺地討論鍾老作品,眼下這本三十多萬字的論文集,實在非有心人無以致此。
雖然我個人也長期提倡臺灣歷史小說的研究,並且自十年前就開設臺灣長篇歷史小說的課程,談過不少次鍾老的作品,但對於這樣重量級的文學巨人,實在沒有留下深入的考察成果。相對於此,鴻鈞兄則慧眼獨具並堅持至今,成果豐碩,實在讓我汗顏。因此,對於他一路以來所意欲開拓的研究領域,我不僅是見證人之一,也是積極追隨的研究同好,眼見他能夠提出這樣夠份量的研究專著,更感臺灣歷史小說研究的主張勢有可為。
如果從研究史的立場上來看,既有的歷史小說研究顯示,臺灣學界並未將不同次類型的歷史小說視為一個有意義的敘事傳統,而是分論個別的作家與作品,彼此互不交涉。然而無論是以臺灣史與中國史為題材,在臺灣所出現的這些歷史小說都是臺灣歷史的實然現象,為求整體思考臺灣歷史小說發展的特殊性與獨特性,實有必要刷新對臺灣歷史小說的認識視野,並尋求更符合臺灣主體脈絡的分析方法。
依個人淺見,若依據題材與美學變革的差異,兼及歷時性歷史小說發展的階段性變化,目前可以理出四種主要的臺灣歷史小說類型,至少包括:
其一是傳統歷史小說:常被歸於大眾或通俗小說類型。此類小說乃受中國史傳傳統影響,以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為主角或主題之小說,強調歷史考證與傳奇性格,如高陽《胡雪巖》、孟瑤《風雲傳》等的歷史小說屬之。
其二是反共歷史小說:「部分」反共小說亦反映國共鬥爭的歷史經驗,以特定史實為背景,重點在揭示江山易幟的根源導因於萬惡共黨,從而描述赤禍綿延的場景,以及暗示來日重新復國的可能,如陳紀瀅《華夏八年》、姜貴《旋風》等的歷史小說屬之。
其三是後殖民歷史小說:習稱大河(歷史)小說。作品重點在於恢復被殖民者的我族歷史,特別著重在日本殖民史、國民黨戒嚴史、二二八史、白色恐怖史的重述。歷經多次殖民的臺灣社會,嚴重缺乏具主體性的歷史記憶,後殖民歷史小說正是以抵拒歷史消音、重建歷史記憶的角度出發的創作,如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等的大河歷史小說屬之。後繼者如莊華堂等,則又將大河小說推進到平埔族活躍的時代,成果可期。
其四是新歷史小說:受新歷史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之歷史觀的影響,改以小歷史為重點,解構主流、權威敘事的傾向明顯,意識形態立場多元紛陳。其中至少有李昂、施叔青、平路為代表的女性新歷史小說;有如張大春、林燿德、朱天心為代表的戰後新移民第二代新歷史小說;有如王家祥、詹明儒為代表的漢人書寫之原住民族新歷史小說。因其尚在發展中,次類型將隨之增加、變動,有待持續觀察、描述。
這四類臺灣歷史小說,彼此有著或隱或顯的歷史因緣,但各自想處理的歷史問題敘事手法又多所不同。我想,必須在理解各種次類型歷史小說的敘事傳統情況下,才能找到適切的研究方法,這與認識論的釐清其實又互為辯證。
鍾老的大河小說,寫的是殖民地問題,寫在殖民地之後,寫於不得回憶殖民歷史的戒嚴時代,這自然是臺灣後殖民歷史小說的當然代表。甚且,此後殖民文本的解殖工程尚不只針對前一個殖民主義,還「意在言外」地針對了如同內部殖民體制一般的戒嚴體制。這類小說在出版之時,絲毫不受重視,反而是中國史的歷史小說大行其道,其間怎能不存在著一種政治體制與教育體制下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如此一來,臺灣歷史小說研究當然需要以更全盤性的眼光出之不可,鍾老的小說更不妨和傳統與反共歷史小說並列而論。
既然鴻鈞兄的工作如此重要,筆者深感佩服之餘,綜觀全書更覺得他所提出來的看法有三大重點,值得有志於此的研究者多加參詳、對話。
二、《鍾肇政大河小說論》的三大重點
重點之一,書中主張鍾老的歷史小說並非以寫實主義為創作觀,而是秉持著浪漫主義歷史觀。
此一觀點,可以解釋鍾老小說主角為何並非取材自特定歷史人物,卻始終充滿著對族群與土地之愛,發揚了臺灣人精神,與帶有國族建構意識的浪漫主義史觀不謀而合。此說可以與既有的寫實主義美學詮釋觀點相互辯證,具有啟發性。書中說到:「如以浪漫史觀中追求歷史進步、民族精神之思想,而歷史動力為精神、人類追求光明的理想與意志來看,鍾肇政的思想,所表現在《歌德激情書》與歷史小說中是一致的。並且也皆以愛情作為更廣大的土地之愛、生命之愛的象徵。換言之,對土地之愛、對人類之愛也正是鍾肇政筆下主角以知識份子視點下個人前進的動力,同樣也是歷史前進的動力」。
文中論證鍾肇政為浪漫主義歷史觀,從其歷史小說乃源自於史詩的文類說起。作品表現皆是英雄人物的歌頌,發而為民族精神的象徵。鍾老選擇的歷史題材都是以反抗不公不義的壓迫行動為基礎,而以風俗民情描寫為輔,眾多勞苦人民跟隨著知識份子的領袖,群起合作團結。而知識份子也懷著向土地、農民學習之心,成長向上,自我磨練。
重點之二,鍾肇政文學在接續文學傳統方面,無疑是連接了日治及戰後的兩個世代,而成為跨語世代的代表人物。本書針對他的大河小說進行研究,實在也是在解釋戰前與戰後文學史的轉折與發展,可以補足目前研究成果上較貧乏的跨語世代研究。
此一世代,歷經皇民化運動與白色恐怖,為了避禍,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話語型態,必須仔細解讀。書中強調:「本書首先是採用的是細讀法,從文本內的象徵、隱喻著手。但是新批評下的閱讀方法是絕對不夠的,所以至此,是說明本書是以作品論為主。而特別要從一些隱微、扭曲、空白的對話與情節的注意,指出作者沒有說明或者隱晦、衝突的部份,甚至顯示作者潛意識的部份,這其實就是一種癥狀閱讀法」。
書中強調,此研究試圖補充對臺灣文學創作發展史的瞭解,諸如解釋鍾肇政與吳濁流、鍾理和之間創作影響的關係。並認為《濁流三部曲》之第三部《流雲》,與他在解嚴後的作品《怒濤》,有相互呼應與連結。《怒濤》又可以說是了解鍾肇政作品在政治意識、臺灣認同表現的入門書。本書討論的作品以《流雲》開始,作為在鍾肇政在解嚴前創作作品的入門書,不僅在意識上、藝術上,特別在結構上,都含有重大意義。《濁流三部曲》裡每一階段的愛情,象徵了民族認同的潛意識心理。愛情與國家認同有隱喻關係,這不僅是佛洛伊德心理學的中個人情慾問題與人格分析,本書更認為是表現了民族的集體意識;另一方面,民族潛意識的作用下,也會倒過來影響到理想愛情的選擇。
重點之三,本書重新塑造「日本精神」的特殊意義與臺灣作家的精神史。
對於經歷過殖民統治的世代而言,談「日本精神」實在是相當沈重的包袱。書中不僅不迴避此問題,相反地,認為「日本精神」帶給鍾老此世代知識分子,一種生命與生活的積極態度,這並非是親日,套句「詭辯」一點的說法,這乃是「知日」。鍾肇政對莊永明的《臺灣百人傳》評說:「好一個臺灣人民的史觀,這不就是說,老友除了擴大眼界之外,還把觸覺深入臺灣人的靈魂深處,予以詮釋、發揚,臺灣人的精神隨之隱約浮現!這該是一項大工程吧。」書中認為:「其實這也正是鍾肇政對自己的生命主題這麼說的。鍾肇政的史觀,也就是臺灣人民的靈魂的史觀,也就是建立臺灣人的精神史」。
例如《滄溟行》與法理抗爭一章中,是戒嚴環境所產生的文學表現。本章由臺灣人精神的源流之一的日本精神,觀察書中主人翁陸志驤的教育背景、性格、活動。以正面的態度理解日本精神,去感受作者所刻劃的追求光明的時代主題與戰鬥不撓的臺灣人形像。本書尚有附錄兩篇,分別是討論《怒濤》與《戰火》,在鍾肇政的浪漫主義歷史觀下,牽涉到日本精神與高砂精神之間的辯證關係。關於「臺灣魂」的問題,鍾肇政如何轉化日本精神是本書的一個重點。
不過,在皇民化運動下所吸收的日本精神,考其源流,日帝所為臺人設定的積極精神,並非用之於解殖,而只是片面的提倡獻身與勇敢精神。甚且,所謂勇敢與積極的生命態度,亦非日本人所獨有,則如何在我族傳統與日本影響之間適當地描述、評價,對於鍾老及其同時代作家的精神史,似乎也還存有不少探討空間。
三、等待黎明:將鍾肇政文學發揚光大的意義
葉石濤於1966年針對鍾肇政的小說,第一次提出「大河小說」一詞來談論臺灣作家的作品。葉老公開提出「大河小說」一詞,乃是在評論《流雲》的時候。〈鍾肇政論:流雲,流雲,你流向何處?〉一文裡,這樣寫到:「凡是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其小說的觀點」。
兩年後,刊載過程幾經波折的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首部小說《沈淪》出版,葉老即時做出評論。他在〈鍾肇政和他的《沈淪》〉中強調:「這種不以特定的個人境遇來剖析時代、社會的遞嬗,而藉一個家族發展的歷史和群體生活來透視,印證時代、社會動向的小說手法,在許多結構雄偉的大河小說(Roman-fleuve)是必然的手法」。
最終,鍾老陸續完成了多部長篇歷史小說,開創了臺灣大河小說的敘事傳統,葉老評論的促進之功實在不容或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葉老之所以期待於鍾老的文學志業,同時也是針對他自己所提出來的期許。試看一段葉老在窮困無法寫作的時代裡寫信給鍾老的話,在1966年1月4日的信裡,葉老說到:
肇政兄:謝謝您的來信。我一生的經歷有如下述,…民國四十年夏末曾坐過監,過了三年暗無天日的生活。目前進入臺南師範就學,沒有收入。家中有妻子及兩名男孩,前途可說是一片黑暗。最大的嗜好是煙與酒,女人也是我的所愛,但僅限於欣賞而已。一生最大的願望也跟先生一樣,就是做文學的鬼(駕馭者)。如果要再補充一點的話,就是我已抱定決心,不惜犧牲一切,為臺灣人確立臺灣文學的基礎。
葉老後來完成《臺灣文學史綱》,證明臺灣文學被她的群眾所忽略的命運,而必須繼續置身在詮釋權爭奪的潮流裡。這樣一個視文學為志業的作家,與這樣為他所相信的歷史作見證的一部書,似乎更能啟發我們作為「人」,或「臺灣人」必須為自己發聲的思考。葉老無非是試圖證明:臺灣有文學,臺灣文學有她自己的自主性格;最終,臺灣文學的歷史必須由臺灣人自己來訴說。
鍾老與葉老的文學志業,其實尚有很多未竟之處,也有更多需要後輩闡釋的地方。因此之故,默默研究鍾肇政大河小說的鴻鈞兄,極像是知識社會學創始人曼海姆在形容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時所說的:「在人間漫漫黑夜中擔當守更人的角色」。他的工作如同在漫漫臺灣歷史長夜裡的守更人,默默為我們留下希望的火種。很多基礎工作,必須有人接棒去做,尤其在黎明之前,更要能夠捱得住寂寞。鴻鈞兄的研究成果,已有豐碩果實,但我相信他還會繼續耕耘下去,因為任重道遠,他所要發揚的鍾肇政文學,仍有待他繼續堅持到底,相信有朝一日,定能讓屬於一代人的寂寞與榮耀都迎向燦爛朝陽,為世人所傳誦、思索。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鍾肇政大河小說論(第一冊)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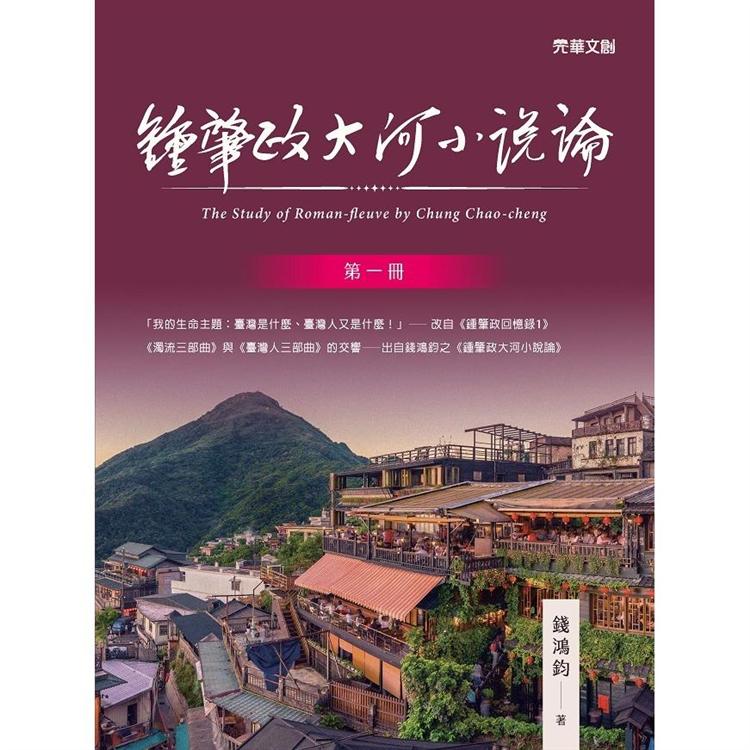 |
鍾肇政大河小說論(第一冊)【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錢鴻鈞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4-15 規格:260頁/23*17cm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60 |
華文文學研究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華文文學研究 |
$ 360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60 |
文學作品 |
$ 360 |
Book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鍾肇政大河小說論(第一冊)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作者提出顛覆性觀點,對鍾肇政的兩部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臺灣人三部曲》提出新看法。從對鍾肇政的訪談、書信、手稿、演講等記錄,提出歷史證明。鍾肇政的寫作初衷,就是要寫出臺灣人的民族史詩、臺灣人是英雄,鍾肇政以小說手法,寫出了臺灣人的精神史。
本書作者針對鍾肇政最重要的六部小說,一一提出新看法,並給予結構上綜合性的詮釋。兩部大河小說互相比美,堪稱一套臺灣人靈魂的交響曲。
商品特色
「我的生命主題:臺灣是什麼、臺灣人又是什麼!」—— 改自《鍾肇政回憶錄1》
《濁流三部曲》與《臺灣人三部曲》的交響—— 出自錢鴻鈞之《鍾肇政大河小說論》
解讀鍾肇政大河小說的最佳論著。
作者簡介:
錢鴻鈞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學士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博士
[經歷]
現任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曾任虎尾科技大學普通物理教師、工研院電子所工程師
[著作]
《大河悠悠:漫談鍾肇政的大河小說》、《錢鴻鈞激情書》、《天堂與地獄:武陵高中成長記》,編有《臺灣文學兩鍾書》、《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並與莊紫蓉合力編纂《鍾肇政全集》三十八冊。
[重要事蹟]
道卡斯族竹塹社人,父親說的是竹東海陸腔客家話、母親說苗栗四縣腔客家話。盼望以書寫回歸祖先的故鄉,與原住民族人的臺灣魂在一起,為地方留下見證。預備出版《從客家人回轉竹塹社(上)、(下)》,並希望能再度與錢寶騎腳踏車環島。
推薦序
推薦序:漫漫歷史長夜中的守更人 /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陳建忠
一、大河小說的命名與研究
眾所皆知,錢鴻鈞教授是鍾肇政文學史料最忠誠的守護人。十多年來,除了整理百萬字的書信,他更鉅細靡遺地討論鍾老作品,眼下這本三十多萬字的論文集,實在非有心人無以致此。
雖然我個人也長期提倡臺灣歷史小說的研究,並且自十年前就開設臺灣長篇歷史小說的課程,談過不少次鍾老的作品,但對於這樣重量級的文學巨人,實在沒有留下深入的考察成果。相對於此,鴻鈞兄則慧眼獨具並堅持至今,成果豐碩,實在讓我汗顏。因此,對...
一、大河小說的命名與研究
眾所皆知,錢鴻鈞教授是鍾肇政文學史料最忠誠的守護人。十多年來,除了整理百萬字的書信,他更鉅細靡遺地討論鍾老作品,眼下這本三十多萬字的論文集,實在非有心人無以致此。
雖然我個人也長期提倡臺灣歷史小說的研究,並且自十年前就開設臺灣長篇歷史小說的課程,談過不少次鍾老的作品,但對於這樣重量級的文學巨人,實在沒有留下深入的考察成果。相對於此,鴻鈞兄則慧眼獨具並堅持至今,成果豐碩,實在讓我汗顏。因此,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漫漫歷史長夜中的守更人
第一部份 綜論
第一章 鍾肇政大河小說緒論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大河小說的辯證
第三節 傳承與定位
第四節 鍾肇政大河小說的獨特性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六節 前人文獻探討
第七節 篇章介紹
第二章 臺灣大河小說的起點
第一節 前言
一、研究緣起
二、前人研究
第二節 《大武山之歌》與《臺灣人三部曲》創作緣起
一、基本史料比對的差異
二、《大武山之歌》的計畫內容
三、臺灣大河小說的特色
第三節 《濁流三部曲》的發表歷程與大河小說的地位
一、《濁流三部曲》的創...
第一部份 綜論
第一章 鍾肇政大河小說緒論
第一節 前言
第二節 大河小說的辯證
第三節 傳承與定位
第四節 鍾肇政大河小說的獨特性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六節 前人文獻探討
第七節 篇章介紹
第二章 臺灣大河小說的起點
第一節 前言
一、研究緣起
二、前人研究
第二節 《大武山之歌》與《臺灣人三部曲》創作緣起
一、基本史料比對的差異
二、《大武山之歌》的計畫內容
三、臺灣大河小說的特色
第三節 《濁流三部曲》的發表歷程與大河小說的地位
一、《濁流三部曲》的創...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