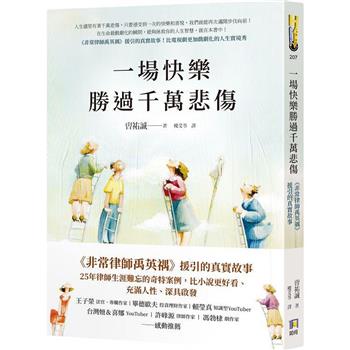宋代人喜歡養動物,並對牠們極盡寵愛,透過與伴侶動物的相處也更加了解這些動物的特性。宋詩獨有的日常性增加了這些伴侶動物在詩中出現的機會,文學作品與繪畫中處處可見伴侶動物的身影。宋人描寫他們如何與伴侶動物相處,也常以動物為喻,表達自己的情志。與伴侶動物的相處親暱,所以觀察到的動物形象往往有與前人不同之處,本書欲探討伴侶動物在宋人生命歷程中的意義,透過宋人和動物間的觀看與陪伴勾勒出屬於宋人的生活情調。
本書特色
伴侶動物的概念原來早在宋代就出現,在本書中你會驚訝於宋人對牠們的寵愛,並且被動物和人之間的互動療癒。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陪伴與觀看:宋詩中的伴侶動物書寫 (電子書)的圖書 |
 |
陪伴與觀看:宋詩中的伴侶動物書寫 作者:游佳霖 出版社: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8-3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1 |
中文書 |
$ 351 |
華文文學研究 |
$ 351 |
中國古典文學 |
$ 351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51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陪伴與觀看:宋詩中的伴侶動物書寫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游佳霖
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學士
經歷
畢業後在大專院校從事行政職,接著不務正業飛到澳洲打工旅遊,享受澳洲慢活悠閒生活一年後,再度回到充滿青春活力的大專院校從事行政職。
著作
期刊論文
歐陽修筆下的白兔──〈白兔詩〉及其唱和詩(收錄於《有鳳初鳴》年刊)
游佳霖
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學士
經歷
畢業後在大專院校從事行政職,接著不務正業飛到澳洲打工旅遊,享受澳洲慢活悠閒生活一年後,再度回到充滿青春活力的大專院校從事行政職。
著作
期刊論文
歐陽修筆下的白兔──〈白兔詩〉及其唱和詩(收錄於《有鳳初鳴》年刊)
目錄
作者序
摘要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二、研究進路
第二章 宋以前的伴侶動物
第一節 犬:田園之意象
第二節 貓:典故之應用
第三節 魚:樂之意象
第四節 鸚鵡:才高不凡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相陪作伴:宋代動物詩之伴侶實踐
第一節 犬:默契之養成
一、機警守盜
二、可識人情
第二節 貓:同床共枕眠
一、捉鼠之功
二、自由來去
第三節 魚:主喚盆池中
第四節 鸚鵡:悶尋鸚鵡說無憀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寓目遊心:宋代伴侶動物詩之觀看內涵
第一節 白鶴與樂天:宋前的觀看經驗
第二節 從白鶴到白兔:唐宋伴侶動物詩之承轉
第三節 睹物觸情:由觀看至喻己
第四節 伴侶動物詩之餘韻
一、犬:歲久識主情
二、貓:貍奴之繼承
三、魚:吞墨應識字
四、鸚鵡:能言是禍媒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摘要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二、研究進路
第二章 宋以前的伴侶動物
第一節 犬:田園之意象
第二節 貓:典故之應用
第三節 魚:樂之意象
第四節 鸚鵡:才高不凡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相陪作伴:宋代動物詩之伴侶實踐
第一節 犬:默契之養成
一、機警守盜
二、可識人情
第二節 貓:同床共枕眠
一、捉鼠之功
二、自由來去
第三節 魚:主喚盆池中
第四節 鸚鵡:悶尋鸚鵡說無憀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寓目遊心:宋代伴侶動物詩之觀看內涵
第一節 白鶴與樂天:宋前的觀看經驗
第二節 從白鶴到白兔:唐宋伴侶動物詩之承轉
第三節 睹物觸情:由觀看至喻己
第四節 伴侶動物詩之餘韻
一、犬:歲久識主情
二、貓:貍奴之繼承
三、魚:吞墨應識字
四、鸚鵡:能言是禍媒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參考書目
序
作者序
一轉眼,從山明水秀的花蓮畢業已經六年,在學期間花費了很多力氣與時間完成本書,期間也受到很多人的幫忙,無論是在生活上或知識上的補充。求學期間每堂課、每位指導過我的老師、每位相互砥礪的同儕,都是促使我完成本書不可或缺的角色,直至今日依然由衷感謝。
大學時期念應用外語系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就讀中文研究所,甚至走上研究宋詩這條路,本書的完成對我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猶記當時,在蜀蕙老師指導下,毫無頭緒的我,決定以自己最愛的「伴侶動物」為研究主題,其實會催生出這個主題,僅是因為和蜀蕙老師各種日常的聊天中談到自己有興趣的各種事物,進而從這些事物中找出和宋人生活緊密相關的。也正是因為以自己最愛的「伴侶動物」為主題,在撰寫本書時,雖然大量使用原典所以耗費許多時間,但是查找過程卻讓我感到非常快樂且有趣,我想,大概也是因為當時在研究主題上下了一個正確的決定,最後才能順利完成本書的寫作。
本書以犬、貓、魚、鸚鵡為討論重點,一開始想法是現代人飼養的伴侶動物以犬、貓為大宗,有了地上爬的,想來水裡游的與天上飛的各擇一來書寫也會很有趣吧,讓我訝異的是宋人除了愛犬愛貓,也愛養魚養鳥。當初選擇魚及鸚鵡其實沒有把握能找到足夠的資料,但事實上雖然資料比起狗和貓相對是少了一些,不過足以見到宋人對魚和鸚鵡的喜愛程度不輸犬貓。本書參考的文本除了詩、筆記、小說外,還輔以當時的畫作,這些作品中皆隱藏著宋人生活的各種文化脈絡。
此書可以順利出版也有賴元華文創的肯定與支持,感謝元華文創主編李欣芳、編輯陳亭瑜不厭其煩的書信往返及細心校訂,並給予我很多出版事宜的相關建議,謹此敬申謝忱。
最後,謹以此書敬獻
讓我無憂完成學業的家人,以及恩師張蜀蕙教授。
一轉眼,從山明水秀的花蓮畢業已經六年,在學期間花費了很多力氣與時間完成本書,期間也受到很多人的幫忙,無論是在生活上或知識上的補充。求學期間每堂課、每位指導過我的老師、每位相互砥礪的同儕,都是促使我完成本書不可或缺的角色,直至今日依然由衷感謝。
大學時期念應用外語系的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就讀中文研究所,甚至走上研究宋詩這條路,本書的完成對我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猶記當時,在蜀蕙老師指導下,毫無頭緒的我,決定以自己最愛的「伴侶動物」為研究主題,其實會催生出這個主題,僅是因為和蜀蕙老師各種日常的聊天中談到自己有興趣的各種事物,進而從這些事物中找出和宋人生活緊密相關的。也正是因為以自己最愛的「伴侶動物」為主題,在撰寫本書時,雖然大量使用原典所以耗費許多時間,但是查找過程卻讓我感到非常快樂且有趣,我想,大概也是因為當時在研究主題上下了一個正確的決定,最後才能順利完成本書的寫作。
本書以犬、貓、魚、鸚鵡為討論重點,一開始想法是現代人飼養的伴侶動物以犬、貓為大宗,有了地上爬的,想來水裡游的與天上飛的各擇一來書寫也會很有趣吧,讓我訝異的是宋人除了愛犬愛貓,也愛養魚養鳥。當初選擇魚及鸚鵡其實沒有把握能找到足夠的資料,但事實上雖然資料比起狗和貓相對是少了一些,不過足以見到宋人對魚和鸚鵡的喜愛程度不輸犬貓。本書參考的文本除了詩、筆記、小說外,還輔以當時的畫作,這些作品中皆隱藏著宋人生活的各種文化脈絡。
此書可以順利出版也有賴元華文創的肯定與支持,感謝元華文創主編李欣芳、編輯陳亭瑜不厭其煩的書信往返及細心校訂,並給予我很多出版事宜的相關建議,謹此敬申謝忱。
最後,謹以此書敬獻
讓我無憂完成學業的家人,以及恩師張蜀蕙教授。
|